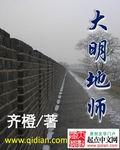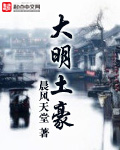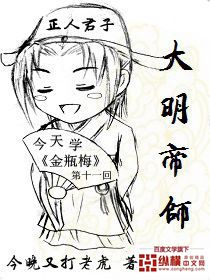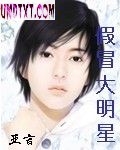大明金主-第1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绱朔至讲阶撸缺哐П吣タ斓枚唷�
传统学徒所谓的边学边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被浪费掉了。
“我这次带出来的少年之中,有些还是去年六月之后才进的书院,如今已经可以出来做事了。”徐元佐道。
“有什么了不起……”沈玉君嘟囔一声。
“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徐元佐道:“不过五年之后,我就可以退股了。”
沈玉君耳朵一竖:“退股?”
“是啊,五年之后,我自己的船队都能起来了,何必还入股你家分红呢?”徐元佐冷笑道:“尤其这回事成之后,想跟我合股的大户,不知会有多少。”他放下手中的茶碗。站起身道:“咱们这就过去看看吧。”
船尚未驶过海口,沈玉君却已经感受到了风暴将至的动荡。
这个时代的势家都担心别人谋夺他们的产业,所以等闲不会叫外姓入股。然而人人又都有逐利之心,颇想入股别家。这就跟小男生不舍得自己女朋友着装性感被人看,却又喜欢紧盯着别人的火热辣妹看。
徐元佐却没有这种保守心态:你们不让我入股没关系,我请你们入股总行了吧?
山不就我。我去就山。
徐元佐既然已经借沈家外戚这重身份插足航运业,要结识圈内商业伙伴,建立自己的航运班底不过是两三格台阶,迈步就上去了。
沈玉君原本不愿徐元佐入股,担心家业被夺,此刻听徐元佐流露出自己开办航运的念头,又觉得受到了威胁,皱眉道:“你这人能否定定心思?既然说好了要合股做生意,哪有三天两头换的。”
徐元佐笑道:“这合股做生意又不是结婚生孩子。求个一辈子长久。在商言商,你若是跟不上我的步速往上走,就只有被离弃掉。同理也是,若是我走得不如你快,你会带着我个累赘么?墨子说得好: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君臣父子尚且如此,你我合伙岂能例外?”
沈玉君憋了半晌。只觉得胸口发闷,良久才捋顺了气。道:“这话也就只有你说得出口。”
徐元佐道:“谁让你是我表姐呢?若不是这层亲戚关系,我岂会与你说这么许多肺腑之言。”
沈玉君别过脸去:“听你这般说,倒是在为我好了。”
“天下广大得很,我不是个吃独食的人,自然希望你家能够跟上我,不至于被甩得太远。”徐元佐道:“你若是不肯听。我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各走各的。”
沈玉君吸了口气,昂了昂脖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你也别小看我家。”
徐元佐摇了摇头:“我不是小看你。你家其实挺有潜力的。底蕴虽然差了些许,但是在未来二三十年间,顺着大流走下来,富至五六十万金总是能够达成的。”
沈玉君颇感茫然。刚才徐元佐说得沈家好像敝履一般,随时可弃。现在又好像沈家大有前景,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对我而言,一个随大流的大户却一钱不值。”徐元佐语调铿锵起来:“我的合作伙伴要想站在我身边,就不能像个乡下老财主一样盯着银子。他得看到潮流,走在潮流之前,引领潮流!他得跟我一起,砸碎挡在面前的城墙,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而不能等着大流流出,然后吃些残羹冷炙。”
沈玉君微微侧了侧身子,双腿有些发软,突然不自信起来。
“你不要不服气,话说在高处,手落在低处。我看得远是事实,而这一路上也都是手脚并用爬过来的。”徐元佐道:“你若是只能听我说话,却不能俯身去做,根本不可能站我身边。”
沈玉君重重咬了咬臼齿。
徐元佐看到她颌间起伏,显然是心中交战,顺手又推了一把:“我若是你,学堂久久不能运营,便亲自带人去挨家挨户问个清楚,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哪怕手段差些,效果弱些,总比夸夸其谈,毫无进益的好。”
沈玉君被表弟说得几乎无地自容,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好。”
徐元佐爽朗一笑,之前沉重气氛登时一扫而空,道:“走吧,咱们去见见那些客人,有些人我发了帖子,却还没见过本尊呢。”
沈玉君叫人去打旗语移船相近,抛锚之后再搭跳板过去,随口又问徐元佐要带多少人过去。徐元佐这回带来的人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锻炼队伍,另有一部分原因是撑足场面。真正要说缺一不可,那就有些糊弄人了。
在这个只敬罗衣不敬人的金银社会里,扮猪吃虎说不定真被人当成了猪。虎没吃到,还惹得一身恶臭,何苦来哉?第一时间把形象树立起来,底蕴放在那里,自然叫人折服。这也是徐元佐很难理解为何有人只以打脸为乐事,浑然不知道这浪费的都是自家资源。
哪怕再不堪的人,他手里的银子总是好的吧。而作为朋友叫他掏银子,总比作为仇人叫他掏银子要好看且方便得多。
徐元佐正了衣冠,仍旧是儒生的遥婪浇恚苯痈嫠弑鹑耍何沂嵌潦槿恕�
读书人总是会享受优待的。
两艘大船在旗语中渐渐靠拢,落帆抛锚。
徐元佐和沈玉君带着随从护卫,走跳板上了客人云集的那艘大船。另外一边,苏州商人——主要是太仓嘉定两州县的商人,也登上了这艘船。
“原来是陆公亲来,久闻不如一见呐!”
徐元佐一登船,就看到一群松江商人从舱楼中出来,齐聚甲板迎接。
“唐世兄,又见面了,看您气色好了许多。”
徐元佐一一打着招呼,热情洋溢转了一圈。
这边苏商也纷纷站定在甲板上,眉开眼笑地看着众星拱月一般的徐元佐。
太仓和嘉定都在唐行的西北面,徐元佐去苏州主要是吴县、长兴这样的东部州县,并没有去到那边。彼此既然没有纠葛,见面便是朋友,此刻船上一团和气,令人心醉。
徐元佐到苏州商贾一侧,也团团作礼,丝毫不慢待了客人。之前这些苏州人听说徐元佐跟翁少山有些过节,还有些忐忑。加上又是自己有求于人,早就做好了受气的准备。谁知道徐元佐这般客气,不由大感轻松。
“外面风大,咱们进去坐着慢慢聊。”徐元佐见了一圈礼,像是主人一般对众人道。
沈玉君再骄傲自负,也终究是个女子,内心中总有些怯让。见徐元佐抢了她东主的风头,非但没有见怪,反倒暗自松了口气,躲在徐元佐身后,仿佛有了依靠一般。
众人自然无不应允,让出一条路来,纷纷道:“敬琏,请!”
“请,请!”徐元佐虚让两下,见没人肯动,昂首迈步从这条夹道中走了进去。
其他商人方才跟在后面,进去一一落座,自然是讲究非常,不会随意瞎坐。
徐元佐与两位举人谦让了一番,人家却是真心实意不肯凌驾其上,他只好坐了首座。
第322章 堂会
众人落座之后,徐元佐扫视一圈,脑中自然浮现出三十二家这个数字。坐在座椅上的都是掌事人,背后侍立的仆从又有两倍之多——徐元佐显然超标了。再算上船上的水手,也幸亏这艘船没有载货,否则还真就超载了。
徐元佐既然坐了主座,当然不能光出风头不说话。他等众人静下来,清了清嗓子,中气十足道:“杂曲里有句唱词,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能够同船渡海,恐怕还得多修十年。”
众人大笑,场面顿时融洽起来。
“在座诸位有老交情的,有神交已久的,不管是否头回见面,就冲着这二十年苦修得来的缘分,徐某便要以茶代酒敬诸位一杯。”徐元佐说罢举起茶盏,拱手一圈,轻轻饮了一口。
众人自然也跟着喝了一口,只等徐元佐继续说下去。
沈玉君坐在松江人与苏州人之间的位置,算是过渡,此刻距离徐元佐隔了四五张椅子,心中暗道:这小子倒是能够镇住场面,哼!
徐元佐控制了节奏,笑道:“咱们无论来自哪里,此番进京无非一根心思:便是要朝廷将漕运之事交给我等舶主,走北海,省漕费。这事说起来咱们是逐利而去,不过平心而论的话,咱们同样也是忧国忧民啊!”
众人一听,知道这是徐元佐要拔高升华,将末业逐利之事抬举到大义的层面上来。这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万一玩得不溜,反叫人骂奸商虚伪,赚了银子还要卖好。
徐元佐是什么人,所有数字在脑中一个翻滚,随口吐道:“成化年以来。漕额定为四百万石。若是走漕运,在这四百万石漕粮之上,更要支付五倍之费!这是徐某臆测的么?非也,朝廷邸报与工部文卷,历历可查。我且报些名目来,大家听听便知:沿途雇佣车船的费用里,便有过江米、脚价米、脚用米、船钱米、变易米、车夫银、脚价银、脚费银、水脚银、车盘银、过坝旱脚银、轻斋银、浅贡银;助役贴补的又有贴夫米、贴役米、加贴米、盘用米、贴役银、(缺字)缆银、使赍银、挖贴银、堤夫银、椿木银之属。”
徐元佐一口气说下来,众人却没个叫好的。因为徐元佐每说一个名目出来,就意味着一笔成本。而这还只是两个大类,另外还有铺垫包装费用,如芦蓆米、折蓆米、蓆木银、松板楞木银、铺垫银;又有防耗防湿的费用,比如尖米、两尖米、鼠耗米、免晒米、筛扬米、免筛扬米、湿润米、蒸润米、润耗米、截银;还要支付运军运夫沿途生活费用,如行粮、行粮折本色银、本色月折银、食米折银等等。
如此重复繁杂的加派累加下来,为了运送一石漕粮到京师,就得花费三到五石的运费。如果按照徐元佐所取的最高额算。国家在运费上每年就要支出两千万石。即便按照成本最低的省份算,运费也在一千二百万石以上。
“那么海运的成本是多少呢?”徐元佐缓声道:“以国朝初年所行海运耗费存档来看,运费与正粮持平。也就是国家花一石米,就能运抵一石漕粮。这一年就能为朝廷省下千万石米,因此受益的百姓不知凡几!”
众人原本担心徐元佐玩弄嘴皮子“操两可之辞”,一旦遇到个精明人恐怕要被戳穿。然而听徐元佐这里一一报出名目,又列出了加派数目,最终汇集起来竟然如此惊人。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海运的利国利民。这就完全不用担心被人攻讦了。
唯一需要确定的问题,这些数据是否确实。
徐元佐是个有良好证明习惯的人。当下叫梅成功去取了《通漕类编》的草稿。这是书坊收集的各府县志中关于田赋的章节,以及一部分实录中有关的内容。因为还没有定稿,所以看起来还颇为散乱。
“这是我找人收集的漕运花费,还只是草稿。”徐元佐让众人翻阅。
众人随便翻了翻,但见里面不是县志、府志,便是实录、邸报。都有书、卷、章号,果然是“历历可查”。他们不是做学问的人,不会真的去查,反正只要有这些东西在,说话腰杆子也就足够硬了。
徐元佐喝着茶。从容道:“大家只有确立了这个心思,咱们才好继续往下说。”
众人纷纷应道:“正是为了国家朝廷效力!漕运苦民久矣,早该走海!”唱高调谁都会,何况这高调唱得有板有眼,有理有据。
徐元佐面露笑意,道:“大家齐心,大事定成!”
“还要仰仗徐君。”有人捧道。
“非也。”徐元佐摇头摆手:“这事恐怕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行。上至阁辅,下至书吏,咱们都得一一攻关。务必要叫朝中有个共识:只有走海有利于国朝,只有走海才能富国富民。此番徐某入京之后要去拜见张相,也会求见大司空,至于其他,恐怕力所不逮。”
徐元佐自己报了门路,其他人也知道该有所表示。
被徐元佐称作世兄的唐公子坐在徐元佐下手,属于第二尊位,自觉接口道:“我当游走兵部,拜见本兵霍思斋,请他沟通运军之事。”运军是卫所编制,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专门有一个提督漕运总兵官管辖。
明朝士人只能进入广义上的文官体系。五军都督府与卫所却主要是靠世袭,其中流官也有,但同样出自世职军户。比如今年正月新任命的提督漕运总兵官,便是总督京营戎政、镇远侯顾寰。
对于士林的延伸——商贾而言,要公关流官还有各种关系网可用。要经营勋贵圈子,难免力所不逮。
徐元佐走张居正、工部尚书朱衡的路子,这是提纲挈领,堂堂皇皇列阵对敌。唐公子自告奋勇走兵部尚书的路线,谋取兵部支持,这是出奇制胜。釜底抽薪。众人知道徐元佐的来历,自然不会怀疑他能否见到张居正。然而这位唐公子却是名不见经传,难免有人会心生疑窦。
“听闻本兵乃是山西人,与我江南实在相隔甚远,不知这位唐世兄……”有人犹疑道。
徐元佐呵呵一笑,替唐世兄接过这招。笑道:“是徐某无礼了。这位便是上海唐副宪的长孙,讳明诚,号文镜。唐副宪当年奉敕总理山西盐政,蜚声天阙,想来是那时候便结下的善缘。”
这些话唐明诚正不好对外夸奖,有徐元佐代劳,只是微笑颌首,显得谦逊儒雅。
众人一听这位也是三品高官之后,更添了一层信心。顺着次序将自家在京师的渠道门路都报了出来。
松江府华亭、上海两县在嘉靖早年着实出了不少进士,莫不是位居高位之后致仕的。嘉靖中晚期虽然也有进士及第,可惜现在要么是外任,要么是赋闲,颇有些青黄不接的感觉。不过各种关系转下来,基本还是能够找到点门路的。
松江这边说完,轮到苏州那边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
这些太仓嘉定的商贾,实在是没有路子。才来抱徐元佐的大腿。
“说来惭愧,乡党中但凡在京师有门路的。都已经自己去了。”一位苏商道。
松江这边不少人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
——你们自己人都不带同乡玩,却来找松江人寻分润,当松江人是傻子么?
沈玉君坐在两帮人之间,本着女性的敏感,瞬息之间就感觉到了异样。刚才还其乐融融的气氛,登时变得诡异起来。松江那边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冷漠和鄙视。苏州客商却都垂头丧气,一副任人鄙视的模样。
同为苏州人,沈玉君岂能看着同乡受人欺负?何况这些人都还是寻到沈家的门路而来,若是她一言不发,更是坠了沈家的名声。沈玉君干咳一声正要说话。却见徐元佐朝她摇了摇头,已经到了口头的话,又被她咽了回去。
“诸位且听我一言。”徐元佐道。
众人纷纷望向主座上的徐元佐,目光中各有分说。
“搭顺风船,历来是被人不齿的。”徐元佐轻笑一声:“不是我们松江人势利,只是在商言商,天下都没有白送好处的事。”
松江人这边纷纷点头:凭什么我们消耗了人脉资源,你们可以随便沾光呢?
苏州人面色不好看,却说不出什么话来。大家都是商贾,将心比心,若是自己手握资源,可能随便给人分润好处么?
沈玉君突然想到了徐元佐之前跟她引用的墨子名言,再看看这些人,果然是只有站在一个层面才有合作的基础。
“不过进京沟通此事的人家,断然不会只有我们这些。”徐元佐道:“有些人家是独自进京的,有些是三五人结伴进京的,咱们这么三五条船一同携手进京,也算罕见。不管怎么说,我看江南这边民声传达到部阁,海运无非就是时间、地点、额度上有待商定了。”
松江众人不解徐元佐揭过一页的用意,只是听着。
徐元佐望向那些苏州商人,道:“朝廷海运额度必然有限,同乡之间未必就肯分润,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终于有人忍不住道:“那我等就要分润给他们么?”
徐元佐朝那人笑了笑:“何必如此?只要他们一样出力便是了。”
那些苏州商人连忙道:“我等愿意出力,只是不知该如何出力。”
徐元佐笑笑:“银钱也是力。”
苏州商人心中一寒:这就是要我们出钱买漕额了。
松江商人却都面露微笑,都说散财童子最会抓钱,果然三两句话就转到钱上来了。
“钱或是船,都可以。”徐元佐道:“我近来一直在想,松江苏州有海船的人家不少,为何大家要一盘散沙似的任人划拨呢?为何不能组建一个堂会,有船出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利润按贡献大小再分配呢?”
沈玉君听得心理砰砰直跳,暗道:你怎么现在就提出来啦?不是说要等五年之后,自己有了船才踢开我们沈家么……
唐文镜突然抚掌笑道:“何必搞什么堂会,直接组建个公司岂不是更好?”
松江许多人家都听说了公司的事,主要是仁寿堂涵盖的人家颇广,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一说,也就众而皆知了。
徐元佐呵呵笑道:“公司这个东西,主要在‘营运’两字。运漕粮这事,一年不过两次,额度也大不到哪里去,组成了公司恐怕大半时候都没事可做呢。仁寿堂主营在牙行和货栈,那个是一年四季都有生意要做的,所以可以开成公司。”
唐文镜略有失望,道:“原来如此。”
苏州商人对公司之说还有些蒙昧,故而没有发言,更上心的是徐元佐要他们出多少银子。
徐元佐拉回正题,道:“首先,咱们都是有船的,共同承担的漕额得论家来分。”
要想从工部和户部抠出银子,实在千难万难,主要盈利点在于走私货。漕额分得越多,利润就越小。如果全船都是运送漕额,没有仓位存私货,那么几乎没有银子可赚,说不定还得赔本呢。漕运如此,海运也不例外。
徐元佐说得很婉转,是“论家”来分。事实上贡献大的人家,能拿出来的船肯定就多。同样承担一万石的漕额,徐沈能拿出十条大船,平均下来一条船千石漕额,还能装三千石私货。若是被人鄙视的小商贾,举家也就是两三条船的实力,还如何运私货赚钱。
“当然这个比重咱们可以慢慢算来,总是不会叫大家吃亏的。”徐元佐道:“其次是始发港。我看最好是在上海。”
“敬琏兄,宝山不好么?”嘉定商人终于忍不住问道。
徐元佐当然知道宝山有天然良港,哪怕四百年后也是如此,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诸位能叫嘉定县或是宝山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