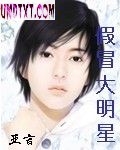大明金主-第1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徐家在华亭的产业可不是几家店铺,谁都想知道这所谓的查封是否会牵扯到仁寿堂,乃至刚刚冒出风头的云间集团。徐阶可以大智若愚地躲在天马山,刚刚加入云间集团的其他松江势家可不愿意白花花的银子打水漂。
云间集团一旦受损,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经销商。全都会因此利益受损。如果是在北方,即便得罪一省的商贾都没关系,但是江南城镇化远高于北方,城镇人口中经商的比例又是最高,此传言一经传播,整个松江府都沸腾起来。根本不需要势家们用力煽动,只须说一句:徐家若是倒了,你们的布恐怕就没人收了;借贷的银钱倒是不用还了,可也没人再借给你们了。
这些还都是周边外围的力量。真正的核心力量却是云间集团的雇员。这些雇员拿着外间不可能拿到的高薪,每年都有令人咋舌的年终奖,日子过得比秀才相公都要好,成为全家人的支柱……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来砸他饭碗么?
云间集团正式员工如今七百六十三人,在松江府的有六百三十七人。下属各单位学徒总人数达到了一千五百余人,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窑厂。同样是以窑厂为主,还有更大数量的日雇短工。这些人连学徒都算不上,但也是指着云间徐家吃饭的。这些人基本分不清公司、股东、董事之类的名头。他们还是传统地认“氏族”。徐家是云间的大股东,在他们看来,云间集团就是徐家的。
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就是保卫云间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不如护院队那样能打能杀,但是为徐家就是为自己这个概念可谓深入骨髓。
对于这些人而言,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煽动。只要各单位作出一定的保护措施,立刻就会触动他们的神经——好企业总是有各种办法叫员工和企业的命运相连,息息相关。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化的江南,这些人可是打算世世代代给徐家打工的。
徐元佐在徐阶的逼问下,有些头痛。这个意外是他无从下定论的。可能是“民抄董宦”那样。最终不了了之;也有可能如同“五人墓碑记”那样,推五个替罪羊出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朝廷肯定不愿意看到税田动荡,百姓也只是一时义愤。”徐元佐顿了顿,道:“其实我若是蔡国熙,只需要公开说:只追究府库案,决不影响松江府的开市贸易,不牵连别家,这股义愤很快就会平息下去的。”
徐阶叹了口气,道:“跟笨人打交道就是太累。”
徐元佐哑然失笑。
蔡国熙可不就是太笨么?如果说他之前没有意识到会发生这种事,那么发生之后也该知道了。可这都几天了,竟然一点应对措施都没有,反倒加强压力,这不是逼着把事态高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隐忍翻案,这是徐家的最大期待,而前两者也是蔡国熙的最优策略——他的收益比徐家更大。可是他却选择了最愚蠢的策略:闹得天下皆知。
“不管怎么说,你们赢了。”徐阶幽幽道。
徐元佐一愣,这回真是完全脱线了。
“我们?”他不解道。
徐阶提了提嘴角:“这岂不是你们泰州一脉最所乐见的么?”
徐元佐这才意识道徐阶的思维之广,跳跃之大,也不免感叹自己实在没把“敲门砖”放在心上。他自己也忍不住“广、大”了一下,想到了未来张居正当国之后捕杀何心隐,激起民变的事。加上更遥远一些的民抄董宦、苏州抗税事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号角啊!
作为一个合格的文科生,徐元佐小心翼翼提炼升华道:“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日子,恐怕会变成天子与生民共治天下。”
“你真觉得世人能与士大夫相庭伉礼?”徐阶隐隐带着意气。
“当年门阀世家也不相信:科举出身的寒家子弟能参与国策。至于这股潮流是天下大势,还是小小逆流,孙儿不敢妄言。不过自今往后三十年,工商市民已然在士林外如山之起,势不可挡了。”徐元佐道。
第398章 战争号角
“刁民!乱贼!”
蔡国熙狠狠甩着袖子,整个人都觉得不顺气。他刚刚得知南直巡按御史已经亲往松江去了。其结果肯定不用多说,府县官是亲民官,只要能镇住场子不叫那些暴民竖起反旗,就算是大功一件。锦衣、刑部奉命行事,也绝对谈不上过错。这么一桩大事,谁来承担责任?蔡国熙想来想去,好像除了自己没有别人了。
早知如此,何必掺合进去?蔡国熙心中颇为郁闷。上回的妄议朝政案还没有彻底了结呢,今遭又摊上了这么桩倒霉事,还让不让人好好做官了!事到如今,只能看高相能否在朝堂上保住他了——万幸高相还手握吏部!
长随看着蔡国熙怒气渐渐平复下来,这才胆战心惊上前道:“老爷,翁笾翁少山求见。”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直捏着衣袖里的银锭,若不是如此提醒自己,还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去触老爷的眉头。
“不见不见不见!”蔡国熙整张脸都扭曲起来,抬起一脚便踹了上去,怒道:“该死的狗才!收了人家多少门包,竟要我见他!”他把讽议朝政案的主谋归在翁氏身上,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那长随挨了一脚,滚到一旁又跪着,壮起胆子道:“老爷,翁少山此时求见,无非为了将功赎罪。老爷只需要拨冗见一面,放手叫他去做,总不至于比眼下更糟了。”
蔡国熙冷笑一声:“本官做事,倒要你来教了!”
那长随吓得跪在地上,连道不敢。
蔡国熙虽然讨厌翁少山,但是也不能否认长随说得有道理。他也是做过苏州知府的人,知道官员虽然风头无二,更多时候却是无力得很。翁少山那样的地头蛇。往往能有更好更直接的办法做一些官员无法做到的事。城狐社鼠,也是自有用处的。
“去跟他说,与其现在来见我,不如事定之后再说。”蔡国熙缓缓道。
长随不敢多问,连忙倒退而出。
翁笾翁少山坐在轮椅上,得到这个答复之后颇有些失望。作为一个商人。他知道该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眼下人家摆明了要把自己当驴使唤,还得驴子自己备足粮草。如何让他能够舒心?不过翁少山还指望跟蔡国熙修复关系,好歹人家也是一省兵备了,眼下谈不上位高权重,日后却有很大可能位高权重。
尤其是翁笾身后少一个徐阶那样的大佬,又不甘愿给势家当白手套,这种高官资源对他来说实在是丢一个少一个。
更何况,他还需要蔡国熙帮他周旋妄议朝政案。此案以来。翁弘农这位翁家嫡长子还在牢里关着。虽然翁家买通了胥吏狱卒上下人等,让翁弘农在狱中也过得颇为舒适,甚至还白胖了一些,但是作为翁家的继承人一直被关在牢里总不是个事,颜面上都过不去啊!
翁笾失望而归,满腔的“良方”无从得售,只好退而求其次,指望事态平息之后再去表功。同去的翁家子侄固然心塞。但是对于蔡国熙也毫无办法,只能愤愤在背后骂上两句出气。十分没出息的模样。
翁家的办法很简单:以暴易暴,以民镇民。
“徐家既然能邀买松江民心对抗朝廷,咱们自然也可以邀买刁民喇虎,打行青手。这些人对那些工商刁民,岂不正是一物降一物?”翁少山身体恢复不错,对自己的这条计谋颇为得意:“尤其这些人都是松江人。本乡本土,外人能说什么?反倒可以说他们是‘义民’,正是不堪徐家鱼肉乡里才起身抗击的。”
翁笾若不是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又岂能如此决绝?自从他中风以来,自觉黄土都堆到了脖子上。若是承继了自己一身念想的大儿子出事,百万家财又留给谁呢?还不如拼死一搏,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翁笾是为了搏出一线生机,徐元佐也不是稳坐钓鱼台。
徐阶受到打击,还可以退往浙江,不失江南士林领袖。而他怎么办呢?难道跟去浙江韬光养晦读二十年书考进士去?徐元佐反身自观,虽然读书时候成绩不错,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再叫他沉下心性去读书,也是难度颇高。更何况这边考试要读的书都很不“友善”。尤其看着自己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帝国刚刚成型,岂能甘心别人挖它墙角?
所以说这场战争里谁都可以投降,就连徐家都可以,唯独他徐元佐不可以!
翁笾在松江收买打行青手、喇虎流氓的事,第一时间触动了安六爷的耳目。安六爷是什么人?那是打行的头领啊!他跟徐元佐一起干掉了黑举人,两人算是一起分过赃的铁党。他一方面派人与翁家谈买卖,一边亲自去华亭与徐元佐商议对策。
在安六爷看来,徐元佐与安六爷见过的所有读书人、士林子弟都不同。他没有卫道士那么强烈的道德洁癖,也没有官员胥吏的贪得无厌。徐敬琏很懂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也知道利益的分润是多么重要。跟这样有背景,有能力,有见识的人交往,实在是如沐春风。
翁笾在苏州名头再大,在运河沿岸的店铺再多,跟徐元佐一比也被比下去了。
徐元佐这些日子都住在华亭,一方面缓和局势,一方面给徐Т蚱P飙'虽然已经脱离苦海,不用像两个弟弟那样提心吊胆,但仍旧对徐家的前景充满了悲观。这也是人之常情,到底谁都不像徐元佐那样能够后知徐家一百年,对他而言当下就已经有覆顶之灾了。
徐元佐在松江的别院也总算派上了用场,非但自己住,还要承担转移徐家细软资产的作用。徐Ъ煸舳孕旒业男判脑妒と魏稳耍哉飧鲆遄痈裢馄髦兀抑兄匾墓哦耐妗⒒实凵痛汀⒔鹨楸Γ疾卦谛煸舻谋鹪豪铩�
安六爷作为徐元佐的重要盟友之一,也是少许几个能够登堂入室的人。
第399章 智珠在握
徐元佐知道安六爷此来必有大事,仍旧气定神闲地请他入座,奉茶,着实寒暄了一阵。最后是安六爷忍不住了,找了个不甚生硬的关节,把话题引向自己打听来的消息。他边说边观察徐元佐的表情,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徐元佐平淡如素,带着招牌式的微笑。
只要对徐元佐上心的人都知道,这种微笑只是表示:我在听。只有那些跟徐元佐不熟的人,才会因此心神激荡,以为云间小财神真心对他微笑。
安六爷正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少数人之一。
“你一点都不担心?”安六爷终于忍不住问道。
“这事为什么要担心?”徐元佐反问道。
安六爷眉头一皱:难道我还多事了不成?
徐元佐笑道:“六爷,你觉得眼下这种境况,我徐家该如何处置?”
安六爷可是本地土著,知道徐家的地位,那是仰着头都看不到顶的参天大树,哪里是他能够置喙的?倒不是怕徐元佐见怪,实在是怕徐元佐见笑。
徐元佐这才悠悠道:“其实要解决这事,只需要辟谣就够了。翁氏偏要以暴易暴,结果就很难说了。”
“敬琏以为呢?”安六爷总算可以反问回去了。
“当然是对我徐家有好处啊。”徐元佐这回真笑了:“原本他们出来辟谣,我们交人复市,大家打个平手。现在嘛,我倒是可以倒赚一城。”
“计将安出?”安六爷神情一振。
“恐怕得要几只白鹅。”徐元佐道。
江南将替罪羊唤作白鹅,在普遍语境下,专指替人扛死罪的人。安六爷一听要几个人出来扛死罪,登时知道徐元佐所言不是虚话。他仔细想了想,觉得相比这点投入。徐元佐的友谊更值钱,便道:“要多少?”
“五六个就够了,但是……”徐元佐微微笑道:“我要倭寇。”
安六爷又是一愣:“倭寇?”
“能搞到么?”徐元佐问道。
“真倭?”
“必须真的。”
安六爷习惯性地讨价还价:“朝鲜人行不?”
“五六个真倭,朝鲜人另算。”徐元佐道。
安六爷忍不住挠了挠额头:“敬琏,我知道你这意思,是要玩勾结倭寇的故事吧?”
“显而易见。”徐元佐笑道。
“这个罪名可是连严世藩都能杀。你要拿他对付谁呢?”安六爷显然觉得翁氏还配不上这个罪名。
“如果对付翁氏,那就用‘私蓄死士’;如果对付蔡国熙,就用渎职枉法;如果上面还有人要跳出来,那就不用客气了。”徐元佐道。
安六爷眼珠一转:他说那上面的人,显然就是高阁老了吧?这也太吓人了些。
“无凭无据的……”安六爷嘶嘶倒吸冷气,这回徐元佐真是叫他知道不寒而栗的滋味了。
“证据嘛,回头咱们凑几个人,从头到尾给他补齐就行了。”徐元佐不以为然道。
安六爷从徐元佐的私密小宅出来的时候头晕乎乎的。冷风一吹,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这该不会是卷入朝争了吧!
朝争呐!那是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就连知府都没资格参与进去吧?不对!说什么知府。巡抚恐怕都只能站在门口看看热闹!一念及此,安六爷不免在害怕之中还有些小激动,不免回顾起自己祖宗八辈乃至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他见过地位最高的官,大概就是县里那几位八品九品的杂职官员了。
徐元佐是个讲究团队作业的人。既然说了要从头到尾将证据补齐,那么首先就需要知道各个环节所看重的证据是什么。哪个位置需要口供,哪个环节要呈递物证,物证的规范如何,谁来负责查验……林林总总各种关节窍门。徐元佐都叫程宰去一一打听清楚,罗列成表。该打点的打点,该请吃饭的请吃饭,给安六爷做出了一张极其详尽的流程表。
安六爷拿到这份表格,只需要一步步一件件去准备,各种人证物证自然就成“真”了。因为给出这份标准答案的人就是日后的“考官”,所以也不必担心题目与答案不符。
至于翁氏那边。因为本就是他们出招,自然难逃各种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隐藏得越精妙,越能显出翁氏的居心叵测和苦心积虑。而且有安六爷作为内应,所有这些他们自认为是精妙的布局,全都红果果地展现在徐元佐眼前。考虑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徐元佐甚至比翁少山更早获知整个项目的进度。
“十七日别安排事了,那边要火烧的升湖书院,等火一起来就开始动作。”徐元佐对罗振权和甘成泽道。甘成泽已经完全接过了安保部的大旗——罗老爹退居二线,负责指导和顾问。罗振权在海事学堂任副校长,同时充任海战总教头,手下也有一批铁杆徒弟。
甘成泽早就迫不及待再次“剿倭”,摩拳擦掌恨不得立下军令状。
罗振权这回没多少任务,只有一次外海的演习,被要求带回一艘倭船——的残骸。在他看来,这哪里是演习,分明是演戏,所以兴致缺缺。他随口问道:“翁老头总算决定了?”
“翁老头大概要后天才知道吧。”徐元佐道:“这是我帮他选的日子。”
罗振权有些被噎住的感觉,干咳一声端起茶水送了一口。
徐元佐道:“十七日就能布局妥当,没必要拖拖拉拉的。更何况我大兄马上就要到上海了,总要在他回来之前把这事了结。再加上我姐姐成亲的事,否则我就更忙了。”
罗振权和甘成泽纷纷点头:“佐哥儿说的是。”
徐元佐就像是一台盛大晚会的总导演,把握着台上台下的一切。
翁笾并不知道“导演”是什么,但是他也有种智珠在握的感觉。尤其面对徐元佐这个令他屡次吃瘪的对手,终于有了翻身做主的感觉。只要这回切切实实地打击了徐家,松江人心一散,又有蔡国熙卡住水陆要道,整个松江府就是个廉价的棉布仓库,任由他们搬运,大可以将利润做到最大。如此这般,他终于可以继续自己的垄断大业,不会有人出来搅局了。
——唔,顺便还可以把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拉出大牢。
翁笾快意地想着。
第400章 舒振邦的出息
舒振邦走在华亭县城里,脚下就像是踩在了棉花上,着不上力,每一步都踩得极重。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作奸犯科的一天。然而一切都有命数,自己固然不愿作奸犯科,但是无形之手却将他一步步推到了如今的境地。
之前舒振邦也是想去考个文凭,混进仁寿堂吃碗好饭。谁知道文凭是拿到了,却是个最下等的。若是早两年,这也足以进仁寿堂了,可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都不肯好好念书科举,但凡读了几年书的人,便想考文凭进徐家的产业,图个高薪厚币的日子。舒振邦真是替他们不值——科举出来当官多好啊!拼死拼活当个伙计?
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还要去学什么数理化,那是高等文凭必考的。舒振邦没法说服家里人脱工去读书,只好望而兴叹。
原本生活就是如此平淡,舒振邦也渐渐接受了天命——给人撑船。他家世代给人撑船,有什么理由到了他这一辈就能例外呢?果然读书改命就不该是穷人该奢望的。舒振邦如此想着,但是每每看到趾高气昂的仁寿堂伙计,还是难免流出一股怨气。
直到有一天,一个跟着牛大力在郡城厮混的喇虎回到了朱里。两年不见,这个曾经一同玩耍的小伙伴竟然发达了,簇新的棉布罩衫下面竟还穿了一件绸缎做的中衣。
“来,你摸摸,可滑了!”小伙伴拉了舒振邦的手,让他小心地在自己绸缎中衣的袖口摸了摸。
——这穿在身上,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舒振邦体会着指尖传来的滑腻,神情恍惚。
小伙伴突然拍开了舒振邦的手:“你这是要把它磨破啊!”
舒振邦油然升起一股羞愧,连忙低下头,讪讪缩回手。
小伙伴检查了一番袖口。确定没有被舒振邦的粗手磨破,方才道:“你也是识字的,怎生混成了这般模样?啧啧,看看你这身衣裳,当年它刚做出来的时候,咱们还拖着鼻涕满地跑呢吧!”
舒振邦羞愧地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衣裳。这衣裳的确上年纪了。那是某一年的过年母亲给父亲做的。父亲穿了传给哥哥,哥哥穿了又传给他。江南人家好颜面,表面不怎么见补丁,内里却已经层层叠叠打了不知道多少个。
“要不然跟我走吧。托牛家哥哥的福,我如今也管着两条街,手下正缺可靠的人。”他道。
朱里也就才两条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