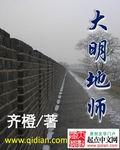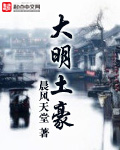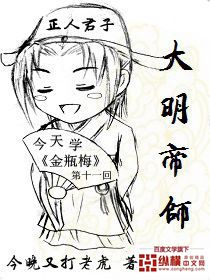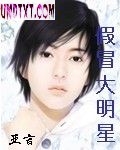大明金主-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胡老爷似乎话中有话。”徐元佐轻轻弹了弹耳朵:“小可不通世情,听不出这弦外之音,还请老爷明示。”
胡琛偷偷看了一眼程宰,见他没有反应,方才道:“并非有什么言下之意,只是开客栈这事,呵呵。公子来做,颇有些让人意外。”他停了下,见徐元佐没有反应,继续道:“这都是那帮小民养家糊口做的事,没甚利润,公子何必参合呢?”
袁正淳也笑道:“倒是公子此举颇有深意,我等老眼昏花,看不出来。还请公子示下。”
“换个人从客栈上头的确赚不到多少银子。”徐元佐毫不客气,夹起一块桂花糕:“三家客栈。一年到头不过是五六百两银子的流水。”
客商在外,非但会住客栈,也有住民宿、寺庙宫观的,还有的会住在船上、货栈、车马行,有手段的还会住驿馆,不一而同。
唐行真正接纳客人住宿的客栈。只有三家。
徐元佐所谓的“五六百两银子”其实是三家客栈的总流水,平均每家不到二百两的营业额。刨去掌柜、跑堂、厨师、杂役的人力成本,再减去日常采购成本,公关费用——包括税金,每家店一年净利润在八十到一百两。
徐元佐做的市场调查虽然不能精确地看到账目。但是误差也不会太大。更何况这还是根据十一月的客流量进行了验证、调整,所以他有这个胆子当众说出来。
袁正淳仍旧一副慈祥老爷爷似地眯眼笑着,程宰微微垂头,像是想着什么,只是胡琛有些颜色微变。三家客栈都是他家产业,竟然被人摸了底,焉能不变颜色?
徐元佐当然也知道这点,又道:“这边客栈的店例银是人纳两钱。照六百两流水算,每客只住一晚,一年下来只有三千客。胡老爷,唐行岂会只有这点客人?”
胡琛面色发黑,道:“微薄买卖,客房本也不多。”心中暗道:这小子竟然是处心积虑来抢生意的,看来此番不能善了。
“胡老爷过谦了。”徐元佐笑了笑,看穿了胡琛心思,又道:“如果老爷以为我是来抢生意的,那可就错怪我啦。”
“公子刚不还说要开客栈么?”胡琛口吻生硬。
“我开了新客栈之后,胡老爷的客栈自然也能跟着生意兴隆。”徐元佐道。
胡琛冷笑:“公子这话说得有意思极了。原本一年里头还有半年淡季,您这客栈开了之后,反倒能叫我生意更兴旺些?却不知哪里来的客人。”
“客人就如布巾里的水,挤挤总是会有的。”徐元佐笑了笑:“首先,我这客栈开了之后,店例银不以人纳,而以房、床来算。官房(俗称的上等房)一两一夜;客房可住两人,六钱一间;下房一钱一床,可住三人。”
胡琛面色稍霁,心中暗道:他那上房一两一夜,鬼才会住!至于两人的客房要六钱,等于一人三钱,却比我这儿贵了三分之一呢!看来他这是专心要做豪客的买卖,下房三人想来也是给人家奴仆住的。
胡琛知道自家客栈都是些小客商,罕见有人带奴仆的。如此看来,两家的客人倒是并不重叠,照徐家这样收钱,自己这边的客人也住不起。
徐元佐知道胡琛已经明了,又望向袁正淳和程宰二人,道:“其次嘛,寺庙道观不纳商税,香火钱收了还不够,还要收人宿资,没有半点利益乡梓,岂不成了只进不出的貔貅?想来家师——咳咳,郑县尊,县尊他老人家很快便会出一纸公文,不许寺庙道观做这生意。”
袁正淳微微颌首,似是肯定,却出言辩道:“人家信士愿意出钱住在寺庙道观,官府又如何管得?”
“寺庙道观就该做些善事,收容无家可归之人,或是其他行脚修士,焉能招纳旅客?”徐元佐道:“官府也不需管他,只要叫做公的日察夜访便是了。”
第110章 一拍即合
寺庙道观环境清幽,住宿干净,僧道们还会提供口味不错的素斋。
碰上有些水平的僧道,还能与客人谈玄论文,对弈手谈,甚或一展琴茶雅艺。是许多出门游学的读书人、寒门出身的官员,最喜欢的落脚点。
而这个客户群体,则是徐元佐的目标群体!
徐元佐挂出郑岳的名头,要以公权力来断了寺庙宫观的生意,一则是告诉他们:自己的确是来吃大饼的,但这块大饼你们原本就没得吃,是小哥我自家烙的。二则也是警告:我可不止有徐家做后援,还有个县尊恩师呢!
胡琛心中一动:若是如此,我这边或许也能分点汤水呢!
袁正淳却道:“若是寺庙道观不合住得,那么民宿也不能住了?”
住在民宿的多是积年老客,带着朋友故旧的意思,并不算是纯生意。就如徐贺在外行商,也有几处是住在民宿的,都是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可靠人。
徐元佐摸清了唐行的市场,自然知道袁正淳是在“声东击西”。问的是“民宿”,其实意指“货栈”。
因为袁家作为仁寿堂的魁首,唐行镇的首富,最大的买卖就是牙行埠头。
人都说明朝禁商,照徐元佐看来其实是朱家皇帝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政策能真正利益商人阶级。
牙行就是典型例子。
洪武二年的时候,朝廷令:“天下府州县各镇市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货物投税之后,听从发卖。”这条禁令的背景是因为蒙元承袭了两宋的“重税政策”,商人赋税极重——除非官僚背景的商家。而官牙负责收税,私牙负责坑骗。都是商人的天敌。
洪武二年的这条废牙行令,正是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保护小商人的利益,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的先声。
然而后来为何又承认了官牙的存在呢?
因为国家要控制人口流动,如果没有牙行,就得靠邸(货栈和旅店的合体)、店承担流动人口检查。而这又缺乏实际操作性。彻底不收商税,怎么都说不过去。再加上商人的确需要中介人从中牵线,否则谁知道上哪里找货源去?那时候既没阿里又没网络,就连报纸广告和黄页电话簿都没有。
见牙行没法废除,洪武二十四年的时候,朝廷又令工部“建屋数十楹,名曰塌坊,商人至者,俾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驵侩(牙人)无所与。”这种官店便是集合了邸、店、牙三者,建立了一个公共平台,实际上仍旧排斥中介。
在洪武帝看来,中介这种转手贸易获利的行为,根本就是诈骗。
事实证明,牙人的确有存在的必要。
有些牙人仿照官店的邸、店、牙合一的形式。依样办理,就成了牙行。
因牙行得有铺面、堆栈乃至客房。并雇人看货、帮手、帐房、庄客,需要一定的资金,所以朝廷只能在《明律集解附例》里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这其实就是承认了牙人的法律地位,并且重启了官牙制度。
袁家的牙行有牙贴,可以算是官牙。不过他一张牙贴管十几个牙行。挂靠他名下的私家牙行更是多达数十,上面不查也就罢了,真要查起来肯定是要依法查处的。
徐元佐道:“民宿也好,货栈也好,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的。官府怎么会查。”
袁正淳道:“就怕县尊老爷一时心血来潮,闹出事端。”
“咱们要和气生财,县尊也指着平平安安进名宦祠呢。”徐元佐道。
袁正淳心中知道:原来还有这个开价。
他不知道徐元佐随口替恩师要了点好处,还以为徐家与郑岳郑县尊已经说好了筹码呢。
“若是徐公子家提倡,县尊自然是肯定要入祠的。”袁正淳抚须道。
“家师也是的确有心造福一方,并非单纯图个虚名。”徐元佐回到正题,道:“我家客栈开起来之后,自然也是愿意交纳规费的。而且地方上读过书,进不了学的生童,我们也愿意雇些来用。至于家底清白,勤劳肯干的杂役,少不得要多雇几个。”
他顿了顿,又对胡琛笑道:“胡老爷若是不打算做这买卖了,您家名下的客栈、人手,我也愿意合买、续聘。”
袁正淳并不关心胡琛的生意,只是问道:“你说的这生童,能雇多少?”
“就看保人的情面有多大了。”徐元佐笑道:“从唐行往西走,北竿山、重固、刘家角、商榻,我都要开店,有的是用人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若是不优做什么呢?自家有产业的还可以经营自家产业,若是自家没产业呢?这些读书人岂不成了“负担累赘”?
在文教不发达的地方,生童还可以做做乡村教授,但是在松江这么个“家弦户诵”的地方,生员都未必能有馆坐,何况那些蒙童呢。
读书人没有相应的出路,对应的就是读书人地位下降,所以乡党之中的举人、生员,都会关注“就业率”的问题。
任何一个体面的职位,都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就意味着人情和银钱。
“公子愿交多少规费?”一直没有说话的程宰出声问道。
徐元佐精神一振,知道这下通往唐行的道路已经彻底打通了。
“得先请问先生,贵地是各自缴税,还是合了一处,由仁寿堂代缴。”徐元佐问道。
若是各自缴税,仁寿堂收的规费就是用来进行乡里补充建设的。比如修个土地庙,铺个地砖,做个社戏之类,花销不会很大。如果仁寿堂代缴整个唐行的商税,甚至田税,那么费用就要高许多了。
程宰道:“唐行镇上的商税是由商家合了一处,仁寿堂代缴的。田税是由大伙帮着催收。徐公子若是只开客栈,年规也不多,十两银子如何?”
商税本定是三十取一,但是英明的太祖皇帝怕官吏残虐下民,在后面补了一句话:不许苛征。
什么叫不许苛征呢?就是去年征多少,今年还是征多少。如果今年比去年征少了,问题倒是不大,各地官员都比徐贺会找借口。万一征多了,反倒得好好解释一下,为何会多。说不定还会引来科道言官的不信任调查。
这种情形之下,大明从建国初期十里不存一户的萧条时期,走到如今“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的商业繁荣时代,即便算上后来增加“市肆门摊税”,但是商税总额不增反降。
三十取一的商税不过是百分之三点三,营业额做到三百两,就该缴纳十两银子了。而规费也只收十两,低得让徐元佐简直无法讲价啊!
“若是乡里有事,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徐元佐爽快地应承下来。
程宰提了提嘴角,显然不愿多说话。
袁正淳见该谈的都谈好了,起身笑道:“徐公子到底爽快人!今日正要为公子设宴,还望赏光。”
“袁老爷客气,日后小可在唐行还要多多仰仗诸位。”徐元佐一笑而起,熟络得就像是自家人一般。
众人纷纷起身,各个脸上带着笑意,好像真是一桩喜事。
胡琛走到徐元佐身边:“日后咱们便是同行,也得互相帮衬才是。”
“胡老爷是前辈,少不得要多多讨教。”徐元佐笑道。
胡琛一边客套,一边随着人往外走。
徐元佐与跟在后面的程宰对视一眼,会意一笑,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个聪明人。他不经意间看了顾水生一眼,顿生疑惑,低声问道:“怎么头上有汗?身子不舒服?”这二月春寒时节,堂屋里火炉也不甚旺,出汗实在太奇怪了。
顾水生低声回道:“唇枪舌剑,太激烈了!”
“啊?”徐元佐一脸茫然:唇枪舌剑?刚才分明是一拍即合两情相悦啊!
※※※※※
注:陆楫在《蒹葭堂杂着摘抄》里说:“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
陆楫距离主角此时已经逝世十七年了,正是南直松江府人,其言论可以一观。
第111章 聪明人
公所等于办公室,是大家照比例分摊买的办公场所,所以够用就好,十分节俭。请客吃饭则是袁正淳做东,一如士子所说的:可谓奢华矣!
寻常的鱼、牛、猪、羊是必备的四道主菜,浓油赤酱,烹制精美,色香味俱全。至于配的菜蔬也足见细心,青菜只取菜心,高汤淋熟;茄饼先用鸡油炸过,又塞以鸡茸,风味尤佳。
尤其难得的是一盘嫩黄瓜,几乎徐元佐质疑起自己的常识。
“现在二月头上就有黄瓜了?”徐元佐问道。
“是种在火室,正好二月头上落盘。”袁正淳面色寻常,好像在说一桩很普通的事。
徐元佐却是知道,现在可以没有玻璃暖房,塑料大棚,这种反季节蔬菜产量肯定不高。说不定今天这桌菜,最贵的就是这盘黄瓜了。
“清香爽口,尤其解了冬馋。”徐元佐嚼了一块,赞赏道。
“若是公子喜欢,我叫人送些到府上。”袁正淳笑道:“就怕太贱,上门不好看。”
“心意可值千金。”徐元佐道:“袁老爷也不必专程送去,有空来夏圩我园子里玩耍。若想起来了带些过来,我大父致仕之后口味清淡,颇爱吃蔬果。”
袁正淳心中暗道:莫说徐家无人,这小子年纪轻轻能代表徐家到处经营产业,果然是有几分手段的。一取一予,不着痕迹。
一餐饭吃完,徐元佐便准备去与屋舍主人签订契书。
袁正淳肯定是不方便陪着的——即便他家跟人做买卖,也没有他出面签契书的道理。
“便叫程先生与公子一道去吧,那几家人都是老实人,见了程先生尤其不会在小节上与公子拉扯。”袁正淳出声道。
“正是,契书非同小可。程先生于明律极为精通,可以为公子拾遗补缺。”胡琛也道。
程宰面带朝徐元佐微微点头,内敛之中透着一股自信。
许多人以后世观前朝,以为大明不讲究契约。其实契约从周朝进入法定阶段,在历朝历代都是十分讲究的。徐元佐看过《三言二拍》,知道无论红契白契。遇到官司就是最直接重要的证据,本就不敢掉以轻心。
他在后世打过工做过生意,来到明朝之后读的第一套大部头就是大明律,搞定房屋买卖的契约自然不成问题。而且卖主也不是大有背景的刁民,充其量在付款细节上争一争罢了。
不过……
“如此甚好。”徐元佐笑道:“我对唐行不熟,也不知道那房子到底是不是卖家的,还要请程先生帮忙认个脸。”
程宰并不多过场,直爽道:“但求能有所效力。”
袁正淳与胡琛便送徐元佐一行到了楼下,彼此别过。
胡琛看了一眼袁正淳。道:“朴中兄以为此子能成事否?”他与袁正淳都是举人,非正式场合便以字相称了。
袁正淳瞑目抚须:“看着便知道了。”
阁老的孙子相较其他人当然更容易成功,但是谁都不能打包票说必然成功。
尤其是徐元佐在开辟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徐元佐与程宰走过拐角,便问道:“程先生府中是做什么生意的?”这个程宰颇为神秘,在镇上的主营业务是“包揽词讼”,说好听点是律师的前辈,说穿了就是个吃了原告吃被告、欺上瞒下的讼棍。
一个讼棍是不可能有资格进入仁寿堂,更遑论座次比胡琛还高。胡琛名下有三家客栈不假。但他更有两个丝行,一个三十台织机的织坊。年入万金是妥妥的。
程宰笑了笑:“不足挂齿。”
面对保护姿态这么强烈的人,徐元佐怀疑光靠语言没办法撬开此人的嘴,于是他取出一锭五两银子,放在了程宰手里。
程宰只觉得手中冰凉,下意识觉察到是分量不轻的银锭,本能反应紧握在了手里。
“公子这是何意?”程宰一脸受惊的模样。这便是孙子所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他要是真的受惊了,才不会写在脸上呢。
徐元佐道:“小弟我初到贵境,得有高人指路。”他道:“袁、胡二位老爷给您多少,我只会给的更多。”
程宰这回是面无表情,可见内心的确大起波澜。
徐元佐见缺口已经有了。乘势道:“先生不要惊讶,我并没有探查到您的底细。整个唐行,从牙行到扛包,我都查过了。您只是热衷调解乡邻矛盾,而座次却在胡老爷之上,所以我猜您定是卧龙凤雏一般的智囊。”
程宰紧握着手里的银锭,道:“那公子也该知道,程某并不是见利背信之人。”
徐元佐笑了:“先生啊,诸君对我成见太深啊。”他走了两步:“要将唐行彻底纳入一人手中,得花多少银子?”
程宰一愣:这谁能算过?且不论土地屋舍这类恒产,光是各处牙行、埠头、作坊、酒楼……林林总总算下恐怕得有百万金吧?就算百万金多半人家也不愿意卖!有人愿意卖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么?
“既然我没法吃独食,自然不会愿意与人结怨。”徐元佐道:“他们怕我分了大饼,却不知我深知‘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事我绝不会干的。”
“公子是想开源。”程宰旋即又道:“不过依程某之见,您的开源终究只是换了一家人抢罢了。”
“哈哈哈。”徐元佐笑了三声:“程先生真是言辞犀利,一针见血。不错,我的确是抢了出家人的大饼。”他顿了顿又道:“先生应该知道,宋人如司马光之属以为天下财富有数,官家取了一分,小民便少了一分,所谓开源,无非是掠民。”
程宰点了点头。
“先生以为如何?”
“有些道理。”程宰低声道:“如今虽然不少人都说他那是迂腐之言,我大明既没有剥掠小民,也没有亏空太仓,不是照样赚到了大钱……”
徐元佐见他停下,知道他这是在衡量自己的见识,属于聪明人之间的认证。于是徐元佐接道:“却不知,我们如今的银钱却是来自海外。大明开源一分,海外便少一分。而海外银钱则开自矿脉,凡人取一分,后土则少一分。”
“物有始终,终有耗竭之日。”程宰道。
徐元佐笑了:“虽然如此,但我们看不到了。”
程宰也笑了笑,觉得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惬意。最为难得的是,这些想法在旁人眼里属于怪异,根本无人可说。而这位徐公子却视作等闲,真乃知己矣!
徐元佐道:“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