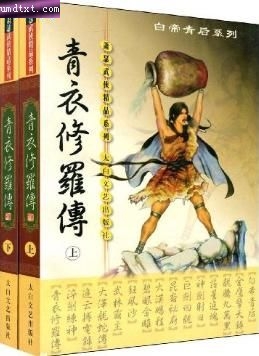善解公子衣-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茴,等你生下孩子,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说话,现在先用力,听话!”他哄着我,在我耳边不停地鼓励我,“快了,孩子的头都出来了,再努力一把,我在这里守着你。”
他温柔地用手拨开我浸湿贴在脸上的发丝,用指腹轻轻抚摩我的脸颊,我一侧头,一口咬住他的手掌,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将所有力量凝聚在下腹中,喉咙中迸发出的那种求生的渴望的喊声,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陌生。
口中尝到血腥味,商陆手掌的皮肉被我尖利的牙扎破,汩汩地流出血来,我像一只嗜血的野兽吸食着他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只想将他吞吃进腹,他的骨和我的骨交缠,他的血和我的血相溶,我们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整体,天与地都无法分开我们。
“哇!”十分清脆的一声啼哭,稳婆兴奋地叫道:“陛下,孩子出来了,是个小公主!”
我松开商陆的手,累得睁不开眼睛,趁着自己还有最后一丝余力,告诉商陆:“商陆,保护好孩子……别让她落到除你以外的人手中……顺遂都不能……”
筋疲力尽,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正文 四十五
四十五
我没什么大碍,死死睡了几日,再醒过来就是神清气爽。醒来的时候是被孩子的哭声吵醒的,我看不到孩子在哪个地方,只能根据声音判断一个大致的方位,下床摸过去。
“哎呦我的陛下哎!”走了没几步,顺遂忽然冲过来,把我拦回床上,嘴里念叨:“您怎么没穿鞋就下地,坐月子可受不得凉。”
我拦住她给我穿鞋的动作:“先去看孩子。”
她的声音逐渐远去,而后又传过来:“没事儿,只是尿了,奴婢这就给小公主换裤子。”
她窸窸窣窣地忙了一阵子,然后说:“陛下,您抱抱小公主吧,可沉呢。”
我茫然无措,不知该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来,像一个木偶似的,由着顺遂把我两只胳膊摆出抱孩子的样子,然后不经意的,一个柔软温暖的小东西就这么落在了我的臂弯里。
有一种从心底生出的感动与柔软漾满了我的全身,生命的延续与交替是这样神圣的一件事。我伸出手,摸索着这个孩子的眉眼,想摸一摸她是不是形肖她的父亲。
顺遂笑道:“陛下,小公主才刚出生两天,眼睛都还没睁开呢。这天下的孩子,刚出生时都长得一个样,和猴子似的皱巴巴的,等满月了,眉眼张开了,可就能看出美丑了。小公主肯定是个美人胚儿。”
我很得意,如果她像商陆,那不用说必定是个美人胚儿,如果像我,虽不至于倾国倾城,但也总不至于中等偏下吧。
我就维持着得意的样子坐在床沿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猛地想起商陆来!我跳起来,差点儿把孩子摔在地下,冲顺遂吼:“商陆呢?”
“谁?”
“商陆!”
“陛下,奴婢不曾听说过此人……”
顺遂并非从从前就跟着我的,所以她不知道商陆情有可原,可我生产那天,她应该见过商陆的啊!
我不可置信地又问了一遍:“你没见过商陆?”
“奴婢……”顺遂不知道哪里惹到我,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有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后下定决心似的,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奴婢确实不知陛下口中所提商陆,陛下……陛下是否要召章太医进宫?”
这怎么可能呢!
我会错认任何人,可只有商陆,我是不会错认的!他哪怕变成了一个水萝卜,也是众萝卜堆中最英俊最洁白最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一个,我怎么可能记错呢!
我惶恐,我觉得自己一定陷入了某一个惊天大陷阱。于是我把长歌海月叫来,问他:“长歌海月,我生娃儿那天,商陆在不在?”
他奇(…提供下载…)怪地反问我:“云小茴,你为数不多的智力又下降了?”
我没空搭理他:“我说真的,我看到商陆了!他是真实存在的,我都咬到他的手了!”
长歌海月断然反驳道:“云小茴,那是你的幻觉。你那个时候奄奄一息,人在濒死的时候,会看到此生至爱之人也是正常的,那一定是你的幻觉。”
我只恨我此刻看不见,不然我可以细细观察他的表情眼神和姿态,好分辨长歌海月是不是在说谎话。
长歌海月根本没理我心里这点小心思,转身去逗弄孩子。他这人也真是奇(…提供下载…)怪得很,平常这样凶残,却十分喜爱孩子。顺遂同我说,我睡着的那几日,这位爷已经送了无数小玩意儿给孩子了,什么长命锁、平安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摸索着走过去,听到长歌海月在逗弄孩子,嘴里发出依依呀呀的声音,显得特蠢。
我把孩子抱起来,没好气:“你那么爱孩子,怎么不让你那些莺莺燕燕给你生一个?”
他要是早这么干了,搞不好他的孩子都可以组成一支蹴鞠队包括替补队员了,啧,想想那场面就壮观。
长歌海月怒吼:“你把我当什么了!孩子是随便生的么!”
我被他吼得一愣一愣,倒是我手里的娃儿被他吓哭了,在我怀里扭动挣扎。
“小宝贝儿小心肝儿,对不住吓着你了,哥哥错了,再也不这样了好吗?”长歌海月一反刚才的凶神恶煞,特意放柔了语气哄孩子。
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没有五斤也有十斤,并且为长歌海月的厚颜无耻感到深深的震惊:“哥哥?你都能做她爹了!还哥哥,要不要脸哪!”
长歌海月立刻嬉皮笑脸:“行啊!只要你肯,我就是她爹啊!现成的女儿谁不要!”
我低下头,为自己的失言而感到后悔,只能装作逗弄孩子的样子,企图蒙混过去。
幸而长歌海月没有死缠烂打,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状似轻松地转移了话题:“名字取了没?”
“还没。”本来这种事情,一本字典在手,我就天下无敌,奈何我这会儿瞎了,也查阅不了,只得先耽搁着。
“我想给她取个既大气又平凡,既恬淡又新颖的名儿,最好还能寓意一生平顺安宁。”
长歌海月很费解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然后郁闷道:“你……你还是自己想吧。不过我告诉你,越是矜贵的名儿,越不好养。你不见从前那些王子公爵,小名总是贱名居多,反倒是那些兰麝啊,月雅啊之类的,总是多病多灾。便是我,都有个小名呢。”
他一时不查,说漏了嘴,我敏锐地抓住他的话头:“哦呀,不知道长歌公子的小名是什么呢?”
他显得无限悲愤:“狗蛋蛋。”
我捶桌大笑,连怀里的小娃儿也不明所以地跟着我一起笑起来,我笑得流出眼泪,上气不接下气的:“狗蛋!哈!狗蛋!”
长歌海月一本正经地纠正我:“是狗蛋蛋,两个蛋。”他特别强调了蛋蛋两个字。
我一听,笑意愈发喷薄而出。自商陆死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笑得这样开怀。
长歌海月的声音显得很无奈:“唉,笑就笑吧,只要你高兴。”
我渐渐止住笑意,明白他是特意为了逗我开心,不由得低低对他说:“谢谢。”
“你……”他欲言又止,“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谢谢。”他甩下这话,走了。
奇了,我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我被长歌海月一番折腾,倒打断了刚才的思绪。不管怎样,关于商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弄个清楚。
身边的人不和我说没关系,我自有打算。
这样想好了,我便借着谈国事的名头,招了江锁衣入宫。
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我生产那一天,好像、似乎、大概、可能,这位爷也闯进来那么一次过。
当时在场的年轻男人,除了长歌海月,就是江锁衣了。如果商陆不是我的幻觉,那肯定就是这个江锁衣无疑了。
我听到江锁衣的拐杖声由远及近,不由得嘿嘿一笑。大概我这笑容太过诡异,他的拐杖声猛地一个停顿,然后小心翼翼地出声询问:“陛下,不知召臣来所为何事?”
我说:“江御史饱读诗书,文采卓绝,取一个名字肯定不在话下。如今小公主刚刚诞生,我为取名头痛不已,不知江御史可有何高见?”
他沉思了一会儿:“陛下可有附加要求?”
我笑:“我想她姓商。”
如果江锁衣是商陆,我就不信他听了这话没有反应。
“这……”他果然迟疑了一阵子,而后说:“公主金枝玉叶,将来许是继承云氏皇朝大统之人,跟一个外姓,臣以为不妥。”
真是滴水不漏。
“好吧,那便按爱卿所言,跟着我姓吧。那么叫云什么好?”
他掰着指头列了一串名字出来,无非什么解忧啊,安平啊,妥妥当当又不出格的名字。
我现在又觉得江锁衣不是商陆了,哪有父亲对女儿的名字这么不上心的!还是商陆这厮隐藏得太好!
我决定使出杀手锏。
我装模作样地嘉奖了他一番,而后为了显示我爱才之心,我亲自摸下龙椅,虚情假意地执起了江锁衣的手:“爱卿啊,真是辛苦你了。”
我一边漫无边际地夸奖他,一边狠狠地摸他的手。我记得我那一天,曾经狠狠咬破过商陆的手掌,才过去三天,我不信他的伤痕会愈合得平滑如初。
我十分猥琐地继续摸他的手,指甲……指腹……骨节……掌心……江锁衣的手掌既大又温暖,一层薄茧,许是执笔写字写出来的,可我翻来覆去地把他的手摸了个遍,也没摸着一道疑似伤痕的东西。
“陛下,我……你……”江锁衣显得十分无措,想把手从我的魔爪中抽离,又不敢用力,像一个被纨绔公子轻薄的良家妇女一样,既满怀怨恨又无奈无言。
我嘴里继续不负责任地天花乱坠:“江爱卿,年初那件停办官员的事你办得挺好……”
我心里想,即使我摸不着伤痕,让我摸一摸这是不是商陆的手也行啊。
但是我马上就悲哀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摸不出这是不是商陆的手。
看官们,这里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作为一个爱人,我曾与商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但却摸不出这是不是他的手,我真是失败透了!
江锁衣忍无可忍,我我我了好几遍以后,终于抽出自己的手,义正词严道:“陛下!”
我惆怅得连敷衍他的力气都没,挥了挥手:“你下去吧。”
我也不在乎我再多一条耽于淫乐色令智昏的罪名出来,反正我已经在猥琐的光明大道上一路狂奔九个商陆也拉不回来了。
我心里既空虚又绝望,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希望,结果眼睁睁瞧着人拿着针戳破气泡一样,“啪”的一声,就什么都没了。
我抱着我的女儿喃喃:“你说你爹是江锁衣呢还是江锁衣呢还是江锁衣呢。”
她自然没有理我,睡得正香。
我却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猛捶自己的脑袋:江锁衣另外那只手我还没摸过哪!
可是御史大夫没有给我再吃一次豆腐的机会,他火烧屁股似的,告假了。
正文 四十六
四十六
江锁衣告假,用的是身体不适的理由。我却没有时间去看他,因为包金刚和金需胜回京了。
我整日整日在议事厅里听他们汇报地方上的情况。赈灾款被贪污多少,贪污的那位官员与朝中大臣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等等,听得血溅三尺。
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我涨奶涨得厉害,十分痛苦,有时候一天得换三四件衾衣,孩子尚小,眼睛一睁开便啼哭着要吃奶。我既当母亲,又当父亲,还得额外担起国事,每日在御花园里团团转,抱着树撞头。
烦躁期的女人是不能惹的。我不顺心,也不能让那些惹我不顺心的禽兽们顺心,于是关于此次贪污的案件,我下手重狠准,该查办的查办,贬谪的贬谪,毫不留情。
那些禽兽们像被我捅了屁股一般嗷嗷直叫,要死要活,朝堂上成天上演老泪纵痕忆苦思甜的戏码。他们哭,我比他们哭得更厉害,他们顶多只能发出一些低沉的沙哑的呜呜呜声,我一嗓子却是通天彻地直上九重霄,嚎得他们一愣一愣直打嗝。
这些难搞的老头子们终于在三天后了悟过来,和我死磕就是自寻死路。我可不在意什么皇家脸面,我是女人,我撒泼我哭嚎我比他们更不要脸。
这一场拉锯战最终以我的全面压倒性胜利告终,我办了这一批蛀虫,心里爽快,抱着女儿亲了好几口,这才想起江锁衣来。
我起初以为他说的身体不适是躲开我魔爪的借口,结果我一连这么多天处理政事,也不见他上朝,私下问了几个平日同他交好的同僚,才知道他是真的病了。
我有些内疚。因为听说江锁衣是疲累过度,又偶感风寒,这才病的。他之所以会疲累过度,是因为我把将近大半的政事交予他处理的缘故。
那段怀疑他是商陆的日子里,我还以公谋私利用职权把他召到议事厅,让他给我念奏折,念完了再让他顺便说出建议来。
所以我在逗弄女儿的时候,他在挑灯夜战;我在吃桂花圆子的时候,他在奋笔疾书;待我泯灭的良知好不容易重又绽放光辉时,他病倒了。
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么想着,叫了顺遂,打算微服出巡,去白玉京江锁衣的官邸里表达一下我亲切的慰问。
工部给他安排的官邸好死不死恰好在从前商府旧址,自复国以后也没有人有这个心思去修复前朝叛贼的宅子,所以听顺遂说,眼前这栋宅子很有些破烂。
再次走进这个地方,我真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如果我看得见,我一定要亲手摸过那些青石砖,迎风落几滴泪,展示一下我小清新小文艺的情怀。毕竟我十五岁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遇到了商陆这个冤家,从此纠葛不清藕断丝连缠缠绵绵到天涯……
我打了一个哆嗦,在顺遂的引领下摸进了江锁衣的房子。进去以后悄声一片,顺遂安静地搜索了一番,然后低声告诉我:“陛下,御史大夫在床上委着呢。”
然后她大声叫:“江御史!”
我恨不得把顺遂的嘴用浆糊粘上,但来不及了,江锁衣已经被她吵醒了。
我努力想象江锁衣朦胧初醒的样子,可脑中浮现的却是以前清晨商陆醒过来的那个骚包样,真是令人怀念。
江锁衣很迷蒙地“唔”了一声,然后静默片刻,噗通一声跌下床来:“微臣不知陛下亲临,微臣……”
我慢腾腾走过去,摸索着摸了摸江锁衣,他的身体滚烫,像个火炉。我方才和顺遂一道进来,沿途也没见什么服侍的下人,整座府邸就他一个人鬼一样地出没,我深刻怀疑我发给他的俸禄是不是被他埋到坑洞里攒老婆本了。
江锁衣还在顽固地坚持要用宫中礼仪给我行礼,尽管已经神智不清,但嘴里还逼叨逼叨念了一堆,我让随同我来的侍卫哥哥把他提溜到床上去,再屏退众人,独留下我与他待在一间房内。
他意识迷离,轻声呓语,滚烫,横陈于榻,我感觉自己不做点什么简直对不起这良辰美景。
看官们,并不是我心猿意马水性杨花要学那褒姒貂蝉之流,我也没那祸水的资本,只是我太想念商陆了,我不愿放过任何一个是他的可能,我都想学那谁谁谁给他做一具莲藕拼的,等他的灵魂来入梦。
江锁衣像一条咸鱼一样在我手下又颠了一会儿,最终抵不过病痛,不知是厥过去还是睡过去了。
我颤颤巍巍伸出我的手,心肝脾肺像在沸水里煮,咕嘟嘟的颤动,然后一使蛮力——扒了他的衣裳。
江锁衣动也不动,任我为所欲为,这更增长了我禽兽的嚣张气焰,我摸到他的锁骨,顺着肌理往下抚摸。
我不熟悉商陆的手,但我熟悉商陆的身体。我知道他征战沙场留下的每一道旧伤在哪里,每道伤痕后又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知道他的敏感点在哪里,每一次碰触他会发出怎样勾人而的低低呻吟;我知道……
一句话,我要如闪电一般噼噼啪啪地穿透江锁衣的直达他闷骚又别扭的小心肝呀啦索!
我摸遍了他的全身,最终确定了一个事实:江锁衣就是商陆,商陆就是江锁衣。
江锁衣平日里身上的草木气息也许是刻意伪装渲染,至少在此刻,我微微伏低到他的胸膛上时,鼻端萦绕的就是商陆本来的气味,熟悉,温存,我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趴在他的身体上无声地哭泣,我自己都吃惊一个瞎子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泪水,那些眼泪在我的脸颊和他胸膛的皮肤之间流淌,蜿蜒成一片水泽。
我守着江锁衣,不,是商陆,在他床边痴坐。瞎子无法感受明暗光亮的变化,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直到顺遂悄悄走进来,递给我一碗药和一碗粥:“陛下,这是奴婢刚派人去弄的,等江御史醒来了,就让他吃下去……陛下,你怎么了?”
她大概看到我脸上风干的泪痕,吃了一惊。
我没有理她,只是点头示意我听到了。
顺遂是个聪明人,这么些日子以来,她一定看出我与江锁衣之间不对劲的地方,但她只缄口不言当做不知道。此刻也是,她放下碗,与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退下去了。
顺遂走后没多久,商陆就醒过来了。我的手一直放在他心脏的部位,等他醒过来,开口惊讶地叫了我一声陛下以后,我笑笑,叫他:“商陆。”
手下他的心脏突然加速跳动,扑通扑通似乎要挣脱胸腔一般。但他的声音却十分镇静,一丝波澜都不起:“陛下,臣是江锁衣,不知陛下口中商陆是何人。”
看官们哪,我此刻心里的脏话那是一串接一串,前翻后滚左旋右转都不带重样的,我硬生生把“何人你娘个锤子”憋回去,略带惆怅地回答他:“商陆是我的夫君,亦是我孩子的父亲。”
商陆继续装死。
我在狂暴地弄死他和包容他那颗别扭的男人心之间徘徊了一会儿,觉得此时出击为时尚早。这种事情,一定要一击得手直戳死穴就像把王八翻个个儿一样让他一辈子都翻不得身!
我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