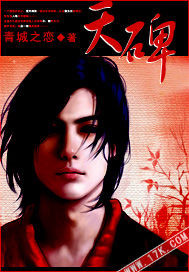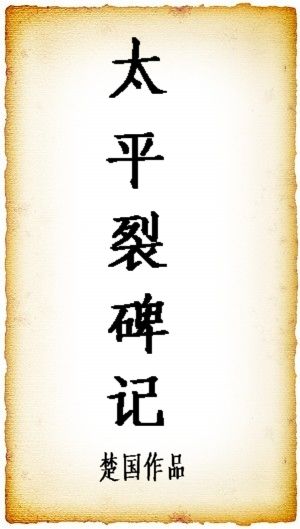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我悄悄捏了下覃瓶儿,站起来拉着她的手,想转身扎进水中逃离浅滩。这女人疯言疯语,愣说我是她的什么人,还说等了我两千多年,不是“半傀”也是妖精,还是赶快溜之大吉,惹毛了她老人家,再整出些吓破人胆的“日古子”出来,想走也走不脱了。
手机中的女人似乎看透我的心理,“想走?你走得掉吗?……你连我的声音也不想听了?……你不想听听为什么会在安乐洞遇到这么多磨难吗?”
最后一句话将我钉在原地。我咬咬牙,妈那个巴子,哪有活人怕死鬼的道理,有本事你咬我一口啊,我倒想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子丑寅卯来。
“说!”我从牙缝蹦出个字。
“……嗬嗬,这倒是你的性格。”女人嗬嗬冷笑,“你果然聪明,猜到磨芋和地牯牛是‘莫留,退’的意思,也敢钻进烈龙蜕下的皮中,我蛊惑猴头鹰把你们其中一个带到阴阳树,本意是留你们一条生路,嗬嗬,谁知道你怕蛇的毛病还没好,居然掉进生漆潭……”
“等等!”我大声叫道,“那两棵树真叫‘阴阳树’?”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我恨你!我就是要缠着你,缠死你……”
“你恨我?即使我是你的……什么人,按阴阳树的情形,也应该是我恨你才对啊?”我想起寄爷说阴阳树包含“恨妻”的意思,实在不愿对一个女半傀说我是她的“丈夫”。
“哼哼……看来你把一切都忘了!”女人转移话题,“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能成功逃脱生、毒、魂、死四煞吗?那是因为……你在洞中哭了四次,不但如此……你们还唱了那些令我心碎的情歌。要知道,我那时就是被你的歌声吸引住的。你的四哭加上那些情歌,无意破了我的诅咒,加上烈龙帮忙,你们才侥幸来到这里。”
哭了四次?真的假的?我仔细回想了下:满鸟鸟跌下悬崖后一次,覃瓶儿被猴头鹰抓走后一次,花儿被夹在岩隙中一次,满鸟鸟被巨蟒缠在“碓窝”中一次——果然是四次。至于寄爷在洞中唱情歌,完全是为了驱逐三个年青人心中的恐惧,没想到居然成为破煞的关键……天意天意!!
“那……”我心中其实还有很多疑问,不过想起来被满鸟鸟性骚扰那件事最刻骨铭心,见那女人呆在手机中并不出来,语气也逐渐温婉,我一屁股坐下来问道,“为什么我看见的是石头裸女,而寄爷看见的却是不同的东西?”
“哈哈哈……你不是最喜欢做那件事吗?”女人肆无忌惮地笑起来,“我就是想看看你来找我时还会不会被我吸引……果然,你的本质一点没变,还是喜欢……喜欢……”女人说不下去了。
鬼也怕羞?千古奇闻!!
覃瓶儿的手轻轻颤抖,似乎开始忸忸怩怩起来。不用看,她的脸肯定红到了脖子根。
黑暗中一只大手牵着我的手到地上一摸,我摸到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剧烈起伏却闷声不响,情知满鸟鸟被寄爷拖上浅滩后吓晕了。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白胡子老汉,“卡门中的白胡子老汉也是你安排的?”
“什么白胡子老汉?”女人的语气听上去好像全然不知这件事情。
“……”我语塞了,我没看见所谓的白胡子老汉,根本无法形容。“那些‘煞’都是你布置的?阿可俾的坟墓是怎么回事?还有天脚山上的云妖以及你在石床上和那男的……”
“……看得见的不一定是事实,看不见的不一定不存在……这是我当年就对你说过的。”
听女人话中的意思,难道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幻觉?这倒与我心中的猜测差不多。
寄爷轻轻捅捅我,把我的手拖向那幅鬼火组成的“水墨画”。我明白他的心思,开口问手机中的女人:“那幅鬼火画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侠马口村?”
“侠马口?有意思有意思……这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女人自言自语道,“你说的侠马口,本身就是一个早就存在的风水局,我把它取名为‘天残地缺’‘七星连珠’。‘天残地缺’指的是地底的情形,安乐洞只是‘残缺’小小的典型,‘七星连珠’是指你口中的侠马口村附近的七座山包连成一线,是整个风水局中最厉害的局眼。当然,安乐洞是我请人布置的,你看见的有鬼火那片悬崖上的岩窟,也是我派族人凿的,埋的是你的族人……”
原来如此。“……血魂碑是什么东西?”我沉默半晌,换了个话题。
“你忘了?血魂碑是你送给我的唯一东西!”女人听我问起这个问题,声音徒然变得忿恨无比,“你派烈龙来偷不说,自己亲自跑来抢了?哼哼……”
我急了,女人口中的“我”到底是谁?怎么会跟这个女人有如此复杂的感情纠葛?难道世上真有所谓“人死转世”、“阴魂不散”之事?果真如此,我早已跟那个“我”脱五服六代了,怎么还被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女人口口声声说成“你”呢?
我还想再问,女人截口说道:“你抢走血魂碑又怎样?你解不开诗锁,你会永远要留在这里陪我……”
第五十章 诗锁
女人忽然住口,阴恻恻冷笑一阵,恨声说道:“……你果然聪明,想套出我的话。我以前就是被你的花言巧语骗得一无所有,连命都给你了……你好狠!”
“啊——!”女人似哭似哭似笑非笑尖嚎一声,手机屏幕突然熄灭,周围又变得漆黑如墨。清脆的水滴声被女人的尖嚎撞得七零八落,含含浑浑,“啊——啊——”的回音久久缠绵不绝……
我摒住呼吸,呆坐不动,眼睛望着手机的方向,内心震骇,默然无语。
我看不见寄爷和覃瓶儿的情形。不过,从他们细弱的鼻息得知,他们一定也是紧抿着嘴,不敢打破这片刻的宁静。覃瓶儿更是紧紧握着我的手,轻轻颤抖着,仿佛直到此时才意识到那女人是传说中的“半傀”,我跟她说了半天话也不是在拉家常“摆龙门阵”。我一摸瘫在地上的满鸟鸟,发现只有这伙计气息如粗重,昏睡不醒,浑然不觉。我很奇怪,换在平时出现这种局面,花儿早就惊天动地吠叫起来了,为何这段时间它一直很安静?据说狗牙是克制普通“半傀”的武器,果真如此,那女人一定不是普通的“半傀”,否则花儿绝不会如此偃旗息鼓,无所作为。
女人的“啊”声终于彻底消失,水滴声重新恢复清脆悠远。
“汪~”过了很久,花儿的叫声打破了幽静,也将我们的思绪拉回现实。
我此时才发现手心里全是冷汗,全身酥软,强撑着的意志从身体各个部分渐渐消失——我从来未想过这辈子能跟传说中的鬼魂对上话,而且是一个滞留两千多年的阴魂,这事如果不是我自身体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会有这么离奇的遭遇。事情变得越来越匪夷所思了!
应该说,我此色的角色还没完全转变过来,脑海里一直在思索我究竟跟那个女人有什么关联,究竟是怎么对她背信弃义,才让她如此对我既爱又恨?听她的口气,我从巨蟒口中得到的血魂碑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有可能就是定情信物。可是,“我”什么要负心于她?她为什么说连命都给了“我”?
我忽然想起,女人承认阴阳树是用于诅咒某个人,而这个人据寄爷当时讲是我们土家族的祖先廪君,难道女人口中的“你”就是他老人家?难道我跟他老人家长得相像?当时石床上那个男的是不是他老人家呢?……这事情真够诡异的,可惜女人走了,不然可以详细问问。
覃瓶儿紧紧偎在我身边,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珍惜眼前的、珍惜最真实的才是最重要的。况且,虽然我到现在还不知所谓的血魂碑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但它既然出现在有爷爷的梦中,按违心的说法,我也完成了爷爷在“那边”交给我的任务。还有,覃瓶儿背上的绿毛图也消失了,对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都有一个完美的交待,这趟安乐洞之行应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我此时最想看到的是那被我漫不经心挥霍掉的阳光。可是,怎样才能再次见到我亲爱的太阳呢?老呆在这个黑咕隆咚的地方不是办法。
我忽然想起女人说的“诗锁”,她那句满怀幽怨的话仍在我耳边清晰回响,“你解不开诗锁,你会永远留在这里陪我……”这句话蕴含的深意非常值得琢磨,那女人似乎给我们故意留下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极有可能就是我们逃出生天的关键。
不过,“诗锁”是什么?诗做的锁吗?诗是什么?锁在哪里?'霸气书库:www。87book。com'
我的历史知识储备非常匮乏,按女人说的“两千多年”推断,再加上传说我们土家族是巴人后裔,而巴子国被秦国所灭,所以那时极有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而我对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历史人物倒是很熟悉,那就是屈原,原因无它,我的农历生日正是五月初五,也就是屈原跳进汨罗江那一天。春秋战国时代的诗歌对我来说,最熟悉的就是屈大夫的《离骚》,从历史角度分析,女人说的“诗锁”有一定理论依据,而且她当时说得那么肯定,应该确实存在一把这么古怪的“锁”!
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诗锁”究竟在哪里?如果要打开“锁”,首先必须找到“诗”,要找到“诗”,又必须先找到构成“诗”的文字,可是,文字在哪里?
我思索半天,终于想到,在这个黑漆漆地方,唯一吸引眼球的也只有对面悬崖上的鬼火画了,所谓的“诗”极有可能就藏在那幅画中。这样想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女人既然对“我”没有完全恩断义绝,我们又闯过了生煞、毒煞、魂煞和死煞,前面应该再没有其它机关或凶险之地,所以,对面悬崖上的鬼火画也许是我们这趟安乐洞之行最后一个难题。
覃瓶儿与我心有灵犀,知道我正在苦苦思索,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时捏一下以示鼓励,并不出言打扰我。满鸟鸟还在昏睡,寄爷隐在黑暗中不知在想什么,只有花儿扬眉吐气时而低呜两声。
那幅悬崖上的鬼火画还在缓缓飘动,幽蓝色的火苗仍然明亮如昔,那八个大字也仍然飘逸苍劲。
我瞪着两眼,死盯着那幅画。我的眼光从画的上面一直扫到画底,又从画底回到画顶,没看见哪里有半个文字,连象形的都没有。我突然想起古人写字是从左到右竖着写,又从左到右来回扫了三遍,依然没发现任何文字,更不用说找到那所谓的“诗”。我看见的只有一团团鬼火连成的线条,以及由线条组成的侠马口村的地形地貌。
所谓的“诗”会不会就是“天残地缺,七星连珠”这八个字呢?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否定了,那女人已经明确告诉我这八个字是她为侠马口村这个天然风水局取的名字,按道理说所谓的“诗”也绝不会如此一目了然摆在那里,同时也不符合“诗”的格式和韵律。
我想我的思维是不是太狭窄了,是不是应该跳出这个束缚,再想想其它的?那女人不是已经肯定我对初进安乐洞的警示分析是正确的吗?“莫留,退”,那么,“诗”会不会藏在我们遇到的事或物中呢?
我把进安乐洞后的点点滴滴仔细回忆了一遍,东拼西凑玩了好半天文字游戏,也没得出一首符合格式和韵律的诗来。绞尽脑汁也没找到丝毫头绪,我望着那幅鬼火画的眼神就渐渐模糊了……
噫?我忽然大惊,转而欣喜若狂。没想到我眼神变迷茫之后,却有了惊人发现——那幅细腻的鬼火画中确实有字,而且似乎很多。那是什么?三维立体画?——对,三维立体画,正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三维立体画。
就这么一激动,眼神收敛,那鬼火画中的文字又消失了。
覃瓶儿感觉我浑身颤抖,附在我耳边说:“怎么?有发现?”我兴奋地点点头,也不管她看不看得见,低声对她说:“从现在起,我念的每个字你都要牢记在心里,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再见到可爱的太阳……”
覃瓶儿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表示明白。
我尝试着将两眼眼光散开,原来清晰明了的鬼火画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那藏在画中的文字却清晰地凸显出来。
我小心翼翼念道:“如花是杯弓蛇巧笑倩……”
我眼光忽聚忽散,努力好几次才将这段文不象文诗不象诗的文字念完,每个字我都牢牢刻在心里,虽然并没得出象“诗”的东西,但我已百分之百肯定,所谓的“诗”肯定藏在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中。
组成“诗”的文字虽然找到,可是这段话怎么念都不通顺,我反复默念了四五遍,感觉这些文字似乎意犹未尽,字与字连起来,有的像成语,有的像“离骚体”的诗句,有的像土家谚语,但都似乎残缺不堪,词不成词,句不成句……噫?我脑海忽然灵光一闪,兴冲冲问寄爷:“寄爷,土家族‘攒言子’的习俗是不是很久以前就有了?”
“听那些道师先生说,土家族最早的长篇叙事诗《梯码神歌》中就有很多‘攒言子’的歌词,现在的道师先生唱孝歌时也用到‘攒言子’。比如我就记得一首是这样的:歌师唱歌真不简,字字句句坚持原,只有愚下缺少见,得罪三方众位先,只有愚下文化浅,未曾读过无字天。每句末尾省略的字分别是单、则、识、生、显和书。这种形式也叫‘明七暗八’或‘吊脚楼’……啷格?难道你刚才念的话也用到了‘攒言子’的方式?”
我没回答的寄爷的话,稍作思索,口齿清晰地念出一首诗:“玉影兮蹈亦,解衫兮难寻,血溃兮乃擒,魂飞兮克城。”诗刚一念完,一声熟悉的女人叹息在黑暗中幽幽响起。听见叹息,我心头一片雪亮,没错,这就是那首解“锁”的诗。
隐在黑暗中的女人似乎在等待我解“锁”,幽幽一叹后又陷入沉默。我欣喜若狂的同时,非常惊叹那女人在两千多前就会运用三维画的原理,在鬼火画中藏了一段文字,并利用土家族‘攒言子’的形式,在这段文字中隐藏了这么一首诗。不过,我细一琢磨诗中的含义,心中大惊——这不是一首表现男欢女爱的淫诗吗?大体意思好像是:你的“玉影”在我眼前跳舞,我脱掉衣服后却找不到你了,血脉贲张的时候才把你捉住,魂飞魄散中终于攻克了你的“城堡”……
我呆若木鸡,好半天才想起这首诗中的意境很符合那个时代的风格。
这么一想,我更有信心了,诗都有了,我还解不开那所谓的“锁”吗?
可是,我还真不知“锁”在哪里,开锁的钥匙又是这样一首诗,那“锁”是什么?“锁”在何处?开动脑筋,想。我暗暗发誓,凭我满鹰鹰这么灵光的脑壳,怎么也得把“锁”找到,我就偏不信你的邪!
我此时已经彻底不去想那女人的“鬼”话了。有“攒言子”成诗这个先例,我推断女人肯定使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招数,借用我们土家族的习俗或特点,安排了一把无形的锁和特定的解锁方式。
“钥匙是首诗,钥匙是首诗……”我在心中反复念叨,脑子翻江倒海,思维势不可挡,“诗又是由文字构成的……”
文字?啊哈,有眉目了,我心里赞叹这招简直用绝了——我们土家族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吗?那女人为何要用这样一首淫诗来做钥匙?这不是一道很明显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诡计吗?
明白了“锁”的关键,我心情大好,麻着胆子在覃瓶儿脸上狠狠亲了一口,摸到满鸟鸟狠狠扇了他几耳光,将他打醒过来。我心里暗想,伙计,你不要怪我手重,与你把我的嘴皮唆麻那件事相比,这简直就是毛头娃娃的虫虫儿——小儿科(蝌)!
满鸟鸟被我打醒,懵然无知,杀猪般叫起来,“哪个打我?哪个打我?”敢情他还以为是鬼在打他。
“是我。借你的破嘴一用。”我赶紧宽他的心,他再晕过去就麻烦了。
“不借!”满鸟鸟显然还在生气,“你不是说过宁愿世有……也不愿看见我这张破嘴么?”
“两条路供你选择。”我嘻嘻笑道,“其一,你把嘴借给我,我们出去。其二,你可以不借,你永远呆在这个地方陪那女人。你选择几?快答,一二……”
不等我数到“三”,满鸟鸟飞快接嘴道:“选一。可是……啷格借?”
“很简单,你只要把我马上告诉你的几个字大声吼出来就行。一个字一个字地吼,直到我听到有反应为止。”
“原来是这么个借法。你说!”
我先把那首诗念给他听了一遍,然后告诉他先吼第一个字。
“玉!”满鸟鸟大声喊道,声音不是特别洪亮,而且有些沙哑,我侧耳细听,除了水滴声,没有任何异响。“再来,声音再大一点。”
“玉!”满鸟鸟清了清嗓子,再次吼道,声音果然中气十足。
嗯?周围怎么还没反应?难道是我想错了?“再来,声音还大一点。”我继续鼓励他。
“玉!”
“声音低一点。”
“玉!”
“再高一点。”
“玉!”
……
满鸟鸟反反复复吼了六次,到第七次的时候,不远的地方“轰”的一声巨响传来。我大喜,摸黑拍拍他的肩膀,“行了伙计,就照这个音量把剩余的几个字吼出来。”
“影……兮……蹈……亦……”满鸟鸟每吼一个字,就是一声巨响。
当最后一个字被满鸟鸟吼出来后,我数清巨响总共是二十次。我在黑暗中全神贯注,等待那道生命之门打开。等了半天,却无仍何动静,周围仍是一团漆黑。
我心里惴惴不安,难道我高估了自己的智力而小看了那女人的诡计?
又等半天,仍无动静。我颓然坐向浅滩,却硬生生刹身子,象根弹簧立身站稳,象个小屁孩般欢呼雀跃,“水涨起来了……水涨起来了!”
寄爷他们听我大喊大叫,起初不明所以,不过他们的脑壳里肯定不是黄泥巴,很快就明白了水涨起来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天然的的梯子吗?
我也明白了那二十声巨响意味着什么,极有可能是那女人布置的巨石受声音的震动掉进水里,堵住水流的同时,开启了另一扇门户,而这扇门户,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求之若渴的逃命之门。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形,我不想多费脑筋去探个究竟了。
水越涨越高,四人一狗相互拉扯着,十条腿猛踩,始终保持浮在水面,我们很快就看不见那幅鬼火画了,也许是被水淹没了吧。
我此时虽然踩水踩得两腿酸软,却不敢丝毫停歇,心里直盼快点找到一个可以落脚并能呼吸的地方好生喘上一口气。只要远离地底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