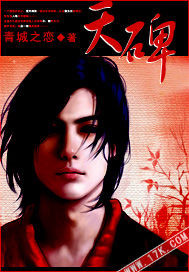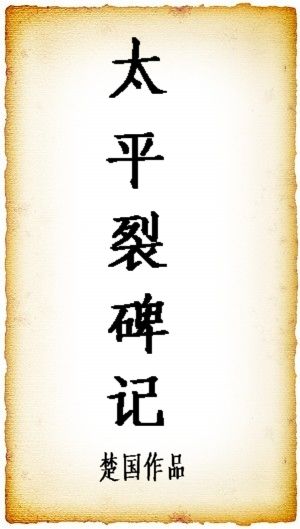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恐怕不是鹰崽崽你想的恁个简单哟!”文书老汉喝了一口浓茶,从寄爷荷包掏出草烟口袋,卷了一只“爆破筒”塞在嘴里,点燃吧嗒两口,磕掉烟灰,意味深长地说。
两杠烟枪同时发威,熏得覃瓶儿赶紧换了个位置,坐到我旁边,远离了烟雾缭绕的范围。我也捏紧鼻子,皱眉侧头问文书老汉:“您家又有什么高论?”
文书老汉难得谦虚了一把,掩饰着吐出一口浓烟,嗫嚅着说:“我老人家哪里有么子高论?我只是感觉事情不会恁个简单而已。”
“听你家的意思,老祖先还有其它任务交给我们?这件事情还不算完?”我对文书老汉的态度一直有一种抵触情绪。这老家伙最善于点火,却总是把灭火的任务交给别人……嘁!
寄爷听我的语气不大对头,剜我一眼,说:“……事情肯定没完嘛!”响鼓不用重锤敲,我听出了寄爷话中的含义,明白他在提示我对文书老汉这个老辈子态度不大友好。回头想想,当初进安乐洞之前,我不也曾经埋怨文书老汉把所有事情生拉硬套往祖先身上扯吗?而事实上呢,我们就真的在安乐洞中找到一块令牌碑,还真不能说那他番上纲上线的理论是信口开河。
我讪笑着递给文书老汉一支烟,讨好他说:“您家莫跟我这个还有奶腥臭的娃娃儿生气,把您家气出个三长两短,鸟叔还不找我扯天皮啊?他那‘格老二’我背不起……”(格老二:拳头)
文书老汉沉着脸,挥手挡开我的手,说:“这烟不倒瘾。……你这些娃娃儿是不晓得廪君老大人在老班子心目中的地位,也根本不理解我们土家族的宗教信仰,平时只晓得信口打哇哇,对土家族的历史也漠不关心……”
我气闷得不行,他之前说的理论有封建迷信的嫌疑,怎么此时倒变成我不关心土家历史的罪证了?这一钉耙打得……我有点晕头转向。
“我们不晓得,您家就讲讲嘛,我早说过您家是土家族的一本活书嘛!”气闷归气闷,我还真不敢再得罪他老人家,仍然很殷勤地说。只是那语气,怎么也拿捏不准,有点阴阳怪气的味道。
文书老汉根本不理我话中的别样味道,边吧嗒着草烟边语重心长地说:“廪君他老人家仙去之后,魂魄化为白虎,世世代代保佑着土家人繁衍生息。‘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廪’的意思就是粮仓,那时节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填饱肚子,所以才尊称他老人家为‘廪君’。你可以想像得到,我们土家先辈在长期的茹毛饮血时期,日子过得有多么艰苦,拥有一个英明的部落首领是多么重要的事,他们为土家人的繁衍生息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我急了,眼见文书老汉的话如放野火一般,很快将成燎原之势,再扯下去说不定会扯出“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你满鹰鹰”之类的话来,于是赶紧打断他老人家,说:“那……那他老人家曾经跟哪个女人有感情纠葛吗?”这个问题才是我最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其它的,先放一边再说吧。听文书老汉和寄爷一口一个“他老人家”,显得十分恭敬和崇拜,我倒也不敢大大咧咧直呼老祖宗的名讳。
“放屁!他老人家啷格会跟一个女人有感情纠葛?你以为都像你们现在这些年青人……脑壳里就是情啊爱的……”文书老汉眉毛胡子一炸,瞪圆两眼怒声训斥我说。
“那……那安乐洞中那个女‘半傀’怎么回事儿?”我不甘示弱的说。同时心里恶狠狠地想,说我就说我罢了,一棍子打倒一大片,连覃瓶儿也连带在内,人家好歹也是远方来的客人,胡子拉茬一大把年纪,说话怎么也不看方向?再说,人吃五谷杂粮,萌生七情六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动物都有“跑伴”的本能呢,何况有血有肉的人呢?你崇拜祖先没错,可是也有点……过头了吧?
心里有火,脸色就不大好看,说话的音量自然也提高不少,个中的意思不言自明。
文书老汉呆了呆,抬头看一眼仍在树上酣睡的满鸟鸟,嘴张了张,无言以对,低头闷头抽烟。我扭头鄙夷地撇撇嘴,心里冷笑,也就这么两把刷子,一到关键问题就拉稀摆带了——您家倒是给我解释清楚啊?
覃瓶儿轻轻拉下我的衣服,悄悄瞟我两眼,示意我说话的语气不要过重。寄爷见我和文书老汉硝烟再起,赶紧打圆场,“……这事儿我和文书老汉也一直琢磨不透呢。按说呢,在他老人家那个时期,讲究的是生殖崇拜,讲究的是传宗接代,女性的地位又非常低,应该不会牵扯到感情纠葛的事儿。可安乐洞中那女阴魂说得那么真实,听其话音,应该对某个男人爱得刻骨铭心哩……”
“她口中的男人不是‘某个男人’,而是我,满鹰鹰!这事儿又怎么解释?”我冷冷地说。想起这个问题我就不寒而栗。
“是啊。这事儿就更奇怪了,难道你是他老人家的转世?”
“鬼扯!”我在心里嘀咕道,转世转了两千多年才转到我身上?鬼才相信!
覃瓶儿冰雪聪明,又善解人意,见我憋得难受,故意岔开话题,找文书老汉闲聊,“满叔,廪君他老人家额头上有字吗?”听见这个问题,我看了寄爷一眼,心道您家交待得还真彻底,不晓得您家是否把我对覃瓶儿那番“摧城拔寨”的举动也告诉了她?
我脸有些发烧,听文书老汉答道:“这个……老班子似乎没说过。”
“那……他跟鹰鹰长得相像吗?”
文书老汉瞥了我一眼,冷冷地回答:“不晓得。”
覃瓶儿毫不在意文书老汉的态度,继续问道:“他老人家养过一条蛇吗?”
“你是想问那条巨蟒?这事儿……我好像听老班子说过,廪君之前的土家人似乎把蛇当成图腾,廪君他老人家是不是养过一条蛇,就不得而知了。”
“嗯?您家不是说廪君是土家人的祖先吗?怎么他之前还有土家人?还有,现在怎么还会有那么大条巨蟒,而且很通人性?”覃瓶儿越来越好奇,声音不大却很急促。
“你这娃娃问得……廪君是土家人有史记载的祖先,但他老人家也不是象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吧?呸!呸!——瞧我这破嘴……至于那条巨蟒能存活到现在,完全得益于安乐洞那人迹罕至的环境嘛,电视上不是经常有各种大型水怪的报道么?”
“哦!——但是能吐出一块令牌碑的蟒蛇就很少见了。”
“嗯。我也想不明白呢!”
“对了,侠马口村和天脚山一直都是这样吗?您家以前知不知道这是个天然的风水局?”
“嘿嘿,我对风水七窍通了六窍……”
……
覃瓶儿和文书老汉聊得十分投机,我暗自纳闷,覃瓶儿怎么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问的都是我想知道的问题?当然,文书老汉的回答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含含混混,对我的思绪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听了半天,仍然搞不清这块血魂碑究竟是什么来历。
太阳已经彻底落山了,天色变得昏暗许多,竹林中的蚊子也多起来,嗡嗡声响成一片,吵得我心中更加烦躁郁闷不已,加上被太阳烤得火热的地气倒涌上来,熏得我浑身臭汗淋漓,恨不得大嚎一声,一吐胸中积存已久的由各种滋味混和而成的憋闷情绪。
满鸟鸟这伙计,不知是蚊子的长嘴刺不透他的皮肉还是怎么的,挂在树桠上睡得怡然自得,我和他老汉吵了半天,居然没将这家伙闹醒。看见他这幅圣相,我拍拍脑袋,决定不再去想安乐洞中那番遭遇。“格老子,大爷我脑壳都快想破了,你小子睡得如此六亲不认,配得上那个‘秤’的称号吗?”我边心里嘀咕,边站起来走到树下,站在一块巨石上,附到他耳边尖着嗓子低声说:“鸟鸟,鸟鸟,快跑,白胡子老汉来了……”
睡梦中的满鸟鸟听见“白胡子老汉”几个字,猛地睁开眼睛,白多黑少的眼珠转了半天,看见天色灰暗,以为还在安乐洞中,吓得“妈呀”一声,双手一撑,抬腿就想跑,却一翻身滚到地上,愣了半天神才醒悟过来,爬起来骂骂咧咧蹦到我身边,劈头就给我一拳,“你这个龟儿子,想吓死你大爷啊?”
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我肩上,打得我差点一坐蹾儿倒在地上,幸好我及时闪身,避开他相当一部分力道,才没将我的锁骨打得碎断。尽管如此,我还是痛得吡牙咧嘴,跟着咆哮如雷,“格老子的,你……你居然下如此的死手……”扑过去就想一顿拳脚相加,将我胸中对他俩爷子的不满一起发泄出来。
幸好覃瓶儿见势头不对,死死抱住我,寄爷也紧紧拉住满鸟鸟,这场架才没有打起来。
我重重塌进躺椅,呼呼喘气,低着头生闷气,为了一个所谓的“白胡子老汉”,满鸟鸟竟然下如此死手,亏他还称“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哩,有这样的“公”这样的“秤”吗?
满鸟鸟见我生气闷声不响,估计也暗自后悔那一拳打得太重了,踌躇了半天,踅摸到我身边,轻抚着我的肩膀讪笑着说:“您家莫生气,是小的不对,来,我给您家揉揉……这也怪你,哪个叫你用‘白胡子老汉’来吓我嘛!”
我一见他那幅痞相,一边咒骂着“痞子痞,打鞋底”,一边顺坡下驴,悻悻地说:“爬开!打一巴掌又给个桃子吃,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嗦?真搞不懂,所谓的‘白胡子老汉’怎么让你怕成这个样子?”
“嘿嘿,不怕刀来不怕剑,就怕白胡子老汉,因为……他是半傀嘛!”满鸟鸟见我仍然气呼呼的,双手撑着我的肩膀,将脸凑到我眼前,陪笑着说。
我一看见满鸟鸟那张大嘴离我如此之近,顿时魂飞魄散,赶紧捂住嘴巴,含混不清地说:“把你的嘴巴拿开……这比白胡子老汉更可怕!”
满鸟鸟双目一凝,不解地说:“我的嘴巴到底是哪里得罪您家了,要的时候就借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嫌是苕洞?”
“我哪时借用你的苕洞了?”
“你的记性被花儿吃了?出安乐洞之前你叫我喊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干嘛?那‘玉’‘影’‘兮’……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是么子东西?”
“玩意儿?没那玩意儿,你恐怕已经成了那女半傀的‘药碴’哩!听清楚了,那是一首诗,叫‘玉影兮蹈亦,解衫兮难寻,血溃兮乃擒,魂飞兮克城。’——听出其中的韵味儿没?”
“没呢,请您家解释下。”
“这首诗嘛——等等!”我忽然大声叫道,接着扭头望向文书老汉,“您家晓得一个叫覃城的人或地方吗?”
文书老汉没料到我会突然问他,态度也很诚恳,呆了半响才说:“覃城?你是问有没有名叫‘覃城’的地方还是人?是古人还是现在的人?”
“……古人吧!”我迟疑了半天,猜测着说。
“晓得啊,覃城是土家历史上最有名的土司王嘛!”
我大喜若狂,不理会几束狐疑的目光,又扭头对覃瓶儿说:“你是不是说过,清和大师叫你回到你应该在的地方?”
覃瓶儿满脸不解,“是啊,怎么啦?”
我从躺椅上腾身跳起,围着几个人转着圈,哈哈大笑,“有线索了,有线索了……”寄爷他们眼光射到我身上,象看猴子玩把戏一样盯着我。
好半天我才控制住激动的心情,从屋里拿来一张纸和一支笔,将那首隐藏在鬼火画里的诗工工整整地写了出来,接着将每句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分别圈起来,递给寄爷,“你看——”
寄爷狐疑地接过纸张,低声念道:“玉……解……血……魂,亦……寻……擒……城?”
“对头。‘欲解血魂,宜寻覃城’,这是一首彻头彻尾的藏头诗和藏尾诗,这八个字就是解开血魂碑之谜的线索,只不过这八个字用的是谐音。”我兴奋地说。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要解开血魂碑秘密,就应该去找覃城这个人?”寄爷(炫)恍(书)然(网)大悟。
“是的。刚才我已经问过文书爷爷了,历史上确实有个叫‘覃城’的人,而且是个土司王,而且是最出名的土司王,想必这个意思应该不会错了。还有,我们到现在不是一直没搞清瓶儿具体是哪里人吗?清和大师很隐晦地说过她应该回到她该在的地方,这两件事情一综合起来,不但说明瓶儿与血魂碑有极大的关系,而且瓶儿很有可能就是土司王覃城的后人……”
“别说,你这个猜测还有点道理。”文书老汉也听出了味道,兴致勃勃地说。
“是啊,有道理……”寄爷心不在焉地说,接着话锋一转,“可是你想过没有,第一,如果这首诗是两千多年写成的,它怎么会预知一定有个叫覃城的后人?第二,土司王覃城已过逝四百多年,我们去哪里找他?”
“这个……”我兴奋过头,倒真没想到这个问题。按照诗中的韵味,如果那女阴魂口中的男人就是我们土家族祖先廪君的话,我可以肯定这首诗就是廪君写给那女人的情诗。那么,难道廪君他老人家真的有先知先觉的能力,知道后世一定会有个叫“覃城”的土司王,才整出这么一首藏头藏尾诗?
照此推论,难道文书老汉口中的“祖先任务”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
第三章 迷境追踪
寄爷提出的疑问显然将其他几个都震住了,一时间没人说话,而脑子里肯定都在思索这两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覃瓶儿双手抓着我的手臂,我感觉她浑身在轻轻颤抖。我很理解她的心情,{炫作为一个试管婴儿出生的女孩子,{书经过一系列诡异的事件后,{网从一首诡异的诗中得知她的先祖可能是土司王覃城,内心肯定是激动和惊喜交加,不能自已。
而此时,我想起了另一个我忽略已久的问题:覃瓶儿背上的绿毛图究竟是怎么消失的?当初在阴阳树那里得知绿毛图消失,我急于想出安乐洞,根本没心思去细想这个问题,而且我当时的认识态度也极不情愿往“灵异”上去想,后来连番遭遇各种“煞”,更没时间没精力去穷根究底了,此时回想起来,这事儿绝不是一件偶然的巧合事件。
更让我感觉诧异的是,将整个事件一梳理,我居然发现覃瓶儿在整个事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正是她将不同的事件片断缝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初进安乐洞是因为她背上的绿毛图,当我们将六月初六怪梦事件解剖得差不多的时候,却得到更多匪夷所思的疑团,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却意外从一首诗中得到解开血魂碑之谜的线索,而这条线索又与覃瓶儿密切相关!
——这事儿,恐怕真的不那么简单。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最大谜团就是血魂碑究竟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会在两千多年后出现在世人面前,又起着什么作用。“欲解血魂,宜寻覃城”这八个无疑成为雪中送炭的线索。解开血魂碑之谜,其它一切谜团都会迎刃而解了,比如说偈语之谜、土字之谜、绿毛图之谜、安乐洞之谜、七星连珠之谜等,甚至清和大师之谜也一定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把想法对寄爷他们一说,他们都什么意见,非常赞同我的分析。
寄爷说:“那……你的意思是?”
“到土司皇城去找覃城,明天就去,哪怕他已经逝世几百年,肯定还有后人在,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坚定地说。
这里的土司皇城特指硒都唐崖土司城,因为它正是覃城偏安一隅独立称王的地方。
我虽生在硒都,长在硒都,却从没去过唐崖土司皇城,对这座见证了几百年土司制度的皇城,我还是从很少的历史资料中和当地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具体详情并没进行深入研究。当然,这与我很少关心土家历史和文化有关。
而我,经过一系列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之后,特别是判断出这些事件与土家历史有联系之后,我对唐崖土司皇城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来还想问问文书老汉有关土司皇城的情况,不过见他老人家阴沉着脸,像谁欠他几十担陈大谷般不耐烦,我暗想难道这就把您家得罪了?心里怪怪的却不摸不着头脑,想想明天就会亲自去那里,唐崖当地人对土司皇城的了解肯定翔实得多,除了张屠夫,我还能吃活毛猪不成?
这一夜我睡得极为踏实,任何梦都没做。
第二天一早,“四人帮”早早聚齐,坐上开往唐崖的中巴车。车上人不多,看装束打扮和听口音应该都是唐崖当地人无疑。
花儿一上车,就引起一片惊呼。我见一些女性乘客露出(炫)畏(书)惧(网)的神色,赶紧宽她们的心,强调花儿不会乱咬人,无需担心。乘客们见花儿温顺地蜷缩在我两腿间,脑袋搁在我膝盖上怡然自得地闭目养神,也就放心下来,看见花儿腿间那个大肉疱,又纷纷好奇地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苦笑几下,解释说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甚至连那个大肉疱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都不知道,乘客们听了胡乱猜测一回,不再追问。
出发之前,我本不想带花儿前往土司皇城,但想起在安乐洞中这伙计几次在紧急关头救了我的命,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帮手,临上车前又看见花儿根本不理我父亲的招呼,执意要上车跟着我,我也就顺它的意,把它带在了身边。
中巴车在绿树掩映的山间公路安静穿行。路是清一色的水泥路,所以车行很平稳,但山间公路蜿蜒曲折,奇异而灵秀的景致象一场立体电影不断在我们眼前变换着场景。这些场景的主色调无疑是那漫山遍野的葱笼苍翠,象一大块翠绿的锦幔,铺满群山的沟沟壑壑,令人陡生想去亲手触摸的冲动;阵阵微风吹过,绿色锦幔波澜起伏,戏弄得缠绵在山间轻纱般的薄雾飘飘渺渺;松涛阵阵,露珠簌簌,勾引得初升的太阳格外卖力,轻狂而慷慨地将和煦的阳光奉献给山山水水,挑逗得绿色锦幔上的水珠晶莹剔透,姣羞无比,遮遮掩掩闪闪烁烁;群山之上,是一片蔚蓝得令人心疼、干净得令人爱怜的天空,几丝不甘示弱的朝霞三三两两围在这片蓝色周围,安静而慈祥地俯视着苍生大地;灰白色的公路在群山环抱中忽隐忽现,象一条悠闲恬淡的巨龙,蜿蜒爬行;远处近处几只不明的鸟儿,扯开歌喉自由自在唱着悠扬婉转的歌谣,惊扰得点缀在山中或红或白的花儿频频点头欢舞,轻快的引擎声、偶尔的鸣嘀声、忽骤忽疏的水滴声、山间小泉隐隐的叮咚声、随风而来又渐渐隐去的犬吠声、牛铃声,都成了一个个欢快跳动的音符精灵,将山水密林营造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