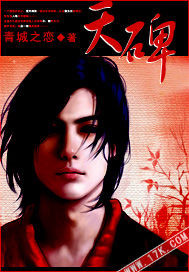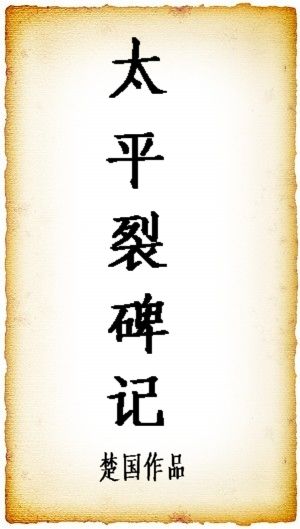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闻言一愣,“怎么有意思?”
“你叫满鹰鹰,他叫满鸟鸟,说去说来都是能飞的,但……‘鹰’字下面是‘鸟’字……这不意味着你一直骑着他么?而且……而且……这‘鸟’字实在是太……”饶是覃瓶儿近段时间变得豪迈、大胆了很多,但说到“下面”和“鸟”字时,语气娇柔得几乎能一把捏出水。
我愕然,这个问题我倒是从来没想过。我悻悻地说:“这可不是我的错,怪他自己字写像鸡刨……”接下来我麻着胆子把“满鸟鸟”这外绰号的来历告诉给了覃瓶儿。覃瓶儿听完噗嗤笑了,“当初第一次听你叫这个绰号时,我就觉得这个‘鸟’字大有来历,也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想不到果然如此。”
“算了,我们不再扯他。”现在不是讨论这些淡不拉扯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赶紧转移话题,“瓶儿,你说你好像来过这里,那你认识牌匾上那几个莫名其妙的大字吗?”
“你都不认识,我怎么会认得呢?”覃瓶儿这句话让我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那……你眼神好,那座石牌坊后面是什么?”
覃瓶儿接过手电,踮着脚尖向墙内扫了几遍,说:“好像也是一座吊脚楼,距离较远,手电光线不足,我看得也不太清楚,不过,感觉这座吊脚楼很大很怪……”
“怎么个怪法?”
“那楼看上去完全是黑色的!”
黑楼?我徒劳地睁大眼睛去看那所谓的黑色吊脚楼,得到的映像是:岂止是黑色的楼,在我的眼里完全是一个黑色的世界……狗日的近视!
“花儿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它不会有事吧?”覃瓶儿很焦急地说。
真的,花儿怎么还没动静?那石梯街道又不长,按它的敏捷程度,即使找不到那只绣花鞋,也应该及时回来找我交差嘛。
我忽然想起花儿自从掉进这里就从没叫过,以及我吩咐它去找绣花鞋时眼里流露出的犹豫神色,脑子霎时就响了,心里开始咚咚呛敲锣打鼓——花儿不会遭遇不测吧?
“花儿……花儿……”我大喊几声,往那条石梯街道跑过去,打算去接应花儿。谁知刚跑几步,脚下一空,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手电扔出去米把远,光线一下子暗淡了许多。我顾不得膝盖火辣辣疼痛,爬过去捡起手电回身一照,发现我刚刚踩空的地方是一条深两尺宽一尺的石砌檐沟。妈那个巴子,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
我此时无暇多想,用昏黄的手电光一扫,模糊瞥见沟底有几截弯弯拐拐的黑色枯枝,心里一喜,天无绝人之路,正好可以做几支火把,要不然手电电池用完,不光是我,连覃瓶儿也会变成睁眼瞎!
噫?这枯枝怎么这么软这么冰凉?这个疑问只在我脑海停留了零点零一秒钟不到,我手一挥,下意识想在檐沟上磕掉灰尘,哪知那软而凉的枯枝几声闷响断成几截……
第十七章 脆蛇(1)
我到此时仍没引起警觉。
我暗自骂娘,妈那个巴子的,人背时,喝口凉水都塞牙,想不到几截枯枝都敢落井下石欺负老子,我打你妈一锤……我嘀嘀咕咕丢掉手中小半截枯枝,去沟底捡另一根更粗更长的枯枝。
“鹰!小心……”覃瓶儿在背后大呼一声,“蛇!”
我脑海一炸,胯下两颗蛋蛋一抽,悚然回头,眯着眼,“哪里……哪里……?”
“在你手上……”我看见覃瓶儿模糊的身影在冲我指手划脚吼道。
覃瓶儿的叫声让我终于意识到手上的冰凉和绵软。我吓得妈呀一声,急用手电一照,只见一条粗大的、通体青黑的蛇儿被我捏在手里!!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我居然无巧不巧握在那蛇“七寸”位置,而那蛇一时挣脱不得,正张开大口,露出两排尖利森白的牙齿,艰难扭头想一口蛟住我的手腕,前端分叉的的信子一伸一缩,几乎只差零点零零零一毫米就要触及我的皮肤。由于近视产生虚影,那蛇的牙齿和信子比实际大小要大许多,边缘模糊,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那样显得轮廓不清……尽管如此,我还是深深体会到那蛇狰狞的面孔!
“还不快扔掉……”覃瓶儿见我呆头呆脑看着那条蛇,又大呼一声。
我如梦初醒,本想把那蛇扔得远远的,谁知手已软得没力气,一松,那蛇就直直掉在我的脚边——这种情形可以用四句土话来形容:年老体质衰,屙尿打湿鞋,本想屙远点,越屙越拢来。当然,这个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谁知更让我震骇的事情发生了,那蛇掉在地上,扑扑几声闷响,绵软滑腻的蛇身竟然齐崭崭断成五截,散落一地。这个情形可以用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诠释:冬天里长长的冰棱高高落下摔在地上的那种视觉盛宴。
我像一只被开水烫了一下的青蛙猛然一跳,蹦到覃瓶儿身边,紧紧搂住她的腰,脑袋几乎深深拱进她怀里。覃瓶儿倒很镇定,也不在意我是不是在趁机揩油,抱着我侧转身,就像蓝球场上护球那样护着我,同时接过手电,眼睛紧紧盯着地上那几截断蛇。默默呆了一会,覃瓶儿声音颤颤地说:“那断蛇……在动……”
在动?那蛇像冰棱一样脆弱,断成几截居然还能动?
我惊疑地侧头一看,地上那几截断蛇像几根熏黑的熏腊肠,正在缓缓蠕动,并且正在缓缓向其中一截靠近,而那一截,正是蛇的脑袋!随着断蛇的蠕动,地上留下一条弯弯曲曲浅浅的血痕……
我和覃瓶儿看得目瞪口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蛇?不但十分脆弱,摔在地上就能断成几截,而且居然死而不僵,每截仍像活体,看这趋势,难道它们还能再次成为一条完整的蛇?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那几截断蛇以蛇头为目标,一拱一拱蠕动一会,很快就变成首尾相接连成一个整体。更耸人听闻的是,每截断蛇都似乎清楚自己的位置,次序井然,丝毫不乱,蛇尾巴绝不会插队到前面,蛇身中间那几断也绝不会谦让,依次排成一个队列……
当然,很多细节都是覃瓶儿告诉我的。
那摔断复为一体的黑蛇仰头看我们一眼,几个S形的扭身,梭到檐沟中去了。
我注意到,那完好如初的黑蛇梭过的地方,没有丝毫血迹!
直到那黑蛇隐在檐沟中不见了,我和覃瓶儿才麻着胆子走上前,往檐沟中一看,里面有七八条大小不一的黑蛇,正在缓缓梭动,并不理睬我和覃瓶儿。
我同时注意到,我第一次捡起的那条被我当成枯枝的黑蛇磕成几截后,原本散落在沟坎沟下的断躯也不见了,地上同样有几条放射状的血痕。我还注意到,地面是清一色的灰白石板,因此那几条弯弯曲曲的血痕在灰黄的手电光中格外刺眼夺目,尤其是在我这个近视眼看来更是触目惊心,夺人魂魄……
我长呼一口气,拍拍胸口,此时才觉得满身冷汗横流。覃瓶儿却扑哧一笑,婉尔说道:“谁说你怕蛇?刚才你不是赤身空拳与它来了一场零距离接触么?感觉如何?”
我气恼得屁股冒火花,仍感觉手上还留有那黑蛇的冰凉和绵软!
我一边在屁股上使劲擦手,一边埋怨覃瓶儿,“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呢?害得我差点魂儿都吓落了……”
“我起初也没看清那是蛇。我见你风风火火捡起一根枯枝猛力一磕,猜想你可能是要做支火把,所以我也准备去捡一根,突然发现那断成几截的蛇身竟在蠕动,我细一看,才发现那居然是一条蛇……我也差点被蛇咬了……”覃瓶儿嘟着嘴说。
妈那个巴子,都是近视惹的祸!
我拉着覃瓶儿远离那檐沟,没有了视觉上的刺激,我心里稍稍好受一些,神情也渐渐放松。照目前的处境来看,那些黑蛇虽然古怪,倒似乎不愿意主动发起攻击。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有余悸,接过手电在周围一通乱扫,发现地面干干净净,并没有那种古怪的黑蛇。这更让我心里轻松不少。
心里放松,我的思维恢复正常。格老子的,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黑蛇究竟是什么品种?这里全是坚硬的灰白石头,它们是从何处而来?它们的身子怎么会那么脆弱?又怎么会断而复活?尽管我知道“土蛇儿”断成几截后也会继续蠕动,但是它绝不会再次整队恢复成一个整体,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每段都是变成新的个体而已。(土蛇儿:蚯蚓)
还有,尽管那些黑蛇现在与我们相安无事,但谁敢保证它们一贯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交正策呢?如果不小心惹恼它们,导致它们群起而攻之,我们除了一支手电,身无寸铁,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再说,即使有幸将它们摔成几截,对它们屁大的影响都没有,对我来说却是一把剜心的钢刀。
如果要将它们斩草除根,彻底打入阿鼻地狱,该用什么办法才会行之有效呢?
这个问题还没想明白,突听头顶一声巨响,似乎又有什么东西砸穿半坡上的吊脚楼顶。我和覃瓶儿急抬头,手电光中,只见一个巨大的黑球从半坡上弹跳下来,砸得一层一层的吊脚楼顶哗啦啦轰响。每弹撞一次,黑球身上就崩飞大量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黑色东西。
我和覃瓶儿还来不及反应,那巨大的黑球在坡底最后一座吊脚楼顶弹撞一次,呈抛物线向我们呼啸而来。我和覃瓶儿只觉一团熏人欲呕的腥风迎面扑来,那巨大的黑球像一个熟透的西瓜直直摔在离我和覃瓶儿的脚不到两尺远的地方,紧接着扑的一声炸开,无数熏腊肠一样的东西飞快射向我和覃瓶儿,有一截甚至差点飞进我大张着的嘴里,那挟裹而来的腥风和几滴温热恶臭的液体,让我的魂魄霎那间就在空中像蒲公英飘啊飘……
我和覃瓶儿失声尖叫,都想躲到对方怀里,相向猛然一扑,强烈的碰撞让我们各自噔噔后退几步,跟着收势不住一屁股坐在满是“熏腊肠”的地上,手上、屁股上、腿上满是冷冰冰肉叽叽的感觉……
第十七章 脆蛇(2)
手电早在那黑球炸开之时就已掉在地上,此时居然在断蛇群中东滚一下西滚一下,光线因此变得很凌乱。借着那昏暗的亮光,我骇然发现那些长长短短的“熏腊肠”,正是先前那种黑蛇的断截身子,此时像溃不成军的士兵,正在乱哄哄蠕动爬行,你拥我挤,看意思是想找到自己所属的那个蛇头重新连成整体。
而此时还有另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由于数量众多,断蛇们一时乱了分寸,好不容易排在一个蛇头后面,却似乎发现这蛇头根本不是自己的老板,所以又纷纷扭转身子撤出队列,两头上翘,东闻西嗅,似乎在极力辨别自己BOSS的方位。因此,此时真正连成一体的黑蛇并不多,大多都还在左冲右突,胡乱翻滚,原本干净淡白的石板地面血痕千丝万缕,很快就变成血糊糊一片,完全像一个憋脚的抽象派画家鬼算桃符的结果……而那手电,已被无数断蛇拱得越来越远!
覃瓶儿在昏暗的光中高高跃起,扑向那翻滚的手电,敏捷地一把操起,扭转身踩着无数断蛇向檐沟跑,边跑边对瘫软在地上的我狂声大乎:“快跑,檐沟那边的断蛇少些……”
我一呆,在覃瓶儿的手电光中,果然看见檐沟那边虽也有很多断蛇在蠕动,却比这边要少许多,很显然是从这边崩飞过去的。我虽然视线不清,但依稀能看见那边露出的灰白地面范围较多,所以才得出这一判断。
我嘴皮抖得厉害,听见覃瓶儿的叫声,双手在地上一撑,试图立身站稳,谁知我此时手脚发软,根本使不上力,屁股刚离开地面几公分,裹着布条的脚无巧不巧踩中一截正在蠕动的浑圆的断蛇,一滑,我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坐得地上几截断蛇像压扁的香蕉,我甚至能清晰感觉屁股已被断蛇的污血浸透,而且断蛇的脆骨也硌得我的屁股生疼……唉!此时此刻,我胯下的两颗“原子弹”早已不听控制,缩进腹腔打死也不归位了,而那枚平日耀武扬威的“火箭”也在危机面前变得蔫头耷脑,其内部却有一股热热的类似氢气燃烧的东西差点喷薄而出……
“怎么还不动?小心蛇头咬你屁股……”覃瓶儿跑了几步,见我呆坐不动,踩着满地的断蛇,一溜一滑折身回来扶我。
此时断蛇们正忙着整队,还没蛇头对我还算丰硕的屁股感兴趣,覃瓶儿一句话却比蛇头真正咬我一口还让我心急如焚。我腰一挺,双手再次一撑,没想到居然摸到两截断蛇。来不及看清究竟是蛇头还是蛇身,强忍心惊胆寒顺手把断蛇掷了出去,哪知心急火燎之下,加上视线模糊不清,我竟把那两截断蛇一前一后向覃瓶儿掷去了。
覃瓶儿脚步一滞,头一偏,其中一截断蛇擦脸飞过,而另一截,覃瓶儿闪躲不及,等反应过来时,那截断蛇已飞近她的耳朵……暗淡的手电光中,我隐约看见那断蛇居然挂在覃瓶儿的耳垂上像一个硕大的耳坠来回荡啊荡!
我以为覃瓶儿肯定会惊呼出声,谁知她纤手一扬,扯脱那截断蛇远远掷开。此时,那惊慌失措的声音才像一把刀子扎进我耳朵,“好疼……”
我懊悔得挥手扇了自己两耳光,浑身霎时充满力量,股肉变得劲鼓鼓的,爬起来扑到覃瓶儿身边,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不由分说张嘴就去她的耳垂猛嘬,一股血腥拌着腥臭飙进口腔。那味道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比小时候那些嫂子的奶香味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此时我哪顾得了那许多?吸一口吐一口,很快我的嘴皮越来越麻,像吃了一把花椒,头昏脑胀的感觉越来越厉害。
覃瓶儿倒表现出少有的镇定,虽被我抱得铁紧,一时挣脱不得,嘴巴倒很利索,“你不要命了?快,我们赶紧跳到檐沟那边再说……”我闻言摸了摸覃瓶儿的脸颊,感觉她并没“长胖”,心中像搬开一块磨盘——此看来,蛇毒基本被我吸出来了。幸亏我的英明决策!
我仍不放心,又衔住覃瓶儿的耳垂,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吸了一口。隐隐感觉飙入口中的液体血腥味越来越浓而腥臭淡了许多,我松开覃瓶儿,脑袋一阵晕眩,站立不稳,差点一坐蹾摔倒在地,幸亏覃瓶儿眼急手快,肩膀一抵扛住我的胳膊,拖起我准备横跨那条既不深也不宽的檐沟。
而此时,那原本在沟底安份守纪的黑蛇不知何故,纷纷立起上身。放眼望去,满沟都是探出沟口的蛇头,吡牙咧嘴,涎水散发出的腥臭扑鼻而来。那情形,就像满沟插满了浸润过毒汁的铁藜……
覃瓶儿意识到事态严重,脚步稍稍一缓,架着我转身想走向那条石梯街道。谁知刚刚艰难跨了两步,头顶又是一通巨响,一个更大的黑球从天而降——那黑球自然是许多黑蛇口尾相连抱成一团碌碌而下。短短几秒钟,那黑球就砸在我们面前,旋即像一个熟透的西瓜摔得四分五裂,一截又一截“熏腊肠”四散开来,落了我和覃瓶儿满头满身。
我意识已渐渐趋于模糊,只凭仅有的一点信念机械地抖落身上的“熏腊肠”。覃瓶儿累得满头大汗,娇喘微微,架着我死不松手。我又模糊感觉覃瓶儿拖着我转身,继续向那檐沟蹒跚而去。我猜测,满地的断蛇肯定断了我们到石梯街道的去路!
头晕耳鸣中,头顶再次传来几声巨响,轰轰隆隆,似乎有无数滚石从坡上滚下来,砸得吊脚楼嗵嗵直响。我勉强睁眼一看,发现已有十数个与先前一般无二的黑球向我和覃瓶儿辗压过来。黑球滚过之后,地上已经像晒谷子一样没有丝毫空隙,全被那通体黢黑的“熏腊肠”占据了。
覃瓶儿用力一顶我的胳膊,从檐沟上飞跃而过,双手仍牢牢撑着我的身子。我已经软得一塌糊涂,而且特别想睡觉,不过仍使出最后的力气艰难抵住覃瓶儿的手,不顾涎水横流,喃喃地说:“瓶儿……别管我……你如果有力气……赶紧爬上那石狮子……再跳到石牌坊上去……吧!”覃瓶儿闻言,不知哪来的力量,顾不得香臀有被黑蛇“亲吻”的危 3ǔωω。cōm险,急转身,腰一躬,后背扛住我的胸膛,双手猛一用力,将我来了个标准的背摔。我在空中飞啊飞的过程中,模糊感觉有黑蛇咬住我的“布鞋”。恐惧象根针直刺心底,我拼尽全力抬腿一摔,只听扑扑几声闷响,我也重重摔在地上。满天的星星还在飞舞,覃瓶儿夹着手电,拖着我的双腿像拉一辆板板车拼命向那石牌坊靠近……
好不容易靠近石牌坊左门,覃瓶儿双手环抱着我的双肋扶我站稳,又转到前面不由分说蹲下身子,双手撑住石门,声嘶力竭喊道:“快!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
覃瓶儿等了一会,回头见我摇摇晃晃站着不动,急了,后退一步,双肩扛住我的大腿,嘿地一声,颤颤微微站起来,“快……爬……”我也急了,再不爬上去,覃瓶儿岂不是要被我压得闪腰?这个念头一诞生,我周身崩发无穷的力量,双手勾住石牌坊,双腿用力一蹬,艰难攀上石牌坊,接着腹部挂在石肩上旋转一百八十度,拉住覃瓶儿的手拼命一扯,覃瓶儿借着这个力道,双腿在石门猛蹬几下,爬上牌坊。
这个过程耗尽我全身力气,脑子一阵嗡嗡乱响,接着什么都看不见了。
意识恍惚中,一张冰凉柔嫩的小嘴含住我的嘴皮,猛力一咬,接着像吸雪糕一样猛吸起来。我被嘴皮上的剧痛惊醒,心里很快明白了。当那张小嘴再次含住我的嘴皮,我稍稍一挣,反含着那张小嘴,也用力一咬,也猛吸起来……
就这样,我和覃瓶儿你吸我一口,我吸你一口,折腾好半天,我的神智才渐渐恢复。
我清醒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抢过手电,借助昏黄的手电光去看覃瓶儿的嘴皮和耳垂。见这两个部位没有变黑淤肿,我心中的一块千钧重石才缓缓坠地。也许,那黑蛇毒液并未修炼到家!
“背时砍脑壳的满鸟鸟,”我仰天大骂,“大爷我在这里受尽千辛万苦,你个背时伙计还在做春秋大梦……”而此时,正急得上蹿下跳的满鸟鸟忽然心惊肉跳,两耳烧得通红。——当然,这是后来满鸟鸟亲口告诉我的。
第十八章 花儿的眼泪(1)
覃瓶儿显然被我突如其来的骂声惊呆了,抢过手电照着我的脸,屏声静气,一言不发。她肯定以为我的脑子被蛇毒攻克了,我想。
我闭上眼睛,裂嘴一笑,说:“我没事,我就是莫名其妙想骂满鸟鸟。你想,要是有他这杆‘枰’在,我这个‘砣’会把你压得花容失色、皮裂嘴歪吗?”
覃瓶儿明白原委,轻笑一声,居然冒出一句地道的方言,“莫日白了,我们还是想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