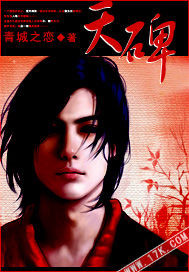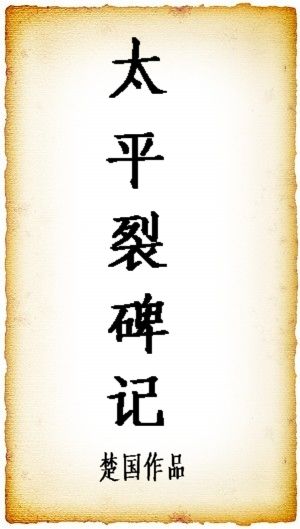土家血魂碑-第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痴呆了许久,我颤抖着声音问满鸟鸟:“你……打开门时,这里有血手印吗?”
“没有。”满鸟鸟肯定地回答道,“我来推门时,看见这两扇门板非常干净,当时还觉得很奇怪,难道这里居然有人居住?当时我还特意在门板上仔细看了几个来回,根本就没看见有么子血手印。而且,你看,这血好像还很新鲜,而且正在顺着门板流动,所以这血手印应该就是刚才那声异响发生时才出现的。”
满鸟鸟的话不无道理。如此说来,这血手印确实刚出现不久。
“那……这门又是谁关上的?”
满鸟鸟一呆,两眼一瞪,“你问我,我问哪个?——瓶儿,是不是你关的?”
覃瓶儿摇摇头,“我进来后一直就在看这个神奇的酒坛,根本没想到要去关门,再说,我有什么必要去关这两扇门呢?”
这么说,关门这件事,排除其它未知原因,只有花儿有最大的嫌疑了。可花儿毕竟是一条狗,它哪会想到主动去关门?再说,即使是它关的门,堂屋又不大,我们离门又不远,为何我们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先前满鸟鸟推门和我后来拉门,这门都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吱呀声,可见这门关得确实无比蹊跷。
想到这里,我越发觉得这堂屋不能多呆了,于是赶紧招呼覃瓶儿和满鸟鸟蹿向那破败不堪、肮脏无比却相对安全些的厢房。
厢房中倒无任何异样,烧烤鼠肉的那个火堆尚未完全熄灭,不时爆出零散的火星,满是灰尘的地上也无其他人的脚印,角落的老鼠粪便、墙角的蛛网、地上各种昆虫的尸体还和先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动,一切都显得正常不过。
几个人各自找到先前的位置一屁股塌了下来,惊魂未定。满鸟鸟最后一个进的屋,为了保险起见,这伙计在坐下来之前居然飞快地关了厢房门。三个人互相望着,眼神中各种成分都有,但都不开口说话,只有墙角的鼠洞中不时传来一阵阵吱吱声。
听见那吱吱声,我突发奇想,莫非刚才那声“啵”的闷响是这些硕鼠闹腾出来的?莫非是它们看见我们三人一狗吃了它们的同伴,因此想出这个办法予以报复?不过,这个想法很快被我否定了,如果这些老鼠愿去堂屋门前,它们早就去了,肯定会留下相当多的粪便和印迹,事实上堂屋吞口那里干干净净,别说老鼠粪便,就连老鼠毛都没看见一根。再说,老鼠能在笔直的门板上爬那么高吗?能在门板上弄出那么一个巨大的血手印吗?——除非它们成精了。
我正在遐想是不是真的有老鼠成精,耳畔隐隐传来“啵”的一声闷响,声音虽小却和先前那声闷响一模一样。我此时的听觉变得极为敏锐,闷响声刚落,我就辨别出那声闷响正是来自堂屋的门板上。
这声闷响显然不是我的幻听,因为覃瓶儿和满鸟鸟像两根弹簧猛地站起来,眼神似乎想穿过紧闭的厢房门,看看外面到底是何方妖孽。不过他们最终没有选择轻举妄动,而是同时把眼光投射到我身上,看样子是在等我拿主意。我咬咬牙,暗骂一声,走到厢房门前。我的手刚接近门栓,外面的“啵”声居然连续地响起来,闷响越来越密,转瞬就有疾风骤雨的趋势。
我猛吸口气,浑身的肌肉绷紧,猛地拉开门,玄衣都邮珠雪白的光芒唰地蹿了出去。泼喇喇的光影中,几只拳头大的黑影无声无息从门前闪过,我仔细一看,狗日的,这些玩意儿不是蝙蝠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奔到堂屋前,发现堂屋门已开了两尺来宽的一条缝,再定睛一看,大约五六十只蝙蝠飞蛾扑火般争先恐后撞向门板上那个血手印。诡异的是,每只蝙蝠在血手印上撞了一下之后,准备飞离堂屋时,却在空中拐了个急弯,像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一般,拼命挣扎不脱,不由自主撞进黑漆漆的堂屋。
我脑子一麻,想起了堂屋中间那个酒坛。本来刚才看见满鸟鸟喝了酒若无其事,我的心已经落回肚里,此时看见众多动作敏捷的蝙蝠居然被吸进堂屋,我已没有心思去看堂屋中的情形了,急转身回到厢房。还没跑到门口,就听覃瓶儿尖叫起来,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嘣地一声撞开门,看见满鸟鸟已经倒在地上翻来滚去,口吐白沫,小小的厢房已被这伙计折腾得灰尘缭绕,十分呛人咽喉。
覃瓶儿见我进屋,缩在一角手指地上的满鸟鸟,“他……他怎么啦?”
我虽然不知道蛊毒发作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此时此刻我已经百分百认定满鸟鸟中了蛊毒。顾不得满鸟鸟满身的呕吐物,一把捞起他放在背上,对覃瓶儿大声喝道:“走,赶紧离开这里!”覃瓶儿来不及细问,捡起满鸟鸟摔在地上的玄衣都邮珠,把花儿拢在腋下大步流星跟上。
一行人急急如丧家之犬下意识向竹桥奔去!
满鸟鸟在我背上痛苦不堪地大声呻吟,双手死命扳着我的双肩,力气大得我感觉自己的肩胛骨快要被他捏碎了,并且他还在我背上拼命挣扎,累得我的脚步踉踉跄跄,好几次都差点歪进水里。尽管我低着头,我还是看见无数只蝙蝠从身侧飞过,旋风般扑向身后的茅屋,“啵啵”声越来越急,那声音,像一颗颗尖利的钉子钉进我的心底。
我咬着牙,尽量不去听那夺人心魄的声音,牢牢托着满鸟鸟丰硕的屁股,拼命向前小跑,到最后我几乎是半拖着满鸟鸟一步一步向前捱。很快,自从我的眼睛只能辨认黑白二色之后,第一次看见了许多有颜色的东西在眼前飞舞——金星!
覃瓶儿见我走得吃力,一路喊着花儿奔到我身边,按着满鸟鸟挣扎翻动的身体,躲避着迎面飞来的无数蝙蝠,跌跌撞撞奔向桥头的黑色采莲船。
那段短短的竹桥似乎越来越漫长。等我们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奔到竹桥尽头,覃瓶儿的尖叫声就在我耳畔炸雷般响起,“那条船呢?”
我拼命梗起脖子抬头一看,桥头空空如也,那艘黑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两只巨龟也不见了!潭面一片宁静,活像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摆在我们面前。
我不由在心里叫了声苦,慌忙把满鸟鸟放在桥上,嗵地一声跳进水里,向前猛跑几步,直到水面快淹到我脖子,我才弯腰驼背去水里乱摸,一边摸一边喊着龟祖宗,想看看那两只我们救过的巨龟还在不在!折腾了好一番,我内心充满绝望,感觉悬着的心在飞快下沉——那两只刚刚把我们送到这里的巨龟确确实实离开了。
而此时,我忽然听见桥上传来一阵歌声,“一哭我的妈呀;不该盘冤家呀;十七十八嘛;哩哩啦,啦哩啦,走婆家呀!哩哩啦……”(盘:养)
第四十三章 哭嫁(1)
虽没回头,我还是第一时间听出这阵歌声正是土家族传承千百年的哭嫁歌。
由于心中彷徨,加上满鸟鸟高一阵低一阵的哀嚎声,以及我扑腾起的水声叠加在一起,起初让我误以为那歌是覃瓶儿所唱,可转念一想,覃瓶儿刚来硒都不久,对土家传统文化的了解几乎是一穷二白,怎么会唱这么曲调幽怨婉转的哭嫁歌?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家汉子都很少听到正统的土家哭嫁歌了。再说,即使覃瓶儿从别处听来那么一两句,在这种场合应该不会莫名其妙的唱歌吧?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覃瓶儿又中邪了,要么那歌根本不是覃瓶儿所唱!
当我倏然扭过头时,我就明确知道答案了。
那歌果然不是覃瓶儿所唱,因为我听见她的尖叫和满鸟鸟的哀嚎此起彼伏,两个人惊恐万状地缩作一团,齐齐盯着离他们眼前不远的一个小孩,不,确切的话,是一个微型的小孩,小孩只是感观上的小孩,身高尺寸远比真实的小孩小得多——只有一尺来高,更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这小孩居然是悬在半空中,身躯上下一抖一抖的。我恍惚意识到,那阵婉转而冰冷浸骨的歌声正是这个小孩发出的。
覃瓶儿拿着玄衣都邮珠乱晃,看情形是想把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小孩从眼前赶开。玄衣都邮珠雪白的光芒不时从她和满鸟鸟的身躯间隙漏射出来,直刺我的眼睛,晃得我的眼前白芒芒一片,我好一阵子根本看不出那小孩长得什么模样,只模糊看见这小孩胖乎乎的。当然,他的整个身体在我眼中都是雪白的,但似乎穿了一件很小的肚兜,因为肚兜是纯黑的,与他雪白的肌肤相比,对比强烈,所以我才能辨别得出他并不是完全裸体。
乍一看见这个诡异莫名的小孩,我一时竟呆住了,口不能言,身不能动,像根木桩桩杵在水中,不知进退。
“满鹰鹰,快来救命啊……”满鸟鸟哀号声中断断续续声嘶力竭叫道。
喊声如闪电一般划进我的脑海,我立马清醒过来,拼命向竹桥扑去,谁知越忙越乱,不知是我吓得手酥脚软还是水流阻力的缘故,我越想尽快爬上竹桥,越是在水中折腾得左摇右晃,一不小心居然还呛了两口水。
我高声咒骂着,拼命往竹桥靠近。耳边仍然传来那小孩冰冷的歌声——
二哭我的爹呀;养奴十八期呀;看看得力嘛;哩哩啦,啦哩啦,要离去呀!哩哩啦!
(啦哩啦;哩哩啦;要离去呀!哩哩啦)
三哭我哥哥呀;小妹要离窝呀;逢年过节嘛;哩哩啦,啦哩啦,来接我呀!哩哩啦!
(啦哩啦;哩哩啦;来接我呀!哩哩啦)
四哭我嫂嫂哇;贤慧又勤劳哇;挑花绣朵嘛;哩哩啦,啦哩啦,是你教哇!哩哩啦!
(啦哩啦;哩哩啦;是你教哇!哩哩啦)
五哭我的妹呀;小奴两三岁呀;操家理事嘛;哩哩啦,啦哩啦,要学会呀!哩哩啦!
(啦哩啦;哩哩啦;要学会呀!哩哩啦)
六哭光兄弟呀;读书要努力呀;长大才能嘛;哩哩啦,啦哩啦,有出息呀!哩哩啦!
(啦哩啦;哩哩啦;有出息呀!哩哩啦)
六哭都哭完那;泪水已哭干那;哪年哪月嘛;哩哩啦,啦哩啦,再团圆啦!哩哩啦!
(啦哩啦;哩哩啦;再团圆啦!哩哩啦;啦哩啦;哩哩啦;再团圆啦!哩哩啦)
……
我的视线被玄衣都邮珠的光芒所阻,所以我既看不清小孩的相貌特征,也分辨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这小孩绝不是人,因为他的声音那么清亮,绝对是一个即将出嫁的姑娘的声音!
一个穿着肚兜的、一尺来高的、悬在空中的、以清亮嗓音唱哭嫁歌的小孩,能说他是人吗?
尽管潭水冰冷,我还是扑腾得满头大汗,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胸腔那里隐隐作痛。这种情况表明我的体力已达到极限,同时心智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
我不知这个诡异的小孩从何而来,我脑中此时只剩一个念头,我要尽快达到覃瓶儿和满鸟鸟身边,要和他们在一起,要想办法摆脱这个小孩。满鸟鸟恐怖的嚎叫呻吟和覃瓶儿尖利的惊呼斥骂完全抵挡不住那小孩清亮的歌声,倒似乎是那歌声的伴奏,听起来格外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惊惧莫名。
谢天谢地谢菩萨,当我感觉自己快要累得虚脱的时候,我终于扑上了竹桥。来不及多想,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飞身扑到覃瓶儿和满鸟鸟前面,伸出双臂把他俩挡在身后,大口喘气带得我的腰一勾一勾,两眼死盯着那个悬在头顶斜上方不远的小孩。
因为有了悬楼那里的经历,我对悬在半空中的物体倒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此时又看见这么古怪的一件事,我竟隐隐觉得心中的好奇占据了恐惧的上风。
此时玄衣都邮珠在我身后,我眨了半天眼睛,总算把这个小孩的相貌体征看得分明:这小孩完全像刚出生三天的婴儿,皮肤细腻白晰,浑身上下都是肥嘟嘟的嫩肉,小脚小手浑若藕节,两只骨碌碌乱转的黑眼珠不安分地盯着我们,樱桃小嘴竟然噙着一抹隐约的笑意,只是那笑意怎么看都是一种嘲乱讥讽的味道。这时我还看清了,他确实是“他”而不是“她”,因为那件小小的肚兜根本掩不住他那根像颗炮竹的小雀雀。
小孩看见我盯着他,停止唱歌,调皮的眼睛对着我连眨直眨,似乎在看一件新鲜好玩的玩具。
“瓶……瓶儿,他……他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肚兜?”我一边死盯着那小孩,一边侧着下巴骨问身后的覃瓶儿。之所以这样问,当然是因为我的眼睛无法看清其它颜色。
“红……红色的!”覃瓶儿声音颤抖,但见挡在她前面,胆子稍稍大了些,把玄衣都邮珠举到我的头侧,一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说。
我不吱声了,因为我心里想起了那本手抄本的另一段话:“……金蚕蛊喜吃人,若干年定要吃一个人。年终岁暮时,主人须和它算账,若有盈余便须买人给它吃,因此算账时,主人打破一个碗要说打破20个,对它说无息亏本,明年再买人饲它。而南靖人的说法,则与此大同小异,他们把养金蚕说成养挑生,金蚕蛊一般放在尿缸边或没人到的地方,不要让人知道,否则便要败露,招致杀身之祸。金蚕能变形,有时形如一条蛇,或是一只蛙,或是一个屋上地下到处跳走的穿红裤的一尺来高的小孩……”
如果看来,这个小孩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最为阴毒的“金蚕蛊”的变身,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么,那茅屋堂屋中的酒坛很可能就是它的栖身之所。
我还没得来及多想,这个谜底很快就揭晓了。
揭晓这个谜底的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我恼之入骨却又求之若渴的人——寄爷!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我和覃瓶儿他们心慌意乱不知如好的时候,我的面门突然涌起一股袭人的热气,那热气是如此熟悉和亲切,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是司刀散发出来的热气。果然,我的眼前很快就有一道寒光闪过,接着耳畔就传来阵阵叮叮的铜铃声和低沉的颂经声。我扭头一看,发现身穿八幅罗裙、头顶宝冠的寄爷站在满鸟鸟和覃瓶儿身后,右手高高举着八宝铜铃,微微晃动,阵阵铃声虽然音量较小,但却清晰入耳,就像那声音本来就在心底鸣响一般。
第四十三章 哭嫁(2)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寄爷,猛听覃瓶儿尖叫一声,手中的玄衣都邮珠唰地伸到我的头前。我悚然回头,看见那个悬在空中的小孩堪堪避过飞射而去的司刀,在竹桥上蹦了几下,弯成一只硕大无比的青蛙猛地跳进水里,震荡起一大团涟漪的同时,那哭嫁的歌声居然仍从它口中传来,“双脚跪斗中,辞别我祖公;双脚跪斗角,辞别我祖婆;下嫁的孙女不孝敬,长大成人撵出去。鸡叫头口已天明,母女即刻要分身,你一尺五寸就盘起,长大就成别家人,费尽心血吃尽苦,燕子衔泥枉操心;穿起一件下贱衣,受人嫌来受人欺,穿起一件下贱裙,又改姓来又改名,青丝帕子盖了头,你的妹是眼泪泡枕头;你的妹妹生错命,眼看就是别家人,爹娘靠你来孝敬,家事靠你来担承……”
不知何故,当寄爷的司刀当啷一声掉在竹桥之后,并不见他老人家有下一步动作,而我和覃瓶儿也许是被小孩变青蛙这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变故惊呆了,一时也没动作,所以这首流传千古的哭嫁歌我们居然听完了。而且那声音哀婉,但从水下传来的声音早已不再清亮,而是变得隐约而闷浊。
尽管如此,我还是听清了这首哭嫁歌正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哭祖”、“哭娘”、“哭嫂”、“哭哥”,正是新娘出嫁那天早上所唱之歌,因为小时候太喜欢找新娘要喜糖吃,所以这样的场面见得太多,对这些歌词还隐约有些印象。
当我还想再听听后面的内容时,那水下的声音却越来越小,渐渐余音飘渺,最终消失不见。
我还在回味哭嫁歌的韵味,猛听身后的满鸟鸟“嗷”的一声,渐无声息。这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响将我的思绪彻底拉回现实,不知何时消隐的焦燥情绪霎时又如潮水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发现寄爷已把满鸟鸟抱在怀里,脸色严峻,一言不发。
“快去挖几条‘土蛇儿’来!”我还没来得及向突然现身的寄爷开口发问,寄爷就抬起头来严肃地向我大声吩咐道。
我又惊又喜,惊的是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到哪去挖蚯蚓?喜的是寄爷终于正常开口说话了而不是用那怪腔怪调的唱歌形式。
“快去啊!再不去,满鸟鸟只有死路一条!”寄爷见我呆着不动,两眼一瞪,怒声喝道。我吓得一耸,“这……一时半会儿哪去找‘土蛇儿’?”寄爷又两眼一瞪,把八宝铜铃放在满鸟鸟的胸口,倏然站起来跑到前面把司刀捡起来塞到我手里,“守着他,一步都不能离开!”说完,他旋风般转身奔向茅屋的场坝,身子一起一伏,活像一只巨大的黑色青蛙在蹦跳。很快,寄爷又跑了回来,接过司刀在满鸟鸟脑门一拍,满鸟鸟像个木偶,紧闭的嘴唇居然一下子张开,寄爷毫不迟疑,捏着拳头把一些东西塞进满鸟鸟那黑洞洞的嘴里。
那些正在蠕动挣扎的东西不用看也知道,正是一条条体形肥硕的蚯蚓!
满鸟鸟些时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任那些蚯蚓滑进喉咙,看得我的胃一阵阵抽搐,覃瓶儿干脆跪在竹桥上哇哇干呕起来。
我此时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只顾呆呆看着寄爷忙碌,既不出手相帮,也不出言相问。寄爷看样子也不时间跟我说话,把手中满满一捧蚯蚓灌进满鸟鸟的喉咙之后,两眼瞬也不瞬地盯着满鸟鸟的脸。顺着他的目光一看,我骇然发现满鸟鸟的脸上似乎有无数条蚯蚓在脸皮拱动,拱动的速度很快,与当初覃瓶儿脸上的东西大为不同。
我虽然没有任何动作,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我的脑海此时居然在邪恶地想,寄爷这老家伙果然越来越神秘了,当初救治覃瓶儿,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此刻看来,居然隐隐有一种胸有成竹的大家风范,这老家伙看来确实有一段能令他脱胎换骨的经历了。
瘫在地上的满鸟鸟低声呻吟一声,吸引我把视线从寄爷转到满鸟鸟身上。
满鸟鸟脸上的东西在这么短的时间就不见了,脸色开始由白转黑,呻吟声越来越大,手脚抖得越来越剧烈。寄爷见此情形,飞快捡起满鸟鸟胸口上的八宝铜铃,单腿跪地一阵猛摇。铜铃声虽然清脆悦耳,听在我和覃瓶儿的耳里却觉得十分的诡异莫名。
当然,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满鸟鸟的脸色黑得像锅底时,满鸟鸟终于忍不住侧身哇哇呕吐起来,呕出来的脏东西腥臭扑鼻。我赶紧捏着鼻子,闭紧双唇,间歇性的吸口气。起初我并没看见满鸟鸟呕出来什么东西,只感觉那团既腥臭且湿腻的脏物中有什么东西在缓缓蠕动,当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