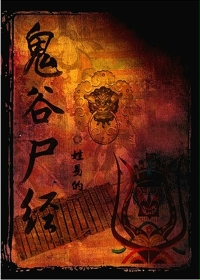道陵尸经-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公子道:“良辰宵刻,怎可少去乐声为耳。”说处,又道:“飘红姑娘,本公子久仰姑娘琴音优雅,今夜,就有劳姑娘为我俩伴耳了。”
飘红身子一震,双颊微微一红。原来,她一直以为,江公子叫她来此处,应是要她抚琴助酒,哪知,却是这样的事情。她虽是青楼女子,但在人家闺房之乐时抚琴,不仅不妥,且还侮辱了她,更玷污了怀中的这架古琴,心中思下,便婉言道:“江公子,飘红忽然偶感身体不适,只怕无法再为公子抚琴助兴,还请公子容我早去休息。”
江公子略是惋惜道:“既是这样,那本公子也不便再行勉留,只是——少了姑娘的琴音,本公子顿感乏味的很,唉。。。。。。只好让飘桃姑娘也随姑娘一道走吧。”
飘红听他这样说,便已知十九是什意思,暗暗骂道:“无耻。”
那边飘桃却急道:“我不走,我不走。。。。。。这里本就是我的房间,公子可要让奴家上得哪去?况且,奴家走了,剩余公子一人岂不孤冷的很,奴家可狠不去那心。”
江公子强作无奈道:“飘桃姑娘可知本公子也不愿这样,只是。。。。。。姑娘若真想留下,还得看飘红姑娘是否愿做成全。”此时,他方露出本来面目,看则爽快答应飘红离去,实则乃是以退为进之策。
斗转星移
飘红咬了咬牙,忖道:“好刁滑的男人。”
飘桃顿了下,思忖道:“江公子可是难得一遇的阔主儿,倘若就这般放弃,岂非可惜的很。”银牙咬处,柔声道:“我的好姐姐,你就忍得一下,当是帮得妹妹一回,依就了江公子嘛。”言罢,居声声低啜起来。
烛火丝丝,映衬着飘红那张略是激动苍白的脸,思索片刻,道:“那好吧!但我只能弹奏一曲,不知江公子可否同意?”
江公子喜悦道:“一曲足够,一曲足够,那就有劳姑娘。”
飘红摆定古琴,倚身坐下,道:“公子喜爱听哪些曲子?只要飘红会的,定当不作推辞。”
江公子大笑数声,即兴吟来诗道:“床间软玉醉温香,佳人美酒伴君郎,不知月下多孤魂,岂可遥望那星辰。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接着道:“今晚本公子有美人,有美酒,有良宵,有天籁,人生至此,只怕连那皇帝老儿都是羡慕不已吧!哈哈。。。。。。”
飘红淡淡道:“公子讲了这许多,飘红还是不明白,公子想听的可是何种曲子?是那红极青楼的‘醉酒会佳人’?还是稍显清音的‘月栖枝头’?抑或。。。。。。”她把几首最常见有名的曲子依序道出。
哪料,江公子却都否却道:“差矣差矣,本公子要听的可是非同俗人。”
飘红道:“那公子心仪的可是?”
江公子道:“斗转星移。”
飘红一阵惊讶,原来斗转星移本是皇宫里的一名擅懂音律的星象官在夜间观望星移变动时所创,后来被后宫的一名嫔妃偶然听到,她觉得此曲柔时细静流水,动时却宛如江涛拍岸,是难得少见一副好曲子,但此曲乃依星运动而生,清奏尚还突显不出它的独特之处,故而加以了修改,并亲手训教了一批舞女,舞随曲动,就如苍穹的夜空,星际流动一般,深得帝王的喜爱。她道:“那可是皇宫里的曲子,我一名青楼女子,怎可轻随抚奏。”
江公子正声道:“本公子要听的,就是以前皇帝常听的那种曲子,难道姑娘不认为,今夜本公子很适合听这样的曲子吗?”
飘红迟疑道:“可是?”
江公子紧问道:“可是什么?”
飘红顿了顿,道:“没什么,那就依得江公子,就弹奏一曲‘斗转星移’吧!”
【第七章 鬼婴现世】
琴缘再续
月色凄寂,柔缀阴黯,屋瓦上的白衣女子心下暗地一震,道:“此青楼女子果不同凡响,难怪常听得二弟提及她来。”又往下望了一望。
突地,一声尖利的喊叫划破将来,白衣女子面色微变,不知屋内出了什么事情?
飘红指尖一颤,琴声嘎然而止,她关切道:“飘桃妹妹,可是出了什么事?”
里面过去半晌才听见飘桃结结支支回答:“没有什事,姐姐自管抚琴就是,毋需理我。”吃吃笑了笑,嘤嘤道:“江公子真是坏死了,奴家都说这样不可以了嘛。。。。。。”
江公子笑道:“有什不可以的,本公子就是喜 欢'炫。书。网'这样来做。”
‘格格格。。。。。。’又是一阵笑骂之声。
飘红脸红了红,心中已然明了实是怎样回事,那接下去的话语,实羞再难听进半语。
琴音复起,尖利的撕夜声一浪高过一浪,飘红柳眉拧锁,内心早已忍耐不及,但不论怎样,既是答应了人家,当也得一曲作罢才可。
‘斗转星移’抚得曲半,飘桃的声音才逐渐轻息下来,不一会儿,便就没了丝毫声响。但飘红经得方才一闹,心已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久久都无法平静。
心既已不安,琴声当也大不如先,但听江公子叹息一声,道:“琴由心声,心乱则琴乱,姑娘如确实弹奏不下去,那就先回去休息吧!”
飘红有些惊讶,道:“公子要飘红走?”
江公子道:“本公子欣赏的,是姑娘的天籁之音,如今姑娘心绪不宁,只怕今夜再也抚不出那般美妙的曲音了,既然这样,那本公子还要强留住姑娘作什?”
飘红道:“可是飘红答应过公子?”
江公子道:“有缘再来相续此曲。否则,就算姑娘有心,怕是琴也不会愿意。”
话音刚落,但听‘嘣’的一声,七弦古琴,已断其一弦。飘红呆了一呆,暗自想:“料不到江公子浮挑好色,却对音律这般懂得。”思处,叹息着道:“看来今晚只能曲半再续,飘红不得不走了,江公子,飘红与你陪不是。”
江公子道:“姑娘客气,要不我让管家送送你。”
飘红道:“飘红不敢劳烦贵管家。”顿了下,又道:“飘桃妹妹,姐姐先回一步,你和公子就早些休息。”
飘桃没有回音,江公子却道:“她已睡下,姑娘如有事情交代,本公子可以将其唤起。”
飘红赶忙道:“公子不必,妹妹既然睡下,还是不要吵醒的好,飘红这就告辞。”
江公子道:“那姑娘慢走,恕本公子不方便出来相送。”
飘红相望一眼,抱上古琴出了屋子。
但瞧翠梅面色焦灼,惶惶侯于门外。原来,翠梅送走张大胆回来,却见小姐已不在房内,但一打听,才知是来了这里,便也匆匆赶了过来。
她见小姐出屋,急忙迎将上去。
飘红轻声道:“我们走。”
二人去后,江公子掀开帘角,只见他衣裳端整,目如凶鹰,一手提着碧青玉盒,行至门后,低令一声:“备轿。”
月残风轻,寥寂的四平古街,忽有一顶软轿缓缓而行,只见轿子出了街口,往西一直抬去。
昏黯的月光,伸手难觅五指,轿前不仅无火杖引路,抬轿的脚夫更是黑纱罩面,但行走的速度却甚是迅捷,不消片刻,轿子已离去四平街十余数里,进到一片浓茂的密林内。
斗转心移
忽然,密林前方一株大树枝顶的枯丫上,突地飞上一只乌鸦,‘呀呀呀’接连叫唤过三声。
只见软轿停了一停,往林中阴处一隐,顿然间消失了。
这时,林内突响起一阵细碎的声音,但见一条白衣女子从一处树下闪将出来,她轻纱遮脸,寻不见表情,但眼中却满腹着疑惑。
她一脚奔至软轿消失的地点,嘀咕着道:“奇 怪{炫;书;网,轿子到了这里怎就不见了?”
怔了一怔,又往前飞速掠去。
岂知白衣女子刚走,阴森的密林黯处,顿现出一个花须老头和一名华衣男子。花须老头先冷冷道:“你为何不让我杀了她?”
华衣男子嘿嘿笑道:“你可知她是谁?”
花须老头险鸷道:“我管她是谁,防碍了主人的大业,便就得死。”
华衣男子笑道:“她可是辛家大美人沈珂雪,就这样让你杀了,岂不可惜的很,再说,主人的计划中,可还有她的用处。”
花须老头白了白眼,道:“那就让她再得意一阵,嘿嘿。。。。。。夜凉风大,一个女人老是窝在房脊之上,那滋味可不见很好受。。。。。。”
华衣男子嘴角冷笑,道:“之前怎没瞧出来,沈大美人也会得几手本事。”
花须老头道:“那又怎样,只待我略施小法,便可叫她有来无回。”
华衣男子笑道:“此些不必你来操心,等得时候,我自叫她瘫于我怀中,依我差遣。”
花须老头嘿嘿一笑,道:“对付女人,我还是挺佩服老弟的。”
华衣男子毫不客气道:“那当自然,我。。。。。。”突地顿住语声,看一眼花须老头,二人赶紧齐身隐没在黯处。
片刻,只见白衣女子沈珂雪又从前方折奔回来,在方才老头与男子讲话的地方停了一停,径朝四平街的方向掠去。
花须老头与华衣男子即出来,花须老头道:“你回去可要小心,千万别走了漏子,叫他人看见。”
华衣男子鹰目一缩,道:“我可是死人,除非阎王爷,谁还能发现的了我。”说罢,哈哈一阵大笑。
花须老头怔了一下,也一齐大笑起来。
窗外星稀暗淡,飘红寝卧在床,辗转反侧,脑中一直在想:“江公子到底是何许样人,行事怎地这般神秘,就连身边的轿夫也得蒙纱示人。不过,他对音律到还有些认识,想来出身该不会太俗。”正当思中,窗棂外忽响来数下响动。
飘红微一激灵,问:“是翠梅吗?”
没有人回答,却见一道白影破窗而入,在地上滚了数滚。
飘红赶紧下了床,拾起地上的物体一看,见是一团握捏成皱巴巴的白纸,里面包着块碎银子。她回到灯下,展平白纸,眉头却顿然拧成一处,但见纸上写着四个刚气的字体:‘斗转心移’。
“斗转心移?”飘红定了定,脸色刹变,喃喃道:“难道。。。。。。难道。。。。。。”
口中之语未有道出,人已冲向了屋外。
黑暗的角落,白衣女子沈珂雪喃喃道:“希望我的猜测不是对的。”叹了一叹,飞掠消失。
飘红一疾来到飘桃房前,只见灯火依旧,那面‘禁’字牌仍然挂着,但独少了守门的江公子的下人。她不及多想,便闯将进去。
房内花香浓烈,烛火折腰,寂静的红帘下,无丝毫声息,似乎与离开时前的模样,不曾有过太大改变。飘红稳了下神情,轻声唤道:“飘桃妹妹,你可有睡着?飘桃妹妹。。。。。。”
家中变故
内房里一片死寂,哪里有人应答。
飘红疑惑般近前,心中顿然有了不祥的兆头。
月下的风声从敞开的门里吹来,红帘猎猎舞乱。突地,飘红暗地一震,从纷飞的帘隙中瞧去,飘桃俯趴在床沿,大半的香肩探在纱帐外面,一头如云的黑发垂延到地,一动不动。
她不安道:“飘桃妹妹,飘桃妹妹。。。。。。你怎就这样睡着?”
飘桃依然无动一下,就像是睡的太熟,一时醒不过来一般。
飘红轻身靠近,轻脚走到床前,轻手揽开帐门。
只见床间俱成乱状,飘桃一手压于胸下,一手指成爪状,死死抓着被褥,而江公子,早已不知去向。
飘红一瞧,顿感不妙,赶紧将飘桃翻身过来。果见,飘桃面色扭曲,双目直瞪,那张樱桃小口,张得比箩筐还大,口中及嘴角还带着丝丝血结。
不过,更触目的还是,飘桃钩往胸口的那只手,指甲已生生嵌进肉中,想像那死之前,该是何样的痛苦。
飘红手下一颤,直退后数步,一张娇美的花容,刹那变得惨白失色。她喃喃着道:“斗转星移,斗转心移。。。。。。我终于明白,我终于明白。。。。。。”身子一软,瘫坐地上。
如初夜色,张大胆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往家回去。
正当行至门外,院中突传来数声响动,但他并未在意,心想该是那几名宿夜的汉子发出的。
昏黯的院落,只有一盏发黄的吊灯在房檐下晃动,一条褛衣人背棺站立。
张大胆推门进去。
褛衣人听见声音,回过脸来,四目相对,两人无不齐时一愕。
张大胆惊声道:“荷心?”
褛衣人微微一怔,低声道:“张大哥,你认得我了?”荷心依旧日间乞儿打扮,脸上的污黑还不曾抹去,但张大胆既瞧过锦绢,怎还能不识她的身份。
张大胆瞧着她,笑道:“妹子既来到家中,怎地不进屋去?”
荷心道:“进屋?哦不,妹子还是愿意在这里与哥哥说话。”她一下显得有些慌色。
张大胆看了看黑暗里那些熟睡的汉子,小声道:“这里漆黑风凉,有什好的?再说,咱也不便打搅了别人睡觉,妹子说对吗?”
荷心呆了一呆,低低道:“他们,他们。。。。。。反正就是不要进屋。”心下一急,使出了性子。
张大胆道:“为什不可进屋?”
荷心嗫嚅道:“因为。。。。。。反正哥哥听妹子的就是。”
张大胆道:“那,那好吧!”
荷心一笑。
但听得屋内‘砰’地一声重响,荷心脸色变了变。张大胆突一震,快步过去提下吊灯,凑近窗户往里探去,但屋内漆黑一片。
旧朴的房屋,只手轻轻一碰,两扇看似完好的户门,便轻巧脱落倒地。张大胆呆了一呆,抬高灯火一扫,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堂屋一片凌乱,家什倒歪有痕,俱无完状。
大祸在临
张大胆脸色变处,喃喃道:“这,这是怎般回事?”
走进屋子,他发现地上,似还有着斑斑血迹。突地,那平常睡觉的卧房踉跄跌出一人来,手上抓着条扁担,见到张大胆,猛然抡起砸来。
张大胆不及防备,眼看削尖的竹扁担就将砸向头顶。这时,屋外一道青光一闪,那人身子晃了一晃,‘噔噔噔’一连颤巍巍退去到墙角。
张大胆呆了一呆,疾身过去,夺下那人手中的扁担,生气道:“过大哥,你为何要打兄弟?”
过老大喉间格格作响,发不出一言半语,手指向屋外,双目惊恐张着。张大胆望去,见荷心满嘴鲜血,凛凛站在那里。原来方才院中过黯,荷心又满脸黑污,顾而没有瞧见她嘴角的鲜血。
片刻,过老大终究不济,两眼圆睁,翘死过去。张大胆一脸错愕,疑端望向荷心。
荷心面色平静,轻声道:“张大哥,你怎么了?为何这般看着我?”
张大胆激动道:“妹子为什要杀他?”
荷心目光一黯,但声音照旧平静道:“我如不出手,受伤的就是哥哥了。”
张大胆一时缄默,半晌后道:“那——那也不能杀人呀。”
荷心咬着嘴唇,悠转过目光,盯看着自己的鞋尖。暗暗念道:“张大哥,就算我不杀他,他也是活不长了,与其他那般痛苦,倒不如死了更是一种解脱。”但是,这一切她是无法与张大胆诉的。
原来,当日前来到四平街时,荷心就感觉这里早已是阴霾弥散,所见到的人俱是印堂发黑,当得夜间观测星象,看到那夜空星月无光,乌纱披影,定星不定,灾星在顶,方知大事不妙,此乃天道将破,冤魂逆天,阳衰阴盛,大祸在临之兆。
天明,她依照事先约下的方式去找张大胆,却发现他家周围早已布有暗人看梢,在不明对方是善是恶,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故装作成乞儿模样,以蒙混哪些在暗处的人,借机将锦娟交于他。
正暗喜一切胜利,神鬼不知间,傍晚街中突现出一顶软轿,叫她好生担心及好奇。她看出那抬轿的四名蒙面脚夫,居然都不是活人,思忖之下,便已乞讨作幌,上前愈探得究竟。岂料,轿旁驰马的老头,性情及其暴烈,抬手挥起一鞭,将她撂倒地上,手给磕破。
她忍住疼痛,心知此时还不是施法教训这些人的时候,便就愤然拦在轿前,希望借机瞧一瞧那轿中的人,但是,轿中人并未出现,而是扔出来两文银子,予以打发。
接下来。。。。。。
她追随软轿,潜进飘飘院,但终因地方不熟,很快便让院中下人发现,所幸她机敏身捷,很快全身退得出来。
出了飘飘院,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张大胆这里。
谁知,刚到得屋前,便闻见里面散出一股血腥之气,她一时担心,便奋然闯了进去,但见屋内横竖躺着数条已经奄奄一息的汉子,所幸中间并无张大胆。
但她还是惊出一身冷汗。。。。。。
棺不寻常
张大胆看着他,又道:“妹子,难道你没话与哥哥讲吗?”
荷心身子微微一颤,心里明白他的想法,但仍然问道:“张大哥要妹妹讲什么?”
张大胆凌然道:“妹子是否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荷心目光攸闪,道:“我不知道,我来时就已经是这样了。”
张大胆道:“那妹子为何早未说,我家中出了事情?”他虽不愿相信这一切会是荷心做的,但言语话间,难免还是会使人误会。
荷心嗫声道:“这,因为。。。。。。我不想让哥哥担心。”
张大胆木怔道:“不想让我担心?”
荷心低了低头。
张大胆看着她,内心涌上一丝温暖,但还是很疑惑。他道:“妹子,你嘴角怎会有那么多血?”
荷心忽地一阵慌张,或许她自己都已经忘却,嘴上居还残带着血污,一时楞在那儿怔怔不所回答。
张大胆静静等着,突地,他似想起什么?飞一般冲出屋子,来到汉子们睡觉的院落,他或许想到,方才这般大的响动,他们不该睡得如此熟。
灯火照见,张大胆身子不禁颤了数颤,其实这些汉子哪是在熟睡,只见他们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