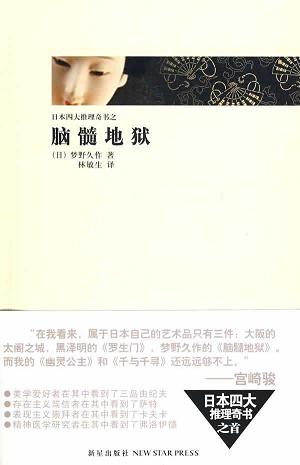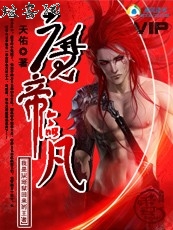脑髓地狱-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上)尽管反覆辩称妹妹干世子离家出走是为了学习刺绣和绘画,但若对照前项疑点,
应该是另有他意。也就是,千世子预料到和姐姐待在同一个家中终究没有结婚的可能,
又认为应该到他乡留下吴家的血统,才在与姐姐的默契下离家,也因此姐姐对于搜寻她
行踪的态度才会稍嫌不够热心。还有,根据姐妹两人都是罕见的好强个性女性这一点点
()好看的txt电子书
来推测,也不难想像两人之间存在某种默契。
(松村松子老师的谈话中)综合所谓“千世子非常会玩弄男人”的事实,以及前述疑问,
足可窥知干世子离家后的行动之一斑。
透过如上各项疑点,可见从事件当初就已充分暗示侄之滨的吴家存在著极端恐怖的血统,而拥有该家最后血统的八代子和千世子两姐妹皆非常清楚这件事。
【十一】剩下问题是,在这次事件里,吴一郎的梦游发作是“依据什么样的心理遗传的哪一种程度之显现进行”
亦即,在第一次发作中,应该认为是梦游直接诱因的有形暗示非常简单,只不过是“一位女性的美丽睡姿”,而且其刺激是由异性诱惑力最薄弱的母亲所给予,因此对吴家特有的令人惊异心理遗传的暗示程度相当浅薄,其梦游内容与该家族特有的心理遗传内容(请参照后段)相一致的唯有“勒杀”一事,然后就转移至受到尸体及其容貌暗示而来的脱轨式梦游,未能显现更多的心理遗传内容。
因而,对于有关前列诸项的一切根本疑问的解决和说明,必须等到这桩事件发生的约两年后,根据在第二次发作中出现的诸般状况分析,方能彻底揭明。
第二次的发作
◆第一参考:户仓仙五郎的谈话
▲听取时日: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侄之滨新娘杀人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一点左右
▲听取地点:福冈县早良郡侄之滨叮二四二七番地,谈话人的家中
▲列席者:户仓仙五郎(吴八代子雇用的农夫,当时五十五岁) ,户仓仙五郎之妻,以及
我(W)
附注:内容使用相当多方言,尽可能以接近标准语记录。
——是的,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当时从梯子上摔下来撞到的腰部,现在还痛得受不了,连小便都要爬著去上,差点丢掉性命。不过今天早上用烤茄子下酒,再捣烂鲫鱼贴上,你看,疼痛已经减退很多了。
——吴太太的家被称为谷仓,在这一带可算是第一的大农户,除此之外,包括养蚕、养鸡等一切,全部由现在的太太八代子独自经营,所以财产庞大,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之多。学校是自己建造,寺院也是祖先所建造,继承家产的少爷(吴一郎)可说是最幸福的人,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少爷乖巧且沉默寡言,从直方来到这里以后,总是在最里面的房间用功,对于下人或邻居不会摆出一副下可一世的态度,风评很好。到目前为止,虽然说是吴家,家人却只有守寡的八代子太太和十七岁的真代子小姐两人,感觉上家中总是阴森森的,但是自从前年春天少爷来了之后,很奇怪,家里突然变得有朝气,连我们都觉得做起事来更有干劲……今年春天,少爷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福冈的高等学校毕业,又以第一名考上福冈的大学,再加上准备和真代子小姐举行婚礼,整个吴家喜气洋洋……
——但是,就在昨天(四月二十五日),福冈因幡叮的纪念馆(一座很大的西式建筑物)举行高等学校的学生英语演讲会,少爷当时以毕业生代表的身分担任一开始的演讲,他穿著高等学校制服准备出门时,八代子太太叫住他,要他换上大学生的新制服,可是少爷苦笑表示还不到时候,不愿意换穿的想逃走,太太却勉强他换上,一面送行一面高兴的拭泪,那情景至今仍深印我脑海。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少爷的大学制服在作祟吧
——然后到了翌日,也就是今天,如我刚刚所说,因为是少爷和真代子小姐举行婚礼的日子,我们从前天起就住在吴家帮忙。真代子小姐也梳著高岛髻,身穿草绿色振袖和红色长裙工作,她那绝世姿色连祖先的六美女画像都难以比拟,而且温柔的气质更如摇篮曲中所形容的“漂亮千金、气质千金,再嫁干金夫婿”。另外,说到少爷,虽然才二十岁,可是不管懂事的程度或是言行举止,连快三十岁的人都比不上他稳重,尤其是他的相貌,你们应该也看到了,根本不逊于王侯公卿,大家都在说,像这样的夫妇整个博多应该没有第二对吧!还有,因为家中有的是钱,少爷又等于是入赘,所以太太废掉一片农田,建造了一栋豪华别院让他们俩夫妻居住,还向福冈最有名的京屋服饰店订购一套和服。至于料理方面,也是昨天就向福冈第一的鱼吉料理店订妥外送的高级料理,从这里也能看出太太内心是何等高兴了。
——昨天的演讲会,少爷的任务很简单,所以出门时他表示再怎么晚也一定在二点以前回来,可是过了三点还足没见到他回来。少爷一向言出必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以我就对老一辈的邻居们表示心中的怀疑,但他们只说“可能是演讲会比较晚开始吧”,完全不当一回事。不过,因为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特别是在这种人生大事的重要关头,我仍旧担心不已,只是后来太忙也就淡忘了。不久,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转为阴霾,天色昏暗有如日暮时分,我忽然想起少爷的事,一看,明天起就是少爷母亲的八代子太太边擦拭著湿濡的手,边把我叫到匡后,对我说“都已经二十岁了,应该不会出问题才是,不过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能帮忙去找找看吗”。我也正好有这念头,就暂时停下修理蒸笼的工作,抽根香烟后,穿著草鞋出门,时间应该是四点左右吧!我搭轻便铁道列车至西新叮,在今川桥的电车终点站顺路拐到我弟弟开的餐馆,问他“有看到我们少爷吗”,弟弟夫妻回答“这……少爷约在两个小时前经过这里,并未搭车,而是步行走向西边,由于他是第一次穿大学生制服,所以我们俩都到外面目送他好久。真是个好女婿哩”。
——少爷一向讨厌这条铁路的煤烟味,即使是到高等学校上学时,也以运动为藉口,每天从侄之滨沿著农田走路前往,但,就算那样,从今川桥到侄之滨只有一里的路途,不应该会花两个钟头的时间……我担心地往回走,时间应该是四点半左右吧!我沿著国道铁路的旁边走,正好在离侄之滨不远的路旁,靠海岸这边的山麓,有一家切割石头的工厂,切割的是称为侄滨石的黑色柔软石头,稍后您要回去时顺便过去看看就知道,不管是从福冈过来,或是从这里前往福冈,一定都会经过工厂旁边。……工厂的石头似屏风般矗立,夕阳照射下的内侧暗处,我似乎见到戴著方帽的身影晃动。
——我的视力虽然不好,也觉得那或许是少爷,走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少爷正坐在高大岩石背后观看某种像是书卷或画卷的东西。我沿著切割好的石头爬过去,刚好来到少爷头顶上方,悄悄伸出头一看,那应该是卷册的一半位置吧?可是,很不可思议的,上面却是一片空白,不像有写著什么内容。但是少爷的眼睛却彷佛见到什么一般,专注的望著空白处。
——从以前我就听说吴家藏有一幅会作祟的绘卷,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不认为在现今的时代里还会存在这种事,就算有,应该也只是谣传,我作梦也想不到那幅卷册就是那个会祟弄人的绘卷。我以为见不到字或图案是因为自己视力下好的缘故,小心的不让少爷察觉,将脸孔尽量靠近,可是,不管我怎么擦亮眼睛,白纸还是白纸。
——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很想问少爷到底看到什么,慌忙跳下岩石,故意绕一圈来到他面前。少爷似乎没发现我走近,手上拿著半开的卷册,望著西方火红的天空,茫茫然下知在想些什么。我轻咳一声,叫著“喂,少爷”,他好像吓一跳,仔细的打量著我的脸,然后才像清醒过来般微笑“啊,原来是仙五郎,你怎么会来这里”,说著转身把卷册收起用绳子绑妥。当时我一直认为少爷是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情,毫不在意的告诉他八代子太太非常担心的事,并指著他手上的东西,问“那是什么样的卷册”,这时,不知何时又背对著我的少爷,奸像忽然惊觉,望著我的脸,又看看手上的卷册,说“这个吗?这是我接下来必须完成的卷册,是一旦完成后必须献给天子的贵重之物,不能让任何人见到”,并将之藏入外套底下的制服口袋里。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问“是因为那里面写著什么,所以……”,这次,少爷脸红了,苦笑回答“马上就会知道了,画著很恐怖的画,也写著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个人说是我们举行婚礼之前必须看的东西……马上就会知道,很快就知道了……”。我觉得自己似懂非懂,伹重点在于,少爷的态度明显像是魂下守舍,所以我执拗的问“哦,是谁给你这种东西呢”,少爷再度盯著我看,凝视良久,才仿佛回过神来似的双眼圆睁,眨了两、三下眼皮,好像在想些什么,紧接著含泪哽咽,回答“送我这个的人吗?那是先慈的朋友,说是送还先慈秘密寄存在他那里的卷册,并表示不久一定会再和我相遇,届时再告诉我她的姓名,然后……就离开了。不过,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但现在还不能说,不能说……你也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知道吗?那……我们走吧”,少爷说完,立刻抢在我前面,在石块上跳跃著回到马路上,快步往前走,速度之快……宛如被什么附身般,与平常完全不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就有问题了……
——少爷一回到家,马上对八代子太太说“我回来了……抱歉,这么晚” ,太太问“见到山五郎吗”,他接著说“是的,石头切割工厂遇上。我们刚从那里回来”,然后指著后面进来的我,匆匆走向别院。八代子太太好像放心了,也没问我什么话,只说声“辛苦啦”,马上对正在一旁摆碗筷并擦拭的真代子小姐使了使眼色,真代子小姐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涩的站起身来,提著水壶跟在少爷身后走向别院。
之后,还有一件在日暮前发生的奇妙事情,我后来才明白其原因……接下来我在后门的栀子树下铺上草席,叼著烟斗继续修补先前未完成的蒸笼。从那里隔著栀子树枝,可以见到别院客厅,所以我不经意的朝那边看去,见到少爷在别院客厅桌前换上和服后,喝著真代子小姐倒给他的茶,对小姐说些什么话。虽然因为在玻璃窗内而听不到声音,但是他的神情与平常完全不同,脸色铁青,眉毛频频挑动,彷佛是在责骂著什么,可是仔细一看,真代子小姐却在他面前边叠好制服边红著脸微笑,不住摇头,感觉上是非常奇妙的景象。
——后来少爷的神色更加铁青,快步走近真代子小姐,指著从这边看就在那三间并排的仓库方向,伸出一只手放在真代子小姐肩膀上摇撼了两三下,本来脸孔火红、缩著身体的真代子小姐好不容易才抬起脸来,和少爷一起望著仓库方向,不久浮现不知足悲或喜的神情,梳著岛田髻的头点了两、三下,脸孔红到脖子根的低垂著脸。那种情景,让我感觉好像是在观赏新派的戏剧……
——见到小姐那种态度,少爷仍旧把手放在真代子小姐肩膀,坐下后,隔著玻璃窗下断环顾四周,不久,仰脸望著屋檐前的黄昏天空,似想到什么般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然后吐出鲜红的舌头,不停舔著嘴唇,他的笑容惨白且邪恶,我看了忍不打了个哆嗦……可是,我怎么也想下到那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前兆,只是觉得很疑惑:心想,有学问的人会表现出如此奇怪的模样吗?伹……后来事情一忙,也就忘记了。
——接下来是昨天晚上。家中的人完全睡著,周遭一片静寂,应该是在凌晨二点左右吧!新娘真代子和母亲八代子睡在正房靠内侧的房间,然后新郎的少爷和代表他家长的我则睡在别院。当然,我比少爷晚睡,十二点过后才上床,关好别院门户之后,睡在少爷隔壁的房间,不过因为年纪大了,今天一大早天色还未亮就醒过来想要上厕所,藉著两扇玻璃遮雨门微亮的光线,来到少爷房前的回廊时,发现崭新的纸门有一扇打开著,纸门前的玻璃遮雨门也有一扇打开,我望向房内,却没见到少爷在被窝里。我觉得奇怪,同时内心一阵下安,但是因为外面下著小雨,只好从崭新的厨房入口拿来自己的木屐,沿著地上铺的跳石绕向正房,见到内侧房间开了一扇门,门前可见到略沾著砂的木屐印痕。我稍微考虑一下后,毅然脱下木屐,赤足沿走廊前进,望向内侧房间的的玻璃纸门,发现八代子太太一只手伸出棉被外熟睡,可是铺在她旁边的真代子的被褥却是空的,睡衣叠放在被褥下方,绋红色高枕置于床褥中央。
()
——当时我才想起前一天傍晚见到的情景,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没必要担心啦”,可是转念一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好,但是少爷的行动有点古怪……我开始呼吸急促。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我认为下能粗心大意,应该趁大家都还没起床……我叫醒八代子太太,指著真代子小姐的床褥说明一切。八代子太太揉著眼睛,好像有点震惊,一边问“你见过一郎最近拿著某种卷册吗”,一边猛然坐起来。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有警觉,回答“是的,昨天在石头切割工厂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读著某种内容不知道是什么、完全空白的长卷册”。当时,八代子太大骤然遽变的神情令我迄今难忘,她嘶哑的尖叫出声“又出现了吗”,用力咬住下唇,双手紧握,全身不停颤抖,两眼往上吊,彷佛有点愤怒失神。我虽然下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也被吓坏了,一屁股坐倒在地。不久,八代子太太好像回过神来,用衣袖拭掉睑上的泪痕,露出又哭又笑的表情说“不,也许我是想错,也可能是你看错,反正我们去找找看”,站起身来,表面上是一副和平常相同的态度,率先从回廊下来,可是事实上她似乎异常狼狈,赤足走向大门口。我慌忙穿上木屐,紧跟在她后面。
——小雨这个时候已经停了。我们很快来到别院前的……从这里能见到的最右侧第三间仓库前面时,我发现仓库北向的铜皮门敞开,慌忙拉住前行的八代子太大,指给她看。事后回想起来,这个第三间仓库在秋麦收成以前一直都是空的,存放各种的农具,人们出入频繁,经常会有年轻人疏忽忘记关闭门户,这时或许也是如此,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但,可能是想起白天的事情吧,我不禁愣了一下,站住。这时,八代子太太也颔首,绕向仓库门前。但是,可能从内侧锁上了吧,怎么都推不开仓库门。这时八代子太太又点点头,马上去拿挂在正房腰板上的九尺梯子,轻轻靠在仓库的窗下,作手势要我爬上去看看,当时,她的神情很不寻常。我仰脸望向窗户,发现似乎有灯火晃动。
——大家知道我一向胆小,所以当时的心情绝对不会愉快,可是八代子太太的脸色相当难看,不得已,我只好脱下木屐,爬上梯子,到最顶端时,双手攀住窗缘看向里面。看著看著,我的双腿脱力,已经无法爬下梯子,同时攀住窗缘的双手也完全失去力量,直接从梯子上掉下来,腰部受到重击,勉强站起来后,却没办法逃跑。
——是的,当时我见到的景象令这辈子想忘也忘不了。堆放在仓库二楼角落的空麻袋在木板地板正中央铺成有如四方形的床褥,上面摊开真代子小姐的华丽睡袍和红色内裙,其上仰躺著梳水滴状高岛髻的真代子小姐一丝不挂的尸体,尸体前方放著原本摆放在正房客厅内的旧经桌,经桌左侧摆著合金烛台,上面插著一根大蜡烛正在燃烧;右边应该是排放著学生用的画具或笔之类的东西,我记不太清楚了。位于正中央的少爷面前,长长摊开著昨天在石头切割工厂见到的卷册……是的,绝不会错,确实是前一天见过的卷册,边缘的烫金图案和卷轴的色泽我都还记得,而且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白纸……是的,少爷面对卷册正坐,身上穿著白花点图案的睡袍,也不知是怎么发现的,他静静转过脸来,微笑,似乎在说“你不能看”的将手左右挥动。当然,我现在说的话都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当时我如同触电般僵住,连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不知道。
——八代子太太当时一面扶住我,一面好像问了什么话,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回答,只记得好像指著仓库窗户说了些什么。但,八代子太他却好像明白似的,重新架好梯子,亲自爬上去。我虽然想制止她,可是我站不起来,连牙关都咬不拢,也发不出声音,只好用双手撑在背后冰冶的泥上地面,抬头看向上面。只见八代子太太敞著前襟爬上梯子,用手攀住窗缘,用与我同样的姿势望向里面。她当时的胆识,我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
——八代子太大从窗外环视里面的情景,用镇静的声音问“你在那里做什么”,这时,我听到少爷从里面以像平常一样的声音回答“妈妈,请您等一下,再过一会儿就开始腐烂了”。周遭一片静悄悄的……这时,八代子太太像是又考虑了一下,说“应该已经腐烂至相当程度了吧?重要的是,天亮了,你还是赶快不来吃饭吧”,里面传来一声“好的”,同时少爷好像站起身,被映在窗边的影子忽然暗了下来。我心想,这是面对女儿尸体的为人母亲者应该讲的话吗?但是,八代子太大迅速从梯子上下来后,边对我说“医师、找医师”,边走向仓库门前。令人惭愧的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就算知道,我也是全身虚脱,根本走下动,只是害怕得不停颤抖。
——仓库门开了,少爷一手拿著钥匙,穿著庭院木屐走出来,看著我们微笑,但是眼神已经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八代子太太迫不及待的轻轻从他手上拿过钥匙,好像欺骗他似的一面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三两句话,一面拉他进入别院,让他躺下。这一切,从我坐著的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