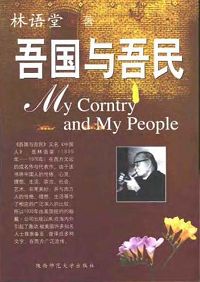吾国与吾民-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思,尽管内战很可能正在他的家门口打响。寻找日常生活中的美,这就是华兹华斯①和中国人想象力的作用。华兹华斯是英国诗人中最富有中国精神的一位。如果雨点打在头上时你也不躲开,你会发现这些雨点是很美丽的。这是明末萧士玮的话。他是在谈论日记写作的非正式文体时说的。不过,这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结论,也是生活中的信条。
『①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
第四章 人生的理想
中国的人文主义
要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这个词含义模糊含混,然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却有它明确的界说。它的意思是: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即中庸之道,也可称作“庸见的崇拜”。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使西方哲学家备受困惑。他们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包括蚊子乃至伤寒菌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为这个自负的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如此这般,人生的意义就从来没有揭示出来过。今生今世自有百般磨难,因而自傲的人类始终无法事事如意。于是目的论又转向来生来世,把今生的世俗生活看作为来世所进行的准备。这与苏格拉底的逻辑恰好符合,即认为一个凶悍的妻子对她丈夫的性格锤炼来说,是一种天然的恩赐。以此躲避人生的难题固然可以使人暂时心平气和,但问题仍旧没有答案:“人生的意义何在?”另外有一些人,像尼采那样知难而上,否认人生“必须”有什么意义,认为人类的进步不过是一种循环,一种野蛮人的舞蹈,而不是去市场采购,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然而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它就像海浪一样不断冲击着堤岸:“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并时时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人看来,人生在世并非为了死后的来生,对于基督教所谓此生为来世的观点,他们大惑不解,他们进而认为:佛教所谓升入涅槃境界,过于玄虚;为了获得成功的欢乐而奋斗,纯属虚荣;为了进步而去进步,则是毫无意义。中国人明确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关系的和睦,儿童入学伊始,第一首诗便是: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在中国人看来,这不仅代表片刻的诗意般的快乐心境,并且是追求人生幸福的目标。中国人就是陶醉在这样一种人生理想之中,它既不暧昧,又不玄虚,而是十分实在。我必须说,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简单到非中国人老实巴交的头脑想不出来。我们时常纳闷,西方人何以竟想不到人生的意义在于纯净平安地享受生活。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似乎在于西方人有更大的能力去获取和创造,享受事物的能力则较小,而中国人享受仅有一点东西的决心和能力都比较大。把精力集中在世俗的幸福,这一特性是我们缺乏宗教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一个紧接着今生今世的来生来世,他就会在今生的一切消逝之前尽情享受,而宗教的缺乏又使这种想法变成可能。
由此生发出一个人文主义,它但白地宣告了人类是宇宙的主义,并规定一切知识都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知识同人类的结合并非易事,因为人类一旦动摇起来,就会被自己的逻辑所左右,成为知识的工具。人文主义只有坚定地把握住人生的真谛才能保佑自己。比方说,人文主义只是在宗教信仰的来生来世与现代世界的实利主义之间,占据一个中间位置。佛教也许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然而与之相对的真正的儒家,对它的影响总感到忿然不平,因为在人文主义看来它只是一种对生活的逃避和对真正人生的否定。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由于机器的迅猛发展,人类无暇享受自己创造的一切。美国营道工人的荣耀使人们忘记了没有冷热自来水我们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法国和德国,许多人伴随着自己的水壶和老式脸盆也照样在他们安逸而漫长的一生中,作出了重大的科学发明,写出了不少宏篇巨著。需要有一种宗教来宣扬耶稣关于安息日的著名教义,并时常告诫人们:造机器为人,而非造人为机器。因为无论如何,人类的一切智慧和知识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类如何保养自己,如何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
宗教
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中国的人文主义者献身于自己所确认的人生真谛,对与此无关的神学、玄学的奇幻异想则漠然置之。我们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孔子在被问及有关死亡这个重要问题时,有一个著名的答复:“未知生,焉知死?”一位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曾经试图让我意识到灵魂不灭的重要性。他说天文学指出,太阳在逐渐丧失掉自己的能量,或许在几百万年之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就不复存在了。“那么,”他问道,“你不认为永生这个问题很重要吗?”我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丝毫不为之困扰。如果人类能生存50万年,就足以使他们做完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考虑另外50万年如何则有点庸人自扰了。试图使自己的灵魂存在50万年以上且不甚满足,这实在是一种乖戾,是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位长老会牧师的忧心忡忡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心灵,正如我的漠不关心是典型的中国人心灵一样。于是,中国人不易变成真正的基督徒。即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也应该变成教友派教徒,因为教友会是中国人所能理解的唯一基督教派。基督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会给中国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是它的教义却会被摧毁,当然不是被儒家的逻辑而是被儒家的庸见所摧毁。佛教在被中国的知识阶层吸收时,即变为一套仅仅是用来保持精神健康的理论系统,而这正是宋代哲学的精髓。
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生活的理想中,有一种固执的东西存在。中国人的绘画和诗歌,可能富有想象力,但是道德伦理学却正好缺乏这种想象力。即使在诗歌和绘画中,所表现的也不过是一种地地道道、全心全意地对庸常生活本能的喜欢。想象力不过是被用来给世俗的生活罩上一层诱人的漂亮面纱而已,而不是用来摆脱它。毫无疑问,中国人热爱生活,热爱这个尘世,不情愿为一个渺茫的天堂而抛弃它。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痛苦然而却美丽的生活。这里,幸福的时刻总是那么珍贵,因为他们稍纵即逝。他们热爱生活,这个由国王和乞丐,强盗和僧侣,葬礼与婚礼与分娩与病患与夕阳与雨夜与节日饮宴与酒馆喧闹所组成的生活。
中国的小说家们所乐而不疲的正是这些生活细节。它们是真实的,人所共有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类直接受到这些细节的影响,那不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吗,全家从夫人到丫环都已午休,黛玉一个人端坐在珠帘之后,听到鹦鹉在叫主人的名字。那不是一个中秋天,或者是某一年那个令人难忘的中秋节的晚上吗?宝玉和他的姐妹们聚在一起,作诗填词,在螃蟹宴上逗笑取乐,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之中。如此完美以至不能长久的幸福,正如中国人所讲的十五的月亮那样,总有阴晴圆缺。或许那是一对天真无邪的新婚夫妇,月夜重逢,双双坐在池边,祈祷上帝保佑他们白头偕老。然而此时,乌云正要遮往月亮,远处传来一种神秘的声音,仿佛是一只在外闲游的鸭子,遭到觅食的狐狸的追捕时,突然跌进水中的声音。年轻的妻子不觉打了一个寒颤,第二天便发起了高烧。是的,如此楚楚动人的美妙生活确实值得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这个世俗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太物欲,太粗鄙,以至不能写入文学作品的,所有的中国小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厌其烦地详述一次家宴各道菜肴的名称,或是客店里一位旅客的晚餐。接下来是胃痛,然后到一块空地——亦即自然人的盥洗室——去了。中国的小说家们这样写了,中国的男人女人们也是这样生活着。这种生活已经够丰富的了,容不了什么灵魂不灭的思想掺和进来。
中国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对世俗生活恋恋不舍的感情,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那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从这两位著名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希伯莱宗教和诗歌与中国现实主义和庸见之间的典型对比。严格讲来,儒家学说并非宗教:它阐发了某种对生活对宇宙的感情,很接近一种宗教的感情,但并不是宗教的感情。世上有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对来世的生活,对灵魂不灭的问题,对整个的神灵世界都不感兴趣。他们的哲学永远也不能使日耳曼民族满意,至少肯定不会使希伯莱人满意,但却使中华民族满意了——大体上满意,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哲学为什么事实上连中国人也从来未能感到完全满意过,而这种不满意又是怎样由道佛两家的超自然主义予以弥补的。然而在中国,这种超自然主义似乎在总体上与人生理想这个问题相脱节:更确切他说,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副产品,或者情感的宣泄途径,使生活更能使人忍受。
儒家学说如此忠实于人本主义的天性,以至孔子及其弟子都从未被尊崇为上帝,尽管中国历史上不少比他们逊色的文学家、军事家都被适当地列入了圣徒名单,甚至被奉若神明。一个普通的民家妇女,如果受辱蒙冤,不得不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她会迅速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地方女神,受到所有村民的奉祀。以下事实也颇能代表人本主义的实质:三国时勇敢忠诚的将军关羽被制成偶像受人敬仰,然而孔子以及平常人祖先祠堂里的列祖列宗都未被制成偶像。反对崇拜圣像的人到孔庙后便无所作为。在孔庙及宗祠中仅有一些长方形的木牌,上写明牌位所代表的祖先姓名,这些与偶像毫无关系。进而言之,这些祖宗英灵并非神抵,不过是一些去世的人物,他们想继续像生者那样对自己的子孙表示关心。如果他们真是了不起的灵魂,他们也许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后裔,但他们自己却需要子孙们的保护,并靠这些孩子援助他们一些食物赖以充饥,一些化为灰烬的纸钱以供地狱中的各类消费之用。他们的子孙也有责任靠佛教的弥撒将他们的灵魂拯救出地狱。总之,他们需要别人关心照顾,正如他们在老年时要孩子们关心照顾一样。这也就是几乎等于儒家学说作为宗教而被崇拜的程度。
笔者经常饶有兴致地观察基督教世界这种宗教文化与中国人坦率承认世界不可知的文化之间的不同,同时也观察这些区别又如何适应了人们的需要,这种需求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共有的。这种差异与人们通常认为宗教的三个作用是一致的。首先,宗教是教士或僧侣权谋的外化形式,包括其教义、使徒传统、对奇迹的出现所寄托的希望和拯救人类于水火并加以赦兔的独家经营权,这些简单而方便的工作,及其实实在在的天堂与地狱等,如此畅销的宗教是对所有民族都适合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可以说它能满足人类文化不同时期人们的不同需要。人们有这种需要,而儒家则不能力他们提供这种需要,于是道教和佛教就来弥补缺陷了。
第二,宗教是对人们道德和行为的一种约束。这里,中国人与基督教徒的观点大相径庭。人文主义的伦理观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在西方人看来,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相互以礼相待,这同样是令人诧异的。人们应该做好事,因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体面的事情,这是应该能够理解的。笔者常感诧异,不知如果没有保罗神学,欧洲伦理学又将如何发展。或许欧洲的伦理学会沿着马库斯·奥里利厄斯①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纯粹由需要来决定发展了。保罗神学发展了希伯菜人关于罪孽的观念,这种观念又给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罩上了阴影。于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类出罪恶之深渊,这就是所谓赎罪论。因为一旦欧洲伦理学与宗教无关就会被视为十分怪诞,所以人们很少想到这种可能性。
『①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ielius,121~180),罗马皇帝。』
第三,宗教提供了一种神灵的启示,一种活跃着的感情,即面对宇宙的庄严和神秘所产生的感情,一种对安全生活的追求,从而使人们心灵最深处的精神直觉感到满足。生活中有这种情形,或许我们刚刚失去亲人,或许久病初愈正处在恢复期,也许是一个秋天阴冷的早晨,我们看到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一种死亡与人生无常的感觉袭上心头,这时我们的生活便越过了五官所及的范围,越过了有形世界而进入来世。
这种情形,欧洲人中国人都会有,但二者对此的反映却截然不同。在我这样一个原来信奉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信教的人看来,尽管宗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从而使人的心灵平静下来,然而,宗教却转移了我们对生活的神秘莫测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这些感觉我们称之为诗。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无法遏制的。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却永远没有保障、也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最终被迫写起了泛神论的诗歌。实际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诗歌代替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情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对中国诗歌的讨论中将涉及。西方人不习惯于这种不信鬼神、纵情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宗教才是逃避尘世的天然方式。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来,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惧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没有足够的诗歌与幻想来充实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麦的山毛榉林中或是在地中海海滨凉爽的沙滩上没有足够的魅力与美景来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恐惧之余,超自然的东西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然而,儒家的庸见认为超自然主义属于不可知的范围故而不予考虑,不去枉费心机;儒家强调人可以超越自然,同时又否认自然的生活方式,或者作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自然主义。这种态度在孟子的著作中阐述得最清楚。儒家学说中人在自然界所处的地位可由以下这个概念说明:“天地人为宇宙之三才”。这个概念多少与巴比特①的三重区别很相似,即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苍天被认为是由云、星等所有不可知的力量所组成的,亦即西方一个法定名词所总结的:“上帝的行为”;而地则被认为是由山脉、河流等所有那些由希腊神话中得墨特尔女神控制的力量构成;人则介乎其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人类知道自己在世界万物中应处的地位,并以此为荣。他的精神,正像中国建筑的屋顶一样,被覆地面,而不像歌特式建筑的尖塔那样耸峙云端,这种精神的最大成功是为人们尘世生活的和谐与幸福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
『①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
中国式的屋顶表明,幸福首先应在家里找到。确实,家在我看来,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②需要修改,以产生出一幅更为杰出的作品。画中应有三个妇女,而不是两个:一个脸色苍白的修女(或者是一个手持雨伞的女道士),一个妖娆的妓女,以及一个神采奕奕、怀孕已有三个月的妇女。其中,家庭妇女应该是最平常、最简朴,然而却是最满足的人物。她们分别代表宗教、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三种典型的生活方式。
『②“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
这种简朴是很难获得的,因为简朴是伟大人物的品德。中国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简朴的理想,当然不是因为懒于奋斗,而是出于对简朴的崇拜,或者说是对庸见的信仰。现在我们来看中国人质朴理想的来源。
中庸之道
对庸见或曰通情达理精神的信仰是儒家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才使得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心思想——得以产生。上一章我们提到了通情达理精神,并与逻辑或理性进行了对比。我们业已指出,通情达理基本上是直觉所使然,与英国人所谓庸见①大致相同。我们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论点“从逻辑上推断是正确的”,那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应该“符合人的天性”。
『①庸见(Common Sense),亦即“常识”。』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懂情理的人,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首先应该是通情达理的人。他通常富有庸常的见解,喜欢随和与克制,痛恨抽象理论与逻辑极端,庸见为所有的普通人所具有。学者往往处在失去这种庸见的边缘,很容易在理论上钻牛角尖;而通情达理的人,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人,应该避免任何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比如,历史学家弗劳德②说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克莱顿大主教却说离婚是受了兽欲的驱使③,庸见的态度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这也许更接近真理。在西方,一位科学家会沉浸于遗传学理论,另一位却着迷于环境意识。双方都固执地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与伟大的愚蠢去证明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而东方人却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就肯定双方都有正确的方面。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论断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错。”
『②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
『③原注:见一本极有启发性的小说《庸见的魔力》(The Magic of Common Sense),George Froderick Wates,(John Murray,London)。』
这种自满常会使一个惯于逻辑思维的人感到愤怒,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