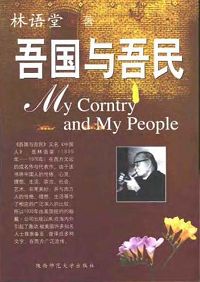���������-��2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ƿ÷���ڶԴ��ⸯ�ܶ�����Ϊ�����е��꾡��д�ϣ��롶���������ֵܡ���ȣ�����ѷɫ������С˵�����ͨ��������ܳ��ġ������״С˵�ڽ�30��������ʱ�֣����������ɢ��������Ϊһϵ�л���û�ж��ٹ�����Ȥ�����£����ܹ��±���������Ȥ����ƪС˵������ʽ����������û�г��֣�ֱ����ʮ�����ִ����Ҷ���ԭ��Ļ����������ѧ����ͼдһЩ���ƵĶ���֮�����ų�¶���ߡ�
������֮���й���ƪС˵�ķ�չ�����ܺõط�ӳ�����й�����ķ�չ����������ģ����۸��ӣ��Ӳ������Ҵҡ���ƪС˵�������Ǹ�����ĥʱ��ģ���һ���ǹ��ϵġ����������㹻��ʱ��ɹ���ĥ�������ֲ�����ȥ�ϻ�ʱ��û�����ɼ���ææ��д�����ꡣ�й���С˵��Ҫ���������������ġ�·�����л��ݣ�˭��·����ժ����
����������ѧ��Ӱ��
�����������Ļ�����ʱ����Ϊ�ḻ�������Ļ�Ӧ�ø��裬��һ����Ӧ���ɣ���һ��ʮ����Ȼ��Ҳ����Ϻ�������ʵ�ϣ����������������ţ�����Ҫ�Ƚ��ɸ�Ϊ���ˡ������ԣ��й���30��������ѧ��˼���ϻ����dz����ȫ�ù鹦��������Ӱ�졣����������ѧ���ݽ�Ϊ�ḻ�������������ϵ���Խ�ԣ���һ��ʹ����ڼΪ����ѧ���ȡ����й���Ϊ��ԼĪ50��ǰ���й��������ӡ���ֻ��ŷ����ͧ��ԼĪ30��ǰ�����Ƕ������������ƶ��������ӡ��ԼĪ20��ǰ�����Ƿ���������Ȼ����ʮ���������ѧ�������ڲ������Ѿ�����������ʶ�����������߱��������Լ������õ������ʶ�������Ϊ�緶��
��������һ�����϶������Ĺ��ȶ��ԣ����ʵ��ʹ�����Խ��ܣ������й�֮���Ѿ����Խ����κζ����ĵز���������Σ���ѧ����ı���Ѿ��������й�����ѧ������������ϵ���̱仯������������2000�������κα仯��Ҫ���������ֱ��Ӱ�죬������������ѧ��ý�飻���ԵĽ������һλ�������������Ⱦ����ʿ���ᳫ�����ġ��ʻ�������ӣ�����ζ�������˴����µĸ�������ǿ�ѧ����ѧ������������ѧ�ĸ���������ڡ���Щ����ͨ��������˼ά�е���Щ�ɲ��ϵĸ����������ơ�����ȷ������˼ά������ԭ���ϵ����࣬����������ı�����ı�����ִ��������������Ա��ϵĵز�������ʹ���Ƿ����Լ��Ѿ�������Ӧ�µ����Ը�ʽ�����������Ϊ��־дһƪ������������϶���Ϊ�˽��ܵ����£�����е�ããȻ��֪���롣��������ʫ��ɢ��ʫ����ƪС˵���ִ�Ϸ����µ���ѧ��ʽ�Ѿ����֣���ƪС˵��д������Ҳ��Ϊ�Ľ�����Ϊ��Ҫ���ǣ��������������뷨���¹ŵ�ѧ�ɹ۵�dz����Ƶ��й�����ѧ�����������ѱ��������¹ŵ�������ʹŷ������һ��������֮�ж�û���ܹ�����ɯʿ���ǣ�����֮������Ǹ�Ϊ���ʡ��ḻ��������ѧ������ֹ������ջ�ʹ��ѧ������߶Ⱥ�г������ʹ���ǵ�˼ά��Ϊ��ȷ��ʹ���ǵ�������Ϊ��ϡ�
������Ȼ������Ƚ��ɸ�Ϊ���ˡ����ɴ����˻��ҡ���������Ȥ�ģ�Ҳ��ʹ��ģ��������ߣ������������dz�ª�ġ�������������й�������ľ���������ʧȥ��˼������ģ�Ҳʧȥ�˻��õ�ӹ��������¾�ѡ��������������һ��Ѱ�����������ܳе������ִ��й��˵�˼ά��ʽ���Ǽ��˵����ɣ�Ƣ������ô�ױ䣬��������ôdz�������⣻�ն��������ѵģ������¶���Ҳ�������ס���Щ�����������壬Ҳ��Щ�����������壻ȱ������˼ά������ȱ�������ȶ����أ����κξɵĶ����������й������еĶ��������е��ܲ��ͷ�����������һ��һ�ȵ�˼�롰��ģʽ��������˹����ȥ��Ѱ���µ�ʫ�ˣ�����������ȥ��Ѱ���µ�С˵�ң���������˽����й����ʱС�Ľ������������У���ֻ��˵���Լ������ĵ�ȱ��������һ��Դ��18���͵��������壬Ҳ��ʱʱϮ�����������ȵ����飬�긴һ��Ŀں�֮��������ת��Ȧҧ�Լ���β�͡�����һ���������ִ��й���Ʒ�����ԡ�
���������Ѿ�ʧȴ���ȶ��������ؿ���������츳�����죬��ѧ�����������ε��Ʋʣ����ұ��ֳ���������Ӫ��һ�����ŷ���˹���壬һ�����Ź������壬������֮Ϊ�ƾ�һ�����ײ�������ҩ������������˼�����������������Ⱦ��й���ʱ��ǿ���١��ɾ��ܱ�����˼���Ѿ��õ��˽�ţ���������ŷ�������͡��ڽ̷�ͥ�������ų���˵Ĵ�ͳ������ļ��Ȳ����ľ�������ȴ��δ��ƽϢ���������ֲ���ֻ���������ִ��������������ˡ���Ϊ������Σ��й���ϲ�����ɣ�����ϲ��һ���������һ��������������ԡ���Щ����ת��ʱ���ij��������������ʱ�������ʧ�ģ�����ֻ�����й���Ϊһ����������֯�úܺõĹ��ȣ����ǵ�����Ҳ����һЩ���е�Ͼ�õ�ʱ��
������һ�б仯��Դ��ŷ����ѧ��Ӱ�졣��Ȼ����Ӱ�첢����������ѧ����Ϊ�й�һ�ξ��ջ�������ѧ���ĸ��ֳɹ������а�����ѧ������ѧ����ѧ������������ѧ�ȷ��棬�Լ�Ϊ�ִ������Ե��Ļ������ݵ�һ����������������������Ķ�ͯ��Ϸ���������赸������Ҳ���ڽ��ܽ�������������ѧ������ʱ�������Ѿ��ܽ��������Ļ����й���ѧ�����еĻ������á�����Ӱ���ֱ����Դ��ŷ����ѧ�ĺ�����������һ����Щ������Ʒ�ķ�Χ�����ݣ��㽫�ᷢ������Ӱ��ij̶ȣ���˳�㿴������Ӱ������͡�
�������İ�ġ�1934�����������У���һ����23���������ʫ�衢��ƪС˵�ͳ�ƪС˵��Ŀ¼����Щ��Ʒ����26�����ҵIJ�ͬ����֮�֡����Ŀ¼�����걸�����Ѻ���˵�����⡣�������ǰ������߶�ѣ�����Щ�����������£�Ӣ��46�ˣ�����38�ˣ�����36�ˣ��¹�30�ˣ��ձ�30�ˣ�����18�ˣ������7�ˣ�Ų��6�ˣ�����5�ˣ�������4�ˣ�������3�ˣ�ϣ��3�ˣ�����2�ˣ���̫��2�ˣ�������ʿ������ʱ���������ݿ�˹�工�ˡ��µ���������ά�ǡ��������ǡ���˹���������ǡ���˹��ӡ�Ⱥ�̩����ռһ�ˡ�
�������������Ӣ��С˵����Ҫ�����Ρ������ء��ƶ������Ѹ���������Ħ����������˹�����١���˹����˹�����ء����˹�ܡ������ؽ��ã���������Хɽׯ���͡�ά���ء�����˾���ء������¡���˹�������˺͵Ҹ�˹�����Ϲ���꡷�����������Ʋ��ƶ������������¶��������������ӡ����������˹����˶���������˫�Ǽǡ�����ʥ���̸衷�͡�����ʱ������������µ���Ʒͨ����磵ķ��룬����˱���Ӣ�����ߵ�������ʫ����Ҫ��˹���������ɺ�������������˹�����ס�ѩ�������̻�˹��ŷ��˹�ء���ɭ��ɯʿ���ǵ��岿����Ҳ�ֱ��ɲ�ͬ�����������������˹���ˡ������Դ�ϲ��������ʮ��ҹ�����������������͡�����ŷ������Ҷ��������������ӿ��Կ����������벻�봿��żȻѡ��Ϸ�緽��Ĵ������и߶�˹���磨�߲����������ޡ���˹��л����������ҥѧУ�����������ɣ��������˵�ְҵ����������ķ����������������ӡ������������ˡ��������볬�ˡ��͡�����Ů������������һ�ɵĴ���������������ᡣ��˵�����ҵĴ�������ķ����ŵ�¡������غ�����˹���ȶ���ķ��ղķ˹������Ͱ�˹�����������ܵ��˺ܴ�Ĺ�ע�����µ������˵����ӡ��������뱾����ɯ�������������뱾�������µġ����������Ļ��͡���ʹ�ĺ�����Ҳ�������H����G��������˹�ɡ�ʱ������������������������Ѱ����������Լ������ȵ���������ˡ���֪�������ԡ�����ʷ�١���������������˹����������С���º�ʫ��������������������Ϊ������֪����ɪ�ա���˹�ƶ����������ѹ���־Ħ��Ӱ���ʮ�ֳ�������������������������ֻ������������������ģ���ȻҲû�а�����������������ߣ����粮���������أ�����Ӱ��Ҳ�Ǿ�ġ�
�������ٱ������������ѧ���������������ֽ�ͨ�õ��뷨����ͬ����
�����������ң��аͶ����ˡ�Ī�ﰧ��Ī��ɣ��ȫ����Ʒ��������ʿ��9����Ʒ�����С�����˿���������뱾�����͵¡�����̩������ʵ�ˡ�����¬�����¼���������ֶ�����������������Ҫ��Ʒ��δ�����������ٰ�����¥�ݣ������������ˡ��������뱾�����С����ʲ����͡�һ�ŵ������ġ�������������С�������ӳ��������ͺ����������ԡ��軨Ů��Ϊ�й�����ϲ��������Ĵ�����Ʒ�϶࣬�С��������������������硷��������ʥĸԺ�����������꡷����ŷ���ᡷ��������������˹���͡�������˹�������ǡ���������������Ĵ������Ķ಼�ﰺ�������������͡����Ρ�����Ƥ�ɵ����¡�ʥ��Ƥ���������µġ��������������ֵġ���ٯ����˹�꡷��Ȼʮ�����˰������֡���������ʮ�ֳ�������˹�Ƶġ�����ŵ��Ҳ���ж��ߡ��Ͷ���˹������С˵�����˳��������ڻ𡷺͡�����������ʹ������������εΪ��۵ġ�Լ��������˹���Ҳ���������뱾����������ġ�����˹�����Ƥ��������˹���͡��������Ľ�������
��������ĵ¹���ѧ��Ȼ���ɸ�º�ϯ���������������������Ʒ�и�µġ���ʿ�¡���������ά��֮���ա��������뱾�������������ء���������ά��������ʩ�������͡���������˹�ء���һ���֣�����ϯ�յġ����ﰺ��������������˶�����������˹�����͡�ǿ�������������������������ȡ��롤�Ͷ���ķ�����������ظ����ż��ߡ��������������輯���Ľ�ѡ�͡�������ɽ�μǡ��������ء�����Ī�ء������ġ��е̺������Լ�ʩ��ķ�ġ����κ����������뱾����ʮ�����С��������������䡶ְ���������칫��������̡Ƥ�������¶����ˡ��ͽ������������������ͽ���������뱾���������������䡶���ӡ���һ�ȳ���һ����־�Ŀ��������������յ����ġ�������̫̫������Ϊ�ִ���������Τ�½�µġ����ش�ء����������¡������˵ġ������Ͱ��ȡ���
�������˻�ɣ��˹�ӷ��ˡ�ŷ�ġ����ˡ����ºͽܿˡ��ص�һЩ������Ʒ֮�⣬���Ƕ�������ѧ����Ȥһ����ڽ�Ϊ�ִ�����Ʒ֮�ϡ���Ϊ�������Ƕ��ն١�������������ʢ���������������ѧ�����йأ�����������13������ɺ�����ﻹ������һ�����˶�������µ�һЩ��ƪС˵�Լ����ij�ƪС˵��û��Ǯ����̫�ˡ���������������ʿ�����ɡ���֡�Ϊ�����������¶ࡤ������������һЩ��ƪС˵��Ϊ���������������˶�ʮ�ֳ������Ƚ𡤰�����������籾��������⡷�͡����ձȵ������������������������ġ���ء������������뱾�����ġ������ǡ��Լ�������ƪ����Ҳ�������
����������ѧ�ij�����1927��ǰ������й�����ʱ��ֵ�Ͼ����������������嵳����ѹ���������˶�֮ʱ������Ӣ����ѧ�ϵ��Ÿ�������ɳ�֮ʱ�����������ϵ��Ÿ�����������ʧ��֮�գ���ѧ�ϵIJ���ʲά������Ҳ���ڹ������ʤ��֮�������й��ġ������˵ľ����飬�����������ƶ���1926��1927��Ĺ����������ʹ֮��Ϊ��ʵ�������ڹ��������������˶�����ѹ������������������ˮ��ʹ������ʧȥ������֮�ء��������DZ�������������һ��ǿ��İ����õ���չ�������Ŷ���ʵ������������������������
�������������ת����������������ѧ�����롰������ѧ��ͬ�壩�ĺŽDZ������ˣ������̵õ��ڶ����ǵ���Ӧ��1917�����ո����˶���������һҹ֮��ͻȻ��ù�ʱ�ˣ��������س�Ϊ�����ˡ���������й����������ˣ�Ҫ�����ǵķ��ˡ���Щ������������ǿ�ʼѧϰ��α��ֳ�Ĭ������ʼ�ղعŶ��������������ڼ������ߺ��ţ������Ƕ����ķ�ӳȴ�Ƚ���Į��������ҪһЩ�����ö�Ķ����������ˡ������͡���˿�������Ҷ���Щ���������ߣ�����������������С�³Ѹ����ս�������ֿ���ɳ�����һ�꣬�������Լ�Ҳ�ı���������
������1928��1929�겻�������ʱ��������̶��г���100���Ķ�����ѧ��Ʒ���Կ��ȵ��ٶ�ӿ���й���ͼ���г�����ʱ�������������������������˹�������Щ�鼮�������У�¬�ɲ��˹�������DZȶ�˹������Ъ��˹������Ү�����ؿƷ���̩��ϣʲ�Ʒ�����ŵ��Ƥ���ˡ��¸�������˹ŵ��˹����ɳ�������ſƷ��з��пˡ������ж�˹̩��������ױ����������ͱ���������ؽ�����ŵ�����ޡ�¬�̡�ɣ�Ῠ���������ȡ��ͺ��״�Ѷ���������Ħά�桢����ϣ����л��ŵ��Ф������ᡤ�ߡ�ά������ٿơ����м��ǿƷ���������������������ŵ���Լ��Ƹ��������������ǵ�Ȼ��δ���ἰ����ǰ�ġ�ΰ��Ķ����ˡ���������ϣ����ڭ���ж�˹̩������������������֮ǰ��Ϊ��������֪�ˡ���ڭ���ȫ����Ʒ�ѱ������˹������ж�˹̩����Ʒ�������20�������а���ƪ���߳��ġ�ս�����ƽ�������룩�������ȡ��������ȡ��͡��������˹��Ү��˹����һλ���ܶ������������ң�����7����Ʒ�����������뷣���������������������Ҳ����Ϊ������֪��������Ʒ21�������������Խ����ʱ���ĸ߶�����Ȼ�����˽�֪�ġ�����ʥ��������Ү��Ͱ���־���������³Ѹ��Ӱ��Ҳ���ܻ�ӭ����Ϊһ�����������ʽ�����ı�־�����ǿ����ἰ��������������ʵ���Ǿ�����100�ಿ������������Ʒ����23�������������뱾���ɲ�ͬ�Ĺ�˾������ͬʱ������淢�У��������IJ�ͬʱ��3���뱾���ڽ�Ϊ���е���Ʒ�У�Ҳ��Ӧ����һ�¿���̩���˵ġ���ɫ�İ�����2���뱾���������ؿƷ�ġ�ˮ�ࡷ��3���뱾�����¸�����ġ���˹�ѡ����Dz��ɷ���ռǡ���3���뱾��������־�����ġ���������3���뱾����������Ħά���Ƥ���˵ĸ��ָ�������Ʒ����ʲ�Ʒ������ŵ���Ϸ�磬�Լ�¬�Dz��˹�����������¡�
������������й�һ�γԵ���ô�ණ�����������Ƕ���һЩ��������������������Ҳ�ɺ�ǡ��ֲ��û�ɣ�Ͱ����ж�������ʿ���Ѿ����ع�ʱ�ˡ��������������Լ����۾����뿴����������ô���£�������ͼ����ʲô�����ǵ�������ʲô�������Σ������ܹ�Ԥ�ϡ����ż������ʵʩ������Ҳ�Ѿ������ж����Ѱ���ǣ���������ʹ���Ƕ���״�е����⣬������;���ɴ��Ŀ�ġ���һ��ıЩ�ò��¸���Щ���ң��ⷽ����ʱҲͦ���õġ��������ֹ�ǰ����ҷ�й����֮�ǣ�����Ȼ����֮�١�����������״�Ľ����ù�������ȷʵ���⣬����������ż�鲿�����������ġ��й������ڿɷ�Ϊ�ֹ������ߺͱ������������ɣ��Һ��߾Ӷ����������������������ԵĹ��������Щ̤̤ʵʵ�����룬����ƽ�������˼ά����������⿿����ںţ���������ʵ������߶߶���Dz�����ͳ�һ���¹������ģ��������ǹ������壬���Ƿ���˹����Ĺ��ҡ���һ���й�������й��������ѧ˵�Ĺ���ϣ������Ը�Ů���Ľ����ԹѸ��ؽڵij�ݵȵȣ����ⷴ����ʹ��һ���й�����Į���С����ͬʱ����Щ�����������������ߣ�Ҹ��Ю�ſ���������˼���������������ҵ�ͷ�������Ŷ������̣����ϵع��������ָ���Ǹ���Ҳ��Ȳ����й��Ŀ��ѡ���ѧ�ⶫ�������ҿ����Ծ�������ѧʿ��������Dz������Ҳ�գ�����Ҳ�ա�
�����ڰ��¡���������
����������
����������֮�������й�������һ�з����У�Ψ���������ܶ������Ļ��������õĹ��ס�������һ�㵱�����м��ҵ����ۡ������й����������ҽҩѧ��ҽѧ�ϵ��о��ͷ����ṩ��һ����������أ��й��Ŀ�ѧ�������Ҳ�����������������й�����ѧ��ԶҲ�������������һ���־õ�ӡ����Ϊ�й���ѧ����ӹ�������Լ���ƽ���嶼����������˥����һ��������ɵģ������й���ѧ����Զ���ʺ��������˺ö����������ʢ�Ļ�����
��������ͬ����ԭ���й��������֯��ʽҲ��Զ�����ʺ�����������ѧ���ڿ̰壬��ѧ������Į����ѧ���������������ʺ���������������ۡ�ÿ��Dz����Աȥ����̽�ա�����������ߴ����ٶȼ�¼�����Ǿ������Ϊ���õķ��ͽ������������һЩŷ�ķ��ɮ�¡�������һ��ʱ������ʮ�ֺ���������ʮ�ּ��ң�������ס�����ɧ���������������ߣ�һλ���ɮ�£���ʹ��������ʱ��Ը����������Ǵ�ز�������ջ�����ŷ�ޡ���ŷ�����������ģ���ͼ����Ϊƽ������֮ʱ�����Ǿ��Եû��ƿ�Ц�ˡ�
����Ȼ����������й�˵�������Լ��������������Ĺ���Ҳ�Dz���ƽ�ġ��й�������������ŵĶ�����ֻ��ͨ�������������еķ��ղ��ܱ���ʶ����Ϊ������ŵ���������й��������м���������Ϊ��ϸ�ĸ��鱻�����е㲻̫����ϲ��������ɱ��ˡ��й��˺��ޱ�������ݺ��棬������һ�������������壻�����������������һ���������ǵĺ�ˬ�����顣��Щ�ƣ�ɫ�ֱ�����ָ�������������г�����߸ߵ�ȧ���ϵ�������˸�ź��ƵĹ�â��ϸ���ž����Ļ��档���������ѧ�ߵ��ż㣬���и�ʽ�����Ĺ���Ʒ���й�������չ�ֳ�һ�־�����г��������й�������Ʒ������������Ѿ����Ʒ֮�֡�
������������ŵ��Cyrano��de��Bergerac�������������Ҽ�ʫ�ˣ���˹������ͬ��ʫ��������̡���
����ƽ�����г���й�����������������Դ���й������ҵ����顣�й���������������һЩ�ˣ���������Ȼ�����ദ�����������������ͽ�Ǯ���ջ����ǵľ�������س�����ɽˮ��������Ȼ����֮�С���ΪҪ�ߣ����DZ����ؽ�̹��������˿��а���Ϊ���Ǽ��ţ�һ�������������һ������һ�����ˡ����������ȡ�������־�������ؽ�����Ҫ��ͨ��������ɽ��������գ���˼ڤ����ﵽ�ġ������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