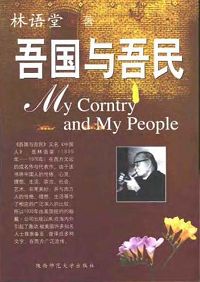吾国与吾民-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路。
『①H。 B。 摩斯(H。 B。 Morse,1855~1934),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著有《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史》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持续的过程,理解哥伦布-水手传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有条不紊地继承下来的。我于是为中国感到难过,可惜不是我们人性的力量,而是我们的黄金,我们作为具有购买力的动物把西方人吸引到了这个远东海岸。是黄金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①所讲的“既预示幸福又预示灾难的女神”把西方人和中国人绑在一起,把他们扔进这个卑鄙龌龊的漩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纽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中国人便问英国人,既然你如此记恨中国,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而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租界。他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英国人认为不值得让中国人去理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国人认为,让英国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着的事。
『①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作家。』
然而,中国人理解自己吗?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讲解员吗?人们公认,自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语言障碍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但中国悠久的历史却能使他颇费精神。她的艺术、哲学、诗歌、文学和戏剧之复杂很难使他钻进去,并加以清理,从而完美地理解和阐明这些问题。他的同胞,同一趟电车上的旅伴,现在正在控制着某省大权的者同学,也都使他难以理解,难以原谅。
可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现代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的心中正在进行着一种乃至多种艰苦的斗争,其中有理想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争;有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这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的灵魂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有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斗争,产生于羞耻与自豪之间,对自己的家庭忠贞不渝,而对家庭的现状又感到不满和惭愧。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时,他的宗族自豪感占了上风,而在正常的自豪感与极端的保守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有时他的羞耻的本能占了上风,而在诚心改革的愿望与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和现代拜金主义之间,距离又是那么小。要想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么,将自豪感与诚实改革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关键在哪里呢?既能欣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结合绝非易事。因为这就要求我们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锗,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捡出那应当捡出的东西。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勇气,有一种罕见的诚实,还有那更为罕见的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活跃头脑。
他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显然有独特的优越之处。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做与耻辱,荣耀与邪恶。看来,我们整理传家主的比喻并不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下意识的民族遗产都已融于中国人自身之中,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可能已经学会玩英国足球,但他并不是真的爱好,他或许已学会羡慕美国人的高效率,但在内心里,却反对这种效率;他也许学会使用餐巾,但他讨厌这种东西;从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中。他听到了一种泛音,这是一种东方古老的民歌和田园诗的回声在诱惑他回到东方来。他昔心钻研了西方美好与难臻的东西。但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在接近40岁时,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了。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服,既平和又舒但。在中式长袍与便鞋中,他的灵魂得到了慰藉。他再也不能够理解狗带项圈这类事情了。也奇怪,他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容忍这种东西。他再也不踢足球了,而开始寻求中国式的修身之道。他漫步于桑田竹林之中,杨堤柳岸之上,做着自己的锻炼活动,这种活动甚至与英语中的“乡间散步”也有差异。这是东方式的漫步,于身心大有神益。他甚至讨厌“锻炼”这个词,为什么要锻炼呢?这是一个可笑的西方观念,甚至那些可受尊敬的人为一只球在运动场上互相追逐也是荒唐的,极端荒唐;更荒唐的是在大夏天运动以后,还要把自己裹在闷热的法兰绒和羊毛绒衣之中。为什么找这么许多麻烦,他想。他记得自己当年也是乐此不疲的,可他那时还年轻,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真的没有这个运动的冲动。不,他生来就是与此不同的,他生来是要叩头,要安静,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颈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时想,自己可能是一头猪,而西方人则是一条狗。狗喜欢咬弄猪,而猪则只是报之以哼哼,这甚至很可能是满意的哼哼。为什么不呢?他甚至想做一头猪,像一头真正的猪那样地舒服。他并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安静地一人呆在那里,狗不要去打扰他。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观察东西方文化的。这是唯一观察和理解东方文化的途径。他有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每每论及中国,他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忍耐、苦难、幸福、坚忍与刚毅。这是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生活。然而却丝毫不比现代文明生活逊色。同样伟大,同样高尚,同样谦逊,同样真挚。这样他真正地了解中国了。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观察中国的唯一方法,也是观察任何一个外国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异乎寻常人的道德价值,通过考察在表面英俊优雅的仪态之下真正的礼貌与谦恭程度,通过考察妇女奇装异服遮盖下的真正妇女特征与母亲气质,通过观察男孩子的调皮与女孩子浪漫的白日梦。男孩子的调皮,女孩子的梦想,儿童们的笑声,他们嗒嗒嗒的脚步声,妇女们的哭泣,男人们的忧伤——这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只有从男人们的忧伤与女人们的哭泣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民族之间所不同的仅仅是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所有明智稳妥的国际批评的基础。
第一章 中国人
北方与南方
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或者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首先要认真研究那个时期的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提起衰亡的罗马时代,我们就会想起马库斯·奥里利厄斯①或者卢西恩②;提起中世纪,就会想到弗朗西斯·维龙③。于是,这些时代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亲切,变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约翰逊时代”这样的名词就比“十八世纪”对我们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回想起约翰逊④是怎样生活的,回想起他经常光顾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讨论问题的朋友们,这个时代才会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时代。也许约翰逊时代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或一个普通的伦敦人会同样使我们联想到这个时代。然而,普通伦敦人的意义可能并不大,因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无几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还是喝李普顿茶,这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然而,约翰逊抽烟,经常光顾18世纪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伟大人物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反映,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他们会影响自己所接触的事物,或者受其影响,他们有这种天才;他们也受到自己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受到所接触的妇女的影响。而这些对另一个缺乏天才的人却毫无触动。他们充分利用并享受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他们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东西,并且用最纤细、最有力、最敏锐的眼光对此作出反映。
『①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年期间在位。』
『②卢西恩(Lucian,约120~200),希腊自由思想家。』
『③弗朗西斯·维龙(Francis Villon,1431~1463),法国诗人。』
『④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辞典编纂者及作家。』
然而,分析研究一个国家时,又不能忽视普通人。古希腊人并不都是索福克勒斯①,伊丽莎白的英国也并非遍地都是培根②和莎士比亚。谈到希腊时,仅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③和阿丝帕霞④,并不能得到对雅典人的正确印象。我们还应该经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儿子来作补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亲治家不力;还有阿里斯托芬⑤的戏剧所描写的人物,他们并不都是爱美的,不都是倾心于对真理的探索,而是经常喝醉酒,贪吃,爱吵架,贪污受贿,喜怒无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样。也许雅典人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正如伯里克利与阿丝帕霞能帮助我们理解雅典的伟大一样。他们这些人,作为个人无关宏旨,但作为一个集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过去时代的普通人也许现在很难描述出来,然而当代的普通人却不同,他们每天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谁是普通人?他是干什么的?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就是口头语言也不会造成欧洲人之间讲话那么大的困难。一个满洲人能够使云南人听懂自己在讲些什么,尽管有一些困难,这也实在是语言上的奇迹。这是经过缓慢的殖民化过程才获得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字的书写系统这个民族团结的有形象征。
『①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5~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免费TXT小说下载
『②培根(Bacon,1561~1626),英国作家及哲学家。』
『③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将军,演说家。』
『④阿丝帕霞(Aspasia,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名妓,曾为伯里克利的情妇。』
『⑤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8~前385),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①,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①涿县,现在河北中北部。』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②: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②英语有一格言云:有规则就有例外。』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嗳——”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
在诗歌中,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尤其在公元4、5、6世纪。当时,北方中国第一次被鞑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这时,伤感的爱情诗在南朝盛行。许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种题材别致的爱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间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对比一下这些感伤的诗歌与北方新鲜、质朴的诗歌是很有启发的。南方佚名的诗人在这种很流行的小曲中唱道:
〖打杀长鸣鸡,弹去鸟臼鸟。
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另一首小曲唱道:
〖途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依时,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一种称作“词”的有独特风格的抒情诗发展起来了。其内容不外是妇女的深闺幽怨,红烛泪干,中意的胭脂、眉笔、丝绸、帏帐、珠帘朱栏,无可挽回的春天,清瘦的恋人,羸弱的心上人儿等等。写这种伤感的诗歌的人应该被写那种简短、质朴、直接描写北方荒凉风景而不加雕饰的诗歌的人所征服,这实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