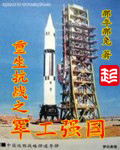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10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想到英国公与梁王、桂王早有反心,一直筹谋待机,当英国公出征,梁王与桂王前往送行,却是一去不返,直接在冀州起兵。
外患未除,又遇萧墙之祸,大隆朝的政局风云突变。
却无疑让贤妃喜出望外,趁着太宗亲征剿伐翼州叛党,她竟然买通了部份文臣,欲再提高祖曾有遗命的旧事,立六皇子为帝,又买通宫人,想在严后药膳里落毒,栽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在严后身上。
严后早起了防心,自然不会让贤妃得逞,非但没有饮下毒药,还捕获了贤妃收买的宫人,贤妃获罪,被赐三尺白绫,对外只称她与英国公、梁王等人勾结,才被处以极刑。
贤妃收买的文臣无一漏网,皆被处死。
至于焦月逆谋案,不过两月之后,就以梁王战败落下了帷幕,楚王作为先锋,亲手射杀了梁王、桂王,而英国公,却在仓促而逃时被自己的部卒杀死,斩落人头一枚,献于太宗面前,以求将功赎罪。
六皇子当年尚才十一,并没因贤妃之罪获死,太宗帝为防有心怀叵测之人借之生事,将其终身幽禁于禁苑。
六皇子未曾婚配,却有宫婢为其产下一子,后,太宗帝病重,崩逝之前,终于将六皇子处死,却赦其子嗣,并解除幽禁。
后,当今圣上登基,又将此子封为阳泉郡王。
要论来,这阳泉郡王算是圣上同辈,旖景得称一声表叔。
虽说建宁候府并非国戚,只是臣子,与宗亲联姻倒可不拘辈分,可毕竟是卫国公府姻亲,当年黄氏五娘被封阳泉王妃,一跃成了旖景之长辈,多少还是让双方觉得怪异尴尬。
当年,勋贵世家对圣上这一旨意皆觉讷罕,黄氏五娘自从婚后,更是深居简出,就连自家姐妹也罕与会面,同旖景姐妹更加生疏。
这其中的隐情,在重新来过的一世,已无从溯原。
旖景当然不知,上一世时,黄氏五娘正是中了算计,在中秋宴上,竟然与阳泉郡王私相会面,并被皇后遇了个正着,两人当时,神智不清,共赴云雨……黄氏五娘当然失去了成为皇子妃的资格,若非大长公主求情,险些被秘密处死,圣上册封她为阳泉王妃,委实是看在大长公主的颜面。
黄氏五娘一直钟情于三皇子,却不得不嫁给一个地位尴尬的郡王,终其一生尚且不知,究竟是谁算计了她,在宫宴之上,糊里糊涂地饮了情药,糊里糊涂就失了身。
当年,她虽注定与三皇子无缘,可未必就没有与金氏六娘一争四皇子妃的资格。
恶人一直在身边,不过没有现形而已。
但当年之“错”,委实让她至少保住了性命,尽管郁郁终生。
而这一世,正在盼望着来年,得嫁“良人”的黄氏五娘又哪里想得到,地狱之门已经在足下开启,她以为的幸福,终究是场,镜花水月。
此时候府闺阁里,黄五娘膝上搁着尚待绣成的嫁衣,看向轩窗之外——岁末就在转眼了,她迫不及待地开始盼望来年盛夏——与他结发。
一旁高案上,莲台乌砚下,静静压着一支花签,正是此年六月,行令时得。
昙花含苞,待时而绽。
只无论当时抑或眼前,无人料得,那本就只有瞬息的惊艳,注定不会绽放了。
☆、第一百三十八章 虞洲来访,对坐闲谈
这一日,十月二八,经过秋雨缠绵,阴沉数日的天气方才放晴,可风声更急,卷得红叶纷飞、芳菲凋凌,窗棂外晃动的阳光洒在面庞上,也没有丝毫暖意,旖景清晨从寿仁殿请安归来,一直就窝在临窗雕花热炕上,先是夺过了春暮手里的锦帕绣了几针,到底没有心绪,又拿着一卷词集有一眼没一眼地瞧,心下渐渐疑惑着尤其沉默的几个丫鬟——若是往年,她们定不会忘记今日,可这时何故没有半分表示?
春暮坐在炕沿上,似乎所有心思都集中于手里的针线,楞似没有回应主子的频频打量,夏柯似乎也一直忙碌着没事找事,先是将屋子里头的几个箱栊整理了一番,这会子又折腾起百宝槅上的玉玩瓷器,一件件地用白叠擦拭,也不管本就洁净无尘,秋霜与秋月更是压根就不见人影。
如姑姑今日被太后留在了跟前儿,不知忙碌着什么,也没空搭理旖景。
就连太后,今日似乎也比往日冷淡,旖景才陪着她说了三两句话,就被打发了归来。
从一清早,好心情就遇到了冷落,旖景本是想往余照苑“问候”的,才到门前儿,便见江薇被罗纹送了出来,才知道虞沨昨夜歇息得迟了些,那时还未起身,众人也不敢打扰……
倒是在路上遇见了三皇子,旖景却不爱搭理他,见礼寒喧几句后,就紧赶着回了玉芳坞。
偏偏这一日如此冷清,实在让旖景心中郁闷。
这可是她重生后的第一个生辰呢,虽说不在自家府里,但春暮几个应当记得的,可瞧这情形,她们是疏忽了?
假若仅仅如此也还罢了,偏偏今日,还来了个不速之客。
当听宫人来禀:“镇国将军公子虞二郎来了。”
旖景的心情便更加阴暗。
沉默了一个早上的春暮总算是说了一句话:“二郎怎么来了?”却与夏柯交换了一个眼神,有些莫名其妙地慌乱。
旖景越发孤疑起来。
这毕竟是在行宫,不能任性使气,虞洲好歹是个宗亲子弟,既然来此,想必是跟随着老王妃一同与太后问安——霞浦苑聚会之后,虞沨“疾愈”一事应当会在贵族间传扬,外人不过好奇议论一番,可老王妃与镇国将军必定关注,尽管两人是出自不同的用心。
总之,既然虞洲来了,她也不能闭门不见。
“春暮,请洲哥哥先去花厅稍坐,今日天气凉,可得准备滚滚的热茶。”旖景不得不弃了手中索然无味的书卷,先吩咐了春暮招呼虞洲,让夏柯替她整理了有些散乱地发鬓,披好朱纱罩面细绒里子的氅衣,磨蹭了一番,才往花厅行去。
虞洲已经等待得有些忐忑了,前次在国公府,他不过一时大意,言辞上对虞沨有所冒犯,就引得旖景冷颜相向,心里酸醋泛滥之余,又很是担忧,生怕旖景这时还怪罪着他,早酝酿了一肚子的花言巧语,才见旖景入内,赶忙起身相迎,又是作揖又是陪笑,却顾忌着丫鬟们在场,总算不好再提那些话,频频暗示着,想让旖景打发了春暮与夏柯出去。
旖景故作不察,懒懒地见了礼,隔案而坐,爱搭不理的模样,眉目间尽是清冷。
让虞洲怎么不急?再顾不得许多,瞧了一眼立在一旁的丫鬟,尴尬地陪笑:“五妹妹,前次是我口不择言,原本长兄之疾,隔了这许多年,让长辈们牵挂不说,次次还落得失望痛心,我只道这一次也会如此,害怕祖母希望越大,失望越重,才抱怨了几句,殊不知长兄本身也不愿,怎可怪错于他?是我小心眼,都是我的错,五妹妹就谅解了这一回吧。”
春暮与夏柯方才恍然大悟,心说难怪今日五娘待二郎这般,竟是为了世子打抱不平,二郎也真是,往常瞧着待人那般和善,不想对自家手足却不如外人,这可不是大家公子风范。
旖景瞥了虞洲一眼,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肺腑之言”,神情并未缓和。
“好在神佛庇佑,这一次长兄总算是疾愈,祖母才听说了这事,当即喜不自禁,昨日原本就打算来的,又听说了霞浦苑里的事儿,知道太后娘娘昨日召了董老夫人来行宫安慰,不便前来,才等到今日。”虞洲见旖景依然不肯罢休,心下越发焦急:“五妹妹,我当真知错了,早先当面与长兄陪了不是,他都不怪我了,你且原谅了我这一回吧。”
“哦?你真跟沨哥哥陪了不是?”旖景有些怀疑,转念又想,只怕虞洲听说世子疾愈,也是半信半疑,今日这一行,本是一探究竟,当确定了此事,又担心自己在世子面前搬弄是非,才干脆先道了错,免得世子心里忌恨他吧。
镇国将军一家,绝不会善罢甘休,上一世是利用她加害世子,不知这一次,又会使出什么手段。
想到这里,旖景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看来,她还是要继续与虞洲虚以委蛇,才好麻痹他们父子。
让他们以为,或者将来还能再利用她一回。
当见虞洲捶胸顿足的保证,旖景方才给了他一个笑脸:“我之所以提醒洲哥哥,也是为了你好,沨哥哥与你是堂兄弟,那些言辞若是被别人听了去,岂不诟病哥哥你不顾手足,心怀恶意?但我知道,洲哥哥原本不是那样的人。”
虞洲闻言大喜,伫在椅子里望着旖景笑得格外痴傻。
一旁的夏柯瞧这情形,捏紧了掌心才忍住笑意——这虞二郎,瞧着比五娘年长,委实是个傻子,五娘把他当孩子哄呢,他尚且不察。
“老王妃今日也来了行宫吧?”旖景心里厌烦,借着饮茶,掩去眼睛里的不耐。
“祖母与母亲正在寿仁殿呢。”虞洲顿了一顿,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加上一句:“长兄也在,我看他的气色,果然比之前好了许多。”立即就终结了这个话题,眼角眉梢都堆砌起奉承之意:“原本因着太后也是在行宫静养,祖母不想让小辈们随行,我好一番纠缠,才得了这个机会,五妹妹,今日可是你的生辰,可惜了是在行宫,不能热闹一场。”
旖景不由忧怨地扫了春暮与夏柯一眼——这一个生辰,大家都疏忽了,反而是虞洲还记得。
春暮与夏柯糊涂本就装得辛苦,这会子更加尴尬起来,再撑不住,春暮拍了拍额头,惊慌失措起来:“奴婢真是该死,因随五娘来了行宫,就把这么要紧的事儿疏忽了,委实该罚,五娘别怪夏柯,她原是才提上来的,疏忽了这事尚还情有可原。”
旖景还没说话呢,虞洲先埋怨上了两个丫鬟:“果然该罚,竟将五妹妹的生辰都疏忽了,难为她待几位姑娘跟亲姐妹似的,瞧瞧你们,还比不得冬雨伶俐,前儿个我瞧见她,她还提醒着我莫忘了五妹妹生辰,记得备礼呢。”
旖景听了这话,眉角微挑:“我不在家,洲哥哥还往绿卿苑去了?”
虞洲连忙解释:“之前候府七娘不是吵嚷着要品螃蟹么?加上七妹妹兴致也高,俩人纠缠不放,因五妹妹不在,我也没有去外头的兴致,干脆就在桂花楼叫了一桌席面,请了荇哥哥、二郎与几个表妹去王府聚了一场,冬雨是跟着三妹妹来的,像是三妹妹身边侍女崴了脚,找不到贴心人儿,见她闲着,才让她侍候着过来。”
旖景脸上依然带笑,心里也是一晒:自己这前脚才走,三姐就与冬雨热乎上了,只不知是谁主动,瞧着那几次冬雨见虞洲的模样,只怕心里已经开始活泛了,前世自己当真白长了一双眼睛,竟没有瞧出冬雨对虞洲的企图心,临死之前,还没有想通冬雨怎么会那般歹毒。
只不知自己“服毒自尽”之后,冬雨有没有如愿以偿,不过想来,以虞洲的手段,应当不会留下冬雨这个活口。
心里百转千回,却是不无惋惜的一叹:“我当真没有口福。”
虞洲连忙献宝,拿出那精心准备的生辰礼来,又说了连串的吉利话,诸如芳辰永驻云云。
旖景打开锦盒,瞧见竟是江月生辰时八娘所赠,梁绩亲笔的《残年录》,当真惊讶了:“这不是八妹妹送给阿月的生辰礼么?”
“候府七娘称五妹妹爱不释手,她倒不甚在意,我便央着她转手给我,五妹妹放心,我可没有强人所难,七娘可是狠赚了一笔,银子就不说了,还要了我收着的一套玛瑙石嵌紫金骑鞍。”见旖景似乎好奇缺席的那场螃蟹宴,虞洲当即将那日的情形一一说来,别的也还罢了,就是二郎苏荏行令时运气不佳,光在黄七娘手下就输了个七、八回,若不是四娘仗义,替他挡了几巡,非饮得酊酩酊大醉不可。
旖景啧啧称奇:“二哥哥性情甚是沉闷,往日里见了咱们,也就是礼节寒喧,从不与姐妹们玩闹的,那日却是例外。”
“所以,他才会时运不佳。”虞洲笑道。
又问起霞浦苑的事情:“这两日连国子监都是议论纷纷,偏偏甄三郎又告了假,想是也觉着没脸抛头露面,我倒是听金七郎说了个囫囵,只闻当时甚是惊险,五妹妹没受着惊吓吧……那甄四娘也忒歹毒了些,小娘子们就算小有过节,哪里就至于谋人性命,狗急跳墙来还攀咬了五妹妹一场,好在五妹妹伶俐,识破了她的奸计,没让她得逞。”
“众人都有哪些议论?”对于这事,旖景还有几分关注。
“都说甄四娘阴毒,连着甄夫人也遭了指责,说她教女无方,甄府五娘正当议亲,原本外祖父还想着替表哥求去甄府的,这回一听说甄四的心肠,也打消了主意,她这般举止,害得下头几个堂妹的婚事只怕都会连累,当真是个祸害,五妹妹且等着瞧,今后有甄四的罪受。”
甄府嫡系也有四房,因老夫人健在,尽都没有分家,甄茉的恶行必然会连累下头待嫁的堂妹,就算有甄夫人明里护着,怕是也会受家人的冷眼。
可相比上一世董音的惨死,她如今所受,委实算不得什么重罚。
其实,以甄家的威势,就算甄茉声名尽毁,也不至独守空闺——名门望族是不能肖想了,可一般商贾之家,或者是招婿,选择仍在,不过以甄茉的“傲骨”,必不会容忍这般委屈,她起初可是连太子妾室都不肖为的,更何况嫁入商贾之家,或者招个身份卑微的上门夫婿。
霞浦苑之事一经传扬,甄茉在贵族这个群体再也无法立足。
但这仅仅是旖景以及多数人的以为。
实际上甄茉本人,却仍然没有放弃,她且还筹谋着,要绝地反击。
总之一番闲谈趣话,虞洲眼瞧着旖景当真展颜,心头的重负才堪堪放下,正想试探一番旖景与虞沨之间的“关系”,话还没出口,旖景便站起了身——
“既然老王妃与二婶子都来了行宫,我也得去问安才是礼数,咱们这就往仁寿殿吧。”
☆、第一百三十九章 口蜜腹剑,坦率阿薇
一路进了寿仁殿,却并没有瞧见如姑姑,宫女们见了旖景与虞洲,也不多问,也不入内禀报,笑矝矝地在前领路,当入偏殿,穿过雕梁上垂下的瑰紫牡丹锦遮,绕开一列八折百花争春的绣屏,一左一右立在门前的两个穿着青花色夹棉比甲的宫人,无声地打起了帘子。
便有暖意夹杂着檀香迎面而来,驱散了周身寒凉,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地下一座画屏,是仙人游山,隔断了隐约的笑谈声。
引路的宫女立在屏前,并没有一句言辞。
旖景自然而然地转过了画屏,一眼瞧见老王妃正拉着江薇的手,满面的笑意,小谢氏立在一旁,也正打量着略显局促的少女,那目光怎么瞧都有些挑剔和戒备。
虞沨坐在下首,安安静静地捧着茶碗,瞧见旖景进来,缓缓地一笑,目光转而又看向跟在身后的虞洲,略略颔首。
“我竟还不知清谷先生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可怜也是自幼没了母亲……”老王妃叹了一叹,又拍了拍江薇的手背:“正如沨儿所言,先生多数时候要在宫里当值,你孤身一人在家可不稳妥,待太后娘娘大好了,就到王府里住去,可别觉得难为情,若不是清谷先生,沨儿的病哪里会痊愈。”
虞洲一听这话,当即品出几分味道来,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江薇,瞧出这女子虽有几分颜色,但度其举止,并无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就很是兴灾乐祸起来,忙赶着上前凑趣:“祖母,这位姐姐便是清谷先生的女儿?如此说来,也算是咱们家的恩人了。”
太后扫了小谢氏与虞洲一眼,便冲旖景招了招手,拉着她就坐在罗汗榻上:“怎么又来了,今日虽说晴朗,可风却比昨儿个还要大些,仔细受了凉。”
“听说老王妃来了行宫,怎么也要来见礼的。”旖景笑道,上前冲老王妃一福。
紧跟着就被老王妃一把搂在了怀里,心肝肉地喊着,这情形竟像是一别数载的亲骨肉般,旖景十分熟悉老王妃,知道她就是这样一副性情,倒不是真有多偏疼她,不过眼下这番,可见老王妃当真是喜难自禁。
小谢氏将旖景与江薇一比,越发觉得两人气度举止是天差地别,纵使她一贯不看好这么一个强势的“准儿媳”,这会子也觉得趾高气扬起来。
原来她刚才瞧见老王妃待江薇的态度,应当是有意世子娶她为妃,如此也好,一个医官的女儿,打小又是在山野村郊长大,一身小家子气,与苏氏五娘这样的名门金闺站在一起,更上不得台面,唯一让小谢氏不甘地是,听说这女子医术了得,兼着又是她父亲治好了虞沨,以后要算计虞沨,再在饮食药膳上动手脚,只怕有些不易。
起初小谢氏一听说虞沨疾愈,相当地惊疑不定,一路之上,还安慰着自己不过是谣言——这么多太医都束手无措,解不得毒,一个游医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不想一到汤泉宫,亲耳听闻太后的话,心底顿时就漏了个洞,忽忽地直灌冷风——盼来盼去,竟盼得这短命鬼痊愈了,这么多年的打算岂不是尽数落空,叫人如何服气?
小谢氏的心里,恨不得把这半路杀出的清谷父女碎尸万断,可怜当着太后与老王妃面前,只好咬牙苦忍,憋得满脸僵硬的笑容,只觉得牙齿根儿都酸涩起来。
旖景听说江薇要住在楚王府,心里往下沉了一沉,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浮动上来,原本不佳的心绪,就更郁结了几分,又被老王妃这么摁在怀里,只觉得气息不畅,强打着精神说了好些趣话,越发逗得老王妃开怀,才放开了她,旖景将将一站稳,就迎上了江薇略带鄙夷的眼神,越发无奈,匆匆避开视线,却见虞沨正安安静静地看着她,澄明的眸光直淌心底,心中的郁闷便像被山泉水冲涤一尽,不自觉间,唇角微扬,愉悦的情绪就像复舒的水草一般,在心底缓缓招展。
小谢氏维持喜悦十分辛苦,太后对她的皮笑肉不笑也是万般不耐,兼着又瞧出她那位二嫂有些欲言又止的模样,便让旖景几个小辈自去一处闲坐,又让宫人领着小谢氏观赏行宫各处景致,只留了老王妃在殿内,一对老妯娌,说会子正话。
见没了旁人,老王妃眼角就红了一圈儿,无非是感念着神佛庇佑,总算是寻到了神医,解了大孙子体内的剧毒,将各路菩萨都感念了一番,才提着锦帕拭了拭眼角,紧跟着的一番“正题”,险些就让太后岔了气——
“眼瞧着沨儿没有性命之忧,我也算放了大半个心,只他受了这许多年苦楚,因为身子骨羸弱,婚事也耽搁了些时候,如今大好了,我琢磨着再没什么阻碍,太后,您瞧着,镇国公府四娘可还合适?”
太后简直哭笑不得,心道难怪回回与上元说起,她都称二嫂糊涂,果然,眼瞧着沨儿才好,她这个当祖母的,就迫不及待地要在孙子身边安排个埋伏,镇国公那家子人,早就被虞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