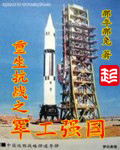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后也是抚掌连连,待虞沨与旖景归座,一手拉着一人:“此曲我并未听闻,可你们两人却甚是熟悉,不知为何人所作?”
虞沨便笑:“是魏师兄所谱,我度量着五妹妹是师兄的学生,必然熟知,果然如此。”
太后方才颔首:“我还道你们早有准备,先排演过呢。”
三皇子心下不甘,挑眉侧目,打量着虞沨与旖景之间的神情,见他们虽无太多交流,只偶然一顾之间,尽管视线不过略触,但不难看出情愫微妙,三皇子便越发急躁起来,饮落腹中的醇酒,竟像是被点燃了般,只觉得从脏腑到嗓眼都火烧火燎的,偏偏这时太后提议,散坐着拼酒,不如行个令好,如姑姑自请做了令官儿,行的也是通俗易懂的骰令,由令官摇骰,全席轮留猜点数,不中者自饮,中则令官饮巨杯。
因是两枚骰子,极难度中,令官自然占了便宜,而三皇子还要肩挑旖景之酒,饮得最多,再兼着情绪不佳,任是他海量,几巡之后,也是支撑不住,渐渐舌大目眩,东歪西倒起来。
太后到底上了年纪,坐到辰末巳初,也觉得困乏起来,见三皇子正是难支,便先起身作辞,嘱咐着宫人侍婢们定要陪着旖景尽兴,但不能饮醉,由世子监督,把控大局,便让内侍进来,扶着三皇子先行离开。
太后一走,宫人们彻底没了约束,又再变了令,依然还是掷骰,却是点将令,众人轮留摇点,得四为帅,直到产生甲乙二帅,两帅猜拳,胜者点一人为将,败者点一人应战,两将又再猜拳,败者饮酒,直至一方之将败完,无人可选,由帅者亲自应战,败则饮大杯,又置一巨杯,由败将分饮。
因虞沨不能饮酒,旖景也称再饮不得,两人便成了旁观,只见席上诸美情绪高涨,挽袖直身,呼呼喝喝,倒也不亦乐乎。
又过了半个时辰,虞沨方才披了斗篷,并未交待,先出了合欢堂。
不过多久,便有一宫人入内,笑请了旖景出去。
如姑姑见春暮等人正在兴头,便没有打扰,只自己相跟着出去,嘱咐几个宫人打好风灯随行。
“这是要去哪儿?”旖景才一出合欢堂,便见虞沨立在一株红叶下面,灯影恍惚在他温润如玉的面庞,照得笑意灿烂,于是紧步接近,虞沨并无多言,只转身向曲径通幽处行去,两人并肩走了一阵,旖景方才忍不住问道。
身前,几个宫人手持风灯,并不曾转身。
身后,如姑姑与一名宫人落后十步开外,并没有紧随。
虞沨回眸一望,忽然伸手,握紧了少女的指掌:“天黑路暗,五妹妹仔细脚下的路。”沿着并不陡峭的石阶往下,当感觉她并没有因为他突如其来的举止感到惊诧,反而自然为然地回应着,两个掌心贴近,十指紧密相缠,他轻轻地笑了出声:“我还不曾送礼,五妹妹难道就轻易放过了?”
“娘娘不是说过,今晚这餐晚宴,多劳沨哥哥筹划,我已经很是惊喜了。”
“你早猜到了吧?”虞沨轻笑:“春暮她们几个,今日委实辛苦。”
旖景汗颜:“是该早猜到的,可我还是后知后觉,直到膳后,听说太后请我赏月……”
“五妹妹,我会记得今日。”他忽然一句。
旖景心中一陷,软软地一番悸动,忍不住去看他的目光,果然,见他正侧着脸,眸心是红叶柯枝上,宫灯晃动的光影。
“愿年年如是。”
年年如是,这一日与你携手,陪你共渡生辰。
旖景微仰着面颊,一直看进他的眸底——重来一世,当再次遇见,他依然温柔如初,可是她委实不知自己有什么好,值得他如此。
“沨哥哥,你为何……”忍不住脱口而出,才发现自己失态,旖景连忙避目,轻咬唇角。
“愿五妹妹年年生辰皆如今日,这般欣喜无忧。”虞沨却说,有一些因由,在没确定她的心意之前,告诉也是负累,他会耐心地等到那一日。
穿过花苑,出了南门,直到灿景阁。
依然登上,顶头一层。
如姑姑早吩咐了宫人在阁下等候,自己跟上去,却只候在阁外檐下,背身而立。
虞沨拉着旖景,直到轩窗之下。
这一室宫灯,素绢为底,上头是青碧的竹,或者婆娑,或者挺拔,悬于梁上,共一十三盏,姿态无一重复。
旖景看在眼里,心头情绪更是复杂:“是沨哥哥亲手所画?”
“那日五妹妹问我为何不画竹,实在是因为担忧画笔有限,不过当知五妹妹爱竹,勉强画成,五妹妹可别嫌弃我画笔粗陋。”依然云淡风清,虞沨温文一笑。
“那日我便在想,倘若沙汀客不能画竹,当今大隆,或者再无人敢画了。”旖景踱着步子,逐盏观望,满带惋惜:“可惜这些不能带回去。”
“悬挂于此,便也是留作纪念,五妹妹当记得此年生辰,是在汤泉宫渡过,抑或数载之后,再有旧地重游的机会,倘若那时还有这些灯盏,五妹妹也会忆起今日之庆。”虞沨站在窗畔,看着她驻足仰望,灯光清照下,面颊有若玉兰,不觉将手掌负于身后,方才忍耐住蠢蠢欲动:“五妹妹若是想要我画的竹,将来只管开口,又有何难。”
“那便先道声谢,沨哥哥可别食言。”
“五妹妹前次的生辰礼价值连城,我就算还以千幅万幅,只怕也是难抵。”
那一幅画,当真不算什么,比起,你的给予。
但这一句话,到底难以启齿。
“沨哥哥今日何故弹那一首《白头吟》?”本是仓促之间转移的话题,却也是从那时就怀有的疑惑,不过旖景这时问来,心跳渐急,却品不出究竟是忐忑,抑或是期待。
虞沨眸光一沉,转身看向森森黯夜。
“师兄说过,古往今来,万千女子当中,他至佩之人,便是文君,我深以为然,为她‘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纯粹,为她‘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绝决’的果断,为她的隐忍与宽容,我在想长卿当真有幸,有多少人,一旦错过,便再不能挽回,可是文君却给了他机会。”
上天同样给了我们机会,旖景,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把握呢?
“所以,一时兴起,便奏了这曲,不知五妹妹如何看待这样的两人?”尽管一直在压抑,可他在这样的情境,似乎还是忍耐不住,想要给她一个暗示。
“得遇文君,是长卿之幸。”她从灯影下缓步出来,慢慢地回到他的身边,循着他背着光影的视线,一齐看向黯沉的夜幕,依然无月,只有模糊的几点星光:“我想,当他们有一日,不得不相别于生死,心怀遗憾,因为曾经的背叛,始终亏欠之人,当是长卿,不知他会不会后悔,那一念的动摇,让本应无瑕的美满,留下了一条不能忽视的裂缝。”若我是他,应当悔之不及,尽管也努力弥补过,但伤害,始终已经造成,相比文君,长卿终究是亏欠的一人。
所以旖景这时想,她要比长卿幸运,回到伤害造成之前,或许才能,彻底弥补遗憾吧。
“如果白头吟是对长卿的指责,那么文君的决别书,就是在委婉地表达她的心意,这也是我,深佩文君的一点,当所以为的良人变心,她没有纠缠,却也没有就此放弃,她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感情,她愿意争取,以维持尊严的方式,用最后的决绝挽留,最终,长卿回心转意,她宽容地接受,照样不离不弃。她不接受同情,不接受勉强,更没有以相互折磨的方式惩罚对方,如此聪明而果断的方式,她找回了幸福。”视线收回,虞沨看向旖景的眼底:“她只接受真心,而不接受勉强,长卿的归来是因为回心转意,所以文君才能放开怀抱,他们的故事虽有睱庇,却无遗憾。”这也是我唯一能接受的,如果你要回来,请不要仅仅只是因为赎罪。
他看着她扶在窗棂的指节,渐渐握牢,清秀的一翦眉梢,似乎被这风声扰得轻颤,她没有回应他的注视,似乎正在沉思。
旖景,放下怨恨与愧疚,你能不能正视自己的心意?
轻轻将手扶在窗棂,与她近在咫尺,虞沨微微一笑,沉默着与之并肩。
一声并不锐利的闷音,在窗外无边的夜色里遥遥响起,黯黑的云层下,突然绽放了一朵灿烂,殷红的火星四散,却不待殒灭,随着声声闷响,不断有金花银焰依次明亮。
大片阴黯的夜空,就这么明媚热闹起来。
是烟火!
短暂地愣怔之后,旖景有些迷茫地眼底,瞬息布满了灿烂。
她忽然侧面,看向他含笑的眼神,满满地不敢置信。
有一抹记忆忽然清晰,远庆十年元宵夜,他说的那句话——明年此时,愿能与你同游流光河,看烟火灿烂。
“傻丫头,别告诉我你从没见过烟火。”他伸手揉了揉了她的发顶,故作不解她的震惊。
“那怎么一样,年年元宵皆有烟火,可今日,这是为了我一人所放。”她明亮的清眸里,带满重重的孩子气,借此掩饰着复杂的心绪。
“别用这么感激的眼神看我,其实这是太后娘娘的安排,我不过是执行者而已。”他说了谎,其实这场烟火是他的提议,太后只是批准了而已。
似乎已经等不及,想与她看这场短暂的灿烂,她应当也记得,他不及兑现的承诺。原本以为,她不会在乎,可她这时的欣喜,如此明亮地闪耀在眼底,是由心而发。
不遗憾了,因为旖景,我给的,总算是你想要的。
“这些都不是我给你的生辰礼。”却不舍地收回了手掌,只将目光依然沉沦在她的眼睛里:“五妹妹,我许你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允诺,无论何时,无论何事,只要你提出,我都会满足你。”
这是上一世,我不敢给予的礼物,因为我害怕,你的愿望只是想让我放你离开。
但这一世,我似乎有了信心把这礼物给你。
“五妹妹,请善加利用。”虞沨微微伏身,微妙的距离,把话吹进她的耳朵里。
窗外火树银花,梁间烛影摇红,此处辉煌绣阁,这时夜阑人静,虽未执手,却有同心——再是灿烂的烟火,总有归于沉寂之时,但这一夜的烟花,会在我们的记忆里,一直绽放到天荒地老,青山无棱。
——第一卷终——
☆、第一百四十四章 姥姥上门,所为姻缘
锦阳京的二月,尽管早已立春,但距离春暖花开尚还有些时候,更兼着从一月下旬纷扬了七、八日的那一场雪,更是让人感觉不到半分暖意,直到二月二,日照终于从湿厚的云层探身,连续数日的晴朗,才让天地之间的苍茫银装逐渐消融,露出青瓦乌柯,黑山白石的颜色来。
雪水渗入青石,终日漉漉,市坊间弥漫着的冷意,比下雪时更胜几分。
卫国公府角门外,两个身着夹袄的小厮儿,正踩着春凳敲打着屋檐上挂着的冰楞,嘴里不断地呵着白气,抱怨着北风还是这么阴冷。
一辆驴车辗着湿泞轧轧地停在门前儿,两个小厮儿才从春凳上下地,打量着那辆青漆剥落很是寒酸的车厢,都有些愕然。
但见半新不旧的厚布帘子一掀,车上下来一位裹着大红色斗篷的妇人,脸上刷着厚厚一层脂粉,额头与下颔白得惊人,偏偏面颊红得像鸡血一般,尽管生着一张银盘大脸,也让小厮儿半咪着眼睛打量了半天,才看清眉目。
一个上前,笑着躬腰打揖:“大冷的天儿,姥姥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国公府二夫人利氏之母。
利姥姥下了车,瞄了两个小厮一眼,只轻轻恩了一声,甩手扔给那车夫几枚铜钱:“本是讲好的,往返共二十文,来这一趟按理是给十文,可你磨磨蹭蹭,短短一截子路,走了竟小半个时辰,耽搁了我的功夫,要是遇着不讲理的人,不让你赔钱都不错,我发个善心,给你五文钱,全当是可怜你没白跑一趟。”
那车夫一听,哪里服气,“通”地一声从木辕上跳了下地,却是个腰粗膀圆的后生,瞪圆了眼睛就大声反驳:“这化雪的天儿,天冷地滑,你又是从外城过来,莫说这等天气,就算平日地上干着,也得要个两刻左右,再说若不是讲好了往返,不让我拉了人来空着回去,谁稀罕走这一趟,姥姥尽可打听一下行情,从外城来这儿,单趟谁不给个十五、六文,瞧着你穿衣也是大户人家,又是一把年纪,怎么竟讹我这几个辛苦钱,五文钱眼下能干什么,买碗阳春面还得花销个七、八文呢。”
利姥姥一见那车夫五大三粗地伫在面前,不由后退了一步,气焰却并没有削弱几分,叉着腰就喝斥了回去:“也不看看这是哪里?祟正坊的卫国公府!竟然敢耍起无赖不成?我可告诉你,我与大长公主可是姻亲,你敢使粗,也不掂量周身骨头有几斤几两,一个贱民,还敢得罪皇亲国戚?”
车夫一听这话,顿时气得七昏八素,又向前逼近了一步:“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皇亲国戚,厚着面皮贪赖平民百姓的几文铜钱,呸!这大话也说得出口,今日若是不给足我钱,就算闹到天子跟前我也不认这个亏。”
利姥姥冷笑一声,指着一旁目瞪口呆的小厮:“你们还不告诉这贱民,我究竟是谁?”
两名小厮儿叠声叫苦,一个连忙上前拉着那车夫好一场劝,一个赶紧上前将利姥姥往门里头请,又有门房听见了动静,出来一瞧,问清事非,只好自己先掏了十余文铜钱出来,好声好气地陪罪,打发了车夫离开,这才进去,却见利姥姥还在门里跳着脚骂,直说那车夫瞎了眼,欺负她是个寡妇,没人撑腰,才敢撒野。
这门房正是春暮的三叔,当差当老了的,自然晓得利姥姥的性情,上前好一场打躬作揖,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才让利姥姥消了火,喘着粗气盯着春暮三叔:“大冷的天,还让我在这儿站着受冻,赶紧备顶软轿来,将姥姥我抬进去!”
于是一番忙乱,门房终于得了清静。
小厮儿见婆子们抬着软轿走远,才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乖乖,摊上这么一个破落户儿,连咱们这些下人都不得清静。”
春暮三叔眼睛一瞪:“休要胡说,姥姥再怎么也是咱们府上的亲戚,可不敢冒犯。”
那小厮吐了吐舌头,这才不敢再议论。
又说婆子们一路抬了利姥姥到沧浪苑门前儿,非但没落着一文钱的赏,还被莫名其妙地排揎了几句,说她们有心怠慢,颠着了腰,婆子们不敢还嘴,只得躬身受了,利姥姥发够了威风,才扭着“伤”了的一把老腰进了院门儿,一路之上,每瞧见个丫鬟都要叫住斥责两句,短短一截子路,她倒耽搁了足有一刻,才被大丫鬟迎着进了屋子。
利氏头上带着昭君套,身上披着件敞襟桃红色的夹棉罩衣,一见帘子打起,才从炕上下来,上前拉了利姥姥上炕,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阿娘怎么来了?”
“怎么瞧你无精打彩的模样?”利姥姥疑惑地看了利氏一瞬,忽而喜上眉俏:“难道是又有了身子?”
利氏没好气地往引枕上一靠:“二爷除了眉氏那个贱人,就是睡在书房里头,就算回了屋子,也碰都懒得碰我一下,我若是有了身子,那还了得?是前些时候下雪,不在意受了凉,请大夫瞧了几回,这才好了些,到底觉得身上懒。”
“你这丫头也太没用了些,就由得姑爷不成?那个眉氏,早该把她提脚卖了出去。”利姥姥恨铁不成钢,拍着炕几咬牙切齿。
利氏翻了翻白眼:“阿娘你说得倒容易,且以为眉氏是个奴婢,卖身契在我手上呢?她可是二爷的青梅竹马,授业恩师的千金,虽说不是三媒六聘,却也是正正经经抬进国公府的贵妾,还提脚卖出去,往常就算我说她句重话,也是戳了二爷的心窝子一般,恨不得一封休书给我,判我犯了妒嫉。”
“再贵也是个妾,还能越得过你这个正头夫人?我从前都是怎么教导的你?”利姥姥气不打一处来,就要滑下炕去:“这事儿我可得与亲家理论理论,哪有放纵着儿子宠妾灭妻的理儿,我们虽是平民百姓,可当年也是对老国公有救命之恩,亲家可不能这般恩将仇报。”
利氏慌忙拉住了母亲:“娘你就别添乱了,自打眉氏进了门儿,就想去婆母身边讨好,多亏得婆母还记挂着我这个正经儿媳,才没有理会她,否则,眉氏上头有婆母为靠,底下有二爷撑腰,当真只能由得她骑在我头上撒野,你再去闹,真想看着我被休不成?”
利姥姥被利氏猛地一拉,当真险些扭了腰,扶着“哎哟”一声,没好气地打掉了女儿的手,坐着喘了阵粗气儿,又疑惑起来:“我一些时候没来,你怎么就会为亲家母考虑了?往常不是总数落她偏心的么?”
“也是四娘跟我说的这些个道理,想想也是,要说婆母待我当真不错了。”利氏闷了一闷,到底有些不甘:“就是不让我插手内宅家务这遭,怎么想怎么胀气。”
“四娘打小就是跟着亲家母身边长大,哪里会为你着想。”利姥姥冷哼一声:“哪点不错了?若不是看着咱们寡母孤女,又不是名门望族,哪里就会允许二爷明目张胆地纳个贵妾?瞧瞧三爷,娶的是望族嫡女,这么些年了,别说贵妾,就连是个通房都没有,要说三爷也不过一子一女,子嗣算不得丰盛,她怎么不再纳个贵妾入门给三爷?”
这话算是说中了利氏的心病,捧着心窝子咳了几声,正要数落几句许氏的不是,又忽然想到四娘往日的劝慰,让她别论闲事,收敛着性情,才能让苏轲回心转意,总算是没有再犯“多言”,只问母亲:“大冷的天儿,阿娘究竟有什么事儿,才从外城来了?”
利姥姥才想起正事,刚要细说,先竟觉得口干舌躁起来,捧着杯子喝了半碗茶,才问:“前些时候你说二娘那门亲事,可有些成算了?”
“可别再提这事,一提我又是胀气。”利氏重重一叹:“甄家是什么门第?那可是太子妃的娘家,甄家三郎才华样貌都是出众的,将来也算前途无量,可就因为甄家女儿与咱们府将来的世子夫人起了争执,好好一门亲事就这么作罢了,我不服,才说了两句,二爷他当头就是一场怒骂下来,只说二娘的婚事有婆母作主,让我不要过问,那可是我十月怀胎才生出来的亲闺女儿,我竟然连问都不能再问一句,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儿。”
“怎么世子的婚事也定了?”利姥姥忙问。
“可不是嘛,眼看六月大娘就要出阁,荇儿的亲事就定在了五月,是董参议家的闺女儿,往日看着也稳重知礼,不知怎么就惹恼了甄家女儿,都是她不懂事儿,白白连累了二娘。”利氏尚且不甘,压根就没想过二娘和甄家的婚事从开始就是她剃头担子一头热,眼下别说大长公主与苏轲,就连二娘自个儿,也再不存嫁给甄三郎的念头。
利姥姥倒没觉得惋惜,反而极为兴奋:“只怕这就是天注定,二娘与那个什么甄家没有缘份,还得靠我这个外祖母替她打算。”
利氏一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