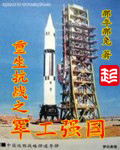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1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世子这神情,似乎不像是沉浸于音律?”三皇子率先一笑。
虞沨似乎疑惑:“我以为,三殿下才是琴艺评判。”
“我原本以为五妹妹会选择诗词一艺。”三皇子微微仰身,与虞沨又接近了几分,看在别人眼里,还道是两人正在评议琴音。
此时场中抚琴的女子,顿时心跳如雷,双靥生热,以为自己的技艺,得到了两个才子的赏识。
“毕竟五妹妹最擅长诗词,今日刚好又是世子为判。”三皇子意味深长:“不想她却选择了对弈。”
“相信以五妹妹的棋艺,定能夺魁。”才应付了一句,虞沨便瞧见如姑姑往这边行来,心念又是一动,不再理会三皇子,而是起身相迎。
“世子,已经有小娘子们完成了诗词,娘娘请您查阅。”如姑姑微笑:“我看着国公府六娘所作,极为不错,年纪小小的闺阁,竟然能将春残花落写得那般大气飞扬,半分不显哀婉颓伤,委实让人耳目一新,不过略微逊了几分细致入微,娘娘很觉惋惜,还要待世子评点。”
虞沨听后,不由暗自一叹——看来这两姐妹,心肠都是一般,能将春残花落写得与众不同,只不知六娘这厥,比当年旖景那首如何。
便与如姑姑一同前往南侧作为赛场的花榭,短短一截子路,已经拿定了主意:“稍后还请姑姑与沨一些时间。”
如姑姑知道虞沨这是有事相求了,并没有犹豫,带笑颔首。
依据“诗词”比艺的规则,众人各自据案,若愿交流,相互鉴赏后修正润色倒也不拘,不过有个“自愿”为限,故而有些只重在参与者,倒可与三两知己商量互评,满意时方才呈卷,跟着退场,等待结果。
因着到底是些闺阁的笔墨,以往评出前三,只公布姓名,并不公布诗作,更不会让郎君们鉴赏,但有那些沽名钓誉者自己显摆出去的当然不论。
或者有人出于好奇也好,不服也罢,也可求了太后一观获胜者的笔墨,但允是不允,就得看求者何人,与太后的心情了。
虞沨才一入花榭,便见其中尚有十余名女子或者品评闲谈,或者独自沉吟,或者奋笔而书,东侧有画展隔开,又见如姑姑直往那头行去,便猜到是太后正在阅卷。
四艺之中,太后最喜诗词,故而年年最为重视的就是诗词比艺。
当见虞沨绕屏而来,太后便先喊了免礼,又说赐坐,先说了一句:“我且以为景丫头今日会比诗词呢,她可倒好,跑去对弈了,教我失望了一场。”又在案上一堆长卷里找了一幅,递给虞沨:“你先瞧瞧,这是风儿写的。”
虞沨接过一看,但见笔锋刚健有力,先赞了一句好字,细细看来,又微微一笑:“果然是大气磅礴,不过到底失了落花的柔美,显得浮夸了些,六妹妹毕竟年纪还小,关健是着笔能有这番气势,实在不错。”
太后便笑:“你这评价公道。”
虞沨又看了余下那些,大多数是伤春悼花,叹息悲咽,甚是千篇一律。
唯有一句“见千红尽谢,虽惜,只比飞絮,尚有隔年期。”似乎别有一副心肠,在千篇一律中脱颖而出,又比六娘所作更贴切残春落红的意境。
“眼下看来,这一首最佳。”虞沨看了看落款,却是秦氏七娘:“却也有些勉强,毕竟来年花开,并非旧时那朵,正如柳絮无根,飘逝后再不归来,但年年有新柳,也不是没有来年期盼。”
太后又再颔首,对如姑姑说道:“我就说了吧,还是沨儿的眼光独到,刚才我看这首,只觉得别出心裁,就没留意到落花与柳絮原本无差。”
说话间,不断有宫人将余作呈上,虞沨一一阅来,依然觉得秦氏七娘所作最佳,直到最后一幅——
眉心微微蹙紧,一看落款,是黄氏七娘。
怎么回事?如果记忆无差,她与旖景非但是表亲,更是十分亲厚的闺中密友。
太后见虞沨的神情,大是好奇,连忙要看此卷,虞沨只得摁捺疑惑,呈了上去。
“好!‘送春何必凝噎语,缤纷出青墙,四海任飘零’这一句当真是彻底扭转了那些个哀切,将落花写得别样洒脱。”太后大赞:“哀家认为此作应为魁首,沨儿觉得如何?”
虞沨心下苦笑——原本以为今时今日,再见不到这一首词——真没想到,竟然注定是要二度夺魁,不过!
作者却换了一人。
黄氏七娘,究竟为何会写出这么一首词?
“娘娘明鉴。”虞沨略微思忖,又再说道:“此作当真为佳,只是为了使人心服,莫如将前三公之于众,供小娘子们品评。”
☆、第一百五十九章 嫌隙难消,心生倦意
因着虞沨突如其来的建议,太后稍微有些犹豫,虞沨复又说道:“虽是闺阁笔墨,不宜外传,可我寻思着,黄氏七娘今年可是连续三年夺魁,未免有人会暗中质疑,莫如将前三作品公开,只消让小娘子们齐集花榭便可。”
太后最终还是赞成了这个提议。
待得琴、棋、画三艺的比试尽有了结果,小娘子们都被齐集花榭之中,这与往年不同的情形,让许多人都心生疑惑。
身为“评判”,虞沨成了在场唯一的郎君,名符其实地引人注目。
才一听说要当众宣布“诗词”的前三,不少贵女都兴奋起来,有一部份,全是因为世子清越如同击玉的嗓音,似乎诸人这时才醒悟,还是第一次听闻这个少年成名,风度翩翩的贵胄说话,旖景微微四顾,便见不少女子粉面含春,这敞敞的一间花榭里,并无春阳照入,可那些熠熠生辉的眸光,却比花叶间的春阳更是明媚几分。
果然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旖景闷闷地叹了声气,一时不觉自己成了兴致最低落的一人。
再看六娘,半是期待半是紧张,一张小脸涨得通红,两个拳头捏得坚硬。
还有江月,显然也是十分着紧,全副心神都集中在虞沨手里的长卷上,但因先宣布的仅仅只是第三,她尚且还不期待。
并没有直接宣布获得名次者,那清越的嗓音,竟然潺潺吟诵卷上诗词。
旖景一见江月脸色瞬间苍白,颇为疑惑,笑着耳语:“阿月也太紧张了些吧,你可并非只是想得个第三。”
黄江月十分勉强地一笑,似乎失了力,整个身子瘫软在了玫瑰椅里,看着旖景,欲言又止,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出口。
虞沨留意到江月的神情,心下已然笃定——当是候府的七娘舞弊了。
看这情形,旖景尚且蒙在鼓里,候府七娘方才如此紧张,害怕旖景当众质疑。
想来,她是忆起前事,才写下那一首词缅怀,却不知何时被候府七娘铭记于心。
她始终是记得的,他曾经告诉的话,不知当时她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忆这些旧事?
高高在上的“评判”,忽然神思游离,竟然有些心旌神摇,将六娘那一首大气磅礴的词,诵出另一种温柔恍惚的意境。
六娘早已经喜难自禁,一惯沉默寡言的她,竟然一把掐住了旖景的手臂。
接下来就是荣获第二名的秦七娘,她显然不如六娘这么兴奋,似乎还有些失望,胜负心便张显了出来。
到了魁首之作,随着虞沨手上纸幅缓缓展开,那些心怀期望的比试者尽都屏息凝神,唯有黄江月,这时心情尤其复杂——她盼望这次的“三连胜”已经很久,但今日怎么也没想到赏春宴上会出这么一个春残花殇的命题,她猜到多数人都会抒发“悼花”哀婉的情绪,很想写出与众不同的意境,偏偏当日去看望旖景,恰逢她有事外出,留在书房里随手翻阅,巧见一本书里“藏”了这么一首小词,当时读来就觉得甚佳,一时铭记。今日无论她怎么绞尽脑汁,竟都不如这一首好。
六娘作完之后,毫不设防地让她“品评”,江月更觉自己脑中词境尚且不如六娘。
犹豫踌躇之下,到底还是胜出的渴望占据了主动,她最终照抄了旖景的词作——尚自庆幸,还好旖景今日选了对弈。
她压根就没有想到今年会当众公布词选,若她真得了魁首……
眼见虞沨手中纸幅展开,江月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恨不得透过纸背,看清正面所书。
依然是清越如玉击的嗓音,缓缓将那一首夺魁之词诵来——
旖景眉间神情一滞,孤疑地看向虞沨。
虞沨这时情绪已经平稳,自然不会让旖景看出半分端倪,当诵罢最后一个音节,才微抬眼睑,看向底下面无人色与满面孤疑的候府七娘、旖景两人。
“今岁‘诗词’一选,夺魁者为建宁候府黄氏七娘。”
不少人惊叹地看向江月,大都折服,当然也有少许不甘之人,比如秦七娘。
但黄江月这时不及理会这些,她紧紧地拽住了旖景的衣袖,目带恳求。
旖景这时已经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可孤疑的情绪尚存——她虽了解江月争强之心,可一惯以为江月是极为自爱之人,怎么会行此“舞弊”之事?
“阿景……”江月艰难地低喊一声,却不知应当如何解释。
假若这时,旖景一句质疑,在芳林宴“舞弊”之行公之于众,若是太后追究起来,轻则也是个“品行不正”的罪名,就算太后不追究,今后江月也会遭人耻笑、声名狼籍。
近处的安慧留意到江月的神情,冷冷一声嗤笑:“不就是个魁首么?犯得着紧张得面无人色,还真是小家子气。”
这时的江月,已经没有半点心思理会安慧的嘲讽。
她已经像是失足峭壁的人,尚且竭尽全力地攀附着最后一线生机,可若是没有人拉她一把,仅凭自己,根本无法摆脱深渊的威胁。
终于,她看到旖景轻轻一笑。
“阿月,恭喜你。”
江月猛地松了口气,才感觉到一颗心重新恢复了跳动,可是终究没有力气挤出笑容来,连一声“同喜”,也说得分外勉强。
甚至太后赏下四枚玉如意,又对三度夺魁的两个少女大加赞赏,特意加赐了两人鲛珠月华裙,并赐“京都双华”的称号,也没能让江月当真欣喜起来,待赏春宴散,众人辞宫回府,她总算是找到了与旖景独处的机会,在平安门前,挤上了旖景的车與。
“阿景心里一定是鄙夷我的吧,可我今日实在要感激你的庇护。”江月垂头丧气,手指把玩着绣裙上的禁步,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旖景从没有想过江月会做这样的事儿,一时更觉得当年的闺中知己或者根本不是自己熟识的那个人,心里也不好受,这时也有些沮丧,闷闷地垂着头问:“为何如此?”
“对于阿景来说,是否魁首,有无才名,实在不甚重要,可我一直执着于此。”江月眼角微涩:“正如安慧所说,我虽出身候府,可并非候爵之女,我不甘默默,将来就配个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太后亲赐的才名,对我来说太过重要。”
车轮轧轧,渐渐从沉肃的平安门驶出,市坊间的嘈杂喧嚣充斥在外,旖景却有那么一瞬的恍惚。
上一世,她从不知江月原本如此功利。
那么,当时那个一言惊人,声称不得称心如意之人,宁愿落发独守孤灯的女子,那般坚持与洒脱的女子,曾让她心怀钦佩的女子,其真实的心境,并非如她当时以为?
江月的张扬与洒脱背后,竟然暗藏的是功利?她追求的并非一心人,而是更尊贵更显赫的姻缘?
那么当年她青春已大却执守空闺,究竟是在企图着谁?
“阿月,我一直当你是知己。”旖景微叹一声,尽管重生之后,她对江月也曾心生防备,可心里委实不愿,希望至少在上一世,她对江月没有认错。
可事实,偏偏如此。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鄙夷我。”江月咬了咬嘴唇:“可是阿景,我只是想依靠自己的努力,谋求想要的姻缘,难道,就错了吗?今日,我只是一念之差……我很懊悔,不该抄了你的诗作,这一件事是我错了,但我并不认为我的想法也错了。”
旖景缄默,心里沉重的疑惑,让她不能将“原谅”轻易出口——假若前世她的结果,也有江月的故意,那么,她一定无法原谅。
“谁让我身为女子,这一世能指望的,也就只有姻缘呢?我能想像的将来,无非是侍奉公婆、执掌中馈,与那些妾室庶子斗法,然后为子女谋划……既然如此,当然要更尊荣显赫,不再受诸如安慧这样的奚落,如果能嫁入宗室,还有谁敢对我不敬?”江月又说:“可我父亲不是候爵,只是个七品的官员,正如安慧所说,就算我有个才女的名号,将来也不一定会享尊荣,更别说默默无闻下去,会出现什么奇迹。”
安慧说得对,“京都双华”的才名并没有给江月带来什么实际的作用,所以,当她到议亲之龄,方才拒绝家里的“安排”,不甘嫁给普通官宦子弟。
旖景忍不住想,当江月的野心与欲望随着岁月膨胀,为了谋求良缘,会不会做出更狠毒的事。
那一世,江月废尽心思地说服她追求“本心”,大力撮合她与虞洲行那等丧德之事,怀的是什么目的?
一念及此,旖景的目光阴晦了下来。
“有些事不可强求,比如赢得众人的敬重,为了这个,行不义之事就更可笑。”旖景缓缓地说:“今日之事我不会声张,也是看在咱们多年的闺阁情份上,阿月,希望你好生体谅。”
本是警告之辞,却让江月彻底地吁了口气,方才抬眸,看向旖景:“阿景之言我会谨记于心。”
旖景没有再说话,她的心情十分沉晦,因她知道,只要她心里对江月还有猜疑,这一世,她们就再不能做知己,可上一世的真相,也许已经无从证实,只不希望猜测成真,与当年好友反目成仇。
她愿意放过这一回,不过是因为江月之行虽说有违德品,但并不曾造成实际的伤害。
而至于那些过去的事……既然无从证实,唯有堤防,总之不会再重蹈覆辄,轻信旁人。
突然想到那一世的今日,她与江月因“京都双华”的才名兴奋不已,互道恭贺,搂在一起又笑又闹……而这一世的今日,她却终于失去了一个知己。
旖景疲倦地倚着與壁看向纱春外模糊的喧闹,还有勾勒在窗纱上游离的光影,忽觉茫然。
掌握不住的变化,似乎越渐增多,她当真觉得有些疲累了。
☆、第一百六十章 虽未携手,早已并肩
其实旖景大可不必觉得孤单无助,因为她的身边,一直有人暗中关怀保护,而这一个人,足以让她依赖与信任。
不过此时的她,没有察觉罢了。
当芳林宴罢,虞沨并未急着辞宫,而是在遗珠园里略作逗留,随着几案撤去,人群四散,桃花林里安静了下来,喧闹不复,唯有满园春色依然明媚,花枝斜影里,春阳微晃于芳草香泥,并不比宾客如云时显得寂寞。
这时,他刚好在思量旖景——他猜测到小丫头当不至于让候府七娘当众难堪,可经此一事,应当会对黄七娘有所防范吧。
表面上黄七娘的行为够不着“歹毒阴险”,却也有失“光明磊落”,与上一世那个直爽热心的女子判若两人,当年旖景将她引为知己,言听计从,无所不谈,多半又是信错了人。
只怕她这时的心情,应当有些失落。
她肩上所负的担子,原不比他轻松多少,或者比他更加沉重。
不但有仇恨,还有愧疚,眼下又加上猜疑,而关于这些,还不能与旁人倾诉。
一念及此,虞沨再一次庆幸自己的重生,多亏如此,才能为她分担一二,至少有一些事情,不需要她废尽心机的解释,他也能懂。
若是可能,也想过放下旧恨,只顾新生。
可是就算他们愿意放下仇恨,仇恨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所以唯有出击争斗,才有赢得平静安乐的可能。
虞沨踱步于桃林,眉心微蹙间,神情有些忧郁,直到听见身后绣鞋踩着芳草的步伐声,才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淡然,回首之际,果然见如姑姑已经站在了眼前。
“世子可是有什么话要交待?”如姑姑的确是个干脆人,直接就开门见山。
“正是,沨有一事相求。”虞沨微微一笑。
关于甄茉的事,眼下他虽有了计较,可在东宫安插耳目却不容易,当见如姑姑,方才心念一动——东宫一定会有圣上的耳目,也许并非出自于防范,但圣上也得掌握东宫的情形,可即使知道这点,虞沨也不至贸然求去圣上跟前,以他猜测,太后对太子妃诸多不满,想来在东宫也有安排。
如姑姑是慈安宫的掌殿女官,极得太后信重,如果太后当真安插了耳目,定是交代给如姑姑操持。
“姑姑莫怪我冒昧。”虞沨拿定了主意,也选择了直言:“不知东宫可有姑姑的人?”
如姑姑怔了一怔,神情便有些端肃了下来:“世子有何打算?”
“我委实是怀疑太子妃不孕的事大有蹊跷,怕是中了旁人的算计。”这个切入点,尚算稳妥:“姑姑当知,东宫子嗣,涉及储君国政。”
如姑姑略有迟疑,却听虞沨又说:“本来我有这样的想法,应当先与太后娘娘商议,可眼下只是猜测,还需证实,倒不好枉言,所以,想请姑姑协助一二。”
“如此说来,世子已经有了几分把握?”如姑姑眉心略蹙:“不瞒世子,娘娘是一直关注东宫,正如您所说,东宫子嗣关系重大……只太子妃甚是谨慎,几个侧妃相继小产倒与她有关,可若说有人害她……”如姑姑摇了摇头:“东宫侍女能得太子妃信重者不多,尤其是打理饮食香脂这些要紧之人,都是出自甄府,比如药膳,唯有一个老嬷嬷能够经手,据说她是甄府几代家奴,不可能被旁人收买。”
再有一点,当初太子妃小产,也的确不是因为饮食,太医们早有论断。
“我是猜测,也许祸端正是起源于甄家内部。”虞沨沉声说道。
如姑姑大是疑惑:“这从何说起?”
“甄四娘十分可疑。”深思之余,虞沨还是暂且隐瞒了甄茉与太子的私情,只得从另一个方面着手:“我今日留意到甄四娘偶尔暗觑太子妃的目光,颇为不善。”
“可她们是亲姐妹……”
“就算如此,也未必如表面那般和睦,如姑姑可别忘了,当日霞浦苑一事,太子妃可是毫不犹豫地将罪名推托到了亲妹妹身上。”
太后应当能洞悉当日的真相——太子妃早有筹谋,促成与卫国公府联姻,董音是大长公主中意的长孙媳,这才会招至甄茉的嫉恨,没有太子妃的支持,甄茉绝不会胆大妄为。
如姑姑神情更是沉肃:“不瞒世子,东宫的确有我预先安排的宫人,眼下虽不得太子妃全心信任,到底还有些作用,世子欲如何证明?”
虞沨见一切正如自己所料,如姑姑也答应了协助,才吁了口气:“具体计划我还在思量,但姑姑若能相助,也许会更有把握。”
“太后娘娘也颇为关注此事,世子若当真能察探清楚,也是替娘娘尽力。”如姑姑又道:“世子若有吩咐,尽可直言。”
虞沨环手一礼:“如此,我就先谢姑姑鼎力相助。”
先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