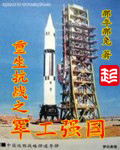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1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施兰心显然已经“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起初中了旖景的算计,实际上孟高就算无辜,却也无法证实疟疾是否当真早发,更无法证明施德就是那个陷害之人,她这时的盘算是——就算追究下去,奉城知县将施德招供出来,也拿不出实据,他们自然矢口不认,这案子一时半会儿不能决断,等传到了京都,金相哪里会坐视不管,当会想办法平息,不过就是让个县官顶罪,施德担个“不察”的罪名,最多也就是降职,可金相还得靠着施德平息黄花蒿一事,一定不会放任并州知州一职易主,有那么一座“稳如泰山”为靠,这事情极大机会便是不了了之。
不说旁人,这时立在堂下的旖景当真对施兰心五体投地——这姑娘面皮甚厚,在这方面的确不输须眉——瞧瞧施德那帮七尺男儿,这时已是冷汗淋漓,显然做贼心虚,哪里及得上兰心姑娘的能屈能伸。
暴怒的是孟高,毫不“体恤”佳人折腰,浓眉一竖,怒火灼眸:“少装模作样,妄图推脱罪责,什么审案不详、妄听人言,当日堂上,正是施德那狗官令人强押我在罪供上按下手印,若非他有意陷构,何至如此!”
施兰心挑眉一笑:“孟主薄,你虽受了冤屈,心怀怨愤,可也不该这般迁怒于人,当日因你解释不清,又惧受刑,方才认罪招供,我当日身在堂内旁听,并不曾见家父强迫于你,关于此点,主薄、判官皆为旁证,你若是执意污篾,却依然逃不得构陷上官之罪。”
孟高被这一噎,更是怒火蓬勃,险些没有青烟焚顶。
施兰心却又转身,面向世子,半分不显慌乱:“世子,孟主薄口口声声称家父是因瞒疫,才着意陷害,可是家父身为州官,当知疟疾自然应当上奏天听,才能及时防治,明知疟疾一旦滋生便势不可挡,瞒得一时难瞒一世,何苦行这死罪之事,更没有瞒疫的动因。”
说完,又看向三皇子,话中更含深意:“金相当知疟疾暴发,旋即寄书与家父,叮嘱家父应说服并州药商,请他们以百姓为重,先行往各地收购黄花蒿救治疫民,而城中药商霍升大义,满口答应,不惜倾尽家财,购得黄花蒿入并先往疫区,三殿下才从疫区归来,因知详情,眼下患者皆得治疗,委实多亏及时二字,家父应金相之示,以苍生为重,原为职责中事,不敢居功,却也容不得他人信口污篾。”
端的是大义凛然的一番话,又提及金相,以点醒三皇子,施德可是金相亲信,若他不保,金相更危,三殿下可再不能坐视旁观。
兰心姑娘这时尚且笃信——三皇子既与太子情同手足,当然不会置金相不顾,就算黄花蒿一事金相并未告之太子,三皇子也被瞒在鼓中,但经她这番提点,三皇子总该醍醐灌顶。
言尽转身,施姑娘一双秋波脉脉,正看向虞沨——世子,想要将我入罪,可不是你想的那般简单……
却忽闻三皇子似笑非笑一句:“这位……施姑娘……我这疫区一行,当真得知了一些详情……疫区之药并非黄花蒿……”
☆、第两百七十六章 舌灿莲花,欲反黑白
三皇子一语惊人!
公堂上顿时有如鼎沸。
因为施兰心“能言善辩”才舒了一口气的州官仿遭雷劈。
堂上正座,虞沨依然云淡风清,这才回应那秋波脉脉,却是眸光幽冷。
施兰心也是瞪目结舌,一切筹谋尽数混乱,脚底下寒意侵袭,满脑子洪涝汹涌。
她惊惧的发现已经彻底陷入迷局。
“三郎,你说疫区之药并非黄花蒿?”大长公主略略扬声,盖过了公堂鼎沸。
三皇子施施而起,冲堂下待命多时的那位太医院药局大使一声嘱咐:“东西抬进来吧。”
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木箱“砰”然落地,箱盖敞开,整整百袋药材坦露眼前。
“姑祖母,这些便是我在疫区带回的药材,据太医们查验,并非黄花蒿,而是普通的青蒿,并不能治愈疟疾。”三皇子面向大长公主而禀:“这些青蒿与黄花蒿价值悬殊,想来,施知州必然心知肚明。”
随着三皇子话音一落,众权贵再难摁捺——
“施德!你竟然敢以假充真!”
“让我们筹集药款,施德却以青蒿充数,足足三百万两银呀,施德你真是狗胆包天!”
“定是这狗官瞒疫在先,炒高黄花蒿价格在后,原来是打的贪桩枉法的算盘!”
“我就说嘛,眼下黄花蒿六十余两一剂,十万剂得花费多少银两,那霍升一介药商,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大手一挥就能拿出六百万两白银,定是施德与那厮串通骗财!”
案上惊堂木静置,虞沨着意放纵权贵们对施德的声讨,但他知道,仅仅靠着这点“证据”,还不足以让施德入罪。
果然,施德被众怒“惊醒”,踉踉跄跄地跌向堂中,手捧一把“黄花蒿”,装模作样地看了又看,双膝一软,瘫跪在地:“世子,下官当真不知情,这药……”
“是你!”施德的话忽然被施兰心打断。
且见她柳眉倒竖,玉指轻出,朝向正袖手旁观,悠哉游哉的“贾拙政”。
旖景一个激灵,顿时斗志昂扬。
她原本没准备这么快出场呀,可看眼下这情形,兰心姑娘是要“狗急跳墙”了。
“是你!你当初转售予我的万剂黄花蒿是假药。”施兰心这会子当真已是方寸大乱,不及细想,只想着牵三扯四,先将事情往复杂里引导,导致个真假难分,是非莫辨:“世子,当初正是此人售予我万剂黄花蒿,用以捐助疫区,定是她以假充真,我因心系疫民,一时不及详察,才落入了他的骗局。”
“施姑娘,你可不能信口雌黄,咱们早已经钱货两讫,你这会子又说我卖给你的是假药,可得拿出证据。”旖景满面莫名其妙。
事实上,她卖给施姑娘的还真是假药,这算不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施姑娘,你为何这般肯定?”堂上,已经沉默一时的虞沨也问:“难道那霍升就如此可信?还是当日将黄花蒿入库之时,已由施知州一一察验,确定并非青蒿。”
这话显然是个陷井,施兰心满心堤坊:“疫情危重,疫病所医官尽数投入疫区,当日霍升交付药材时,州衙无人能够鉴别,故而,不曾有验。”
权贵们却并不买帐,纷纷质疑:“价值数百万两的药材,怎能不经察验?这话万无人信。”
“诸位,相比霍升,此人更是来历不明。”施兰心是咬定了旖景,竭力平息慌乱,信口胡诌:“当日他从东阳镇那几个药商手中收购,就曾欺哄他们是为捐助疫区,故而,以二十两银平价购得,结果,转手予我之时却狮子大开口,要价六十两银!此人欺骗药商在先,居心委实叵测,无非是为重利,或者还有陷害命官的意图,否则他才一得手,便离开并州,何故这时归来?又与孟高串通一气,咬定家父瞒疫,分明是早有企图!”
这还真是……旖景暗叹,见施兰心那纤纤玉指已经快戳到她的鼻尖,伸手重重一抚:“施姑娘,明明当日是你一番以势压人,从我手中以二十二两银购得万剂黄花蒿,怎么转眼就成了六十两银?”
施兰心冷笑:“我当日与你面谈,只带了个侍婢,如何做到以势压人?客栈里人证可是不少。”
“你是知州之女,开口闭口便是百姓为重,言之凿凿要治我坐地起价之罪,难道不是以势压人?”旖景也据理力争:“再者,当日那些药商交付黄花蒿之时,你可是与我一同前往,我碰都没碰这些药一下,就转手给你,怎么偷梁换柱?”
“那便是你与那些药商原为串通……”
“施姑娘,那些个药商可是先将万剂黄花蒿售予了大长公主,难道那些也是假药?”旖景又问。
“施姑娘休要牵三扯四,当日我可是让人察验过那些黄花蒿,的确是真药,并不掺假。”大长公主这时悠悠开口。
“公主,那些奸商或者正是打的这般算盘,先以真药售予,料到公主您会察验,如此,旁人便不再设防,而之后万剂,却是青蒿,以高价售予我,谋利的同时,又为今日污篾一事埋下引线。”
旖景满心“钦佩”——才女就是才女,当真有颠倒黑白的本事。
“敢问施姑娘,当日是你主动寻的在下,提出要收购黄花蒿,在下怎么能预先布局?就算在下神机妙算,能料中大长公主有‘恤民之心’,也料不到施姑娘一介闺阁,居然也能如此大义。”这话,实在有些暗讽的意味。
“家父乃并州父母官,眼下疫情危重,当知有人手中有黄花蒿,必然会先行收购,何足为奇?”到了这个地步,施兰心还不忘往自家脸上贴金。
旖景叹息,抖了一抖玉白敞袖,从中摸出一纸契书:“施姑娘,你口口声声称在下将药按六十两银一剂售予你,可是当真不记得咱们白纸黑字的约定?”
施兰心愣怔当场,一句“那不可能,契书已毁”险些脱口而出!
还好,她及时吞咽了下去。
假若当真以六十两银收购黄花蒿,根本就没有签定契书的必要,再者,事后特地要回契书焚毁更加蹊跷,难免让人生疑。
但她笃定,这封契书是假的!
虽当日她不能核对指印,但那契书为她亲手执笔,自己的字迹能不认识?明明已经焚毁,又何来凭据?
施兰心冷笑:“当日我一心为疫民安危着想,任由你信口要价,只料你既得重利,便不至反悔,何曾立契?”
旖景又是一叹:“施姑娘,这契书上头,可有你玉指朱印一枚,是真是假,一验便知。”
那日两人交锋,旖景见对手“气势如虹”又“谨慎缜密”,哪里会不多加堤防,施姑娘那手字的确不错,煞是漂亮,等闲人不易模仿,但旖景于书法上却也深有造诣,更何况还有虞沨这位“大家”,仿她一纸契书又有何难?
施兰心焚毁的那张是假的。
眼下旖景手里才是货真价实的契书。
施兰心见对手胸有成竹,已经心虚了几分,这时美目一睨,见那契书上果然是自己的字迹,面色当即煞白。
这时,好一阵没有反应,缩在人后的霍起见施千金面色大变,心下也是一凛——假若不能让这个不知来处之人背黑锅,施德父女必然会将罪名推到霍升身上,为了大局,自己这个兄长也不能替弟弟辨解,今后霍升可只能“消声匿迹”,过一世东躲西藏的日子,这还是好的,依他对金相的了解,极有可能会将霍升灭口!
到底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可不能坐视不管。
霍起到底是曾走南闯北之人,在霍真受到金相重用之前,他也是市井当中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个中高手,早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起初情形紧迫,他还没留意这个“白脸后生”,当施兰心与之一番对恃,却讨不到半点口头便宜之时,霍起不得不注意此人,发现了一个真相——
“世子,此人之言不可信,她分明是女扮男装,有心欺瞒,可不就是居心叵测!”霍起及时援手,将众人的关注点从契书上转移开来。
女扮男装!
施兰心短短一怔,当即冷笑:“原来如此,亏你还狡言善辩,若非居心叵测,何故存心欺瞒?”
公堂上顿时又是一片议论。
世间多奇事,今日尤其多,从孟高一案牵扯出真假黄花蒿,眼下公堂之上,竟然是两名女子之争。
旖景身份被揭穿,却也不急不躁,反而笑靥若花:“女扮男装便是居心叵测?当日施姑娘与在下面晤商谈之时,似乎也是女扮男装吧?施姑娘起初声声强调实据,这会子怎么在意起在下是男是女来?”
“三娘为官宦之女,岂是你能相提并论?”霍起满面不屑。
眼下,不仅在意男女,居然还拿身份说事,旖景暗忖,这霍起的“辩才”比施姑娘相差远矣。
三皇子戏看到这儿,觉得实在有趣,见旖景尚且端着大家闺秀的身段,不肯“以势压人”,轻轻咳了一声,半是愉悦半是宠溺地“提点”旖景:“五妹妹,快将你手中的契书拿来瞧瞧,我好奇了半天,都说施知州家千金仗义疏财,将六十万两银购买之药助于疫区,美名遍传华北,怎么听你说来,原来她竟是沽名钓誉,明明只花了二十余两,却鼓吹惑众。”
三皇子今日注定了语不惊人死不休!
能得他称为五妹妹之人,身份怎么也不是施姑娘一个五品官员女儿能比。
旖景暗叹——看来,她的表演基本落幕了。
并州官员彻底面如死灰。
施兰心更是身子一晃,脑子里的经脉彻底绞成一团,再也无法运转。
却又有虞沨打趣三皇子一句:“这话殿下也能当真?别说施姑娘一个未出阁的女子,便是整个施家,若非贪赃枉法,也拿不出这六十万两银来,若施姑娘真用了六十万捐助,倒更让人讶异,难道贪得无厌之人,也有改邪归正的一日?”
话音才落,公堂上竟然诡异地“哄堂大笑”,紧绷的气氛顿时过渡到滑稽。
☆、第两百七十七章 已在死路,尚不知悔
施家并非望族,施德之父施幸原是东明末年一介疱厨,因为北原犯朔,被东明朝廷强征为兵,眼见城池不保,立即丢盔弃甲趁乱逃命,后走投无路,方才投靠了楚州军,至金榕中之父金准麾下。
施幸本乃贪生怕死之人,自是不愿冲锋陷阵拼杀疆场,靠着一手厨艺,与溜须拍马的讨好奉迎,混成了金准“近卫”,虽说表面是个兵甲,实际上做的尽是侍候吃喝之事儿,大隆建国后,他依然在相府“侍候”,说白了就是个没签卖身契的家奴。
但习惯荣华富贵后,又加上大隆渐至国泰民安,战乱平息,眼看金家如日中天为一国支柱,施幸倒也有了“望子成龙”之心,将儿子施德自幼往“文化人”的方向培养,顺利成为金榕中的慕僚,并甚得信重,被荐入仕,一帆风顺就到了五品知州。
施家并无家底,更无皇家封赏宅田,一个知州的年俸不过才三百两银,哪有一掷万金的能力。
不过金相亲信,靠的当然不仅仅是朝廷的俸禄银养活,施德为官多年,“积蓄”自然丰厚,施兰心自打出身便是锦衣玉食,不知油盐柴米,且认为这荣华富贵是理所当然,而并州权贵尽知施德为金相“自己人”,原本没人会以为他“两袖清风”,只要不伤及自己利益,哪会关注施家家底厚薄。
平民百姓多数只知官员权贵皆富有,更是没人在意此等细节,算这笔细帐。
施姑娘一心估名钓誉,更不会顾及“家财外泄”,其实莫说六十万,就算二十万,对施家尽管不难,却也不可能白白捐助,两父女打的主意是以“垄断”为借口,这本金还得摊在几家贵族身上,借着他们的钱,使施姑娘美名远扬不说,从中白白赚了四十万的利,当真是名利双收。
眼下被当场拆穿,堂中那几个成了“冤大头”的贵族自然面如锅底,其余权贵哄堂大笑、讽刺不断,就连堂外百姓也都如醍醐灌顶,这时,没人再信任施姑娘的“大义善良”,那些性情急躁者已经摁捺不住叫骂出声,附和着孟高的话将施德斥为“狗官”。
“什么并州明珠,我呸!真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用盘剥咱们百姓的钱,扬自己的名声。”民众们到底淳朴,这时还没想到更深的阴暗。
却已经让“凌云大志”的施兰心难以忍受,扫了一眼那几家“同谋”,暗暗一阵咬牙——这些白眼狼,难道打的竟是袖手旁观的主意?假若自家今日罪名难逃,他们难道就能独善其身?当即把心一横,胆气一壮,回身面对言辞愤愤,依然是高扬面颊:“我何曾说过捐助万剂良药是施家一家之善?宁平候、阳明候、鞠世伯几位自从听说疫区缺药,也甚为牵挂,由他们出面,筹得不少善款,几位世伯不欲张扬,才交予兰心出面……”
虞沨蹙眉,立即洞穿了施兰心的盘算,她这当真是要“狗急跳墙”,企图将那几家“共谋”拉下水来——今日目的是要坐实施德之罪,而那几家,已经上书圣上自请罪罚,圣上顾及他们手中兵力,就算“小惩大戒”难免,也会另寻借口,必不会将他们参与其中的事公开。
在座中人,不乏秦相党羽,他们一旦握得把柄,必不会善罢甘休。
而旖景只见虞沨略一蹙眉,虽想不及深,却也猜到他是不欲牵连过广,当即轻笑,脆声说道:“施姑娘,你眼下是否还坚持是用六十万从我手中购得黄花蒿,我这里可有一纸实据……难道说,你竟是为了那四十万的重利,才狡言污赖……原来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是贪心不足,目的竟是要侵吞善款?”
这话一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施兰心面色煞白,狠狠盯向旖景:“你!”
“我怎么?难道我所言不实?那施姑娘当着众人的面,不如细说一回,究竟是用多少钱从我手里购得黄花蒿,又收了人家多少善款?”旖景挑眉。
霍起原不知施德父女竟还有这么一着,此时心中大恨——好一对狼狈为奸!为了蝇头小利,居然就这么得罪了那几家大爷,眼下情形不好,看来得尽快了结此事,正盘算着“弃卒保车”,让施德父女顶了这“以假充真”之罪,暂且敷衍过去,遣人急报金相,让他老人家拿个章程出来。
忽闻一声重响,哄笑一静。
却是虞沨再次拍了惊堂木,长身起立。
这时,秋阳透过天窗,光芒远远映入,使那黯沉的牌匾上铁划银钩的“明镜高悬”四字若泛波光。
“知州施德,我来说说你瞒疫的动因。”世子眉心平静,墨眸宁澈,只微抿的唇角,略带着凌厉的肃意:“疟疾早在两县洪涝之前便已发生,主薄孟高察觉,欲上报省府以呈天听,却被你以杀人罪反污入狱,为的,便是暂时隐匿疫情,使人以平价垄断华北药市治疟良药,再囤积炒高,当疟疾暴发,圣上必会下令拨款平疫,于此,你便图得暴利,假若仅只于此,还不算罪大恶极,可恨数百万利益还不能满足你之贪欲,行下以青蒿假充,置数万染疫者生死不顾,将价值百万的黄花蒿转手牟利,如此丧心病狂,简直死不足惜!”
世子话音才落,堂内堂外再生喧哗,便是连那些贵族都忍不住破口大骂,百姓们更是义愤填膺——
“狗官,该当千刀万剐!”
“这可是数万人的死活呀,真是狼心狗肺。”
“狗官不死,不以平民愤!”
“亏那对父女往日还口口声声心系疫情,想不到竟是这等蛇蝎心肠!”
但也有一些沉默者,比如监察御史与那两个最高行政,他们自是不信仅凭施德,便能狗胆包天,几乎不用怎么转脑子,就想到了金相。
虞沨当然也是存心只斥施德,至于金榕中,还得等施德定罪之后,交给秦相党羽“追根究底”,毕竟金相是在幕后,而知情者如常信伯等人,也是牵涉不得的,而此案一出,朝中必然大哗,眼下湖南、直隶还有不少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