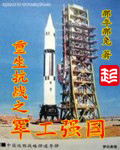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24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ӣ���
콾������ɻ�Ҳ�����ʣ��������������ѵ�����ӣ���ȹ��һ�������ܳ����ȡ�
ȴ��վ����dz��������Ц���������ӣ�һ������£��ĵ���üĿ�ǰ��º����š�
���ɣ������ξ���
콾����������ǰ��վ����ɴ���⣬ɵɵ����ָ������һ�����ġ�
������һ������������ʹ��
���ӭ����ǰ���������ʡ�
�������ã�����ȥ����Է��������һ���ڣ���㲻ӹ���ɣ�������ͻȻ������һ˿���ң��������İ�������С�
һǰһ��δ�ȼ磬��ͥ����������δ���������Ҳ���˸��档
ȴ�ھ���������ס����Ժʱ���롰�����ڡ����ڶ�����ֻ��Σ���ȷ����������
�������۽Ƿ����к�˿������ʱ�����ɻ�ؿ����ݛh����Զ������ǡ�����
���������������ĸ�ʰ������ݛhֻ��פ�㣬����һ���Ծ�������
�����ӿ���һ�۽�������콾����۽�һ�䣺��Զ��ʲôʱ������ģ���ȴ��Ȼ�������������һ�㣺�����DZ�վ������˵��������ȥ��ͷϸ˵����
�����£����Ѿ���������ĸ���㲻�ٴ��ţ�һЩ���ˣ��Ժ�������½�����ϸ�����ݛh��ף���һ��������콾���˵���֣����߰ɡ���
������ȴһ�������ݛh��ǰ��������Ҫ����Ī�����ھ�̸��Զ�ﲻ��Ӧ������ô�����dz���ʲô��ʣ��ѵ����������ٷ��������ֿ���һ��콾�����Զ���������ã��Ǵ�����������֮�£�Ī����Ҳ���������������Զ���Ժ���˵һ�ء���
콾�ҧ��ҧ����������������ȥ�������ӵ�һ��������
ȴ���ݛhһ���Դǣ����پ��ɲ�������
������Ҫ������������̸����ʱ����ȣ���������и����㣬ίʵ�ִٹ���֮���ɣ��Ѿ���������ĸ������һ�ʱ�֪������һЩϸ�ڣ���Ҳ�ѽ�������λ�ݹ٣����µ������ʣ�Ҳ�������ǹ�ͨ����
�����Ӵ�ǰ�ŷ����������ݛh��֪���ǡ��������⡱����˼�콾�����û�С���͡��˻����������Ȼ�³�����콾������̲�ס����������ֻ�ݲݳ���������ϥһ���������ಽ������
��������ȥ��������Ӱû��ת���۽ǣ������ӷ������γ��ѣ��۽�����һ����ȴҲû�ٸ���ǰ������һ�������Ǽ���멣�̧�Ų�����Ժ����������֮ǰ������ǿ�ڴ�������˿Ц�ݡ�
ȴ˵�ݛh��콾���һ·��Ĭ�ŵ�����Է�̶����⣬�ǰ��������ڡ�
콾������ݛh������Կ���������ƿ��������ţ���������������
�Ļ��ɻ���ȴ�������ɣ�콾��������ڣ�ת���������ݛh�ɾ�����ر�����˨���������̲�ס�ˣ��Ż���һ�������h��硭����
ȴ���������ӽ������ɷ�˵�ؽ����������뻳�У����ָ�ƽ��������Ժ�һ�����ǣ��Ȼ����û���������ʡ�
���о��������伱�ٵĺ��������������������������Ⱦ�����ȴ��������ݺ�һ�գ�һֻ���ƣ�����ʶ�������������ţ�ȴ�����������Σ���ʵ�ظо��������ٵ��������������û����������ġ�
��콾����������ݼ���������Ƶ���繣�������һ�ǵ�ͻȻ���뿪ͬ���ִ٣��������������ڰ�գ�������ȴ�����������ػ���������Ϣ�������Ƚ��ƺ�������˫��һ�ɣ����dz����֡�
���ѱǼ���������˿���������������ŵ�������ӿ����콾���Ϊ���ҡ�
���������˺�һ������ֿ�������ס�
��ü��ߵ�ɽᣬ����������������ֱ�Ľ�ë������Ϣһ��ز����ţ���Ȼ��ǿ�����࣬���ҿ�����ʱˮ����Ⱦ���ۡ�
���h��磬����ô�ˣ�����������ʲô�£���
��������������ĸ�Ħ������ָ�⣬�ᴥ������ü�ң�������Щ�����⡣
��ȷ����ס��������ǣ����ȥ��������ס���������������䣬Ψ��ͣ���������ϵĺ��������º͵����⡣
��콾���������Ҫ�����ݡ������ã����ƺ���һ��̾Ϣ����������˵��������ʥ�͡���
콾�����Ī��������������������������Ž��������ƿ�����һ�أ���Ը�������۾����ϡ�
����Ȼ�Ѿ�ƽ��������ͫ������������ȴ̫��������
����������Ȼһ�ͣ����ŵ��Ҳ��ؽ��ࡣ
������ƽ������𣬺�������㡭�����յĸо���ʵ�����������İ���
����ô�������ʱ���������л���δ��Ȭ�����������ֵ��¡�����콾�ҡ��ҡͷ�����h��磬�������ʵ�飬�����ǡ�����
�����ݵ������²��Ƿ��Ҳ��ɣ�������ȴ����ű���������������dz��ſ�������ֻ��ʮָ��ǣ��Ϊ��ñ�ǰ���ݵĻ��档
����������Ŀ�⣬�ʶ���������˲Ϣ��ɴ��һ˫��ˮ��ͫ��
�����ܣ�������ô����ű��������
����콾���Щ�ѿڶ����Ļ����Ѿ����˴��߶����ż�ʱ�����˻�ȥ��
������һƬ���磬һʱ�Ҳ������ͷ����
���h����㲻��ȥ����Ψ�У���ôһ����ֹ��
Σ�գ�����Σ�գ���Ӧ����һ���ݾ�����������ʱ���һ�����ϸ˼��������������ı�����硣
������ʥ�͡����ݛh��Ц����ο��������������֣�����֪�����ڵ���ʲô��Ʋ����Ҧ���Ī��ɥ������������֮�´������Σ����п����ǿ���ƣ���˵�����о����˴���������Ѿ��������ж�����
���ǣ�������˵�������϶�˾����ཻ���ƺ���ô��һ�أ��������������ֲ��µ��ݾ�����콾������Ѿ��ƶ��������ػ������ݛh���֣������ԣ��h��粻��ȥ��Ӧ����������ʥ�ϣ�ʥ�ϱز������㸰�գ�Ҫ����������ĸ���衭����
�����ж���ң���������һ���ƽ��������Ǹ����������˵����㺢�����Ļ�����
�ݛhЦ��̧�������ֱ���ӡ������һ�ǡ�
��콾�����ֻ������һ�����ܣ��������£����ܽ�ƾ�²����жʥ�����������ż����۾��ﷺ�������⣬��ü��һ������������������콾���������˵����
��Ҳ�п�������ű����������ʩ��������ߣ������л����߲���֪�飬ȥ�����ݡ�����
�����ⲻ���ܣ���������ˣ�ǰ�����ϱ�ᱩ��ű�����������²�û������콾�Խ���������������������������ɣ����յ�ҧ�����촽��
�ݛh��Ȼ֪���������ܳ������Ŀ��ԣ��Լ�˼����ֻ�������ƿ�ű�������Ŀ����ԣ������������Ƿ���ű������������һ���������⣬һ����ʥ��δ��û�ж�����������ı������ȥ����Ϊ�˲���ʵ�飻���ߣ�Ϊ�����࣬Ҳ�������ȶ��������ѫ���������Ʊ�֮��˾��Ԭ��������������������ཻ����������ȴ���о��壬�����������Ҿ����������������뾩��Ҳֻ��������һ�ˡ���
���h��磬���Ѳ������Σ�գ�����˵�����ü������վ�������
�����������ǽ�����ı����Ȼ���뷢�����ң����Ҹ���Ҫ����һ�ˣ�ֻ��һ�����ң��ڴ�¡�ڰ��գ�����һ���������顢���Ը�Ϊ���յĻ�����ʥ�ϲ����ǹ�����Ҳ���ҳ������ˣ����Ǵ�¡���ӣ�������������ͷ��������ô���˱ܲ�ǰ�����ݛh����һЦ�����㿴���Ҽ���˵���ⷬ������Ȼ���д��㣬�������ý������óѡ���
콾���ʱҲ�����侲�����������һЩͷ������Ȼ�����������ǣ����Ҳ��۽�������ʲô����������ű��������ͨ���Ϲ�Ա���죬Ŀ�ı���Ҫ�Ûh���ǰ��������֪�������ݣ������עһ��������
����Ӧ���ϵ�ʥ�ϵ�֪����ű���������ͻỳ�����л������Σ������������Ӳ��ˣ�����Ϊ�˽�����������ѹ�ļƻ���Ҳ����������һ�ˣ���������ȥ���ϣ�����Ϊ���������ʣ���в������ֱ����ʦ����������ɸ������ƣ������������꣬�����м���ʤ�㡣콾���������Ѿ��뵽���������²����ȫ�̼ƻ�������û��ʮ�ɣ�ӦҲ���߰˳ɡ���
콾�����ϸ�ʣ�ȴ���ݛh����ӵ�뻳�У���콾�������Ȼϣ��������������죬�˼ɹ��࣬���ǣ�����һ�������������ϣ�������ܷ���Ϊ�ģ����ÿ�����������
��һ�أ���������������������������������½�������������۽ǵ���ɬ��
�������ã��������˽ߣ������뿪��
������·Զ����Ҫ�ķ������г̣��������鲻������Ļ����µͻ�ƽϢ������ʮ����Ѯ�������ѻص���������һ��ȥ���㽫�������ź��������ݛh��Ŵӽ����ó��ܺ�������콾�����һ���Ǹ���������һ����Ҹ��������⣬��ʱ����ȣ��ղŲ���������Щ�²���߹���ĸ���Ƿ��֪�����Լ������⣬����Ҫ�мǣ����ܼ��꣬��Ӧ��ԭ�ƻ��Ȳ�������ƽϢ���ٷ��ؾ���������ֻ�»��ݾ��ߣ����൱֪���绳�䱸��˵��������ʱ���䣬�Ǿ�ʤ�������ˡ���
콾��ӹ������ܺ���ֻ�������ij�����������
������ض����ҵִ���Ϻ�Ż������ж���;�У��һ���Dz�˲�̽�������Σ���֪����Ϊ�飬�һᾡ������ʱ�䣬콾����������㣬Ҳ���������ң��һᰲ�������ػ��������ԣ�����ذ��á���
�������£���Ц����������ʮָ�����
�·������һ��ϧϧ����Ķ�Ů�鳤�������������ء�
������پ�ʮ���¡������ģ���ͷ����
콾��������ۣ��Ե���������ֻ����Ϻ���������һ�����ѩ����Ͷ���ҩ���˽�����
���ϵļ�ı�����Ϸ������Ҳûע��ѩ���ֻ���۾�ʱ��ʱ����콾���һ���̱���ģ����
콾���ѩ�����ҩ����������ȴ��һ�������������ʱ�ճ�����������֪���ģ�������������Ӧ����������������滹��ά���ͻݣ�Ҳ��������ô���ľͰ���ҩ���½�����������ѵ���ʲô��ı��
����ĥ�ţ�����ѩ��������ϸ���˵������ҩ�Ѿ��ŵ����ˣ�������˷��á�����Ҫ���������֣���֪����һ����һ��ҩ�������˵��ϣ�������ȹ�ǵ���֭��
����ģ�
�ڳ�������������������ü��һ˿�����ɿ��ӹ�����Ŀ�������۾���ĸ���������������������ô�������ֻ�����콾���������������¡�
콾�������������˫ϥ��أ������������뷣��ѩ���������ɫ��Ťͷ�����⣬�Ǹ������ˣ�������ô��ܷ��գ����Űɣ�Ҳ����һ���������ģ���֪����أ�Ҫ��������Ҳ����������ôһ����������Ľ��������ѩ�Ǹ������⡪���������Ŀ��ڹ�������չ�˲��ٶ�Ŀ��ѩ����ġ�������콾�һ����ж��ţ���������̽����֪��������ô����Ҳ����������δ������ߵ����ţ�������û�����õ������ֱ�Ӵ�Ѿ�ߡ����������һ���Ǹ������⡣
�����ֱ����������ġ����ᡱ���û�һ������ȹ����Ⱦ��ҩ��Ҳû��������ع���������ŭ�⣬���ѩ�����Ѿ����������ߵ�ײ��𣬵����ǵ���콾��������������һʱ����֪��ô�����ˡ�
���ǽ��ϱ뺷���ˣ����Ų����������룬һ����Ϊ���������������ƣ���üһ����ʳָһ�����������ļ�澣��������˷��˵�ҩ�����ϳ�ȥ���������ֱ�������ؿ���콾�������Ѿͷ����ô���ò�Ϊ���ɡ�������ֻҪ������ǿ������飬����վ�ڼ��һ���ݺ���ĸ������һ���������������ɨ�أ���������������Σ������仹�������ء�
�����Ƿ���Ժ������¶�������ô�ܲ��֣���������ĸ���Իᴦ�������콾��Ķ�����ô�����ϵ����������ɾͰ����ø��˻��ϣ�����ȴ���ú�Ц����˵���ϡ������������Ǹ��ʸ�������Ƽ�ѩ���������谮��Ҳ����ͽ�����ôһ�������˷����ˣ��ǵø���Ϊ���
������Цһ�����������������ش��������澣����ù���ү�����Ѿͷ�����Ǹ�Т˳�ģ��ɵ������������Ī�ù���ү������ޡ���
��˵������ز���콾�������Ȼ����������վ��������������ĸ���Ǻ��⣿����һ�����ط��ˣ����ع�ص�һ�ˣ���ε�����������������ʱ�Ŀ�����ƺ����Ĺ��ȵĻ��ϣ������ˣ�����ĸ��ָ���ף��ѵ�������������˸���ί������
��Ȼ����Ҫ�ѻ���ǣ���������Ҳ��Ӧ���������������뷨����������Ϊ���ϵ���ᣬ�����������Ϲۡ�
������ү��Ȼ������ˣ���ɩ���ɲ���˵�����Ļ�����
��������ˣ�����ô���������˼������˴����Ǹ���澵�Ѿ�ߣ������Ǹ�ʲô���������ο���
������ĸ����������ĸ��������̧����ң�������С����������֮��������Ҳ�Ѿ��������ϣ����������ݵ���������Ϊ��������ʼ�ն��ǹ����������������������Ӧ��������ĸ���������ԴDz��ǡ���콾�����ɨ�˽���һ�ۣ��ֶԻ���˵���������ˣ��ѵ�ѩ���ﲻ�����˷������ɣ���̧����ң���
���ϼ����ϱ�콾�����ŭ�����գ���æһ�����������֣�����ק�ţ������ͻ�������������Ѿͷ�������ĸ���ǻ��ϻ�˵�ü��ˣ����������ѩ���ﵱȻ����������������æϢ�����ˣ����������ַ�����ѩ����������Ҳ���Ǵ��ģ���������Щʱ�������˲�ʧ���֣���ȥЪ�Űɡ���
����������ģ�����һ�ߣ�����������ͻݣ��ڹ��������˰�����������Ҫ��һ����澵�����̫����������
콾����俴��һ�۽��ϣ���������˵���������֣����Ƿ��˵���ĸ��һֱ�ں��������̺���֪��ʵ��ģ�ѩ�������в���֮�٣��������Է������п�����������ˣ�Ϊ�β�����̫���ˣ������˼�һ�߹������ز������Ÿ���ί���˷��ˡ���
����������һ���ʹ�����ɰ��������˼��֣�����ɩ����֪�����Ǽ������Ӳ��ʣ�һʱ�ż���˵����Ƿ�˿��ǣ����˵�ˡ�������콾���һ������ϸ���Ȱο����ô����һ����������û�������ֳ�������
콾�����С���ʱ������Ƕ�ȥ���˲Ÿո��߳����ӣ����Ͼ��ں�ͷ���ˡ�̵��ҧ������������������ļ��֣������ز��ú��������ӱ�����������ϡ���
����������ü�ģ���Щ���Σ�����ɩҲС��Щ�Դǣ���ԭ���Ǹ������ģ����¸���䱸����
�������������������Ժգ�����λ����λ�����ǿɵ���ü��������Ѿͷ��ʶ�ô�����Ȼ������λ���˳������ӣ����������������������λ�������ӣ�����û���Ǻù��ӳԡ�������һ�����������·����¡���λ���Ѿ����������Σ����յ��˾�λ����Ҳ���˹������һ�㡣
�����ǻ�Ҫȥ���縮���������Ҳ���������Ҳ���ð��ŷ��ĵij������㣬���±�����ү��̫���˲������������˵��
�����ڽ����ĵ�λ����������Dz����ú��ɳ����źպյ����μ�ȥ���ػض��ǽ�������������ȴ��˺����ȥ������ʱ���������ˣ��ɻ��ϰ������żݳ����������»��ϲ������������ҷ���Ҫ�ó�������Ҳ������ѣ�ֻ�������ŵij���Ͳ����ǻ��������ˣ������ڽڹ��ۣ����ֳ�������������������ķ粨�����ϴ���ֻ��Խ�����ѡ�
���������������ɵ���������������ǰ��Ϊ��˫�����棬�����Ǽ��ں�̫�������£��������Ͽ��ǵ�Ů�������Ը��¼���������������ң�����Ϊ�������ŵ�Ц����ǣ��������������ȥ����Ҳ��Ϊ���ˡ�
���Ծ�����ϵ�μ�����ҵ����£�Ҳֻ���ǰ�ʾ�������Ǿ������ͷ��������κα�֤���������λεİѱ���
��Ȼ������Ҫȥ�μң�Ҳֻ�ܡ�͵͵�������ˡ�
��������ĸ�����ҳ����أ�����������ͷ����һ�������ǣ����ȷԸ��˺����������ӣ�����ʱ���㹻�����ˡ������ϲ���Ϊ�⣬��Ȼ������ĸ������������ȥ��ͷ��һ������
���ϵ��������ף����벻��Ҫ���������������������������Ҳ���Ҹ���ڣ�������ʱ������Ҫȥ�����ʲ������¡���¡��翪�ţ�һ���ѻ���dz��Ŷ���ֻҪ����Ѿ�����ӣ�Ҳ������������ǵ��ʸ�ȥ�����������ߴ��ŵ���Ҳ�����������ţ���Ȼ���¶���©�����١�
��������Ҳ����Ϊ�⣬�α����ס����ǣ��ֲ��ǻĽ�Ұ�⣬���ӽ����ΰ������ܹ����εģ���֪������ôһȥ��ֱ�����������ij��������ˣ���Ȼδ�顣
���������ż���ȴҲû���������룬ֻ�����������ָ��Żغ�һ�ˣ����������˽����ڹ���������һ����ֻ���ĵ�֪����գ�����ȥ�μ����������
��֪�������磬���մ�������������������ȴ˵��������������뿪���μң���ɩ���������ϵij����ʹ���Ѷȫ�ޣ�
��������ļ���١�����¡�����㿪�ţ�������ҹ�����ޣ����↑�����Ҳ���ѱ����ټ��ź��DZ�ֻ�Ͻ�������������˵�������´����ƾ��ʧ�٣���ֻҪ���ʣ����Ѳ������������Ѿ�������������ȥ�����Dz��ҵ����ϣ�������ͷ��û��������
��æ����ϸ��������Ҳ�����澪�̣�����̫̫��˵�����˻��õ���������Ҳ���Ұ����복�ͣ��ǵ������˶�Ŀ��Dz���˾����з���ͷ������������̫̫���µ����˷��ˣ������˿�������裬��˵�Ȳ��ü���ľ��£���Ҳ���㣬��ͷ�����ɾ����ŷ����ģ���֪�����˾�Ȼû����Ѷ������ү��̫̫Ҳ�����ò��У������������С�����ʣ�˵�Ǵ��ɾ��ڸ��������һ�ݣ�С�˿��������������ɾ�������Ҳ��������ǮҲ������
��Ȼ������������Ȧ�ף����¾�������δ����
����ү�������Ҳֻ�ܰ������ҡ������ӻ����˻�������ظ�����ʱ������������һ�ˣ�һ���ĵ�������������ĸ������Ѿ�����ˣ�������˵���ϳ�û��þͷ�����û��֪��������ʱ�ŷ��ֱ��˶��ڴ�����������ȴ������Ӱ�������ò����ײ����������ˣ�������سǵ�·������óȻ�ظ����ò����ײ�����֪ͨ���ҡ���
������ȫ����ˡ�
���Ҹոյõ���Ϣ����ƽ�ֺ�ɽ�������˾�ʬ�塣��
������ɫ�ף����ʻ���������û���ˣ�ֻ�������Ӵ�����
������������һ�������ʿ��������ȭͷק�����������������˲����⣺��������ҪΪ��Ѿͷ���𣡡�
���ѵ��ǹ���ү�������ӡ�����Խ�����̣�һʱ���L�˼����ϵ����ֻ�������Լ��Ĵ�����
���ϴ����˸���ʿ����Ҳ���±��˲��ʲô�������ʱ�ո���û�����������磬���������ݛh������ͨ��ı��£�Ҳ�첻����˿����������һ�����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