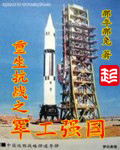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28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
一旁祝嬷嬷瞄了一眼小谢氏,趁着老王妃怒火未消,话里极有深意:“要论来,少夫人可真是大胆,空口白牙就敢陷害世子妃,世子妃是什么身份?哪容一个市井无赖就能定罪,奴婢以为,也许少夫人身后还有人指使,总不该以为这错漏百出之计就能陷害了世子妃,说不定那药里真有什么名堂,少夫人笃信有毒,昨日才会这般心有成竹。”
小谢氏心下大怒——好你个贱人,果然是你!
旖景也笑笑着说道:“的确有些蹊跷,祖母,莫若再拘了弟妹身边儿的丫鬟责问一番,才能察个是非黑白。”
小谢氏正想说话,哪知老王妃却蹙了眉头:“到底是家丑,息事宁人也就罢了,何必闹得个沸沸扬扬,传去外人耳里也是不美,这其中哪还有什么蹊跷,那药可是阿祝你交给我的,怎么会有毒?”
祝嬷嬷笑容一僵,干咳两声:“唉,奴婢也就是瞎猜疑罢了。”
“我看就是黄氏心胸狭隘,想法又太过简单,且以为搬了娘家来撑腰就能逼得我不问青红皂白责罚了景儿替她出气。”老王妃冷哼一声:“都是娶了这么个不省心的闹家精,从前咱们一家子和和睦睦,就算老二媳妇为着聘礼的事对景儿有所误解,也都是摊开来讲,哪有人像她在背后挑唆,用这些阴谋诡计,我昨日瞅着,栋儿两口倒还公正,并不曾偏听偏信,总归还明白沨儿与景儿不是阴毒之人,黄氏是新妇,是个什么样的性情也拿不准,哪会听她空口白牙造谣。”
小谢氏一听这话,心道老太婆果然还是糊涂懵懂,不由得意地扫了一眼旖景,笑着说道:“媳妇自然更信得过景丫头。”却忽地又心生伤感:“母亲,这回终归是二郎媳妇的错,闹得这般张扬,我也觉得无颜见人,二爷心里更觉愧疚……原本二爷早有了爵位,就该分府另居,那时长嫂身子不好,母亲让我协助着内务,才一直耽搁下来……眼下沨儿已经娶了媳妇,景丫头又是个能干的,论理我也该把中馈的事慢慢移交给她……总有一日,二爷是要在外头立府的,虽咱们心里舍不得母亲……”说着说着,眼角泛红泫然欲泣,却偷眼打量得旖景两眼放光的神情,小谢氏忍不住一阵咬牙。
就知道这白眼狼打的是过河拆桥的主意!
哪知就听老王妃毅然决然说道:“你们舍不得我,我难道就舍得下你们?这些年来,也多亏得你里外操劳,景儿再怎么能干,始终年轻,我又最烦这些家务琐碎,她没个长辈在旁提点,哪里就能处理得好这般复杂的人事。”
小谢氏一听这话自然欣喜若狂,又见旖景垂头沮丧,越发得意,却仍是含泪:“可二爷因着昨日那场事故,只觉得无颜再面对母亲与王爷,更觉对不住沨儿与景儿两个晚辈,就怕将来再有什么冲突矛盾……昨晚就商量了媳妇,想请旨立府置居,若是母亲舍不得咱们,等闲大可去将军府里住上一年半载,也让儿子与媳妇尽尽孝道。”
这话说得,明显是被逼无奈,担心楚王一家不肯谅解,因为江月之故心怀芥蒂,不得已才打算立府置居。
若搁从前,老王妃当然会心怀不忍,至于如今嘛……老王妃依然“不忍”:“这叫什么话,原是一家人,又什么误会当面说开就好,错在黄氏,有谁敢议论老二与你的是非?事情过去就莫再提,所谓家和万事兴,昨日之事且当教训,谨记在心,都莫再借题发挥。”
小谢氏心满意足而去,当然告之了江月,称赞她这以退为进的法子果然不错,彻底堵塞了旁人背后挑唆的路子,婆媳俩击掌而庆。
她们自然不知,老王妃目送小谢氏离开后,一把就拉住了旖景的手:“果然就像你说的那般,一字不差……我刚才那话说得可好?”
旖景也微笑着与老王妃击掌:“祖母厉害!”
☆、第四百七十三章 候府阖墙,纵容之祸
腊月初一那番兴师问罪之后,建宁候府自是铩羽而归,黄三爷自是满心不甘,他也说不出个什么由头,甚至没闹清楚这场事端的根底,唯体会到的几点是——
卫国公府仗势欺人,大长公主与卫国公不顾姻亲,包庇放纵旖景插手王府二房的婚事,害得女儿的风光大聘落空,六万两聘金呀,就被她几句话说得没了大半!
老王妃偏心,苛待庶子,主事不公,看她对旖景与江月的态度,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楚王与虞沨不顾亲族,狭隘孤寒,枉为堂堂亲王、天子信臣。
总之个个仗势欺人,当他们候府是落魄寒门么?
更气的是自家兄长,只知一昧地趋炎附势,胳膊肘子往外拐,有什么资格袭爵当家?!
一回候府,就满腹怒火地要与太夫人商量计议,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却反而遭到一番痛斥。
这当然是太夫人离开王府又见身边没有外人,才再无顾及,总算将心里的责怨暴发出来——诚然,起初江月一番挑唆本就让偏心孙女儿的太夫人将信将疑,突地又发生了“腹痛中毒”江月一口咬定无关饮食而是中了旖景的算计,更加让太夫人惊怒,压根没有细想,也不认为江月会买通外人陷害旖景,撇开护短这一层原因,太夫人也明白旖景出身显赫,又得太后顾惜,江月怎么会用这么漏洞百出轻易就被人拆穿的把戏嫁祸?
当太医与马大夫当堂对质,并验明药中无毒,太夫人眼见江月的手足无措,才不敢置信地醒悟过来是自家孙女儿的错失,可当着楚王府与卫国公府众人的面,她也只能咬着牙替江月开脱。
尽管如此,太夫人心里未必就对江月没有埋怨,自然更觉三爷对聘金一事耿耿于怀实在丢脸,愧怒加交的同时,更为江月将来处境担忧,根本无睱听三爷无理取闹又毫无意义的吵嚷,只以一场斥责了断。
三爷自从懂事以来,跋扈蛮横了大半辈子还从没受过太夫人如此严厉的责骂,只觉得天灵盖都要被怒火灼穿,回屋之后好一番发泄,怒吼声险些掀开了屋顶,惊吓得一院子的莺莺燕燕花容失色,不敢近前。
叫骂声好不容易低沉下去,三太太才敢拉着身边贴身侍候的丫鬟香蕊上前,沏茶给三爷消火儿。
一边劝道:“三爷也别只顾着发火,还该仔细为月儿打算打算,她在嫁妆上原就吃了亏,再经这事一闹,在夫家更没有立足之地,大长公主竟全不念及多年姻亲的情份,一昧只给景丫头仗势……景丫头不仅是十里红妆出嫁,兼着身份原就比月儿高上一头,在王府连将军夫人都奈何不得,瞧瞧老王妃护她都护成什么样了?纵使今日吃一些亏,又算得了什么,非逼着月儿认罪……亏月儿从前还把她当做亲妹妹看待。”
三太太没留意,连香蕊听了这话都忍不住撇嘴——有这么是非不分的人?就因为人家身份更尊贵,就容得你栽赃陷害,还拿从前情份说事儿,真顾及一丝半点的情份,这出闹剧哪演得出来?
可三爷却爱听这话,接过香蕊递上的暖茶仰头饮尽,接着又抱怨了一番“姻亲无情”“手足无义”的话,狠狠地磨着牙:“月儿也只能先忍耐着,好歹虞栋与二哥那一层关系,至少不会刁难,且让景丫头风光一时……待光禄寺少卿那职位到了手,这回定要好生经营,有秦相为靠,我还怕没有显赫的机会?别看着卫国公与楚王这时受重,风水也有轮流转的时候……只要让我得了势,今日之辱必要加倍奉还,总有把他们千刀万剐的时候。”
三太太却不无担忧:“今日这么一闹,大哥倒更卖了好,连母亲都被大长公主埋怨上了,就怕卫国公与楚王为难三爷……秦右丞与卫国公也是姻亲……三爷调任光禄寺的事不会有什么变故?”
“我连这层厉害都没想到就会和卫国公府闹翻?”三爷冷冷一哼:“这么多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的,亏得咱们候爷与老太太一昧地重视国公府这门姻亲,若卫国公真要提携,我还能是个七品闲职?捞不着一丁点的油水,日日还得去衙门里应卯,这等姻亲再显赫,巴结着能有什么用?”
三太太腹诽,谁说没用?当年翁爹老来糊涂,被人当了枪使,不知怎么开罪了秦相,被御史参得降职,受太宗帝疏远,一气之下中了风,让大哥袭了爵位,终究不如高祖帝时得用,若非老国公苏庭提携照顾,大哥只怕也就是空顶着个候爵,还能入了兵部?更别说眼下卫国公仍得信重,荐了大哥任大理寺卿真真就是轻而易举,只不过人家只提携长房,看不上咱们三房罢了,也不怪人家,姻亲到底隔了一层,候爷还是自家手足,都没有半点提携,反而是对龙家姑爷,废了多少心思才将人调回六部?
真是亲疏远近不分,三爷才和他是一母同胞呢。
又听三爷信心十足说道:“右丞和卫国公府虽是姻亲,不过就是个庶女嫁了庶子,能比得四皇子更加牢靠?四皇子才是右丞正经的女婿呢!二哥眼下又是四皇子的人,殿下开了。,右丞哪还会搭理卫国公,光禄寺连调令都下来了,就等着吏部出道手续,虽卓尚书和卫国公是一党,也不敢当真为难我,他就不怕得罪了皇子?将来说不定是哪个能得皇位!这些个奸官心思活泛着呢,谁不是见风使舵,哪能将事情做绝……光禄寺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今后可得仔细笼络好秦家,总有我扬眉吐气痛打落水狗的时候!景丫头敢折辱月儿,这笔帐我得记下,将来连本带利一起讨还!”
三太太也听得意气风发,冷冷笑了一阵,须臾间又担忧起来:“三爷还是管管四郎,一昧就听他大伯的话,窝在书房里头读死书有什么用,咱们公候之家,难道还能好比那些寒门般指望着科举?他已经是监生,正该和权贵家的子弟多来往来往,他倒好,固步自封不说,听说还在国子监同人为了什么策论争执起来,岂不是白白得罪了人家。”
又是唉声叹气:“当初就不该听嫂子的话,给四郎娶了个什么书香门第的媳妇,若搁这会子,秦相还有几个孙女待嫁闺阁呢,未必做不成亲。”
三爷又是一阵埋怨,直斥四郎不长进,儿媳又是个不通转寰的,右丞夫人身边有个得用的婢女,到了年龄想放出来嫁人,那婢女眼界高,瞧不上家奴管事,右丞有回还提了出来,让帮着在外头寻个富裕人家,秦相多大权势,还找不到这样一户人家?无非就是暗示罢了,纳回来给四郎做妾有多合适,偏偏儿媳规矩大,说什么纳别家府上婢女为妾不合礼规,再者她进门不够一年,也没到纳妾的时候,什么书香门第的闺秀,真真是个不知体统的妒妇。
四郎只帮着媳妇说话,竟然敢忤逆父母!
都是得他大伯的挑唆,是非不分的东西,十多年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两夫妻你一声我一句的抱怨,压根不在意这些话全进了香蕊的耳朵。
于是当天,话就传到了建宁候的耳里。
三太太是庶支出身,当年也就带过来四个陪嫁丫鬟,有两个根本就不得用,显然是临嫁时才找来凑数,十五、六岁就打发出去嫁了小厮,又有两个倒是贴身侍候的,尽都被三爷“收入囊中”渐渐也就与三太太成了相互忌防的妻妾关系,再不能信任。
香蕊还是后来调来的三房,本就是候府的家生子,身契捏在候夫人手里,再兼着三房这两位又不是明主,对丫鬟奴婢从来都是呼呼喝喝,打赏少得可怜,建宁候一说要香蕊当耳目,甚至不需要用金银买通。
可笑的是三太太还给香蕊画了个大饼儿,说什么好好侍候忠心事主,将来少不得她的好,意思是要给三爷开脸做了通房,就以为香蕊对她会死心踏地。
别说香蕊压根没有与人做妾的主意,眼看着三爷待那些姨娘,新鲜劲一过,丢在一旁死活不问,三太太虽还算贤良并不多妒,不会阴谋害人性命,可实在狭隘孤寒,姨娘的月例银都克扣着不发,公中按例发的四季衣裳也被“截流”眼下还活着没病死那两个,可怜沦落至衣无二件的境地,还不如候夫人身边一个三等丫鬟光鲜。
若为此就死心踏地,脑子是被水煮了吧。
又说建宁候,听了三爷的话气得目瞪口呆,尤其那些“千刀万剐”“痛打落水狗”的恶语,这哪还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简直就是生死不容的对头,他可不以为三爷只是嘴上发狠,当了几十年的兄弟同住屋檐下,彼此性情也都清楚,三爷自私阴毒、睚眦必报建宁候早有领教。
当初太夫人身边有个侍女,一早是准了给四爷,哪知被三爷看中了眼,求了许多回,无奈那侍女本身不愿,太夫人到底顾及许多年的情份,也不愿强迫了贴身丫鬟,只这情形,再给四爷当然不再合适。
于是就把那侍女指了个管事,放出去备嫁。
三爷便恨上了侍女不知好歹,跳着脚的发誓要让她不得好死。
那时三爷年才及冠,太夫人与建宁候且以为他争强好胜一时觉得没脸才嘴上发狠,并没上心。
哪知三爷竟真闯去了侍女私家,把人掳了出来,欺凌侮辱一番,坏了人清白。
太夫人气得个绝倒,见侍女要寻死,生怕张扬出去于家声不利,到底还是趁了三爷的愿,把侍女给了他。
没过多久就被三爷捏了个把柄,大冷天儿的罚着在院里跪冰盆,侍女到底受了寒,病得起不来身还被三爷着人抬去庄子里头,喝令不让请医,生生病死了。
太夫人与建宁候知情时,侍女已经被卷席子裹着扔到乱葬坑。
建宁候自此对这兄弟灰心丧意,连个婢女都不放过,如此心胸,还指望他将来能成大器,为家族繁荣助一臂之力?
不过从前三爷到底还能做到“兄友弟恭”至少在家人亲族面前不会这般跋扈蛮横,建宁候哪能想到三爷竟对他这个长兄心怀怨恨,都到了恨不能千刀万剐的地步。
看来三爷这回是笃信有黄陶撑腰,攀附上秦相与四皇子为靠,又认为江月嫁入宗室风光显赫,彻底地有恃无恐,再不愿忍辱吞声。
此隐患必成大祸!
建宁候也是重重一拳头擂向几案。
☆、第四百七十四章 试探得因,总算决断
平安坊一处酒楼的雅室里,即使是到了寒冬腊月风霜雪雨的时候,因为铺设着烟道,也自温暖如春,轩窗上糊着透亮的白桑纸,窗边上坐着景泰蓝的美人觚,插在里头的几枝寒梅半开半含,已有暗香沉浮蕴漫。
一桌子佳肴美馔,桌旁三人却肃色围坐,气氛实在与一室暖香格格不入。
建宁候举盏而饮,又将空盏重重一顿,他正好是临窗而坐,可透入的天光仍是驱散不去眉目间的阴霾。
卫国公与虞沨对视一眼,心下不约而同暗忖,只怕是候爷依计试探后,那结果当真一如预料。
就听建宁候说话,低哑的语音里甚至带出了几分沉涩的哽咽:“沨儿早说老三是隐患,早晚会给候府引来大祸,劝我莫要心慈手软,彻底废了他的仕途……我总归顾念着他与我一母同胞,就算听闻那些锥心刺骨的恶语,还不忍心……自从听说老三与老二早有勾结,想着五娘,我是怀疑老三父女下的手,可没有实据,到底是血缘至亲手足同胞,总不能凭着蛛丝马迹的猜疑就坐实他的罪名,行手足相残之事。”
原来就黄三爷的“处置”三人已经商议过多回,卫国公因是姑爷,并不便太多插言,虞沨却直言不讳,指出黄三爷狭隘阴狠,若不彻底断绝他的仕途,让他再不能兴风作浪,将来必成隐患,可建宁候始终有些犹豫,到底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想着五娘的事并无实据,万一冤枉了三爷……仍偏向于搅和了三爷这回调任的事便罢。
月初一场闹剧,建宁候又听了黄三爷那番恶语,才觉得心肺俱冷,三人又碰头商议了一番,建宁候始终难下决断,还是虞沨提醒——即使黄五娘的事难察实据,可三爷夫妇头脑简单,眼下黄江月已嫁,他们连个商议的人都没有,其实只需一二试探,让他们露出马脚不难。
就算不能因此把他们送去衙门依法定罪,建宁候一旦确定三爷是五娘“恶疾天折”的帮凶,也再不会有任何顾及。
三爷与江月心狠手辣至此,全不顾及血缘亲情,建宁候若再心慈手软,养虎为患,必然引火焚身累及全族。
趁着已是腊月,离新岁不远,各府名下的农庄田户都要赶回主家对帐纳产,自然少不得管事仆妇从郊野赶回,奉供收成的粮米蔬果,建宁候知会下去,有意让五娘从前的侍女,那个收了黄江月送去的衣裳,首当其冲患了痘疹,却饶幸逃生名唤青梅者随着管事归府。
青梅得了叮嘱,有意“买通”三太太身边管理衣裳钗环的香蕊打听,把当时收下的几套衣裳形容了一回,问香蕊可曾留意果然是三太太日常穿着的衣裙?
香蕊自然把这事禀报了三太太:“隔了多久的事,青梅还念念不忘,奴婢只觉得孤疑,问她才知,原来是六娘还惦记着,又遣了人专程去农庄里头问她。”
三太太唬得心头乱跳,忙问香蕊怎么做答。
“奴婢哪还记得,不过因着往日当差仔细,太太的衣裳钗环哪些赏了人都记在本子上,却没先答允青梅……总归太太怎么嘱咐,奴婢就怎么答复。”
结果三太太二话不说就逼着香蕊交了记录,并叮嘱她回应青梅,就说察了本子,衣裳果然是太太穿旧了闲置着没用,后来才赏了下去。
当晚三爷喝了花酒回来,三太太便让香蕊守在门外,两个在屋子里嘀咕。
香蕊得了这机会,光明正大地听了墙角。
“六娘总盯着这事不放,我心里总不安稳,要说当年那事……你我都被瞒在鼓里,也不知二哥是个什么用意,拿了那盒子衣裳来,还用几层棉布包得严实,只交待让月儿收着,等时机合适再交给五娘的丫鬟们……还是月儿聪明,就想到那衣裳不对劲……后来五娘得了痘疹,月儿才叮嘱我千万别说漏了嘴,我才知道这衣裳上有疹毒……月儿主意大,也不知怎么反而拿捏住了她二伯,诈了千余两银,还争取她二伯搭桥牵线,攀附上宗室……只眼下六娘还不罢休,都隔了多久了,这该怎生是好,月初又才闹了事,我也不方便再去寻月儿商量,要不二爷与她二伯碰碰头,商量个一了百了的法子出来?”
“一个出了阁的丫头片子,能折腾出个什么花样来,你那样处理就不错,怎么一了百了,难不成还能灭了六丫头的。?任她折腾吧,不过得给二哥叮嘱一声,免得他那头再出了纰漏。”
话传到建宁候耳里,简直就是五雷轰顶!
次日果然发现三爷去了外城找黄陶“碰头”。
“再无可疑,再无可疑!果然是这几个狼心狗肺、猪狗不如的东西,枉我还顾念着手足亲情!当年六丫头就怀疑……我还责骂她疑神疑鬼……三弟妹好个贤良妇人,害死我一个女儿不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