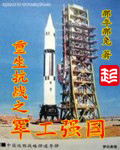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3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倒不是说太后有多看好太子,但太后重嫡,而太后身后的严家又与大长公主息息相关,是大长公主的母族,卫国公的外家。
眼下卫国公一府已是极盛之势,再兼苏明高中探花,当真是烈火烹油。
“圣上之意,必是要争取国公府助力,将来在废太子以及奠定新储一事上竭尽全力,如此,咱们说不定先就得与太后、严家为敌。”大长公主越发沉声:“就算能规避这点,储位非嫡非长,便当立贤,可贤之一字哪有固论,诸皇子必会手足相争,苏家嫡长女是福王妃,可福王显然不得圣心。”
大长公主并没有说明,其实她也看出圣心是在三皇子身上,可仅有圣心,还不足以让三皇子坐稳储位,四皇子势大,五皇子也不弱,德妃一族不容小觑。
那时让旖辰嫁给福王,也是天家之意,意在稳固与卫国公府的联系,着手铲除金逆,改革官制,但时过境迁世事变移,涉及储位之变,就连与世无争的福王因为身后有卫国公府,不可避免也会卷进储位之争。
相比卫国公府,楚王府是宗室,无论远近亲疏眼下都更得圣上信重,两家虽是姻亲,可一旦涉及国政大局,出难以做到确实的“心心相映”至少在天家与世人看来是如此。
所以,天子为了更加稳固与苏家的君臣之义,有意提携苏明。
就此一来,卫国公府不但有勋贵之荣,甚至成为将来新兴势力之首,权势威重,就必须做出选择。
“儿子认为圣上并未给咱们选择的余地。”卫国公说道:“要保福王不受波及,家族尊荣居安,必须遵圣令行事。”
三爷苏轹表示赞同:“可四弟这回高中探花,不待圣上提出废储之议,几个皇子身后的助势就会对四弟起拉拢之心。”
事情很显然,苏明到底是庶出,还是“忽然入籍”世人鲜少会认为苏明与大长公主几个嫡子真能做到一心,卫国公三兄弟无疑会被划为福王一党,苏明倒未必不能拉拢。
“福王暂时不提,我认为咱们也该布布迷障,示忠只对圣上即可,团结一致更不用向外人展示,一来也是留条后路,二来是替圣上行棋试探,以备将来废立所用。”三爷又再说道。
卫国公与苏轲都表示赞同。
虽然苏家忠心可鉴,但自保也极为重要,要留后路,就不能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提篮里,这必须得掌握好火候,一来要保持圣上的信重,不至真让圣心生疑,二来在旁人眼里,苏家的态度还要维持暧昧,不让一眼看穿。
“今日四弟高中探花,咱们却没有立即大庆,便已经走出一着。”苏轹又说。
大长公主颔首:“老二,这话得借着你媳妇的嘴张扬出去,就说我的意思是顾忌盛极必衰,故而叮嘱了霁和让他略有保留,哪知中了探花,我有些不喜。”
至于让利氏张扬给谁,在座诸人都心知肚明。
“当然,霁和既高中探花,卫国公府当然要行宴为庆,这点表面文章还是必须做的。”大长公主又说。
☆、第五百五十四章 归人在途,又遇故旧
远瑛堂议计一定,黄氏很快就在与利氏“闲聊”时听说了大长公主的不喜,利氏尚不知自己的头脑简单口舌发达是被人利用,所以黄氏并没发现蹊跷之处。
回到和瑞园后,她倒是冷笑起来——就说婆母没有表面这般“宽容豁达”无非是见着苏明师承大儒,官制又经改革,必能通过科举入仕,于是展示姿态允他认祖归宗,一来也是怕引发闲言碎语,有这么个庶子明晃晃地存在,瞒得了一时还能瞒过一世?二来干脆让苏明入族,尊她为嫡母,将来也好把控。
可不,苏明这回阳奉阴违,真中了个探花回来,大长公主就有些摁捺不住了,非但没有好比旁家那般庆祝,人一回来,就拎去远瑛堂教训了一回。
这事,该给四皇子支应一声。
黄氏拿定主意,却没有亲自往四皇子府,而是打着去看望江月的名头,让江月前往讨好。
她也是无可奈何,自打对门老王妃生辰之后,自家嫡母让人来请,没头没脑地训斥了一场,让她这个做姑姑的要多为江月打算,别一昧地偏心旖景。
“景丫头就是你婆婆的眼珠子,身后有整个卫国公府撑腰,嫁去王府,又成了老王妃的心尖尖,更别说世子对她的纵容,不需要你这个继母为她打算,也能在王府横行,唯独可怜的是月儿,父母是倚靠不住,你哥哥还得仰仗苏家与楚王府争取圣眷,在将军府面前不能挺胸抬头,就你这个当姑姑的,堂堂国公夫人,便是常常去将军府走动着,月儿日子也好过着些。”
黄氏就知道,上回威逼不成旖景,江月这个难摊子得落在她的头上。
一为耳根清静,二来也为江月眼下与旖景是势成水火,黄氏当然会维护几分。
于是江月这回终于见着了秦妃,把这事情一说,情谊总算是又重新联系上。
接下来卫国公府的门槛就险些被上门“道贺”的人踏破,固然有的是出自真心,极大多数都在转弯抹角地打听四爷苏明的婚事,又有极大部分明里暗里都打着“四皇子党”的标签。
不过其中也不乏五皇子、六皇子,甚至七、八、九几个的母族或者拥趸。
甚至严家也闻讯而来。
他家倒没尚且待嫁并且适龄的闺秀,就算有,也是和苏明差着一辈儿。
严夫人是真心提醒大长公主:“听说婚事是先过了小定……公主可别怪晚辈多嘴,实在已经听见些人背后嚼牙,说您若真为庶子打算,哪会赶在会试前定下个并非显赫的姻亲,若是等霁和高中探花,即便是庶子,也配得高门望族的嫡女。”
大长公主一脸正色:“我行得端坐得正,不怕这些人诋毁,已经是和林家过了小定,难道要背信?霁和是庶出,年龄也过了三十儿,若非高中探花,哪家高门望族愿以嫡女相配?林家女儿温柔贤惠,又知书达礼,出身是差着些,品貌足以为配,我苏家虽为勋贵并非世家,也做不出背信弃义的事。”
自然也有人借着饮宴喝大了舌头的机会,把这些嫌话“吹”进苏明耳里:“虽说过了小定,可没过大定作罢者也不算少,霁和眼下可不比当初,多少名门等着嫁女儿给你,可惜都是失望而归……林家无势,就算退定,难道还会与卫国公府理论不成?唉,霁和可是将来天子信臣,若得了门强势的外家,前途不可限量。”
言下之义,无非就是嫡系打压庶出的手段。
苏明自然不以为意,但因为他没有反驳,那些人且以为计策达成,更兼着四皇子举办文会,苏明赴会,与四皇子十分投契,更让这一党看到了无限希望。
四皇子一边笼络苏明,还不忘把心思用在顾于问身上,他虽是寒门出身,却有韦相这个岳丈,更高中状元,自然也是前途无量。
于是顾于问有回赴宴,多喝了几杯,当晚被四皇子殷勤挽留,歇在了皇子府。
迷迷朦朦地睁开了眼,见着的是窗纱外微晃的灯火,夜至深沉。
顾于问将将坐起身,便有一双手托着白玉盏递上。
新科状元一抬眸,瞧见的是一张让他大惊失色的容颜!
这一晚接近子时,四皇子尚且没有安歇,而是在书房里接见了冷汗淋漓的顾于问。
“殿下……微臣……”才华出众的状元郎竟然说不出句囫囵话来。
四皇子长长一叹,起身,拍了拍顾于问的肩头:“见着人了吧?你也太大意了些,盘算着瞒得了一世?亏你也是东明世家子弟,就算家境落魄贫寒下来,也不该把事情想得这般简单,葛氏虽是农户家的女儿,却是你的明媒正娶,侍候着你父母双亲多年,二老过世,她又披麻守丧,你以为把她困在乡下,让两个旧仆看着,就保万全?山长水远就没人能听得见半点风声?你这可是停妻另娶,若张扬出去,功名都保不住。”
正如四皇子所言,顾于问原是东明世家之后,因没能得秦家招拢,大隆建国后就渐渐远离朝堂、家业凋零,他是家中独子,摊上个病弱的父亲,为了保命将田产折腾一空,不幸又遇火灾,好容易逃出性命,安身之处却被付之一炬。
那一年祖籍陇西大旱,族人自身难保,再难周护。
于是顾于问便随父母南下,投靠舅舅一家,分得薄田靠耕种度日。
顾于问自幼聪慧,也跟着家族里略微昌盛的族亲蹭了几年学堂,不甘就此默默,于是干脆收拾行装拜别父母,打算投拜名师搏个将来,也是他的命数,其才智志气被魏望庸看中,收入溟山书院。
若待学成,有魏望庸荐书一封,入仕也算顺畅,可惜顾于问因为家境之故“急功进利”入学两年后就把心思花费不少在结识冀州当地权贵望族身上,趁闲常陪着纨绔们花天酒地,有回卷进了斗殴事件,进了一回衙门,还是书院出面将他捞了出来。
魏望庸大失所望,将顾于问逐出。
有两年顾于问又过上了漂泊的日子,后来结识了四皇子府的幕僚,投靠了四皇子,他吃过浮躁的亏,行事就谨慎下来,好几回暗暗出谋划策,得了四皇子赏识,却并不愿称功,甚至不愿公开与四皇子府的来往联系,表明可为四皇子暗探。
于是就被安插在了韦相府中。
“殿下,葛氏原是难民,孤苦伶仃到了微臣少年时栖居之地乞讨,当时家父病弱,家母一来是因为怜惜葛氏孤弱,二来有她相助家事,也算助母亲一臂之力,原是当义女抚养……后来家父家母也不知怎么打算,竟瞒着微臣娶了她……微臣于她虽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顾于问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婚姻之事可是以婚书认定。”四皇子摇了摇头:“我理解于问,好容易谋了个前程,自然认为葛氏毫无助益,唉,她远在岭南,又非得你心意,你不把当她为妻也是情理当中,我并不怪你隐瞒着我,再者你被韦相看重,成了他的东床快婿我也乐见其成,罢,葛氏我替你收留皇子府,也免得有心之人捏住你的把柄。”
很显然,四皇子是担心顾于问得了锦绣前程心生二意,把葛氏握在手里,以此作为要胁。
与此同时,已经送亲归来抵达并州,与三皇子商议之后顺便去了趟郫南,想看看当年遭灾受疫之地眼下如何的虞沨,也正在县城驿站里,将刚刚到手的一封信函凑在了烛照上。
铜洗里一团火光,将信函渐渐卷没,顾于问的名字化为灰烬。
在另一个房间,穿着一身鸦青长衣的妖孽皇子,正挑眉斜睨着榻前膝下匍匐在地的女孩儿。
灯火下,穿着一身粗布衣裳的女孩儿抬起面孔,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两眼泛红,却强自摁捺,没有流下泪来。
“殿下哥哥,你真的是殿下哥哥?”女孩儿似乎不敢置信。
一边的薛东昌因为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再一次摸了摸鼻梁,他实在不明白,三皇子今日去县衙饮宴“净房”途中正巧遇见这个丫头,当时就叫她候在原地,然后暗中开口找县令讨要在手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
而眼下看来,这个十岁出头的丫头竟是旧识?
“盘儿是吧。”三皇子缓缓开口,薛东昌依然不明所以。
“是,果然是殿下哥哥,世子哥哥可也一同前来?”盘儿眼睛里灼灼发亮。
世子哥哥?!薛东昌依稀对这称呼有了几分耳熟。
“她没有来。”三皇子微卷唇角:“我且问你,你为何到了县衙为仆?”
盘儿突地“爆发”直起腰身:“上任胡县令是个狗官,我爹爹服役,修筑河堤时失足落水淹死,他竟看中了我娘,起初还装模作样,说什么怜惜孤儿寡母,照应我们母女……我娘不防其他,想着爹爹一走,家里没了劳力,一年耕种所得堪堪能抵赋税,不如与县令签了活契,还能落个温饱,哪知狗官竟逼我娘……我娘不丛,却抵抗不过,被狗官强占了身子,一头撞死了……狗官只说我娘自己想不开投了井,我起初原也不知真相,后来狗官调任,县衙里的陈嬷嬷才敢告诉我实话,我想告官,求现任县令为我娘伸冤,陈嬷嬷拦住我,说官官相护,我闹出来反而会获死罪。”
三皇子颔首:“陈嬷嬷的话不错,你说你娘是被逼迫至死,却无凭无据,以奴告主,先就得受杖责之刑,就算没有官官相护之说,也不能将胡县令绳之以法。”
盘儿目瞪口呆。
“你可愿跟我去锦阳,若你今后做了皇子府的奴婢,我答应必能要了那狗官的性命,也算为你报了杀母之仇。”三皇子悠哉游哉开口。
盘儿呆怔了好一歇,才如梦初醒一般,匍匐在地重重磕起响头。
“让人把她好身安置。”三皇子大手一挥。
薛东昌去而复返后,仍是满脸的疑惑:“殿下,收着这小丫头可有何用?”
三皇子整个人彻底斜倚了软榻,微咪眼角:“没用,举手之劳罢了,我有时也会发发善心。”
薛东昌:……
“狗记性,还没想起来,上回咱们在郫南村庄遇险,广平郡主就是被这丫头拉着去了她家避险。”三皇子揭开谜底。
薛东昌才总算醍醐灌顶:“属下哪有殿下过目不忘的本领,不过依稀记得‘世子哥哥’四字耳熟。”心下却想,难怪殿下发了善心,原来又是与那位有关,但也不过就是一面之缘而已……殿下还真是有走火入魔之嫌。
三皇子像是洞察了薛东昌的心里话,眉梢一扬:“我与这丫头也算有缘,若非她家里备着弓箭,让郡主顺手救急,说不定那日真会中了老四的毒手……东昌,待这回归京,就得开始计划,那个狗官胡县令你可记得?”
薛东昌一脸莫名其妙。
三皇子长叹一声:“他是老四的人,我手里收集的罪证就有他的一份,正烦恼挑谁下手,正好遇见这事,就是他了!”
三皇子又一挥手,打发了薛东昌离开,却忽地像长了精神,从软榻翻身而起,两步走到靠窗设置的长案边,挥笔书下“胡世忠”三字,盯着龙飞凤舞的书法看了好一阵,待墨迹初干,这才将纸一把扯起,凑于灯火点燃。
☆、第五百五十五章 掌家主妇,恩威并施
已经被薛东昌遗忘的胡世忠,在并州水患之前,实际上任着的是直隶香河县令,没错,就是那位与四皇子府陈长史很有几分交情,同当地富甲李家更是莫逆,引荐了孙孟成四皇子府的幕僚,间接造成与世子妃甚是相似的倩盼姑娘与李氏大娘进入三皇子府的关键人物。
远庆六年秋,并州水患相隔一年,疫情早已平息,遭洪涝泛滥的两县村庄业已重建家园,灾区百姓正当休养生息,定河高段的泄洪滩涂尚未完建,因为复建有功,原郫南、汤县县官在吏部考核期大受朝廷表彰,都升官调任。
陈长史便为胡世忠求情,通过四皇子背后操作,将此人调任来郫南接任了县令。
当然是为了攒积政绩,虽郫南民居田园复建已毕,但上流泄闸与沿岸河堤尚在修筑,又兼着朝廷免了受灾之地百姓三年赋税,郫南县令只需监管好水利筑建,两年间让当地民众温饱无忧,政绩就张显出来——谁让朝廷尤其重视两县灾区的民生。
那场水患引发的灾难当年闹得沸沸扬扬,工部官员自是不敢再疏忽水利筑建,其实不需严加监管,没人胆敢吊以轻心。
于是远庆七年,当上流险段防洪泻闸工程完工,低处河堤筑建坚固,并州定河沿岸顺利渡过洪汛期并未遭灾,胡世忠轻轻松松就赚得功劳,又因为四皇子有心提携,秦相党羽从中操作,盘儿口里的狗官胡县令竟升任了建昌知府,今年五月业已赴任。
三皇子早从倩盼李大两姑娘这条线索,察得胡世忠和四皇子的联系,对这人摸察了一番。
那时南浙官员未被打击之前,大隆官场整体风气实在不算清明,香河是直隶,胡世忠虽不敢有如南浙官员般贪婪张狂,区区县令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强夺民财,索贿贪赃,但是这位狗官好色,并且有个独特的癖好,专好风韵成熟之妇,而不喜青涩少艾。
达官望族的贵妇们胡世忠当然不敢觎觑,便将目光盯在了丧夫守寡的民妇身上,好比盘儿她娘的遭遇,早早不算首例。
可胡世忠行事还算稳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留下什么把柄,便似盘儿这般,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不知生母死于淫威,而仅凭县衙那个官奴陈嬷嬷的空口白牙,自然不能治堂堂从五品地方要员的重罪。
但只不过,若系小人得志必猖,胡世忠自打升官到了建昌府,警慎的作风就有了变化,三皇子挑了几个与陈长史关系甚笃的地方官重点监督,胡世忠就是其中一人。
此人刚刚得到提拔还不及贪赃,却忍不住好色,这回他瞄上的是一个工匠之妇,丈夫未丧,于是便造祸陷害,判了工匠一个窝赃之罪处以徒刑,将人在牢狱里活活折磨至死,如愿强占妇人,逼良为奴,这妇人倒没有盘儿娘那般贞烈,尚且忍辱偷生,对胡世忠十分谄媚,眼下已经坐稳了姨娘之位,甚是得宠,依三皇子看来,此妇是楚心积虑在打消胡世忠的戒备,期望能收集他害死丈夫的罪证,当时机合适,替夫申冤。
因为妇人已经暗暗联络上丈夫生前好友——某家境贫寒的文人,常受工匠夫妇接济,因这回复兴科举,顺利通过童生试得了秀才的功名,可惜未能通过乡试,但身份上已经得到提升,眼下受聘于一户乡绅,做了几个童子的开蒙先生,也在准备三年后再下考场。
三皇子手里当然还掌握了其余几个四皇子党羽的罪证,正犯选择性障碍,一时没定找哪个下手。
理论上来讲,逼良为奴强占民妇的罪行不如贪赃私昧严重,又因受害人地位卑贱,操作起来诸多不易,并且就算整治了胡世忠,也实难从根本上打击四皇子。
不过妖孽的思维不同旁人,正好又与盘儿巧遇,倒让他瞬息拿定了主意。
那工匠之妇凭一己之力想要扳倒胡世忠实在有若蚍蜉撼树,但三皇子若要暗中相助,这事就并非异想天开,胡世忠这回有栽赃陷害之举,当然会留下把柄,更何况他的一言一行已经有人暗中盯梢。
至于怎么和四皇子一党扯上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得创造机会了。
次日,三皇子起了个大早,在登船之前,先就喊来了薛东昌,一一交待他晚间半梦半醒之际临时拟定的计划,立即嘱咐底下人实施。
这时水路通畅,因三皇子虞沨一行特意拐来并州,干脆就走了定河,不经通州港,直接就到了白沙渡,三日后抵达京都城郊时,正是卯初,天色未亮。
及到广宁门时,内城尚且不到解禁时候,一应浩浩荡荡的随扈不能靠近,唯三皇子、世子两人车與同规制定数范围的亲兵得入外城。
世子到了祟正坊的楚王府,才将将及到卯正,晨钟未响。
车與直接到了关睢苑门前,世子下车,且以为世子妃仍然未醒,哪知一路到了中庭,却见还显苍茫的晨蔼笼罩下,檐下廊间灯火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