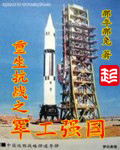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再许芳华-第4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再怎么能,也不能够短时之内便在陈夫人身边安插暗人。”虞沨垂眸,这话倒也不假,庚帖遗失、传言四起之前,他其实也并没将对手这桩挑唆之计放在心上,更不可能未卜先知早早在陈夫人身边布下眼线:“今日我追问了陈参议,有此推断而已。”
便说了六娘庚帖不翼而飞的始末。
“在场唯有那婢女与安慧,庚帖是放在锦盒里,婢女从柜子里取出之后,放在就近的妆台上。”虞沨大至说明了一下陈夫人房中妆台与锁柜的位置:“婢女接下来,肯定是要锁上壁柜,她一转身,安慧便能趁其不备打开锦盒,将庚帖藏入袖内,然后惊呼盒内空无一物,婢女惊慌,自然会去柜中翻找,安慧大可趁此时机将庚帖暗藏犄角旮旯,抑或干脆趁着让她的婢女去外传话请回陈夫人时,将庚帖藏于院中。”
“那婢女管着钥匙,一旦庚帖不见,势必最大嫌疑,她再怎么愚蠢,也不会被人收买行这显而易见之事。”旖景也分析道。
虞沨颔首:“安慧自知婢女无辜,势必料到她会反咬,可安慧一早将庚帖转移,是以,故作光明磊落地让陈夫人搜身,陈夫人应当不疑安慧,当搜身之后,更加笃信,一时也只会将注意力放在婢女身上,安慧大有时机将庚贴转移,估计已经销毁,因为从一开始,庚帖不是关键,之所以不见,是为了造成祖母怀疑陈夫人借故不还,进而怀疑太皇太后背后指使。”
旖景咬牙:“当初安慧说了那番话,我只以为她当真不怀恶意,哪曾想她会与旁人勾结。”
虞沨摇头:“安慧智计不足,这回很有可能是被利用,她这时安稳荣华皆靠翁姑庇护,应当本意不在让长房受损,她应是真心想为陈夫人解忧,并不料对方目的是让长房与卫国公府生隙,我猜,安慧自授把柄于人,今后势必会再受胁迫,她一定焦头烂额,六妹妹轻易一诈,不难逼出真相,安慧跋扈惯了,六妹妹捏着她这么一个把柄,她不得不服软,毕竟这事,只有六妹妹不追究,安慧才不会被人要胁,今后六妹妹足以让她俯首贴耳。”
六娘嫁入陈家尘埃落定,庚帖的去向自然无足轻重,但安慧做了这桩祸事,利用她的人一定会要胁她在关键之时受其所用,否则安慧已无娘家倚仗,再失了翁姑的庇护,在陈家不能立足,但安慧即使智计不足,也晓得与旁人勾结不利长房今后也只能落得个兔死狗烹,唯有六娘宽恕,才能为她求情转寰,倘若六娘落井下石,安慧处境可想而知,有了这个把柄,她在六娘面前再难跋扈。
至于六娘是要宽恕,还是要落井下石,全凭心情。
“而我们要留意的是,也许不待六妹妹大婚,对方就会再有阴谋诡计。”虞沨以掌覆案:“此事就算果如对方预料,能让国公府与慈安宫生隙,还远远不达反目成仇,我猜,接下来严家会有祸事,而这回陷害严家的人,只怕与国公府息息相关。”
☆、第六百八十九章 凤阳来人,刁难候府
傍晚时分,永昌候府的角门外,车與垂帘挑起,神色郁卒的中年男子躬腰而出,他才刚刚进门,就听迎上的仆从禀报,候爷请他立即往书房。
这男子正是当今翰林院学士严昶久,而他之所以郁卒的原因,则是今日太皇太后诏见,便得知了苏、陈两家联姻之后,全是太皇太后的无可奈何,尤其当太皇太后诏了大长公主入宫,苦口婆心地解释了一番当日六娘在圣上跟前亲口表达情愿嫁入陈家,圣上当即决意趁热打铁,她完全找不到借口反驳的苦衷时,大长公主淡淡一句“我一直明白五嫂的苦衷”再不肯多提这茬。
太皇太后大是苦恼——她为陈六郎说情在先,结果后来又闹出陈家“出尔反尔”交还不了庚帖,钦天监官员女眷“说漏了嘴”引得传言四起,诏见黄氏母女当日便即赐婚,别说大长公主会怀疑其中猫腻,便是太皇太后自己都觉得百口莫辩,她很晓得几分大长公主的性情,倘若不存芥蒂势必直言不讳,这番不冷不热的态度足以说明已生隔阂了。
严学士今日也尝试与卫国公沟通,卫国公倒也没说什么,但态度远不如从前热络,显然也有介怀,苏、严两家也可算通家之好,多少年的情份,不想还是逃不过被人算计这一场。
严家两个子侄身上的罪名仍未洗清,虽有陈参议牵头部分言官力保据理力争,那些针对严家的抨击仍然摁捺不住,在这关头,卫国公府再与严家疏远的话,无疑会影响一批勋贵世宦的态度,严学士怎能不郁卒?
他且以为父亲今日这般焦急的请他去书房议事也是为了怎么挽回与苏家的关系,一路上就将那些个想法理了一遍,自己都觉得没有把握,因此愁眉苦脸一直维持到了礼见时,刚一直身,却见父亲也是一张愁眉苦脸,甚至暗带焦灼。
永昌候衣袖一甩,指着椅子让儿子落座,自己却负手来回踱步,好半天才组织好言辞,摁着书案支着身子,语气沉肃:“今日有个生人登门,自称是打凤阳府来,门房见他连名帖都没备,态度又显倨傲,只回禀了管事,哪知这人声称能救严家于水火,闹着要见我,管事的拿不定主意,只禀了一声琼儿,那人眼见琼儿只是个后生,竟只甩下一句知道曹大的下落就扬场而去。”
“这人知道曹大的下落?”严学士大惊。
“能说出曹大,势必是知道些内情者。”永昌候长叹:“琼儿到底年轻,虑事不细,见那人狂妄自大,且以为是打算讹诈钱银,非但没留人,甚至没问人名姓在哪落足,更没着人跟着。”
严学士大约也晓得自己的长子文人清高楞头青的脾气,也跟着叹了一声,沉吟一阵说道:“这人既有意接触,势必还会再来,儿子会嘱咐门房不可怠慢,若此人真晓得曹大的下落,廷益的冤屈便有望洗清了。”
严廷益是昶久的堂侄,原本是在凤阳下辖滁州任着判官,正是这回被人弹劾“贪赃枉法”者,起因是滁州两户商贾因为商事纠葛,闹得纵火伤人,案子本来简单,严廷益没费多少功夫就审结,判了凶犯死罪,移交刑部复核,哪知竟忽有被告一方去凤阳状告严廷益收贿循私,污陷良民,也不知从哪儿找的人证,一口咬定严廷益与原告暗中来往,甚至打探仔细原告曾给了严廷益确实数额的贿款,金额清楚,便是存于哪家银号汇票私章都一清二楚。
这时市面上不凭印鉴只依票据兑换的银票面额不大,一般大桩款项都得凭借存款者与银号事先约定的私章才能兑取,“收买人命”的贿款万万不可能只有三、五百两,故而行贿者一般不会采用银票而用汇票。
提刑得了检举,立即着手调察,严廷益自认无辜,但却被人在他府中搜检出了罪证——正如检举者言,汇票金额与私章无一差错。
这下严廷益百口莫辩——汇票与私章是从他府上搜检出来,但存放罪证的箱栊却并非他的物品,而是严妻娘家一个族亲,原本也在涂州下辖县城任着县令,因为到了任期,需回京等待调令,有几箱子书籍不便带走,暂时存放在严家,严妻是个警慎人,当时也让管事仆妇开箱一一验看,并拟好单子,加了封锁。
两家本是亲族,纵使为了财物纠纷,当面拟定清单落锁封存已算慎重,万万不会一本一册的翻看,但罪证偏偏就是压在了其中一箱书籍底下!
曹大正是严妻族亲家的管事,存放箱栊是由他经手送来,案发后,严妻族亲自然也被波及,一问之下,那曹大却已不见人影——安排好府中物什保管后,并没如约往京都与主家汇合。
虽然严学士一党的言官咬定是有人有心栽赃,不过曹大这个主要人证没有落网,严廷益的嫌疑始终不能洗清,就算太皇太后力保,眼下还暂且被免职待审。
这案子不结,严学士始终有“包庇族人”“治家不严”的诟病,尽管不算大罪,一但定论,自然没有资格在领着翰林学士一职,这对太皇太后甚是不利。
这时突然有人放话手头有曹大踪迹,难怪永昌候这般重视。
可出乎严学士预料的是,那个神秘人并没有再度登门,甩下那句话扬场而去后就毫无音讯,永昌候越发焦急,待进一步问清那人衣着普通瞧着不像富贵人,说话口音也与京都本土人士区别明显,便猜测着应是在客栈落脚,安排府丁家仆暗暗打听,因为孙子冠琼见过那人,这任务主要就交给了他,一连在京都寻了近十日,却没蛛丝马迹。
冠琼也渐渐心焦。
当日那人登门,言谈举止甚是张狂,他只以为是无赖有心讹诈,被父祖事后一教训,才知道自己太过轻疏,为将功补过,这些日子鼓足了劲搜找,全是无用功,心焦懊恼之余难免沮丧,折腾了好些日子,这日正在西城一片挨家客栈打听,忽遇国子监时的同窗,被几个硬拉着去了一处酒肆,把盏闲谈。
落座不久,便见一身穿青灰长袍吊儿郎当的男子踩着木梯上来,连声呼喝着跑堂,让上茶水,嚣张的语气震彻一个楼层,引得不少人侧目。
这处本是一些文士雅客常来,不比得那些喧闹的酒肆,鲜少见人这般张狂,严冠琼自然被吸引了注意,也跟着用不满的目光盯向来客,哪知这一瞅,他也拍案而起,激动得险些撞翻了靠椅。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废功夫——此人不是别个,正是让严家上下忧心如焚的不速之客。
冠琼兴奋起来,也不及与同伴交待,几个箭步就冲向“青灰长袍”,也顾不得摆士子的架子了,草草一揖,先说一句“上回怠慢足下”,就要请人回府细说,哪知那人却不忘嚣张,冷笑拂袖,开口就是一句:“贵府既然狗眼看人低,眼下何必又说请字”,一副高高在上又讥讽嘲笑的模样。
严冠琼心里窝火,却因着心系大局,只好忍了,好一番低声下气。
那人却不吃软,抬脚便走。
冠琼心急,动手牵衣为阻,却被那人推了一个踉跄,到底冷笑而去。
冠琼哪肯就此放过,跟着追了下去,彻底忘记了一众同窗。
非但同窗们面面相觑,厅堂里也有不少识得永昌候府郎君者,也都悄有议论,猜测着堂堂候府长房长孙,怎么对这么一个粗蛮落拓的无赖“死缠烂打”,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冠琼追出之后,虽没被那人搭理,但总算察明他落脚之地,竟是附近赁的一处民宅,屋主得了严家郎君的好处,泄露那人路引上的名姓,叫做吴籍,果然来自凤阳府。
严家长辈们得闻此事,悬在半空的心落下一半,永昌候沉吟一阵,到底是让二儿子备了厚礼,次日正式拜访,岂知那人依然不买帐,说他上回被人怠慢实难消怒,再不登严家的门,倘若永昌候真要知道曹大的下落,三日后在平安坊四海阁置上一席,他才信得过永昌候的诚意。
这人就是一“无业游民”,却要永昌候亲自宴请,实为狂悖,但永昌候为解家族之急,也顾不得太多,三日后果然去了四海阁,为表诚意,还订了间尤其豪华的雅室,哪知那人却不依不饶,硬是要坐大厅,当众喊说害怕永昌候府杀人灭口!
永昌候这回理解了为何冠琼当日断定此人为地痞无赖,话也不肯多问一句。
大堂人多眼杂,永昌候自然不好追问曹大之事,只叫了一桌好酒好菜,对那吴籍陪礼。
纵使如此,堂堂公候对个庶民费心讨好,并那庶民还这般张狂的蹊跷事,还是被在场宾客引为奇闻,窃窃议论。
而楚王虞沨早在严家私下搜寻凤阳来客时就留意上了这事,他的耳目跟着严冠琼已经有一段时日,严冠琼与吴籍在西城巧遇自然瞒不过他。
虞沨对吴籍的了解甚至比永昌候更进一步。
当然是利用卫冉手头五义盟的资源打听仔细,天察卫既然被太皇太后“接管”,有的事便不好再通过这个机构。
吴籍确为凤阳人士,也的确是个市井闲徒,靠着放点小利钱为生,也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就来了锦阳。
“你怎么看?”虞沨问卫冉。
“吴籍显然是被收买了,他若真有曹大的下落,势必不会这么张狂,真解了严家之急,势必会有重利为酬,哪会这般张狂,分明是得了授意,有心闹事。”卫冉微微蹙眉:“这吴籍当众让永昌候府难堪,怕是活不久了。”
虞沨满意颔首:“关键是他会死在谁的手里。”
总之不会是永昌候府。
“吴籍一死,永昌候府势必受疑,但这与卫国公府何干?陈、秦两家再大的本事,要买通卫国公的亲信总归不能,要是随便买个家丁下手,也难以牵连上。”卫冉大感不解。
自打太皇太后赐婚,大长公主与卫国公也预料对手会有后着,对家仆幕僚看防甚紧,来往密切的故交旧部也得了“小心门户”的提醒,按理来说,被人瞅着空子的机会并不太多。
但所谓百密一疏,防不胜防,虞沨就发觉岳丈仍有遗漏。
他只是以己度人,倘若他要行此阴谋,会择中哪个做为目标。
虞沨正要说明,却忽而以手覆额,半屈手臂撑于案上。
“王爷可是又觉眩晕?”卫冉连忙关切。
数息之后,虞沨才用掌腕慢慢揉着眉心,移开时,面颊颇为苍白。
卫冉没有多问,拉过他的手腕便诊。
一刻后,见卫冉蹙眉不语,虞沨问了一声“如何”。
他微握更显瘦削的指掌,指节越发显突,手背的青脉清晰可见。
“还是那句话,王爷不宜太过操忧重思。”卫冉说完后,自己却无奈一叹,在这节骨眼上,要想静心保养谈何容易。
“江汉医术十分精进,王爷何不让他长随身畔,才更加保险。”卫冉又说。
虞沨却已经放下微卷的衣袖,唇角笑意淡淡:“我已说服江汉,最近他便要入太医院任职。”
说完话已经起身,步伐虽缓,还好稳当,但卫冉看在眼里,眉心却依然紧蹙不放。
“王爷打算去何处?”他问。
“打算遵从医嘱。”虞沨挑起锦帘:“早歇静养。”
☆、第六百九十章 张氏利氏,连袂出场
十月才过,子若姑娘忽然被天降喜讯砸中了天灵,整个人都变得飘忽起来,好心情让荣禧堂的一众仆妇都有感受。
尽管这喜讯只是晴空代转,子若姑娘至始至终未能见到朝思暮想的良人,就算她处心积虑想要对王爷当面表达感激之情,烦扰了赵大总管数回,一直未能趁愿,秦子若的欣喜若狂也没略减两分。
这喜讯便是——王爷颇废周折,好容易才找到江汉,已经将人请回锦阳,但王爷认为让秦家出面荐江汉入仕才更加稳妥。
江汉兄妹其实在年余之前,就一直居留王府别苑,不过这事属于要秘,秦子若当然不得而知。
因着安然有孕,江薇早去了殷家照管,子若姑娘更不知情。
总之,得闻喜讯的秦子若立即让郑氏送信去了秦家一处自营的商铺,于是秦夫人就又来看望了一回女儿。
江汉顺顺利利地进了太医院,在他亲爹手下任了个院判,专门负责中宫脉息。
小事一桩,并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除了江清谷对于儿子突然入仕大是疑惑,避开闲杂人等,满面肃色的追问。
江汉的表现却甚是傲骄,只回以一句:“院使大人可是觉得在下医术不佳,没有资格进入太医院?既然如此,大人何不直谏,将在下除名。”就此对江清谷不理不踩,我行我素,太医院诸位医官虽察知这对父子不和,但也没谁多事打听,谁家还没点家务事,江清谷自打作证先帝传位口诏,地位固然稳若磐石,谁也不会自讨没趣。
太皇太后最近被诸多烦难缠身,也没理会江清谷之子突然入仕一事,甚至没在意声名远播的“送子圣手”为何被秦家举荐,便是江汉为“送子圣手”这事,还是卫昭有意无意时提了一句。
太皇太后关注的是吴籍,但这人滑不溜手,永昌候也算软硬兼施了,吴籍却使终不肯将曹大的下落实述,这位提出的条件是——他要入仕,还不能是闲职,至少也得讨要个凤阳府的同知,赫赫地方五品大员,也就比知府矮着一头,大字都不识一筐者怎能胜任?太皇太后自然不会允准,永昌候这会儿也恨不得直接剖了吴籍的心肺,翻找出他肚子里的秘闻。
与此同时,锦阳内城功德坊,一家名为“朝暮馆”的酒肆,东家张明河也突然在十一月的某日,面临了他人生的又一重要抉择。
这位张明河不是旁人,正是卫国公庶子苏荏生母张姨娘的兄长。
倘若没有当初高祖时候“焦月谋逆”,张明河这时也已位及伯爵,但世上没有这么多如果,眼下的他,靠着与卫国公苏轶的幼时情谊,好容易才在商界立足,财富有余,身份上却始终位于屈末。
其实张明河自打主谋了张姨娘“爬床”案,他与卫国公的“发小”情份就一笔勾销——当年卫国公待他有如异姓兄弟,便是对少女时代的张姨娘也是温言细语,可惜张明河年轻浮躁急功近利,不甘为人仆役,一门心思要重获富贵,这才一手策划下药,造成苏轶“意乱情迷”,与张姨娘生米熟饭。
张明河是眼看当年大长公主心记旧部之谊,认为有空子可钻,那时的世子夫人又贤良宽善,不是好妒之人,事情果如所料,世子夫人倒能容人,殊不防大长公主因而厌恶极了他们兄妹,苏轶也因而生怨,妹子倒是成了姨娘,他却被“下放”农庄成了最下等的奴役。
但这张明河也不是普通人,颇能隐忍,毫不气馁,任劳任怨的做了几年耕种劳务,讨好得底下庄头对他青眼有加,学了一手稼穑实务,兼着他又是八面玲珑的性情,居然默默笼络了一批管事,甚至当地乡绅也把他看作能人。
后来,国有大赦,兼着张姨娘产下庶子,老国公苏庭大约是见张明河真有几分本事,竟为他脱籍,并给了他本金自营商务。
但世人大多以为是苏轶因为张姨娘之故,有心提携“爱妾”兄长。
实际上张明河能凭着并不充沛的本金,成为京都“小富”,卫国公府并没有过多提携。
但世人自会认为是因为苏轶的赏识。
张明河其实早生懊悔,那时倘若思谋得更为周全,而未行惹苏轶反感之事,他的成就还不仅眼下。
这人也颇为自觉,这些年间,就算与张姨娘来往,也是依循俗法,从不以卫国公府“姻亲”自居,他深知妹子打小也算被大长公主“娇养”,眼高于顶,性情跋扈,往常多有劝解,警告张姨娘认清身份,切莫挑衅正室,但他对二郎苏荏甚是大方,从不在意钱银,还算是个慈祥的“舅舅”。
朝暮馆是他开办的第一家酒肆,经营多年,也算有些名气。
他也习惯了在朝暮馆“坐班”,处理商务,后院专备他日常“办公”的厅房。
张明河这时长子也已娶妻生子,一些普通事务他有所放权,这日,长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