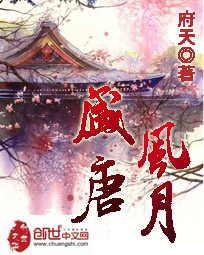风月总无边-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毕竟是北周,当司命拿出杨家的令牌时,一切妄图觊觎有心的拦截的,尽数退了个干净。
“杨氏自汉朝来,直到魏晋南北朝均是的名门望族。杨忠当年亦是与独孤信共同辅佐宇文氏建立北周,为开国功臣,因此获封随国公,”司命边前行,边对阿禄,道,“而杨坚就是杨忠的长子。”
自踏入人世,这还是司命初次谈及杨家。
阿禄走在他身侧听着,暗记于心,道,“如此说来,杨家与独孤家是世交?”
司命颔首,道:“除王姓外,此两族乃是北周最显赫的世家,自然多有走动。”
两大望族,联姻乃是必然。司命没说,她自是明白。
她更晓得,若是极为简单的,倒也不用将她扔下来掺和。只是当年天庭上各位都交代的极为隐晦,只说此二人因机缘巧合,结下了凡间九生九世的金玉良缘。九生九世的金玉良缘在月老那处的说法就是,世世相扣,于这最后一世变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死结了。
死结如何解?只有一条路——快刀斩断,永绝后患。
但此路一走,二人因这世世相扣的纠缠,必有其一因此断了根基灰飞烟灭。一个是鬼界太子,一个是观音童女,哪个都死不得……
哎……阿禄只觉前路渺茫时,前路急匆匆走来一人,身后随着几个身着官府面容肃穆的人,那人行到不远处便已开了声,道:“苏公子啊苏公子,你可是叫老夫等的好苦——”
司命遥一拱手,道:“元将军。”
那几人所到处,皆是行人慌忙避让,让出一条宽街来,倒更显得来人急切。
待到近前,那长须老者方才愣了一愣,指着那轮椅道:“公子不过走了两月有余,这是——”司命轻拍了拍自己的膝盖,道,“自幼落下的风湿寒症,无妨,过几日便可下地了。”那老者一听这话,方才缓了神色,哈哈大笑道,“老夫当真是被你吓死了,你当初可是说离开一月便回,这一去竟是今日才露面,竟还……坐了这么个东西,哈哈——”
那老者笑的爽朗,竟当玩笑一般,拍了拍司命的肩,接着道,“随国公他日夜催促,只说若是苏公子现身了,便要即刻启程前往长安。你若再不回来,老夫怕是要提着脑袋回去了。”
那元将军性子直,更在话语之间显出与司命的关系不凡来。
阿禄瞧在眼里也不多做反应,只闲闲地随着这一路人进了将军府,待到厅堂上各自落座,奴婢奉茶时,那将军方才像见到司命身旁人一般,道:“苏公子历来是形单影只的,这怎么突然多了个女子相伴,莫非——”他似有所猜想,话语中多了几分取笑。
司命摇头笑道:“元将军莫要乱想了,这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苏禄。”
同父异母——
阿禄正是踌躇时,却听他这句同父异母,惊得手中茶杯滑落,一声脆响,让那将军不由又多看了她一眼,笑道:“原来是苏公子的妹子……小姐莫慌,老夫这粗言粗语的,多有得罪了——”边说着,那后边伺候着的丫头早就上前清理了碎片,又奉上了一杯茶。
此趟奉茶,就连那丫鬟眼中都多了几分敬重。
阿禄这心里刀割一般的,哪里顾得上再去寒暄俗礼,只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却不答话。倒是司命先开口岔开了话题,道:“我这妹妹自幼被养在深闺,又逢战乱颠簸流离的,见了生人自然会怕些,元将军莫要怪罪才是。”
“不怪不怪,”元将军拿起茶杯一饮而尽,道,“方才老夫还想着是什么落魄美人碰上少年书生的桥段,却没想到公子此番潜入南梁竟是寻到了失散家人,当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就在这元将军一连串的可喜可贺里,阿禄就如此成了司命的亲妹子,苏禄。
司命与元将军整个下午都在书房议事。独留了阿禄一人,在府中无所事事。
既是北周将军府,景致自是与南梁相府相差甚远。
那处是亭台楼阁,石桥碧水,此处是高墙阔院,马场箭靶。
因是暴雨后,碧叶都多添了几分绿意,瞧着倒平复了几分焦躁。
阿禄打发了跟着的丫头,就坐在射箭场子外,独个儿瞧空荡荡的箭靶,打量这四下无人,便走到木架上,挑了个趁手的弓,自箭袋中抽出四枝,走到场中,满弓试了试力度。
若说她活了这许久,却仅有这射箭还能拿得出手。
只是,这一技,连司命也不曾见过。
在东胜神洲的仙岛上,日日不是吃酒便是下棋投箸,哪个神仙会设下这种场子耍?话说回来,若非此次下凡,她也不会晓得日日摇扇的司命,会是那马上将军。
昨夜那光闪,上通九霄苍穹,下抵弱水河畔。
那一刻,手握光闪,以雷鸣为鼓的司命,竟是如此陌生……
阿禄手抚弓弦,竟一念想起了那个人。
万年了,若非观世音一纸书信撼动九天,若非司命翻了命薄寻出姻缘,怕是万万想不到他便是那鬼界太子相柳,怕早不晓得这万年轮回后,他已投生哪家哪户,与哪个女子相伴厮守了。
当年那山间尼姑庵内,唯有他一个男子寄住,而那庵中除了师傅师伯和那个老得睁不开眼的师祖外,便只有自己一个带发修行的弟子。在他走后,曾几番猜想,倘若并非只自己一个年轻的少女,他或许就不会青眼有加,若自己不是带发修行的弟子,怕他也不会多看自己几眼的。
只是纵有那么多“倘若”,却终究是自己人间唯一的情劫。
曾经,他亲手做弓,教自己射箭之法。遥记那日,不过三两只箭,自己便觉颇为上手,待十数枝射出,便已能直抵靶心。那日,是自己那一生最为骄傲的时候,他眼中的惊奇和赞叹,毫不掩饰……
心底难得一股暖意上涌,阿禄微微挑了嘴角自嘲一笑。
伸手,满弓瞄靶,猛松手一道黑影射出,随着一声闷响,正中靶心。
看着那尤还颤着的羽尾,她暗淡的眸子豁然亮了几分。想来还真是独擅于此,竟是万年没碰了,仍能一箭中靶。
她自来是个想得开的,自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痴心,司命却皆是不动生色地避开,任是傻子也瞧出了,自己又并非当真是傻。
苏禄这名字……也还过得去。
抬臂,衣袖滑落于肘间。待凝视片刻箭靶后,嗖嗖又是两箭,毫无悬念的正中靶心。
“好箭法,”场外传来一声喝彩,“世子你瞧,元将军府内,竟连个女子都有如此箭法——”
“嗯。”
简单一个声音,淡而无味,却轰然一声,将阿禄定在了当处。
万年前,那场黏腻的春雨中,他被将军府前来的部下接走时,坐于马上看着自己,曾说:务必等我。那一句务必等我,等了足足一辈子,却终究没再见,徒留人间青史成灰。
万年后,在春雨停歇后,他就这样不期然地出现了。
阿禄放下手中弓,缓缓转过了身。
箭场外,站着两个少年。
他依旧是那副模样,只是双眼中多添了些血丝,几许疲惫尽在眉梢,却仍盖不住那孑然而立的孤傲。就连,那紧抿的唇仍如记忆中一般的熟悉……
身侧少年手舞足蹈,他却自成风骨,轻裾随风。
“姑娘,”他身旁处的少年极为兴奋,道,“你这箭法真是好!和我家世子比,那也是不相上下的——”
阿禄看着他的眼,他的脸,没有说话。
倒是杨坚先开了口,道:“在下杨坚,方才唐突了。请姑娘莫要介怀。”
他眉目依旧,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色依旧。只是阿禄从没认真思量过,前世那场浅缘,如今却唯有自己还惦记着,于他,倒是干干净净的,尽数抹去了。
原来,这凡人七情六欲,最残酷的竟是遗忘。
阿禄只摇头,勉强笑道:“无妨,我不过一时兴起,世子见笑了。”
杨坚略一颔首示意,便带着那少年离开了射箭场。
北周的世子
因挂着苏禄之名,她自是吃好喝好,却也因这身份,不用避嫌地与司命住同住了一个院子。
阿禄略打量了四处,便晓得这宅院是司命常住的。那树下的藤椅比寻常的要宽大些,有舒适的锦裘铺垫,藤椅旁的矮几上摆着各色茶具,书不多不少放了五册,有一册尚还半开着,像是看书人方才离开一般,无人去挪动分毫。
她走过去,看了一眼。唔,正是下凡时他日日读的那卷。
晚膳时,将军府下人来请,她问了句苏公子可会去,那侍女忙道因大世子忽然现身,故而本是安排的晚宴已取消了,那几个还在将军房内议事。她本就是个随性的人,听这么说就推脱说自己路上劳顿,只要了一碗清粥几碟小食,坐在藤椅上翻看司命留下的书卷。
她本就是个懒人,于天界时,想读书却不愿筛书时,总随手拿过司命读过的。这书卷,司命读了大半,自己便也读了小半,如今倒恰好用来打发时间。
直到深夜,司命方才自元将军那处回到住处。
他自推着千年桃木轮椅入院时,正瞧见阿禄蜷缩在藤椅上,抱着书打瞌睡。此时恰过了梨花花季,月色下,唯有些残败的花瓣偶被风吹落,辗转而下,如雪如絮。
这一眼,竟如那东胜神州,万年闲散日一般。
他停在院门处,只轻浅地看着阿禄,半晌,方才继续伸手推着木轮行至藤椅旁,道:“阿禄,”停了片刻,见她迷茫睁了眼,方道,“夜深了,进房去吧。”
阿禄唔了一声,坐起身滑落了锦裘,接连打了两个喷嚏,才道:“他们没瞧见你病的都不能走了,竟还拖到这么晚?”边随口抱怨着,边起身趿着布鞋,一边絮絮叨叨又说了不少话,自觉推着司命先进了房。
这屋子掌灯的早,如今光亮反倒暗了些。阿禄正走到灯边,揭了开挑弄灯芯时,司命才看她背景,平平道:“今日你见到杨坚了?”
这一问,阿禄骤然停了手,缓了缓心神,方才嗯了声。
“他来时曾拜访过独孤信,”司命自推了木轮到桌边,行至特为他备下的火盆旁,赤红的火焰于他脸上映出变幻光影,“独孤信已生了嫁女的心思,如今那独孤伽罗生母病逝已有两年,三年守孝期满后,杨家便会上门提亲,择日完婚。”
原来这成仙的好处,竟是眼瞧旧事重演……
阿禄自去将火架上的铜壶拿起,将那茶壶满上,倒了杯茶递给他,道:“北周两大望族联姻,我这凡俗花花草草的,又怎能入了世子爷的眼……怕此番你我只能无功而返了。”好吧,她承认,她退缩了,自午后见杨坚那一面后,她便生了退让的心思。
万年前,尚有那落难时的恩在,他仍旧为了大局而放任自己枯灯死守。
这一世,不过是萍水相逢,又有何德何能去破了那强强联姻的局?
“阿禄,”司命自将手炉笼在手里,道:“我会帮你。”他说的坦然,只是眸光竟有些黯然,不过瞬间便已抹去。
他会帮自己,这是必然的。
就如同自己初执司禄之职时,错将天帝七皇子写成了宦海浮沉,终身不得志,被他一力扛下,挺身相护。就如同自己在观音说法时,不留神踩断了童女良姜的玉如意,他三言两语淡化去了该得的罪责。
就如同……被他护惯了,倒养了不少毛病。不过好在,那举目无亲的天庭,每一次他都会挺身而出,而如今,竟连这尘世姻缘也要倾力而为吗……
阿禄暗自苦笑,不知是该感恩戴德,或是黯然神伤才是,只恹恹地手捧茶杯,吹着热气,道:“如何帮法?你是鬼界的将军,又是这北周的第一谋士,听你的倒也好。”
“听说你的箭术了得?”司命偏就不细说,转言到午后之事,道,“我只道你这万年练就了些琴艺画技,却没料到,竟还有一武技傍身。”
咔嚓一声清响,火盆中一块木炭恰被烧成两段。
那火苗猛然一暗,随即重新窜了起来。
阿禄,道:“东胜神州各个是谪仙,历来均是尚文弃武,我这小伎俩如何拿得出手?”
“看来,不止是小伎俩而已,”司命,道,“杨坚对你赞誉有加。”
阿禄随口嗯了一句,心道那箭法就是当年他教的,虽如今这命盘全乱了,昔日有情人成了路人,也总有些相通之处。她不是没看到,那一瞬的赞叹,和当年一般无二。
司命没再说下去,草草打发了她去睡,只嘱咐翌日要早些起身。阿禄这一路来,穿的用的均是那株并蒂莲娃娃备下的,算是毫无追求,给什么用什么。
是以,当她早晨摸了衣裳换上时,自家呆了一呆。
素色白袍广袖,腰间淡金色腰封,着实……不俗。
待拉开门时,司命正站在树下,折扇敲着手心,瞧不分明面上的神情。
她难得穿的如此特别,展袖走下石阶时,竟觉有些窘迫,只道:“你这两个小童也不知想些什么,这衣裳倒是特别,只不过……有些抢眼了。”她抬眼间,恰如九天碧落,波光潋滟。
“百花争艳,终是那一抹别色,方才能直敲人心,”司命自云淡风轻,道,“这衣裳是我为你选的。”话语间的坦荡,就如同说这菜是他点的一般,不以为意。
只是,说者未必无心,听者却注定有意。
阿禄顿时手足无措,只慌忙低了头,道:“这么早,可有安排?”司命颔首,道:“陪我去买笔墨纸砚。”言罢,掂了掂手中折扇,慢步踱出了院子。
笔墨纸砚?阿禄无言。
但她自晓得,凡是司命所说所做的,必有其用意。
只是,这用意到了临城最大的聚宝斋,却也没想通半分。阿禄只随着他进店,瞧着那欢喜的掌柜跑上跑下的,老树开花一般左一句苏公子又一句苏大才子……想来,这司命竟是此店的常客。
司命和颜悦色,道:“贾掌柜,此番可有好砚?”
“有有,苏公子请先饮茶慢看。”那掌柜继续在脸上拧花,连忙将他们领入里间儿,放下玉珠帘子,倒了上好的茶,亲自端了托盘小心放在了案子上。
那托盘上覆着上好的锦缎,只是被那几台砚一比,却是暗淡无光了。
阿禄自瞧着那砚,司命则端茶慢饮,道:“贾掌柜,你可是怕我没银子付?我昨日到了便已听说,你此处得了北齐宫廷至宝——”
那掌柜一听,微一怔愣,似有所犹豫,却碍于司命的身份不敢直说。
正在他满面纠结时,隔间儿的布幔忽地被掀了开:“掌柜不必为难,既入了这聚宝斋,便要守这一方土地的规矩,”迈步而出的竟是元将军,他哈哈一笑,道,“苏公子,世子爷晨间便已定下了那芝生砚,老规矩,哪个肯出血,这台砚便是哪个的了。”
这聚宝斋的几个贵客隔间儿本就互通,均有一道布幔做假门,美名其曰,“绝不私藏奇货,绝不私护权贵,有银者竞得之”。方才二人进来时,隔壁并未有声响,阿禄倒也并未留意,如今那元将军掀帘走出,才瞧见随后而出的杨坚和昨日相随的少年。
司命将茶杯放于案几上,起身拜了一拜,道:“世子爷。”
杨坚颔首,道:“苏公子无需多礼,”只一句,却将那视线落到了阿禄处,“昨日一面之缘,却不知竟是苏姑娘,多有得罪了。”
阿禄忙也站起身,道:“世子爷接连两日赔罪,阿禄断然担当不起——”
这几句寒暄下来,倒有些冷场,亏得杨坚带着的少年明朗一笑,道:“苏小姐——苏姑娘——苏禄——阿——禄,”他一字一句拖着声音,分外讨喜,边说着边走上前,长揖一礼,道,“小生精通百般武艺,唯独不会射箭,世子爷又不肯屈尊教我。昨日箭场一面,夜不能寐,今日既是有缘再见了,还请阿禄姑娘不吝赐教收我为徒——”
他这一迭声叫阿禄,委实凄惨,听得她噗嗤一笑,道:“不敢不敢,你精通百般武艺却还不知足……人无完人,若是无缺者必遭天妒的。”
那少年起身,竟当真仔细琢磨起阿禄这话来,半晌才道:“我以为我家世子爷是最有城府的,可姑娘竟也能说出一般无二的话来……”他盯着阿禄半晌,忽地又是长揖一礼,道,“姑娘高才。”
这结论得的蹊跷,听得元将军哈哈大笑,直拍了拍他的肩,道:“当世第一高才就在眼前,你却偏就不理,竟去刁难起苏姑娘来了。”
少年听他一说,自是晓得那第一高才指的是司命,却分外不屑,只哼了一声,忽地又露齿对阿禄一笑,直笑的她哭笑不得,心道这少年若非七窍不全,便是心地过为纯净了……
不过,倒也多亏了这少年。
方才那霜降般的冷气,终是被他这一搅合,成了场闹剧。
那掌柜抹了一把额上汗,适时插嘴道:“世子爷……那台宝砚……”
“拿出来吧,”杨坚,道:“只是……凡苏公子开的价码,本世子均要加上一两银子,”他自看着司命,道,“怎么样,苏公子可是想好了?”
“此砚……”司命悠然回视,敲着扇子,笑道:“依我看来却是无价之宝。”
既是无价,又如何加价?
少年听了骤然冷下脸,下意识握了拳。那元将军却是干笑着难以出声,彻底僵掉了……
“聚宝斋于北周七十二家店面,纵是国宝也有明码标价,从无特例,”杨坚向桌边踱了几步,恰就站在阿禄身侧,道,“不过,苏公子既如此喜爱此物,公子开个价,我便加上一两银,送与苏姑娘做见面之礼了。”
只言片语间,却是剑拔弩张,轻踱几步,便已云淡风轻。
阿禄不禁瞧他,却发觉他眸如碧水深潭不见底,只瞧着便平白的让人心慌。不觉收了眼,心想难得这冷了的场子又回春了,总不好再去陷大家于危难,只得尴尬笑道:“那便多谢了。”
杨坚倒没料到她收的坦然,只收了目光,吩咐少年,道:“凌波,去拿那砚来。”
话音未落,少年已身形微动,还未待阿禄回过神,便觉怀中一沉,价值连城的宝贝已被丢入了怀中……这国宝,竟是被他当做大白馒头一般扔到了自己怀里。
阿禄抱着这价值连城的物事,还真是哭笑不得了。
“姐姐不必谢了,”那少年嘻嘻一笑,拍了拍手早已站在了杨坚身后,道,“教我射箭便好。”他还真是孩子脾气,说来说去却仍忘不了这一件事。
阿禄也不好一而再拂了他的意,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