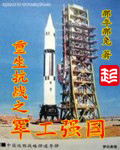废后重生:权倾六宫-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裘太后立即照准,并下口谕:着花期等三名女官,照壁等六名粗使宫女,并拨四名内侍,随邹氏迁往掖庭静居。清宁宫其余人等,兴庆宫留十七名,余者发往六局为女史。
明宗接连接到这一请一答,只觉得头晕眼花,抓着孙德福问:“这是怎么回事?太后何时与邹氏见过面?”
孙德福便嘟囔:“上回要跟您报,您一听是皇后的事儿就不耐烦听,还赏了我一脚呢!”
明宗顺手又凿他个爆栗,喝道:“还不快说!”
孙德福叹口气,方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最后道:“也是赶得巧。那天晚上您在仙居殿陪贤妃娘娘听梨园制的新曲散闷,所以咱们谁都没注意皇后的琴声。”
明宗的眉头拧成了个疙瘩,仔细回想:“那日,似乎是德妃着人请我去的仙居殿,曲子也是她安排的……”
孙德福吓一跳,忙道:“谁想得到皇后能为了宫人做成这样?您别瞎琢磨!都这样起来,咱们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明宗摇头,摆手让孙德福不要插嘴:“你不明白。贵妃有这个脑子,却没这个当机立断的狠心。”
心中一转,忽然问孙德福:“你说余姑姑事后一直琢磨什么事来着?”
孙德福道:“哦,是说皇后对着太后的自称,一路从恭谨到亲密,都自称儿了,还不肯称呼太后做阿娘,只肯说到母亲,令人不解。”
明宗顺着孙德福的话仔细一想,片刻后,叹了口气:“她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自家阿娘的愚蠢,便不肯将这个词放在太后身上,你看着吧,到得她死,也不会称太后一声阿娘的。”
边说,边铺纸蘸笔,亲手写圣旨:“皇后邹氏,误伤皇嗣,拒不认罪,有悖皇后恭顺之德。着废去后位,降为充仪,赐字幽隐,七日内迁居掖庭,非特旨不得回归大明宫。钦此。”
孙德福伸着脖子边看边念,然后自己咕哝:“幽隐,幽隐,有因,那不是说事出有因?”
明宗一笑,斥道:“就你聪明!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孙德福会意一笑,看皇帝用了印,赶紧伸双手去接,笑道:“我跑一趟吧?”
明宗手一缩,一转弯递向一边侍立的孙德福的大徒弟郭奴:“你替你师父跑一趟。”又笑着对孙德福道:“你去?你去不就是告诉别人赶紧下手害她么?咱们以后提都少提她。你要记住了。”
孙德福眉开眼笑:“是是,我这个榆木脑袋,糊涂了!”
旨意还没送到清宁宫,邹皇后和裘太后的问答已经传到了好几个地方。
沈府。
沈迈拿不准自家闺女会不会掺合宫里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宫里的信儿现在是沈将军第一关注,羽林的人心领神会,仙居殿清宁宫两边的人都将事情原原本本交代了一遍,沈将军对照着一看,顿时怒不可遏。
妈的,坑害邹家就坑害邹家,竟然顺手算计到老子头上来了!竟然还是算计已经死去的老子的内院!真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沈将军豪阔,却不蠢。脑子里一转,幕后的主使便猜了个七七八八,立即破口大骂:“这不是福王那个白痴就是宝王那个混蛋!来人,去给老子查!”
待想到自己搭了一个娇滴滴的宝贝女儿进宫做小,饶是如此,皇帝的疑心还洗不去,越想越气,怒火便几乎要烧到屋顶。左想右想,忽然一拍桌子,有俩可以出气的地方——喝令自己的亲兵:“去,把这些东西都给老子送去邹家老头儿那儿!告诉他,他自家孙女死不死老子没兴趣,但如果连累了我姓沈的,老子就算被剐了,骨架子也要一把火烧了他的太傅府!”
自己则转身去了沈大郎家里,关起门来和哥哥乒乒乓乓打了一架不说,就连几个侄子也一人一拳打在腮帮子上,临走冷冰冰放了一句话:“求大嫂以后再也莫管兄弟的家事!”
沈大夫人自有自己的消息来路,知道丈夫儿子都是在替自己挨揍,此刻早已面红耳赤,哪里还敢说话?深深万福着送了沈迈出门,自己一回身便晕倒在地,一病便是半年。这是后话。
再说邹府收到沈将军的信和传话,邹老太爷一看之下,又气又怕,差点便厥过去。邹太夫人闻讯忙忙赶来,看到邹老太爷坐在那里老泪纵横,不由慌了,正待要劝,只见邹老太爷举袖擦泪,低沉道:“没有个好母亲,女孩儿便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打落牙齿和血吞。我家田田今年十七岁,十七年,一天好日子没过过,如今还要被连累。”
邹太夫人听着老爷子这话是冲着周氏去的,心里便突突地跳起来,颤声问:“难道沈家有不妥?”
邹老太爷自己接着低语:“都怪我。当年就算放弃了二郎,也不该给他凑合了这样一房媳妇。既然已经知道是愚人,当年就不该领旨,哪怕即刻便把田田许给谁,也比现在这样强。”
邹太夫人见问不出来,伸手拿过老太爷手中的信,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后怕,看到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我苦命的田田!都怪祖母,固穷了一辈子,临老临老利欲熏心,鬼迷心窍,怎么就能听了你那个蠢娘的话啊!”
邹老爷子一脸木然,道:“今日起,所有送入宫的消息,不论大小,必要经我。你回去将二儿媳禁足,一辈子不许她再出后院半步!”
邹太夫人一行哭,一行应诺,又道:“恐怕一半日田田被废的圣旨就要下来了,这个只怕瞒不住她。”
邹老爷子面上杀机一闪,冷笑道:“你是怕她寻死罢?哼!我谅她也没那个勇气!”
说完这话,老爷子振衣而起,不见老态龙钟,但见脊背如松,且自嘲一笑:“看来就是闲不住的命。刚歇了小半年,我这个前帝师,就又得开始动脑子了。”
说着,喝命窗外:“来人,更衣备轿,去周府!”
事情传到各处,所有人都拊掌大笑:“邹老头儿这个哑巴亏吃定了!沈二拳头果然是个妙人!”
圣旨传下,邹府一片死寂。沈府鸡飞狗跳。
明宗听着孙德福绘声绘色的回报,笑意浮上嘴角:“沈迈是个纯粹的武人,直性子,好就大碗喝酒,不好就大打出手,不然怎么会落了个沈二拳头的匪号?不过,这下子,沈迈和沈家老宅、邹家、周家都算有了心结了。”
孙德福看着明宗言犹未尽,便笑着小声补充:“而且,有他这样上心地找仇人,盯着那边两家,咱们就能……”
明宗便瞥了孙德福一眼,孙德福自知失言,忙讷讷退到一旁。
明宗自己却无论如何也掩不住笑意,万分忍耐不住地轻声道:“而且,邹氏和沈氏,怕是再也好不起来了……”
孙德福心底一凉,偷眼看看明宗,暗自叹气,不再多言。
清宁宫。
邹皇后听横翠将邹府传来的消息讲完,也有些惘然,过了许久,才令横翠:“无论如何,传话回家,我阿娘必要好好活着;否则,与沈家的结便再也打不开了不说,还会凭空担上更难听的恶名。”
横翠脸色早已白得怕人,低着头牙根紧咬。
花期在旁边边听边垂泪,却一声不吭。
离开清宁宫的时候,邹皇后,哦,现在应该叫做邹充仪了——邹充仪都没有回头看一眼清宁宫的大门。反倒是特地来送行的沈昭容,一眼又一眼地打量清宁宫的正门。
花期、横翠和丹桂此刻都安顺得很,低着头,并不管主子们在说什么。
邹充仪看着依旧飞扬的沈昭容,神色多少有些怪异。
沈昭容就笑了起来,趴到她耳边悄悄说:“我知道圣人不希望咱们俩走得近,可我凭什么要按他希望的过日子呢?我只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日子——你说的,这宫里,其实我可以横着走的!”
邹充仪忍俊不禁,便伸手拍了拍沈昭容的手,真诚地谢了一声,又颇有深意地开了一句玩笑:“那我岂不是应该说欢迎你常去掖庭看我?”
沈昭容满不在乎地一抬下巴:“有何不可?”
邹充仪笑着摇摇头,微微福身:“嫔妾谢昭容娘娘宽和。嫔妾告辞。”
沈昭容被这样的称谓叫得笑容一僵,待邹充仪走开了两步,方才猛然想起似的,匆匆忙忙地扬声道:“裘昭仪托我跟您说再会!”
邹充仪心下明白这是小女儿故意要跟喜怒莫测的皇帝与心机深沉的闺蜜作对,不过,总是对自己的处境有三分益处,便回身,遥遥地一拱手,道一声:“不敢。”率着十几个人,各自提着包裹,车声辘轳,迤俪而去。
终于,站在原地没动的沈昭容,在仙居殿大床上卧病的贤妃,在明义殿给方婕妤准备“膳食”的德妃,在清晖阁查阅账目的贵妃,在紫兰殿对坐沉默的崔充容和程才人,以及在长庆殿与裘昭仪吃茶的裘太后,在御书房与沈将军分析情报的明宗,数个府邸书房或密室里的主仆们,先先后后,早早晚晚,都抬起头来看向掖庭方向,心里,默念着同一句话:清宁宫,易主了。
第一卷终
☆、68。第68章 幽隐
一晦一明日月,一生一灭春秋。一荣一损时运,一朝一夕白头。
掖庭宫北部是太仓,南部是内侍省、殿中省和羽林卫,中间的绝大部分地方,是宫女们的住处、浣衣处等处罚犯错宫人的地方,以及,众人口中的俗称:冷宫。
冷宫其实只是个象征的说法,真正需要幽禁的宫妃,都住在一个叫做静思殿的大大的宫殿内,一人一个房间而已。
然,还有一些,皇家不舍、不能或不敢扔进冷宫的人,都只是在旨意上草草说:迁居掖庭。所以,对这些人,一般都是在掖庭宫中部,找个小巧的院落安置,其实仅仅是离大明宫这个权力中心远了些而已;衣食住行,仍然有一定的规矩分例,温饱是不成问题的。
邹充仪就被安置在了这样一个小院当中。
小院收拾得极为雅致。
庭前不是垂柳,而是枣树和杏树,一春一秋,树上要么花香绵延,要么果实累累;角落不是盆栽,而是一畦菜地,像点缀一样种着瓜菜,绿莹莹的,平添几分农家田园之乐。院中正房、耳房、厢房、厨房俱全,大大小小竟有十几间。后院掩映着几株大大的梧桐树,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子,里头连锦鲤带草鱼鲫鱼,竟也热闹得很。
邹充仪看着极为诧异,忙遣了横翠去打听。半天横翠笑吟吟地回来,才知道这原是内侍省绞尽脑汁修了打算孝敬孙德福的,孙大太监哪里会这样奢侈打眼?不收又伤了徒子徒孙们的心。正不知道怎么推辞呢,恰巧赶上邹充仪迁居,直接在明宗面前备了案,孝敬给前主人娘娘了。
邹充仪听了便道真个是巧,心安理得地住了进去,只是私下里令横翠送了一盒上好的小南珠给孙德福,让他“留着赏人,也不跌你两省大太监的份”。孙德福二话不说便笑着收了,还轻轻地跟横翠谢了一句:“谢皇后娘娘赏。”惊喜得横翠跌跌撞撞跑回来,说话都结巴了。
邹充仪却没有她这样激动,只是让人开始洒扫庭院。
丹桂感到非常奇怪,邹充仪似乎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彻底习惯了“冷宫”生活。甚至还卷起袖子,立马挥毫写下了皇帝赐的“幽隐”二字,令人拿去贴在小院的大门空白匾额上,又传令:“这二字我每日写一次,着专人看觑,若遇有风雨霜雪,但有损毁,立即来报,我马上写新的。务令此御赐字样给咱们当好了门神!”
花期却一直木呆呆地,只是邹充仪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也不做事,也不吭声,只是跟着而已。
丹桂看着花期的样子,半天叹口气,卷起袖子,去收拾邹充仪的内室了。
三天后。幽隐小院平平静静地进入了过日子的状态。
邹充仪传令,大家先改了称呼,要么叫做充仪,要么直接叫娘娘,无论如何,再也不许呐出“皇后”二字。
最先犯错的是花期。其实,也许不是不小心,而是心里残存的执念罢。
邹充仪平静地令人禁了花期的足,整整三天,送进花期房间的,只有清水而已。
花期沉默了三天。
三日后,花期到前庭跪倒,给邹充仪磕了九个响头,禀报:“婢子蠢钝,愿将掌事之职让与丹桂。”
邹充仪坐在正房的榻上写字,偏头看她,道:“圣旨既然只说降我的位份,没说降你们的等,那你花期就还是这宫里除了余姑姑之外的唯一一个四品女官。花期,你真的不愿意再掌管我这幽隐小院了?”
花期直挺挺地跪着,半天才又抬起头来,平静道:“是。婢子愿意帮着丹桂做事情,但不想再继续做掌事。陪嫁库房失窃,娘娘的贴身饰物被偷,采萝因此丧命,娘娘因此被废,婢子身为掌宫大宫女,难辞其咎。再继续做下去,婢子心不安,神不定,诚惶诚恐,难以胜任了。”
屏息静气的众人闻言,面面相觑。
丹桂和横翠并肩站着,听了这话,看一眼横翠发白的脸色,悄悄拉住她的手,轻轻一握。横翠回看她一眼,有泪盈睫。
邹充仪这边,屏息写了一行字,才道:“既然如此,可。”
花期像是长出了一口气,又给邹充仪叩了一个头,才站了起来,却看着众人朗声道:“来人,本官要用饭。”
邹充仪下笔顿了一顿,抬头看着忽然间神清气爽的花期,微微笑了。
丹桂和横翠对视一眼,也都轻轻笑了。
小宫女们也松了口气,笑嘻嘻地忙各自的活计去了。
似乎在这一瞬间,在花期交还掌宫权力的这一瞬间,大家都放下了曾经的芥蒂和疑心,似乎一切又恢复到了曾经的美好。
不过,谁知道呢?
邹充仪低头继续写字,心中转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同舟共济总是比安享富贵更容易,这真是奇怪啊!
邹充仪自此足不出户,每日只是写字、看书、饮酒、抚琴。
然,她自己闲适,却不肯让宫女们也闲着。想了两日,便命丹桂伙同花期,扯了裘太后的虎皮做大旗,从六局请人来教授各种手艺:女红针线、制作首饰、厨房手段,甚至,邹充仪亲自,与丹桂花期横翠几个人轮流着,教给粗使的六个宫女写字看书。
半个月功夫,丹桂便安顿好了所有的人。可她自己,看哪一样都不爱,整日里便百无聊赖起来。
一日清晨。
丹桂托着腮坐在案几边上看邹充仪写字。一脸的无聊。
邹充仪一旦沉心写字,便百事不闻。
半个时辰后,邹充仪抬头,活动一下肩臂和脖子,便瞧见丹桂还是那一个姿势,呆呆地看着庭院外的枣树,和旁边正在一起学习刺绣的宫女。
邹充仪皱了皱眉:“九娘?你也想去学么?”
丹桂回神,“啊”了一声,摇摇头,懒懒道:“不啊。只是无聊罢了。”
邹充仪站起来舒展身子,顺手也将丹桂拽起来,问道:“那你去挑一样别的学着玩啊!我看你都闲了半个多月了,这样闲下去,非生病不可!”
丹桂打个呵欠,懒道:“学什么呢?都怪腻烦的。我已经是女官了,不好跟她们学一样的,仿佛在抢她们的差事一般。何况小宫女们的那些东西,我都粗粗懂一些,跟她们也学不到一起。我家里本是杏林世家,家祖家父都在太医署做事,除了药香,别的我也懒怠闻啊。”
邹充仪皱着眉头轻轻揉捏自己的手腕,仔细地想:“那你做些什么呢?女红么,前天我看你已经闲得开始裁剪缝制咱们冬天的帐子了——”丹桂听了,便回身指指里屋大木头箱子,意思是已经做好放起来了;“厨房么,你一进去就要跟人家长篇大论地讲药膳,比陶司医管的还宽;首饰么,司珍司宝的人给你当徒弟都不配——九娘,你做点什么好呢?”
丹桂笑眯眯地享受着邹充仪的夸赞,末了投桃报李:“所以婢子也就是能跟着娘娘学点诗书礼仪了。”
邹充仪便摇头,神情中有些莫名的东西:“这可不行啊。不能满院子里,只你一个是我的亲传弟子。”
丹桂闻言,心中一跳,不由挑眉道:“娘娘是怕她们嫉妒?”
邹充仪微微一笑,凝神片刻,才道:“我怕她们要了你的命。”
这一句话语声轻缓,用字却血淋淋地可怕。
不过丹桂似乎已经习惯了。
“没事的娘娘。反正我已经跟娘娘这般好了。就算没如今这样的境况,我恐怕也是她们除之后快的对象。只不过,好歹我是兴庆宫长庆殿的人,她们动手之前,只怕也要想想清楚,到底惹不惹得起我家师父。”
邹充仪看着丹桂越抬越高的下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好好,知道你厉害,行了吧?”
片刻又愁容:“可你老这么闲着,真的很烦人啊。”
丹桂这才反应过来:“娘娘,您是在嫌弃我天天围着您转?”
邹充仪:“我是在气愤只有你游手好闲的看热闹!”
又过了几天,邹充仪无聊时,突发奇想,拉了丹桂问:“你想要恢复本名么?”
丹桂下意识地摇头:“怎么能是现在呢?”
邹充仪便笑着令人召集大家都来,又道:“为什么不能是现在?”
待问过同样问题,众人面面相觑,半天才有一个小宫女怯怯地问:“娘娘,婢子本姓邴,小名儿叫做阿舍,可以么?”
邹充仪点头笑道:“为什么不可以?以后大家就叫你邴阿舍。”
丹桂只觉得心头温暖,眼前雾蒙蒙的,但仍旧马上开口:“娘娘,婢子本名桑九,请娘娘赐回。”
邹充仪拉了她到身边,笑着对众人道:“我不怕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沾了九娘的光。她心心念念想恢复本名,我是为了她,才干脆让大家都自己选一下。”
丹桂听了这话,不禁哽咽起来,紧紧地抓着邹充仪的手:“娘娘,婢子如何敢当?”
邹充仪拍拍她,无限温和:“你当得的。”又问众人:“还有谁想恢复本名么?”
花期和横翠因是邹家家奴,此时自是不吭声。而四个内侍一直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此刻虽然微微动容,但仍旧袖手旁观。几个粗使宫女就都忍不住了,叽叽喳喳地都要叫回原来的名字,还有人说愿复姓,请娘娘赐名的。
邹充仪呵呵笑起来,长袖一摆:“都依你们!”
小院里,生机盎然。
只有花期。
虽然似乎活了过来,但却越来越沉默。
白天,拼命做事,什么都学,什么都做;夜里,一炉香,一个蒲团,不停地念往生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