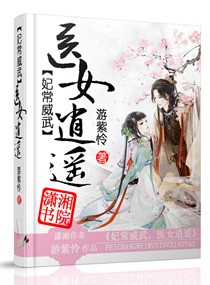妃常宫闱-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雪便也挽了她的胳膊。
“你怎么也来的这么晚?”回雪笑了笑道:“可是又睡晚了,你不用服侍皇上,却也赖床。”岑梨澜听了撇了下嘴道:“晦气死了。一大早睡不着,带着苗初在宫里散心,正撞上去承乾宫的青嫔,打破了她的婢女招儿手里端的补汤,气的她七窍生烟。骂我说“你又不用侍候皇上,这么慌里慌张的,没个消停。”我又不是故意的,被她这么一说,心下不服,嘴里说道“我不是侍候皇上。怎么青嫔娘娘这么慌里慌张,是去侍候皇上?”她便更怒了,不理我。便带着婢女走了。”
回雪听了差一点笑出来,压低了声音对岑梨澜道:“你也是个多嘴的,你弄洒了她送给荣妃的汤,还这样戳她的软肋,小心她给你使绊子。”岑梨澜听了。却并不为意。
烟紫走在前面推了把门,回雪跟岑梨澜二人便走了进去。
景仁宫已许久没来。本以为会是蛛网横结,院落荒芜,没想到一进院子,便见铺着大红的宫毯,宫毯两侧也栽种了长青灌木,虽是小小的两排,从灌木下的新土看,也是内务府新移栽的,而这两抹绿色,也让人心头猛的一阵欢喜,进到景仁宫里面,见众妃已来了不少,以前请安摆放的椅子还按照原样摆在那,只是地上的毛毯换成了大红印凤戏牡丹的图案,椅子边对称放着些乌木茶桌,茶桌后面是对开的两扇黄色镂空凤凰边帷帐,帷帐的悬钩,竟然也是赤金做成,帷帐前进门处放着一只三尺多高的飞燕舞天景德镇瓷瓶,瓷瓶一角又放着几个或红或白的花瓶,走进内室,各人按品级行了礼,回雪在椅子上挨着岑梨澜坐下,抬头见内室壁上画着一副画,画着一个侍女站在一松石之下,面含微笑,又带腼腆,但那侍女旁边却用墨汁深深的提了四个字:恭顺柔嘉。这笔迹略显苍劲,笔画却又连绵不绝,回雪一看便知是皇上题的字,这“恭顺柔嘉”四个字,用来形容原来景仁宫的主子,倒是贴切,只是不知道景仁宫今日的叶赫那拉皇后人变的如何,又会不会担的起皇上的这四个字呢,想来是皇上觉得亏欠她不少,所以竟然还题字悬于景仁宫,这种荣耀,怕是荣妃,都没有过的。一时婢女给各人上了茶,众人还没喝,便听到王福全响亮的声音在景仁宫院里喊了起来:“皇上有旨,叶赫那拉氏接旨。”说着,便带了小太监进了景仁宫内室,在大红印凤戏牡丹的宫毯上站定。
叶赫那拉氏从众妃嫔进来一进没有现身,听到王福全的声音,侧室里才算有了动静,一阵窸窸窣窣之后,便是一连串的环佩叮当,众人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今日里的叶赫地拉氏身着一件暗棕色镶金边旗袍,袍上绣着凤凰于飞的图案,袍子的下摆更绣着淙淙的流水,幽静的青山,飘逸的云朵,更有凤舞九天之祥瑞,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米白色玛瑙穿东珠朝珠,头上带着赤金钿子,发间又斜插着点翠压鬓,另一鬓边插着的凤衔珠的簪子,行走间,一阵清脆之声,人还未到,香气却是传遍了整个内室,加上内室窗户甚严,又烧着炭火,这香气更是弥久不散,闻的人脑袋发晕。叶赫那拉氏拿眼扫了扫众人, 又把眼光留在王福全身上,伸出手来道:“王公公来了,可让本宫久等。”回雪看着叶赫那拉皇后的手腕比原先瘦了不少,想来冷宫的日子并不好过,只是她瘦弱的手上又带了两个赤金点翠镶翡翠的护甲,这护甲华贵的模样,倒跟那手不很十分相衬。
王福全听叶赫那拉氏如此说,本以为她看自己来传旨,心下会高兴异常,不说赏些银两,也应该说些客气的话,但皇后此时却是一脸的高高在上,说话的神情或是口气,都是主子在冷淡的对待一个下人,王福全在宫里怎么说也算是皇上身前的红人,不管是内务府的太监宫女还是这宫里的妃嫔,谁见了自己也都是表面主子奴才,实际上对自己都是礼让三分,就连宫里的大人们,也都探着口气跟自己说话,今天在众妃面前被叶赫那拉氏这样一说,王福全心下有几分不满,但又不表现在脸上,只是张口说道:“皇上有旨,叶赫那拉氏听旨。”
皇后听了,便带着众人跪下,王福全一字一句的把旨意念完,又意味深长的说了句:“娘娘好福气,这景仁宫的荣耀,在这宫里可是独一份,奴才恭喜娘娘。”叶赫那拉氏听了,欲站起身来,王福全却又接着道:“岑梨澜岑小主接旨。郁嫔接旨。”众人听了,也只得跪着。王福全又一点点的把圣旨念完,岑梨澜因在宫里一向本分,皇上心里高兴,便封她为贵人,而素答应因是回雪的姐姐,虽已死,实在是受人陷害,如今做乱的人有了应得下场,皇上怜悯,便复素答应的妃位,还是原来的素妃。所以让回雪代为接旨。
王福全离开后,众人又对着皇后说了一会子恭维的话,皇后倒也显的很是受用,只回雪手里握着皇上的圣旨,想着姐姐怕是再也见不到这个旨意了,心下一时五味杂陈,差一点流出眼泪,因是在景仁宫,不想被别人看出,努力平复了好一阵的情绪,才算好了一些。
“这大红印凤戏牡丹的宫毯,我听内务府说,是青嫔的阿玛特意为本宫挑选的。本宫看着不错,你阿玛费心了。”皇后说着,伸出手来接过婢女端过的茶喝了一口。青嫔被皇后一夸,脸上带着骄傲的神采,嘴上却说道:“我也没什么大能耐,不过是求得皇后娘娘一笑,可有些人哪,不得皇上笑,也不能得皇后娘娘笑,整个一惹事精,就不知道留着有何用了。”说着,拿眼扫了扫岑梨澜。
众人听了青嫔的话,不禁一阵嬉笑,岑梨澜有些生气,却不能发做,只回雪淡淡的道:“能让皇后娘娘笑固然是好的,但能对娘娘恭敬,我想也很重要的吧。”
“郁嫔是什么意思?”皇后一边听着,一边摆弄着手上的护甲道。
“臣妾看这地上的宫毯,或是臣妾多心了吧。”回雪故意没有说完。皇后果然耐不住道:“你往下说。”
“这宫毯的大红色是好的,可这图案,也可能是臣妾想多了,凤戏牡丹也是好的,比如娘娘衣服上的图案,都是内务府找上好的绣娘一针一线才做出来的,说是世间就此一件,也不过分,可这衣服穿娘娘身上好看,这凤戏牡丹的图案却被臣妾们踩在脚下,臣妾真是惶恐的很,但臣妾又不是鬼,不能飞在天上,也只有踩着了,还望娘娘宽恕臣妾的大不敬之罪。”
众人听了回雪的话,不禁又是一阵笑声,笑过之后,见青嫔脸上蜡白,皇后也是冷着脸,又觉得自己的脚也是踩在宫毯的凤凰上,一时抬脚不端庄,不抬脚得罪皇后,倒让人无比尴尬起来。
“皇后娘娘,我……”青嫔欲起身解释,哪里解释的清,只得恨恨的看着回雪,皇后脸上失了刚才的笑容,比这冬日的冰霜更让人害怕,淡淡的吐出一句:“你们回吧,本宫还要抄经。”众妃嫔听了,只得行了退礼,一个个在婢女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作品相关 第一一四章 一只脚
见众人都出了景仁宫,回雪便带着烟紫留了下来,给皇后轻轻施了一礼道:“刚才臣妾乱说了话,求娘娘恕罪。”皇后听了回雪的话并不答言,只是又退回到椅子上坐着道:“本宫说了要抄经,你还有事吗?”回雪往前一步道:“臣妾前些日子让王方去了娘娘身边侍候,不知他……怎么样?”
皇后听了,坐在椅子上低头抚了抚自己的护甲,慵懒的道:“怎么,你想把他要回去?”回雪本有这个意思,一听皇后如此说,倒也不好张口,只得道:“臣妾不敢,只是……”话还没说完,便被皇后打断道:“他本是本宫的旧奴,不过一个奴才,也值得你郁嫔挂在口上,你回吧。”回雪见皇后赶自己走,一时也不好强要,只好行了退礼,刚退到廊下,便听到皇后在内室里声色俱厉的道:“还不快把这凤戏牡丹的宫毯给本宫撤下去烧了,哼,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不太毒,最毒女人心,怨不得她叫青嫔,原是配她这颗黑心。”
走出景仁宫不远,烟紫便抢上一步问道:“主子想要回王方,皇后娘娘不答应,只怕王方以后的路便更不好走了。”
“你注意景仁宫门口的小李子了吗?”回雪问道,烟紫点了点头。回雪接着道:“想来是昨晚他私放王方出去被皇后发现了,所以皇后连他一起责罚,看他的样子,应该是挨了不少板子,王方就更凶多吉少了,怎么着他也侍候姐姐一场,对我也算尽心,此事又因我而起,我不能……”
“郁嫔娘娘。您快去永和宫瞧瞧吧。”回雪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急急赶来的苗初给打断了,苗初身上只穿了件薄薄的夹袄,脸上冻的通红,一双手也早早的起了冻疮,行过礼后,便把手缩回了袖里,来回的磨着,想来是冻疮遇热便会发痒,她一路跑来。手上出汗,冻疮便更难受了。回雪见她焦急的喘着气,宫道上又不时有人走来。便也不好多问,带着二人向永和宫赶去。
自良嫔去后,便很少有人来这永和宫了,上次太后的意思,让岑梨澜住这里。不过是看她也得了皇上的宠幸,怕她跟回雪拧成了一条绳,对硕绘不利罢了,没想到太后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硕绘死猫上不了树,竟然还连带她去了庵里修行下半生。想来这暗无天日,无穷寂寞的伴着佛主的日子,也是她的报应。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虽永和宫的主子换了一茬,永和宫却还是原来的样子,琉璃黄瓦。雕花廊柱,宫墙宽厚。朱漆醒目,虽房子还在,但里面的风景却是大不相同了,夏日里阳光从院墙外照射进来,照在院子里两垄花上,烟紫也曾帮着良嫔修剪过这些枝桠,那时候承熙还很快乐,手里扯着纳兰送给她的风筝,一些欢声笑语如这些曾开放过而又枯萎的好一样,无奈的落下,又深深的融进了土里,就像人从来没有出现过,花从来没有绽放过一样,无声无息,琉璃瓦上托着厚厚的一层雪,晶莹洁白,在阳光下放射出七彩的颜色,又随着稍微升上来的一点温度慢慢的融化,一滴滴的落了下来,回雪不禁眯起了眼睛,打量着满院的萧瑟,自打岑梨澜住进永和宫后,内务府按例也分派了几个侍候的人,只是这些人如今或站在廊下,或坐在永和宫偏房的木栏上,手或揣在袖里,或抱在怀里,一副懒懒的模样。
听到永和宫内室传来“哎呦……哎呦”的声音,回雪也顾不上打量这些懒惰的奴才,只急急的进了屋子,只见岑梨澜此时正斜靠在榻上,背后垫着两个塞棉花的绒垫子,两个小宫女正束手无策的站在一边守着,岑梨澜的一只脚穿着高底青帮旗鞋,另一只脚却是褪去了鞋袜,轻轻的放在榻沿上,见褪去鞋袜的脚红肿了好大一块,就连脚踝处也起了两个燎泡,回雪不禁上前去,心疼的很,却又不从下手,只忙着道:“怎么这么不小心,伤成这样,叫太医了没有?”岑梨澜脚上生疼,嘴上却还笑着说:“已经叫了。”回雪正要问是如何伤成这样,便听到内室的帘子掀起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年轻的太医,身背一只小药箱,脸上挂着些许汗珠,顾不得擦汗,便给二人行了礼,半跪在榻前仔细的给岑梨澜看起了脚,岑梨澜因见他是年少的太医,便觉得不大好意思,伸出的脚下意识的往回缩了缩,那太医倒是面无表情,只是用手轻轻的按住了她的脚道:“奴才是太医,在太医的眼里,只有病人,并不分男女,也没有众生相,还请娘娘放松,让奴才好好给您看一看。”岑梨澜听了不禁笑了出来,没有众生相,这话说的倒像是他不是太医,而一位高僧,听了他的话,便也不排斥,伸直了脚,太医拿出一场棉布来倒上药汁,轻轻的在她的脚面上擦拭了一会,又从箱里拿出一个淡紫色的瓷瓶,把那药粉倒在她的伤处,拿出细布来轻轻的给她包扎好,另开了一副散瘀消肿的方子让小太监去抓了药,才缓缓的起了身,往后退了两步道:“娘娘的脚想来是被炭烫到了,脚面上留有的炭灰,奴才已给娘娘擦净了,如今下了方子,天又冷,伤也易好,只是请娘娘多坐着,不要轻易下地行走,不然磨破了脚,不但疼,恐会留下疤痕。”说完,又示意小宫女去拿了一床薄毯子来道:“娘娘还是盖的厚些,不要招了风,对脚上就不好了。”说着,又行了一礼,才准备背着小药箱回去,烟紫看的入神,这个太医年纪轻轻,却如此懂的关怀病人,说话又如春风拂柳,让人听了一阵暖意,不禁多看了两眼,太医退后三步准备出去时,却正好撞在她的身上,烟紫脸上一红,嘴里只喊着:“对不住了,是我……。”是我两个字说出了口,却不知道接下去怎么说了。
“是奴才太过鲁莽,请姑娘恕罪。”那太医见烟紫尴尬,便行了一礼。回雪见他知分寸,便问道:“你是新来的?”
太医又给回雪行了一礼道:“回郁嫔娘娘,奴才苏思维,因补刘太医的缺,被太医院进招入院,不懂宫里规矩,冲撞了娘娘,姑娘,还望恕罪。”回雪见他说话很是客气,薄薄的嘴唇,胡茬青灰,棱角分明的一张脸,眼神里也清澈明亮,便让他退了出去,烟紫不敢看他,只是听他嘴里刚才叫着姑娘二字,不禁心里如投了一块石子,回雪无暇注意这些,只欠身坐在榻沿上道:“宫里的炭盆都是奴才们收拾,你的暖炉平日里也是苗初捧着,怎么就伤着了脚,若留了疤,皇上不喜欢了,我看你如何是好。”
岑梨澜听了叹了口气道:“皇上喜欢不喜欢,我倒不怎么在意,自咱们在储秀宫一起住,你也知道,我不是个争宠的人,皇上的心在哪里,我也不以为意,我平日不过是喜欢看看医书罢了。”回雪听她这样说话,便屏退了身后的小宫女,让她们站在廊下守着,压低声音对她道:“你怎么说这些丧气的话,如今你可不是被皇上封为贵人了,这是好事,在这宫里,你不好好活着,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欺凌,为了你的家人,你也要活着,虽然,有生之年,恐怕我们也没有多少机会见他们了。”说完,回雪也叹了口气。
“是青嫔娘娘故意用暖炉子烫的我们主子。”苗初听她们说话,便插了一句嘴,岑梨澜想拦住,苗初却又接着道:“就是早上打翻了她送给荣妃的汤,她便记恨在心,出了景仁宫不远,奴婢见青嫔脸上没有好气色,便也不敢去招惹她,没想到她故意等我们主子到跟前,装出一副和气的样子,跟我们主子说了会子话,又装做不经心的样子,手上一滑,那暖炉连炉带炭便掉在了我们主子脚上,她比我们主子位分高,又说不是故意的,我们主子没办法,只好扯着我回来了。这不,才伤成这样。”说着,苗初转身去沏了两杯茶放在榻前的小方桌上。
回雪听了苗初的话,自然明白青嫔不单是因为那汤的事,更多的恐怕因为自己提了那宫毯的事,皇后在众妃嫔面前给了她难堪,她不过是借机给岑梨澜使绊子罢了。想到这,心里有些内疚,岑梨澜好像看明白她所想似的,淡淡一笑道:“我没事,你都是为我好,只是这青嫔,也太毒辣了点。”
回雪把桌上的茶递给岑梨澜道:“你且养着,她犯的事我们自然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总有她兜不住的时候。”
岑梨澜喝了口茶,也压低了声音道:“你最近身上可好?可有什么不舒服,这前几个月,书上说可是要好生养着,永和宫离的远,你以后可别来回的跑,若有事,我去相印殿找你。回雪低下了头,告诉她自己一切还好。”岑梨澜又半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你可少侍候皇上,万一他耐不住,你可小心你的肚子,那就得不偿失了。”
回雪点了点她的鼻尖,笑她多心了,然后说道:“你怎么这么说皇上,怎么说他也是你的夫君。”岑梨澜听了有些不以为意的道:“夫君,我的?他是全天下人的夫君吧,古人道眠花宿柳,形容天天光顾妓院青楼的男人,皇上又何尝不是这样,你当他是唯一的一个,他却视你为众人中的一个,这不公平。”回雪听岑梨澜越说越不着边际,便打断了她道:“尽是胡说,伤了脚又不是伤着了脑袋,这话让皇上听着,别说脚,你就连脑袋也不保了。”
作品相关 第一一五章 一碗凉茶
回雪正跟岑梨澜说着话,便听到永和宫院里一阵脚步声,岑梨澜赶紧把光着的脚盖进薄毯子里,不多时,王福全手拿拂尘进了屋子,给二人行过礼,便传话道:“皇上请郁嫔娘娘去一趟。”回雪听了,便从榻上起身,因惦记着永和宫里的太监宫女侍候岑梨澜不很尽心,岑梨澜本身不是个挑剔的人,又大大咧咧,苗初平日里性子也静,一些不知轻重的奴才眼里便没了主子,延禧宫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于是便向着烟紫,指了指窗外廊下的奴才,才跟着王福全去了。
烟紫心下明白回雪的意思,等她们走后,便来到廊下,召了永和宫的大小奴才站成一顺,嘴里说着:“咱们本都是做奴才的,我也本没资格站在这同大家说话,只是主子上头有交待,还请各位听仔细了。”苗初听到动静,便也掀了帘子出来,烟紫接着道:“你们主子性子好,苗初姑娘也是个宽怀的人,这是好事,大家当职也少受些委屈,但还请各位自重,不要因为主子好说话便敢不尽心,岑贵人如今伤了脚,还得大家以后好好侍候,若不然,有一星半点传到相印殿或是皇上耳里,那后果,大家可知是什么。”众人听了训话,心下跟明镜一般,这下场可能会送回内务府,也可能会挨板子,重一点的,怕是命都难保,于是都噤若寒蝉,过了一会,才有胆子大的轻声回道:“奴才们记住了。定不敢偷懒。”
岑梨澜靠在窗下不禁一阵感动,回雪如此细心周到替自己想到了,也不枉自己跟她相交一场,只是不知道,这王福全急急的叫了她去又是有什么事。
回雪到了养心殿时,皇上正坐在书案后愣神,行过礼。皇上便抬起头问她道:“你跟承熙是有交情的,朕知道,这纳兰,你也是熟悉的?”
回雪不懂皇上为何如此问,见王福全也一脸严肃的远远的站着,嘴上只好回着:“臣妾跟他们……是熟悉。”说完这话,自己心里也是无比忐忑,自己当时跟纳兰有过青涩的时候,但也绝对是相对以礼,并未干出半分伤风败俗之事。怎么如今皇上倒这样问及,难道是有人在皇上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