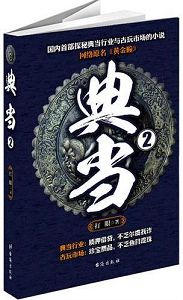黄金时代-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差公家管饭,武装民兵押着蹲在地上吃。吃完了我和陈清扬倚着拖拉机站着,过来一帮老婆娘,对她品头论足。结论是她真白,难怪搞破鞋。
我去找过人保组老郭,问他们叫我们出这种差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无非是让对面的坏人知道这边厉害,不敢过来。本来不该叫我们去,可是凑不齐人数。反正我们也不是好东西,去去也没什么的。我说去去原是不妨,你叫人别揪陈清扬的头发。搞急了老子又要往山上跑。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事,一定去说说。其实我早想上山,可是陈清扬说,算了,揪揪头发又怎么了。
我们出斗争差时,陈清扬穿我的一件学生制服。那衣服她穿上非常大,袖子能到掌心,领子拉起来能遮住脸腮。后来她把这衣服要走了。据说这衣服还在,大扫除擦玻璃她还穿。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陈清扬说,在家里刚洗过澡,她拿我那件衣服当浴衣穿!
那时她表演给女儿看,当年怎么挨斗。人是撅着的,有时还得抬脸给人家看,就和跳巴西桑巴舞一样。那孩子问道:我爸呢?陈清扬说:你爸爸坐飞机。那孩子就格格笑,觉得非常有趣。我听见这话,觉得如有芒刺在背。第一,我也没坐飞机。挨斗时是两个小四川押我,他俩非常客气,总是先道歉说:王哥,多担戴。然后把我撅出去。押她的是宣传队的两个小骚货,又撅胳膊又揪头发,照她说的好像人家对我比对她还不好,这么说对当年那两个小四川不公平。第二,我不是她爸爸。等斗完了我们,就该演节目了。把我们撵下台,撵上拖拉机,连夜开回场部去。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
我们跑回农场来,受批判,出斗争差,这也是一阵阵的。有时候团长还请我们到他家坐,说起我们犯错误,他还说,这种错误他也犯过。然后就和陈清扬谈前列腺。这时我就告辞,除非他叫我修手表。有时候对我们很坏,一礼拜出两次斗争差。这时政委说,像王二陈清扬这样的人,就是要斗争,要不大家都会跑到山上去,农场还办不办。凭心而论,政委说的也有道理,而且他没有前列腺炎。所以陈清扬书包里那双破鞋老不扔,随时备用。过了一段时间,不再叫我们出斗争差,有一回政委出去开会,团长到军务科说了说,就把我放回内地去了。
有关斗争差的事是这样的:当地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破鞋。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但是他们怎么娱乐的,我可没见过。他们斗破鞋时,总把没结婚的人都撵走。再说,那些破鞋面黑如锅底,奶袋低垂,我不爱看。
后来来了一大批军队干部,接管了农场,就下令不准斗破鞋。理由是不讲政策。但是到了军民共建时期,又下令说可以斗破鞋,团里下了命令,叫我们到宣传队报到,准备参加斗争。马上我就要逃进山去,可是陈清扬不肯跟我走。她还说,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
团里叫我们随宣传队活动,是这么交待的:我们俩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说,罪恶不彰,要注意政策。但是又说,假如群众愤怒了,要求狠狠斗我们,那就要灵活掌握。结果群众见了我们就愤怒。宣传队长是团长的人,他和我们私交也不坏,跑到招待所来和我们商量:能不能请陈大夫受点委屈?陈清扬说,没有关系。下回她就把破鞋挂在了脖子上,但是大家还是不满意。他只好让陈清扬再受点委屈。最后他说,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也不多说。您二位多担戴吧。
我和陈清扬出斗争差的时候,开头总是呆在芭蕉树后面。那里是后台。等到快轮到我们时,她就站起来,把头上的发卡取下来衔在嘴里,再一个个别好,翻起领口,拉下袖子,背过双手,等待受捆了。
陈清扬说,他们用竹批绳,综绳来捆她,总把她的手捆肿。所以她从家里带来了晾衣服的棉绳。别人也抱怨说,女人不好捆。浑身圆滚滚,一点不吃绳子。与此同时,一双大手从背后擒住她的手腕,另一双手把她紧紧捆起来,捆成五花大绑。
后来人家把她押出去,后面有人揪住她的头发,使她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低下头,所以她只能微微侧过头去,看汽灯青白色的灯光,有时她正过头来,看见一些陌生的脸,她就朝那人笑笑。这时她想,这真是个陌生的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她一点不了解。
陈清扬所了解的是,现在她是破鞋。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她知道是因为她,但为什么这样,她一点不理解。
陈清扬说,出斗争差时,人家总要揪着她头发让她往四下看,为此她把头发梳成两缕,分别用皮筋系住,这样人家一只手提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揪她的头发就特别方便。她就这样被人驾驶着看到了一切,一切部流进她心里。但是她什么都不理解。但是她很愉快,人家要她做的事她都做到了,剩下的事与她无关。她就这样在台上扮演了破鞋。
等到斗完了我们,就该演文艺节目了。我们当然没资格看,就被撵上拖拉机,拉回场部去。开拖拉机的师傅早就着急回家睡觉,早就把机器发动起来。所以连陈清扬的绑绳也来不及松开。我把她抱上拖车,然后车上颠得很,天又黑,还是解不开。到了场部以后,索性我把她扛回招待所,在电灯下慢慢解。这时候陈清场面有酡颜、说道:敦伟大友谊好吧?我都有点等不急了!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正在打开包装,于是她心花怒放,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它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现在她把自己交到了我手里。
在农场里,每回出完了斗争差,陈清扬还要求敦伟大友谊。那时总是在桌子上。我写交待材料也在那张桌子上,高度十分合适。她在那张桌上像考拉那样,快感如潮,经常禁不住喊出来。那时黑着灯,看不见她的模样。我们的后窗总是开着的,窗后是一个很陡的坡。但是总有人来探头探脑,那些脑袋露在窗台上好像树枝上的寒鸦。我那张桌子上老放着一些山梨,硬得人牙咬不动,只有猪能吃。有时她拿一个从我肩上扔出去,百发百中,中弹的从陡坡上滚下去。这种事我不那么受用,最后射出的Jing液都冷冰冰,不瞒你说,我怕打死人,像这样的事倒可以写进交待材料,可是我怕人家看出我在受审查期间继续犯错误,给我罪加一等。
黄 金 时 代
(十)
后来我们在饭店里重温伟大友谊,谈到各种事情。谈到了当年的各种可能性,谈到了我写的交待材料,还谈到了我的小和尚。那东西一听别人谈到它,就激昂起来,蠢动个不停。因此我总结道,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但是没有锤动。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为了伟大友谊,我还能光着屁股上街跑三圈。我这个人,一向不大知道要脸。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我认识那里好多人,包括赶马帮的流浪汉,山上的老景颇等等。提起会修表的王二,大家都知道。我和他们在火边喝那种两毛钱一斤的酒,能喝很多。我在他们那里大受欢迎。
除了这些人,猪场里的猪也喜欢我,因为我喂猪时,猪食里的糠比平时多三倍。然后就和司务长吵架,我说,我们猪总得吃饱吧。我身上带有很多伟大友谊,要送给一切人。因为他们都不要,所以都发泄在陈清扬身上了。
我和陈清扬在饭店里敦伟大友谊,是娱乐性的。中间退出来一次,只见小和尚上血迹斑斑。她说,年纪大了,里面有点薄,你别那么使劲。她还说,在南方呆久了,到了北方手就裂。而蛤咧油的质量下降,抹在手上一点用都不管。说完了这些话,她拿出一小瓶甘油来,抹在小和尚上面。然后正着敦,说话方便。我就像一根待解的木料,躺在她分开的双腿中间。
陈清扬脸上有很多浅浅的皱纹,在灯光下好像一条条金线。我吻她的嘴,她没反对。这就是说,她的嘴唇很柔软,而且分开了。以前她不让我吻她嘴唇,让我吻她下巴和脖子交界的地方。她说,这样刺激性欲。然后继续谈到过去的事。
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做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听了这话,我笑起来。但是她说,我们在干的事算不上罪孽。我们有伟大友谊,一起逃亡,一起出斗争差,过了二十年又见面,她当然要分开两腿让我趴进来。所以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更主要的是,她对这罪恶一无所知。
然后她又一次呼吸急促起来。她的脸变得赤红,两腿把我用力夹紧,身体在我下面绷紧,压抑的叫声一次又一次穿过牙关,过了很久才松驰下来。这时她说很不坏。
很不坏之后,她还说这不是罪孽。因为她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她是如此无知,所以她无罪。一切法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陈清扬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要说明她怎会有这种见识,一切都要回溯到那一回我从医院回来,从她那里经过进了山。我叫她去看我,她一直在犹豫。等到她下定了决心,穿过中午的热风,来到我的草房前面,那一瞬间,她心里有很多美丽的想像。等到她进了那间草房,看见我的小和尚直挺挺,像一件丑恶的刑具。那时她惊叫起来,放弃了一切希望。
陈清扬说,在此之前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她走到院子里去。那时节她穿着棉衣,艰难地爬过院门的门槛。忽然一粒砂粒钻进了她的眼睛。这是那么的疼,冷风又是那样的割脸,眼泪不停地流。她觉得难以忍受,立刻大哭起来,企图在一张小床上哭醒,这是与生俱来的积习,根深蒂固。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陈清扬说,她去找我时,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穿过衣襟,爬到身上。我呆的那个地方可算是空山无人。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在一件薄薄的白大褂下,她已经脱得精光。那时她心里也有很多奢望。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
陈清扬说,她到山里找我时,爬过光秃秃的山岗。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吹过她的性敏感带,那时她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它放散开,就如山野上的凤。她想到了我们的伟大友谊,想起我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去。她还记得我长了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论证她是破鞋时,目光笔直地看着她。她感到需要我,我们可以合并,成为雄雌一体。就如幼小时她爬出门槛,感到了外面的风。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天上还有鸽子在飞。鸽哨的声音叫人终身难忘。此时她想和我交谈,正如那时节她渴望和外面的世界合为一体,溶化到天地中去。假如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那实在是太寂寞了。
陈清扬说,她到我的小草房里去时,想到了一切东西,就是没想到小和尚。那东西太丑,简直不配出现在梦幻里。当时陈清扬也想大哭一场,但是哭不出来,好像被人捏住了喉咙。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真实就是无法醒来。那一瞬间她终于明白了在世界上有些什么,下一瞬间她就下定了决心,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心里快乐异常。
陈清扬还说,那一瞬间,她又想起了在门槛上痛哭的时刻。那时她哭了又哭,总是哭不醒。而痛苦也没有一点减小的意思。她哭了很久,总是不死心。她一直不死心,直到二十年后面对小和尚。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面对小和尚。但是以前她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
陈清扬说,她面对这丑恶的东西,想到了伟大友谊。大学里有个女同学,长得丑恶如鬼(或者说,长得也是这个模样),却非要和她睡一个床。不但如此,到夜深入静的时候,还要吻她的嘴,摸她的Ru房。说实在的,她没有这方面的嗜好。但是为了交情,她忍住了。如今这个东西张牙舞爪,所要求的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就让它如愿以尝,也算是交友之道。所以她走上前来,把它的丑恶深深埋葬,心里快乐异常。
陈清扬说,到那时她还相信自己是无辜的。甚至直到她和我逃进深山里去,几乎每天都敦伟大友谊。她说这丝毫也不能说明她有多么坏,因为她不知道我和我的小和尚为什么要这样。她这样做是为了伟大友谊,伟大友谊是一种诺言。守信肯定不是罪孽。她许诺过要帮助我,而且是在一切方面。但是我在深山里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彻底玷污了她的清白。
黄 金 时 代
(十一)
我写了很长时间交待材料,领导上总说,交待得不彻底,还要继续交待。所以我以为,我的下半辈子要在交待中度过。最后陈清扬写了一篇交待材料,没给我看,就交到了人保组。此后就再没让我们写材料。不但如此,也不叫我们出斗争差。不但如此,陈清扬对我也冷淡起来。我没情没绪地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回了内地。她到底写了什么,我怎么也猜不出来。
从云南回来时我损失了一切东西:我的枪,我的刀,我的工具,只多了一样东西,就是档案袋鼓了起来。那里面有我自己写的材料,从此不管我到什么地方,人家都能知道我是流氓。所得的好处是比别人早回城,但是早回来没什么好,还得到京郊插队。
我到云南时,带了很全的工具,桌拿子、小台钳都有。除了钳工家具,还有一套修表工具。住在刘大爹后山上时,我用它给人看手表。虽然空山寂寂,有些马帮却从那里过。有人让我鉴定走私表,我说值多少就值多少。当然不是白干。所以我在山上很活得过。要是不下来,现在也是万元户。
至于那把双筒猎枪,也是一宝。原来当地卡宾枪老套筒都不希罕,就是没见过那玩意。筒子那么粗,又是两个管,我拿了它很能唬人。要不人家早把我们抢了。我,特别是刘老爹,人家不会抢,恐怕要把陈清扬抢走。至于我的刀,老拴在一条牛皮大带上。牛皮大带又老拴陈清扬腰上。睡觉Zuo爱都不摘下来。她觉得带刀很气派。所以这把刀可以说已经属于陈清扬。枪和刀我已说过,被人保组要走了。我的工具下山时就没带下来,就放在山上,准备不顺利时再往山上跑。回来时行色匆匆,没顾上去拿,因此我成了彻底的穷光蛋。
我对陈清扬说,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在最后一篇交待里她写了什么。她说,现在不能告诉我,要告诉我这件事,只能等到了分手的时候,第二天她要回上海,她叫我送她上车站。
陈清扬在各个方面都和我不同。天亮以后,洗了个冷水澡(没有热水了),她穿戴起来。从内衣到外衣,她都是一个香喷喷的LADY。而我从内衣到外衣都是一个地道的土流氓,无怪人家把她的交待材料抽了出来,不肯抽出我的。这就是说,她那破裂的Chu女膜长了起来。而我呢,根本就没长过那个东西。除此之外,我还犯了教唆之罪,我们在一起犯了很多错误,既然她不知罪,只好都算在我账上。
我们结了账,走到街上去。这时我想,她那篇交待材料一定淫秽万分。看交待材料的人都心硬如铁,水平无比之高,能叫人家看了受不住,那还好得了?陈清扬说,那篇材料里什么也没写,只有她真实的罪孽。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撩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耳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待材料的人,一个个都面红耳赤,好像小和尚。后来人保组的人找了她好几回,让她拿回去重写,但是她说,这是真实情况,一个字都不能改。人家只好把这个东西放进了我们的档案袋。
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在人保组里,人家把各种交待材料拿给她看,就是想让她明白,谁也不这么写交待。但是她偏要这么写。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陈清扬告诉我这件事以后,火车就开走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