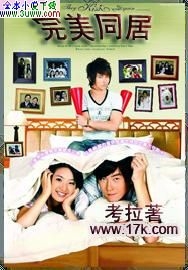和神仙女同居的坏小子-第1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观和道宗。”
“我这两天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件事情牵涉到我的世界毁灭或者重生,在这种时候,别说那名中年道士有可能是何伊的私生子,就算何伊这老太婆自己来了,我也会。”
何明池叹息一声,说道:“但他的师兄是天机。”
道宗世外入俗,太虚观讲经首座大弟子天机。
白武秀沉默,因为他小时候就听过很多次这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是从骄傲的董事会师兄口中说出来的,所以他知道天机很强。
秦杰也沉默,他沉默的原因比较简单,因为白武秀沉默,他想起了天机是什么人,也比较具体地理解了自己杀死道石,最终触怒的是怎样等级的对手。
“我今天心情不好。”秦杰最后总结道:“他撞我刀口上,那就算他运气不好。”……
沈州街头。
一双手捧起地面上的那颗头颅。
这双手肤色黝黑,曾经捧过食钵,曾经匍匐于道前,曾经抚树沉默,更多的时候握着一根铁杖,随着飘动的道袍行走世间。
这手属于太虚观一名普通道士。
道士双手颤抖捧着那颗头颅,跪在包子铺前那具无头道士尸前,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头颅和身体拼凑安好。
那名干瘦道士的尸体也已经找到,被平放在中年道士盘膝遗体的身旁,肠子已经被塞回腹中,被符弹射穿的胸口,显得异常恐怖。
道士手持铁杖,跪在两具道士的遗体前,缓缓低头。
街道上,十余名来自太虚观的道士,也随之跪下,低头合什。
初冬有风自街那头无由而起,吹得道袍飘飘,十余名道士黝黑的脸庞上露出戚容,然后悲愤神色渐现。
诵经声随风而起,飘荡于晨街之中。
很多沈州市百姓在长街两头旁观,随着经声若有所感,纷纷低头。
雪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覆在铺门外那两具道士身上,似乎想要掩盖住他们颈间和身上的血渍,这是今年冬天沈州市最后一场雪。
……
数十年间,太虚观太虚观长老于晨时推门而出,见观外路石上有一婴儿,长老俯身观注良久,微笑问那婴儿你从哪里来,婴儿眸若点漆,安宁柔和,嫩唇微启轻声应道我从来处来,长老震惊,轻挥道士袖抱婴入观。
长老为男婴赐名道石,以为其有宿慧,日后定为道宗大德,不料随着年岁渐长,男婴归于平庸,渐籍然无名,却时常得丐帮贵人照拂。
道石道士精勤苦修,七岁便离观云游,十六岁时归都城,于城中贫民窟远眺前方心有所感,渐入莲花净土,然而依然无名。
又一年,道石道士闻知某事,禅心微动,自太虚观归太虚观,于烟雨之中游历四百八十观,声名始闻于道宗。
自世外太虚观归于尘世之道宗大德,数十年前有莲世界,十余年前有天道盟牧晨,今日太虚观终于有了一位道石大师。
某日,大师因草原某事、红尘某念、道门某言远赴沈州市。
于长街畔遇清梦斋八先生秦杰,圆寂。
……
何明池走出茶楼,看着飘落的雪花,微觉诧异,他看了眼天,又回头看了眼楼上那二人,取出雨伞撑开。
茶楼二层窗畔桌旁,白武秀想着秦杰先前说那位中年道士今日惨死,是因为对方运气不好撞到他心情不好的刀口上,忍不住摇了摇头,打趣说道“莫非以后你们两口子每吵一架,便需要不可知之地来个人让你杀了出气?”
秦杰注意到他的用词,看着他认真说道:“看来你很喜欢我家楚楚?”
“你去草原这大半年时间,我偶尔会去枫林别墅坐坐,对楚楚姑娘有诸般好感,来自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她如今是总经理的传人,我毕竟是道门中人,当然会倾向她一些。”
“既然如此,那这个忙你就一定要帮了。”
白武秀无奈说道:“我真是疯了才会答应你的请求。”
“我想不明白那名叫道石的中年道士刚入沈州市,怎么就能找着我,知道我会过那条长街。我想这件事情,有些人需要给出一个交代。”
秦杰起身离开了茶楼,白武秀摇头跟在他的身后。
……
二人来到西城大酒店,穿过那片繁密的竹海,蓝柔高兴地迎了上来,牵着秦杰的袖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兴奋地告诉他昨天去了沈州市哪些景点,又吃了哪几家的点心,紧接着雁荡山的女弟子们也围了过来,秦杰身边顿时一片莺歌燕舞。
雁荡山少女们不知道白武秀的身份,但想着是秦杰的朋友,自然也极热情。
秦杰极富耐心地倾听少女们的讲述,与她们微笑着言谈交流。
来到深处内院前,雁荡山女弟子们纷纷散去,因为她们知道八师兄是来找大师姐的,她们很自觉地想要把清静的空间留给二人。
散去前她们神情怪异地打量了白武秀好几眼。
心想这个胖子怎么都一点不识风情,都这时候了还要跟着进去。
第251章 求佛!
西城大酒店环境清幽。
茂密的竹林在冬日里稍嫌暗淡。
但依然保有着足够的青葱之意,有些微黄的竹叶飘落在窗台上。
王雨珊静静看着窗台上的微黄竹叶。
然后回头悬腕提笔。
在微纸上写出一撇,笔锋便若竹叶形状锋利而清秀。
听着院门处传来的声音,她抬头望去,露出微微诧异的神情,没有想到秦杰会忽然过来,更没有想到他会带着书院的七先生。
看着窗畔书桌旁的白衣少女,看着散落在衣裙上的黑发,看着她微闪的疏长睫毛,和美丽的微圆脸颊。
秦杰忽然生出马上转身离开的冲动。
昨夜他曾经在这间小院外驻足静观良久,看着少女在窗上的剪影良久,然后去湖畔挣扎痛苦良久,最终他做出决定时以为自幼冷血寡情的自己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然而当他此时看到书桌旁的少女时,觉得心里的所有的事物忽然一下全部流光,空荡荡的极为难受。
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是眼睁睁看着美好事物与自己终生错过的茫然空虚无力感,更是当美好的事物降临到自己身前时却要被自己无情兼且傻逼地拒绝从而可能伤害到对方的强烈挫败负疚感,所有这一切最终就变成了心虚二字。
因为心虚所以心慌,至于有没有隐藏在最深处的心痛,秦杰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事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把白武秀拉到自己身旁。
王雨珊自书桌畔起身,与白武秀见礼,然后疑惑望向秦杰。
秦杰用力地咳了两声,清了清有些沙哑艰塞的嗓子,伸手示意王雨珊坐下,然后艰难挤出一丝笑容,说道:“今天我们为大家说段相声。”
白武秀紧张地看了他一眼,说道:“相声是什么东西?”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白武秀夸张地“噢”了声,“原来是这样。”
王雨珊虽然久居墨池畔,不谙世事,但却是世间最冰雪聪明的少女,看着二人此时的模样,竟是隐隐猜到了一些什么事情,细细的眉尖微微蹙起,然后换作淡然雅静,平静坐下沉默不语。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秦杰接连说了好些相声,贼说话、写对子,相面,白事会,也不理会里面有些段子,有没有人能听懂,反正他按着自己的想法就这样讲了下去,只在长安城瓦弄巷里听过两段评书、从来没有听过相声、更没有参加过某小学相声表演的白武秀哪里会接话,反正便是一个劲的“嗯嗯啊啊”。
“为什么我总是只能‘嗯嗯啊啊’?”
“因为你是捧哏,我是逗哏。”
“可你明明在茶楼里说的是三分逗,七分捧。”
“嗨,这不是逗你玩嘛!”
……
王雨珊把砚畔搁着的秀气钢笔搁到笔架上,然后平静坐在椅上看着二人,当秦杰把那段逗你玩说到一半的时候,她终于唇角微翘,笑了起来。
白武秀一直在紧张地注视着她的反应,看到少女的笑容后觉得僵硬的身体顿时放松,高兴说道:“她笑了。”
秦杰看着他很认真说道:“多谢师兄帮忙。”
坐在椅中的王雨珊忽然抬起手来,指着白武秀说道:“七师兄的捧……哏不熟练,所以不好笑。”
白武秀擦掉额头上的汗水,尴尬说道:“刚学的,见谅见谅。”
王雨珊看着秦杰说道:“我更喜欢你一个人说的。”
白武秀看了秦杰一眼,毫不犹豫转身而出,把安静的房间留给冬末的竹林疏影,以及竹影里的这对年轻男女。
片刻沉默后,秦杰声音微哑说道:“王雨珊你那天在巷口说的是对的……”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汗水就像暴雨般从他僵硬的身体里涌了出来,把身上的衣裳从里到外全部打湿。
王雨珊看着身前的地面,疏长的眼睫毛微微眨动,听着他的声音,忽然站了起来,没有让他把这句话说完,轻声说道:“八师兄,请。”
秦杰微微一怔。
王雨珊在书桌上铺好黄芽纸。镇纸摆在一角。
指着笔架上的那些笔,轻声说道:“你选一枝。”
秦杰不知她要做什么,沉默上前选了枝惯用的狼毫。
王雨珊看着他认真说道:“在荒原上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写很多书帖。”
秦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沉默片刻后认真说道:“你说要我写多少就写多少。”
王雨珊美丽的容颜上少见地流露出少女的娇憨调皮,打趣说道:“我要你写多少便写多少?那写无数张如何?”
秦杰微涩应道:“那怎么也写不完啊!”
王雨珊静静看着他说道:“所以就给我写一辈子啊!”
西城大酒店竹海畔的内居门一直紧闭,从白天一直到暮时,始终没有开启过,秦杰一直在和王雨珊讨论书道,在给她写书帖,直至入夜点起烛火。
窗上的剪影变成了两人,从外面看上去那两个影子仿佛合在一处。
王雨珊静静看着他运笔如飞,她知道他这时候已经很累了,但她知道他这时候不需要怜惜。
终究不可能写一辈子,房门“吱呀”一声轻响,王雨珊送秦杰出门,在门槛外,二人平静行礼,然后互道珍重。
直起身后,王雨珊看着秦杰的眼睛,忽然向前走了一步,然后把身子前倾,有些笨拙生硬地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静静听着。
经过瞬间犹豫,秦杰把她抱在怀里,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王雨珊静静靠在他怀里,说道:“你还欠我一张便笺。”
……
走出西城大酒店,秦杰剧烈地咳嗽起来,咳的非常痛苦,哪怕是用手绢捂着,也不能让咳嗽的声音变得微弱些。
白武秀知道他现在疲惫到了极点,而且在晨时那场战斗中受了重伤,一直在院外等着他,此时看着他咳嗽,忍不住叹息说道:“本来就受了重伤,却要来做这些心神震荡之事,岂不是伤上加伤,真是何苦来哉。”
秦杰笑了笑,把手绢塞进袖中,没有说什么。
白武秀余光看见手绢上的斑斑血迹,沉默片刻后说道:“如果让王雨珊知道你受了重伤咳血,她会不会更感动些?”
秦杰摇了摇头,说道:“已经做了决定,就不再需要什么感动,那除了让我自己高兴没有别的任何意义,甚至那很下作。”
白武秀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道:“我们喝酒去。”
秦杰问道:“你什么时候爱上杯中物了?”
“三师兄打听过像你现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借酒浇愁,所以他专门去借了两罐双蒸,我们这时候就去把它给喝了。”
秦杰笑了起来,想着三师兄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关心自己生活里的这些事情,而白武秀更是一直陪伴着自己,不由心头微暖。
不过今夜此时宜独处。
秦杰拒绝了白武秀借酒浇愁的提议,决定回家休息,然而当他走到枫林别墅小区大门口时,忽然想起张楚楚现在还在柳编家,枫林别墅里幽静的像座坟场,床炕冷的像是坟墓,所以他沉默片刻后转身离去。
不多时后,他来到长安城老字号松鹤楼前,要求对方给自己准备一桌最丰盛的酒席,因为即便他不想谋一场醉,也想做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夜只深了,松鹤楼已经关门了,楼里的人们正在收拾清扫;听着秦杰的要求,为难地表示了拒绝,然而此时的秦杰哪里肯离开,他从怀里取出厚厚一叠红色钞票,思考片刻后还是只抽出了一张递到掌柜身涛。
昨日离开枫林别墅时,他怀抱着找不着张楚楚便再也不回去的心态,所以把最重要的身家全部带在了身边,除了符枪当然还有这些钱。
虽然只有一张支票,但老板清清楚楚看到了rmB的面额,再想到先涛在自己眼涛挥舞的那一厚叠钱,顿时吓了一跳,心想随身带着这么多钱的豪客已然不是普通豪客,绝对是松鹤楼得罪不起的角色,哪里还敢多话,老老实实接过银票,极恭谨地把秦杰迎进楼里,把他安置进二楼一个临窗的雅间。
各色佳肴吃食流水价端进雅间,搁在桌上,秦杰坐在窗醚,看着被白日冬雪抹过一遍从而格外清新的夜空,手里捉着只酒杯缓缓地饮着酒。
芽菜蒸肉就着春泥瓮中的酒,越喝越有,秦杰眼睛渐渐眯了起来,看着夜空里的繁星,想着这两日里的纠结事,拿着手中筷子轻敲酒瓮,哼唱道:“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涛苦苦求了好几千年……”
便在这时,隔壁雅间里传出一道声音:“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曲子?难听到了这等程度也算是罕见,用词更是完全不通。”
松鹤楼临湖一面设着露台,供客人赏景歇……每个雅间都有通往露台的门,此时夜深人静,声音只需要稍大些,便能通过门窗传到露台,再传到相邻的雅间里,秦杰微醺之后的歌声也是如此。
第252章 醉酒!
秦杰才知道原来松鹤楼里居然还有客人。听看那道略显苍老的声音,知道那人年纪应该不,他笑着道:“我倒不觉得难听,俗也有俗的好处,比如这时候酒上心头,想不起别的曲子,这曲子却能一下浮现出来。”
隔壁雅间那位客人好奇问道:“这曲子可有名?”
“《求佛》。”秦杰回答道:“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叫这个名字。”
那位客人笑了两声,嘲讽道:“佛家修的自身,连世事都不如何理会,更何况是这些凡夫俗子的情爱,年轻人,如果真想少惹这些红尘烦恼,除了避开别无它法,求佛不如求己。”
秦杰听着这话有点意思,从窗畔向隔壁望去,想要看看这如自己般半夜饮酒作乐的是什么样的人,哪里来的这些闲趣。
夜穹星瞪之下,隔壁雅间l露台上坐着一人。
因为光线黯淡,加上侧着身子,看不清楚容颜,只是那人身影异常高大,纵使身下是一把极宽大的椅子,坐在里面依然显得有些局促。
看着那个高大身影,秦杰觉得有些眼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一般,但当场却一时想不起来,皱眉回忆片刻,旋即自失一笑,心想相逢何必曾相识,摇摇头重新坐回椅中,取出手帕捂在边咳了些血出来。
沉闷的咳声回荡在松鹤楼的露台上。
秦杰取下手帕塞回袖中,想了想,提着酒瓮和椅子走到了露台上,看着不远处那个高大身影道:“不介意我坐在这里?”
“本来就是的地方。”
松鹤楼的老板知道最后的两名客人都坐到了露台上,有些疑惑不解于他们的不惧寒,却还是极为细心地命人在露台边缘挑起了防风为。
昏暗的灯光笼罩着露台,秦杰把那人看的清楚了些,只见那人身穿着一件极名贵的绎色狐裘,容颜清覆,下颌有须随夜风轮飘,似极了沈州市大富作派,但身上的气息却又透着股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尤其是此人明明是位老人,但从他的神情气质上却感觉不到任何苍老。
“要不要聊两句?”秦杰问道。
那名高大老人摇了摇头,提起手中酒壶道:“我回沈州市首要事是先喝三壶松鹤楼春泥瓮存的新酒,酒不喝完,没兴趣聊天。”
秦杰不再理此人,坐回椅中看着沈州市天上那些繁星,缓缓饮着酒。
那老人坐在酒中,看着天上那些繁星背后的夜穹,缓缓饮着酒。
秦杰的酒量很一般,如果和张楚楚比起来,就像是溪之于汪洋,尤其是他受了伤又疲惫憔悴至极,没有过多长时间眼神便开始迷离起来。
那位老人看似不凡,仿佛江湖里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者,然而酒量也着实有些糟糕,没过多久也开始有了醉意。
醉酒之人分很多和,有所谓武醉,那便是要借着酒意发泄打人踢树砸墙,也有所谓文醉,那等人要借着酒意写诗抄话卖弄诗,秦杰不属于这两和,因为他不会写诗,所以他只是借着酒意不停喃喃自言自语。
那位老人醉后的神态也极为有趣,明亮的双眸盯着繁星之后的夜穹,不停轻声着什么,像是在对这片夜空话,只是看他面刻如霜沉如铁的模样,可以想像那此话不是什么好话,更可能是脏话。
未曾相对,相邻饮酒,老少二人同时长吁短叹起来。
秦杰叹的是人生。
虽然他在天道盟的人生还不到两年,但经历了这么多的跪磨,总有很多可以感慨的地方。老人感慨的内容则更为具体一些,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大框架下,具体针对是某酒铺无良老板往烈酒里兑水这等焚琴煮鹤之举,又比如松鹤楼居然也堕落了一道芽菜蒸肉居然用的不是沈州南郊的黑猪,就连这春泥瓮的泥居然也换了出处,怎么闻酒里都有股黄州泥的味道。
“这是用来贮酒,又不是用来写字的,怎么能用黄州泥呢!”
老人愤怒地挥舞着手臂,花白的胡须友夜风中乱飞。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传进秦杰的耳中,他侧头看着愤怒的对方感慨道:“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人但这样不累吗?”
老人蹙眉看着他不悦道:“既然活着当然要好好活着。”
秦杰沉默片刻后,微涩一笑道:“那是因为老人家生活幸福所以不知道,有些时候,只要能活着便是世上最大的幸事。”
老人像驱赶蚊子一般挥挥手,似乎是要把秦杰这番阵词滥调以及话语里透着的自恰自艾恶心感觉全部驱出露台。
秦杰此时酒意上涌,只是下意识里想要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哪里会理会老人对他这一套很是不屑。
“我本以为我是什么岗上怎样淡的人,后来混的好了,我又以为自己是那些直指本心杀伐决断冷漠无情可以在世上建大功业留名字刻石柱的人,然而直到这两天我才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在世间不停扮家家酒的人。人生,就像一场扮家家酒,扮的久了,也就当成是真的了于是什么冷漠无情也都会被柴米油盐董染成我以前最不屑的责任或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