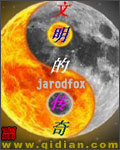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医生并没有独占分析专利的历史依据。
相反,直到最近为止他们始终是以一切可能损害分析的手段——从最浅薄的嘲弄到最恶毒的中伤——来对待它的。你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回答说这已经属于过去,不见得会影响将来。我同意,但是我所看到的将来恐怕同你预见的并不一致。
请允许我改变“庸医”这个词的法定意义,而赋予它应有的意义。
根据法律,庸医就是没有证明他是医生的正式文凭而给患者治病的人。
我倒愿意提出另一个定义:庸医就是没有从事治疗工作所必须的知识与能力而给患者治病的人。以这个定义为立足点,我冒昧提出这样一个见解:在分析领域构成庸医主力军的就是医生——这一情况不仅限于欧洲国家。他们常常是没有学过也没有理解分析疗法就从事分析治疗工作。
你一定会反驳说,这样做从良心上说不过去,你没法相信一个医生竟能这样做,不管怎么说,一个医生毕竟懂得医学文凭并不等于许可证①。患者也决不是违法者,我们时刻都应相信医生总是真心诚意想要治好患者的病,即使他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你这样反驳是没用的。
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希望他们确实像你所认为的那样。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一个医生是怎么可能在精神分析中采用一种他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会小心避免的方法的。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一个医生在医学院所接受的训练同他后来从事精神分析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是多少相对立的。他的注意力被引到了有关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方面的各种可以客观地考察清楚的事实上,而医疗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这些事实的正确鉴别和合理影响的。他对人生问题的考虑完全局限于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范围,亦即通过那些在无生命本质中也能观察到的力量所起作用来解释的内容。生命现象的精神方面引不起他的兴趣;医学并不涉及对更高智力功能的研究,这种研究属于另一学科的任务。
只有精神病学可以处理精神功能的紊乱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以什么方式、抱着什么目的来处理这一问题的。它是要寻找精神疾病的肉体成
①即并不等于给他私人开业的执照。
因,并像对待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它们。
精神病学这样做并无不当,医学教育显然也非常出色。
如果有人把它说成片面,他就必须首先找到他据以指责这一特征的立足点。
每一门科学本身都是片面的。
它们必须如此,因为它们都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课题、特定的观点和特定的方法。抬高某一门科学以贬低另一门科学,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根本不愿这样做。归根到底,物理学不能抹杀化学的价值,它既不能取代化学,又不能被化学所取代。
精神分析学作为研究无意识心理的科学。
()免费TXT小说下载
无疑是特别片面的。
因此,我们不能对医学科学拥有的片面权利表示异议。
如果要从科学的医学理论转到实用的治疗方法,我们只需要找到我们所寻找的立足点就行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他会使我们想到,即使是那么难以把握的精神现象也是不应该从生活的图景中抹掉的。
确实,神经症患者是复杂得令人失望的人,无论是治疗学还是法学和兵役制都是一样,对他们无可奈何。
但是他们还是存在,需要医学对他们特别的关心。
然而医学教育对于理解和治疗他们却是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从我们区别为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来看,我们可以指望有一天从有机生物学和化学通向神经症领域的知识道路能畅通无阻——更希望它们能互相产生影响。
这一天似乎仍然很遥远,目前我们从医学的途径还无法触及这种疾病的真相。
倘若医学教育仅仅是本能在神经症领域给医生们指出方向,那倒还可以容忍。可是它所做的不仅仅是如此而已,它还给医生们灌输了一种虚假的、有害的态度。
对于生命的心理因素没有产生兴趣的医生往往容易低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把它们斥之为非科学的现象。
正因如此,他们就不能真正严肃地看待同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的任何现象,从而也认识不到他们在这方面应尽的职责。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外行一样陷入了对心理研究缺乏重视的境地,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毫无疑问,既然神经症患者也是病人,也来向医生求医,他们当然必须得到治疗。
医生应该随时乐意进行一些新的试验。
但是何必自讨苦吃去做这种费力而又乏味的事呢?
我们可以应付自如,谁能说得准他们在精神分析学院教授的内容有没有用呢?——对这方面的问题了解得越少的医生就变得越大胆;只有真正了解实情的人才会谦虚,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的知识是多么欠缺。
由此看来,你为了安慰我而提出来的分析专门性与医学其他分支专门性之间的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外科、眼科等等医学分支说来,医学院本身提供了进一步教育的机会。
分析训练学院数量少,历史短,也没有权威性,医学院始终不承认它们,并对它们置之不理。
年轻的医生一直都不得不极大地信赖自己的老师,以致很少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因此,要是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一个尚无公认权威的领域里充当一下评论家,他们自然会高兴地抓住不放。
他们以精神分析医生(其实是庸医)的身分出现还有其他的好处,如果他们试图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他们的白内障摘除术和角膜切除术就会失败,病人就再也不上门来诊,他们的冒险生涯也就很快告终了。
从事分析治疗却较为安全。公众已经被眼科手术一般都能成功的事实娇惯坏了,因此总是指望手术后能够痊愈,但要是一个“神经症专家”未能使病人恢复健康,谁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人们还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娇惯坏:神经病专家至少“在这种疾病中花费了很多心血”,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只好走着瞧。
就拿女人来说吧,首先是来月经,然后是结婚,接着是绝经,最后就是死亡,一劳永逸。而且,精神分析者对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医疗工作也是那么不明显,以致没法找到指责的理由。
他治病不用医疗器械,也不用药。
他只是同患者谈话,试图通过谈话向他灌输什么或者使他发泄出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分析者避免触及令人痛苦、令人不安的话题的话。
一个在医疗中不拘泥于课本知识的分析者无疑不会忽略改进分析方法的尝试,总会努力拔去分析的毒牙,使患者不对此感到讨厌,不过他应该停留于这一步才是明智的。因为他要是真的敢于唤起患者的抵抗,却又不知如何对付它们,那说实在的,他就真的会使自己不受欢迎。
为了诚实起见,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个未受训练的分析者对他的患者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一个技术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小。分析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充其量只是使患者白费精力和费用。延误或减少治愈的机会。再进一步说,分析疗法的名声当然也会降低。这一切都是极不理想的,但是同外科庸医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危险根本不能相比。根据我的判断,即使是拙劣的分析治疗所造成的病情严重加剧或持续加剧也不必害怕。过一段时间这些不良的反应就会自然消失。同触发疾病的生活创伤相比,这一点点失误算不了什么。事实无非是,以不合适的方法试图治愈,因而没有给患者带来益处。
“我一直在听你谈论分析中的庸医,没有打断你,不过我倒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你好像难以克服对历史解释中的医疗行业的敌视态度。但是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要从事分析,那就应该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来从事。
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种训练吗?“
我想大概是这样。只要医学院对分析训练机构的态度保持不变,医生们就难以抵挡贪图方便的诱惑力。
“不过你好像始终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达对外行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的推测是,因为不可能阻止想要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说是出于报复而想通过剥夺他们在分析中的垄断权并把这一医学活动向外行敞开大门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种更不偏激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强调这个要求:凡没有经过特定训练获得分析权利的人都不应从事分析工作。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你究竟要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呢?”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一步,而且是否会考虑到那一步我也还说不准。
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问题,并首先触及一个特殊的要点。据说当权者在医学界的煽动下想要彻底禁止外行从事分析治疗,这样的禁令也会影响到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界会员,而这些会员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已在实践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术。
如果这一禁令付诸实施,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有一些人被剥夺了从事某种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得很好的活动的权利,而另一些无疑也具有类似把握的人却可以自由从事这同一项活动。准确说来,这不是法律应该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一特殊问题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难以解决的。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们很可能会移居到德国,在那儿没有法律会阻止他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认。只要希望使他们摆脱这一禁令,减轻法律的严厉程度,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做到的。
在奥地利帝国,允许一些臭名昭著的庸医亲手从事某些领域的医疗活动——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真实能力——是经常发生的事。
这类人大都是农民行医者,他们的推荐证明似乎往往是由某一位公爵夫人——这种贵妇人曾经多得很——提供的;但是这在城镇居民中根据一种不同的、仅仅是专家的保证也应该可能做到。这样一条禁令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因为有了这条禁令之后,它就不能接受来自非医学界的训练学员。
这样一来,一项在其他国家被准许自由发展的智力活动又会在我国遭到阻制。我是最不愿意声称自己有能力对法律和各种规章作出评判的人,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我们的反庸医法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如今我们多么向往的德国国情①;把这条法律应用于精神分析的现状不免有点时代错误,因为在该法律付诸实施时精神分析还没有问世,神经性疾病
①这当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
的特异本质也还没有被认识到。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在我看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似乎更为重要。精神分析的实施是否应该普遍受制于官方的干涉?让它自然发展是否更为有利?此时此地我当然不想就这个问题作出决断,但是我想冒昧地在你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供你考虑。在我们国家,热衷于禁令早已成为惯例;也就是说,总有人喜欢把别人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喜欢干涉,喜欢禁止,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这种做法并未结出什么特别好的果实。
在我们这个新的奥地利共和国,情况似乎也还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凭想象认为你在判断我们正在考虑的精神分析问题上要表达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并不知道你是否有愿望或有影响去同这种官僚倾向抗争。
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向你表达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浅见。
在我看来,过多的规章和禁令会损害法律的威信。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禁令较少的地方,人们总是小心的遵循;而在那些每走一步你都伴随着禁令的地方,人们反倒不知不觉地对此置若罔闻了。而且,即使有人愿意认为法律和规章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认为它们经常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并伤害我们的正义感,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会伤害我们的正义感,认为从当权者的呆滞僵化来看,常常除了大胆违反以外没有其他纠正这些有弊无利的法律的办法,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渴望保持对法律和规章的尊敬,那么他在制订任何法律和规章之前,都应该首先肯定能够很容易监视它们是被遵守还是被侵犯,否则还是不制订为好。
我在前面所引用的关于医生从事分析治疗的观点,有很多都可以在此重复,因为它们也同样适用于法律正在竭力阻止的外行从事名符其实的分析治疗这一情况。
分析治疗的过程极不明显,它既不用药也不用任何医疗器械。
其主要内容只是谈话,交流思想;要证实一个外行的确是在从事“分析”相当容易,只要他宣称自己只是在提供鼓励和解释,只是试图使那些正在寻求精神援助的人接受健康人的影响。仅仅因为医生有时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要禁止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可能的。在英语国家,基督教科学派①的实践活动已经相当普遍——他们的宗旨是在信仰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辩证地否定生活中的一切邪恶。
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一活动代表了人类心灵的一种不幸的变态;但是在美国或英国又有谁会想到禁止这种活动,并对此予以惩罚呢?难道当权者真的是如此确信救世的正确道路,以致敢于阻止每个人去努力“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②”
吗?假定许多人一旦任其行事就陷入了危险,遭遇了痛苦,那么当权者们难道不会更为小心地标出禁止人们侵越的界线,反倒是尽最大可能允许人们在实践经验和互相影响中获得教育吗?
精神分析学是刚刚诞生于世的新鲜事物,人类大众对此尚了解甚少,正统科学对它的态度仍游移不定,因而在我看来,现在就用法定的规章去干涉它的发展未免操之过急,让我们允许患者自己去发现,向那些尚未学会如何提供援助
①一八七九年在美国波士顿创立的一种宣传靠信仰治病的宗教派别,代表人物是科学家玛丽。贝克。艾娣夫人。该派别声称,只要人把自认为有罪、受苦和将死的错觉纠正过来,就可以获得健康。——译者注。
②源出一句名言:“在我的国家,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据说这句名言系腊特列大帝所说。
的人去寻求精神援助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这样解释,并提醒他们加以防备,但是大可不必予以禁止。在意大利的各条大道上,我们能见到那些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上印有一条简洁而醒目的告示:“Chitoca,muore〔小心触电〕”。
这完全可以起到提醒过路行人不要碰触可能悬挂下来的电线的作用,相应德语告示就表现出一种多此一举的、令人生厌的噜嗦:“DasBeruhrenderlietungsdrahteist,WeillebensgeAtahrlich,strengstensverboten〔碰触传播电缆有生命危险,所以应严加禁止〕。”
()好看的txt电子书
为什么要禁止呢?
任何珍惜自己生命的人都会自己禁止的;而任何想要用这种方法自尽的人是不会请求准许的。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举出一些反对外行分析的合法先例;我指的是禁止外行施行催眠术以及最近实施的禁止举行招魂仪式和成立招魂会的法令。”
我不能说自己赞成这些措施。后者其实是完全公开地利用警察的干涉来侵犯、破坏知识界自由的行为。
我本人当然并不怎么相信那些所谓的“神鬼现象”,也根本不渴望它们得到认可。但是这样的禁令并不能扼杀人们对那个假定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它们可能会带来很多危害,可能会阻碍一种公正不倚的好奇心的正常发挥,而这种好奇心也许会导致一种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扰乱人心的可能事物的判断。但是这又是只有在奥地利才有的事。
在其他国家,“灵学”研究并不遭到法律的阻碍。
催眠术的情况和分析的情况多少还有些不同。
催眠术的作用是触发一种反常的精神状态,如今只被非医学界的人用于当众表演的目的。假如催眠疗法还保持着开始时的那种前程远大的面貌的话,它本来也能达到类似分析疗法的地位。
不巧的是,催眠术的历史却以相反的方向为分析疗法提供了先例。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讲师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医生们愤慨地抨击催眠术,宣称它是骗术,是魔鬼花招,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
今天他们却又垄断了这同一种催眠术,并毫不犹豫地把它用作检查患者的方法;对于一些神经病专家来说,它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治疗手段。
但是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根本无意以分析中应该偏向法律控制还是偏向任其发展的决定为基础提出任何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权人物的偏爱很可能比具体说理更有影响。我已经阐述了在我看来是赞成laisezfaire〔放任主义〕政策的意见。假如采取另一种决策,亦即采取主动干涉的政策,那么在我看来,仅仅以站不住脚的、不正当的措施无情地禁止非医生从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