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稍事休息后)
我想谈一谈目前我感受到的中国创作环境上的某种东西。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我现在提出来一个口号,我要打假。我感受到周围充满了伪的气息。我说的这个伪就是说(有些是我的朋友),他做了一个东西,他做完了之后不去诚恳地谈他怎样做的这个东西,然后他要另一种说法,这就是我称之为伪的东西,这种假劣,我要与这种东西做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东西非常非常无聊。包括在纪录片领域里,在戏剧领域里,就是被人们被媒介关注的所谓地下也好边缘也好非主流也好等等,在这个里面,我认为从来就不是铜墙铁壁一块。我特别强调旗帜鲜明的个人性,自己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大家不要绑在一起,被称作什么什么。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利用空间差,一个人可能在德国呆了几天,他会说他在德国学习什么什么。我觉得非常可笑,你在这里面要营造什么呢,想贴金呢还是怎么着?还有一个人,不点名了,他说上哪哪哪考察,因为我太清楚他去考察什么啦,逛了一趟妓院就变成艺术考察了。我个人认为逛妓院无可非议,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如果逛妓院也变成艺术考察,就要另说了。这种行径特无聊。可是这种东西都会变成这个人在国内的一种资本,因为在中国从演出这一块来讲大家了解和评判的标准太少太少。
汪:《零档案》开始时是用的职业演员……
牟:现在我觉得《零档案》是这样的(最近我看到吴文光的一些文字,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要对他进行纠正),《零档案》吴文光他们介入只有一个星期,在前期创作上我个人不认为吴文光对这个戏的整体创作上有什么个人贡献,包括讲述自己这种方式,这是这个戏决定的,是在他进入之前就产生了的。我这不是说不好听的话,只是明确创作事实。《零档案》开始时的工作过程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每天不愿进排练场。原来有3个演员一起合作,是职业演员,他们也觉得与我的东西不能沟通,我更多地认为这是我没有能力和他们沟通,但也许我们双方都没有错,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撞到一块了,最后实际上在感情上还是伤害了这3个人,就是全部把他们换掉了。
汪:你认为不换的话会不会有现在的结果?
牟:不知道,这怎么能知道呢?
汪:换了演员以后,你就完全改变了排戏方法?
牟:不能说改变了排戏方法。因为跟文光、跟蒋樾、文慧这么多年在一起,首先大家在工作上特别敬业,另外他们没有对戏剧的某种特别固定的理解,所以合作得很愉快。《零档案》现在跟它有距离了,可以客观地谈,如果有什么不满足的话,还是因为结构过于简单,另外故事还是比较表面化。包括《与艾滋有关》。这个戏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人物的说话,我希望的是更琐碎更无聊的谈话,可事实上那里面还是谈到了性,谈到了艾滋,但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控制,因为现场上它是自由的。
汪:有了《零档案》,才有了后来的《与艾滋有关》……
牟:对,这肯定是一个过程,一个创作过程。这里面牵扯到几个问题,一个我刚才谈了,因为我的这种非职业出身,跟职业演员合作时我本身有我的障碍。如果根本就不能沟通,那应该是我的能力问题,但是,是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对职业演员的那种表演质感越来越不喜欢,那么从吴文光他们身上又看到了这种非演员的质感、魅力,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我到今天丝毫不排除再回过头来跟职业演员合作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主要是导演的问题,这是一个戏剧观念的问题,我不喜欢他们(职业演员)的表演状态,不是说我不喜欢某某人,我觉得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但我认为某些人,你有能力找到一种方法,去教给他们一种东西,那合作就是正常的。
汪:就是说将来你会用职业演员?
牟:没准儿还给国家剧院排戏呢,这谁知道呢?
四
汪:很想听你谈谈斯坦尼体系。
牟:我觉得我们首先谁都没见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象个鬼魂一样,充满了整个戏剧环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种训练,在咱们中国连他孙子辈孙子辈的这种训练我都没受过,但我主要是从理论上,译介的关于斯坦尼的这些书,另外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关于斯坦尼的研究文章,只能说是带有理论性质地去学习。在美国的时侯,我就提出希望看看美国院校的斯坦尼体系的训练,我就觉得我宁愿相信我看到的那个就是斯坦尼。但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太多了,而我对整体环境又不是那么清楚,我只能看到那个东西,我感觉,哎,这个挺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20世纪戏剧界一个非常伟大的戏剧家。为什么?因为他一生都在变,他从来不固守自己,仅仅是从这一点上我说他是伟大的。他每一个阶段都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他非常矛盾,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正常的现象。他在晚年的排练否定他早年所谓的内在体验的东西,特别注意形体的表达。他在临死前排《哈姆雷特》时,已经完全抛弃了内心体验的东西。可是从我目前有限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斯坦尼体系就是50年代来了一批苏联专家,这批人应该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的学生,他们每个人可能都固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个创作生命中的一段,然后把他固定了。在中国这批人又带出一批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了老师、教授,又教出了学生。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没有生命力可言了,那么最后发展到80年代就变成了小品教学。我记得于是之先生在戏剧学院讲课的时侯,专门谈到这个。他说学表演的不是学编剧的,不是整天在那儿编故事。后来小品借助电视媒体很快就泛滥成灾,一直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小品跟人的身体跟人的心灵毫无关系,它更多的是靠一个噱头,说一说方言,它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我无可非议,有一些好的小品我看了也非常高兴,象宋丹丹和黄宏的小品。但我认为把它排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甚至教学的一种基础手段,我就觉得不可理解,它只能作为其中的一个东西。
霸气书库(www。87book。com)好看的txt电子书
汪:从斯坦尼体系里,你得到了什么没有?
牟:在方法上,因为我没有真正受到过学习,所以只能从理论上去感受它。但我看过他排演契诃夫的戏剧的书,因为他的导演计划出来了,咱们都出版过。我现在实际上不太同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契诃夫戏剧的解释,事实上我看资料,契诃夫也不很满意。契诃夫一直强调他的东西是喜剧,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它变成了悲喜剧。但另外我也看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处理剧本时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有整体的感觉,这种东西都是无形的。我可以说我直接从格洛托夫斯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儿得到了什么东西。但是肯定他给予过我。
汪:那么布莱希特呢?
牟:我不喜欢布莱希特。我觉得所谓的假定性是一个谈了很久很久的,是一个特别不重要的提法,这是一条死胡同。争论来争论去,是假定性还是写实性,我觉得在我的创作里不存在这个问题,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有能力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布莱希特的剧本都看过,但我对他的剧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同意一种国外的分析,因为原来一直认为布莱希特有一种表演方法,事实上他没有,他只有一种表演美学,他提出了一个任务,可是用什么方法来体现他这个东西,他没有这个系统。格洛托夫斯基完成了这个东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提出了自己的技术系统,格洛托夫斯基所做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所开始的一种东西。格洛托夫斯基是我真正的、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人。
汪:这也是我想问的,你为什么特别崇拜他?
牟:中国对格洛托夫斯基一直有种误解,从黄佐临先生开始,一提到格洛托夫斯基,我最常看到的字眼,就是说他是强调演员的技术,而把其他一切都去掉,说〃这个我们京剧里早就有了〃,我简直不止一次地听见不止一次地看见。这个东西就说是京剧里面早就有了,但我要问一问每一个搞话剧的导演,你自己有没有?京剧里有了,跟你自己有没有这有什么关系?一种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在那儿作怪!我最早接触格洛托夫斯基是通过他那本被翻译过来的书《迈向质朴戏剧》,这本书我快翻烂了,不同的时期都在翻,不同的时期我有不同的感受。书里包括他的技术方法,开始时跟着练,后来从冯远征那儿又学习到一些。格洛托夫斯基他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跟戏剧发生关系?他说事实上就是要让自己身体内部某一部分不透明的东西变得透明,而他最重要的是变得透明的这个过程,冲破身心内的篱笆。我跟他的这种感受很靠近。用格洛托夫斯基的一个演员的话来讲,他是从战胜某种心理障碍开始的,他的心理障碍是在跟人的交往上。我觉得格洛托夫斯基的戏剧是真正的先锋戏剧,他在今天,有人说他过时了,但他对我没有过时,他关注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事实上格洛托夫斯基的观众是很少的,因为剧场不可能容纳很多观众,而且他对观众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看他的戏,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的戏。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而且格洛托夫斯基到现在,你看他最早认为一切多余的东西他都可以不要,但只有两个最基本的元素:演员和观众,但到了80年代左右,他连观众都不要了。他现在发明了一个词,叫节日。他走得更极端。他的原话是一些毫无畏惧的人相处在一起这就叫节日。我看这个话本身就已经很激动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非常纯粹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格洛托夫斯基实际上创造了一种非常系统的演员训练方法,几乎被全世界采用,可能只有中国没有普遍地采用。他的方法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博采众长,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从印度的古代戏剧那里,从京剧的、日本的古典戏剧那里,从欧洲的哑剧传统里,从意大利假面喜剧的传统里,从瑜珈里,等等等等,只要是他感受到的,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东西,他都融汇到一起。这里面有一个概念问题,对人的训练,他吸收的东西更多的是古代东方的一种哲学智慧,跟佛教、禅宗里的修行是一样的,他是通过正身来正心。他认为人的身体的改变会改变人的肌肉,同时改变人的情绪人的心灵。他非常非常重视演员身体的开发,包括声音。在格洛托夫斯基的文章里,他强烈地批判戏剧院校采用美声唱法来培养声音,因为美声唱法它要求一个位置,身体只有这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现在就造成了话剧演员所谓的那种话剧嗓子。大家经常开玩笑说话剧嗓子,他只有这一种嗓子。而格洛托夫斯基他在声音上叫全身共鸣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声,他要求的声音是真实和力度。要按我们选择演员的标准,象我这种嗓子,吴文光这种嗓子,绝对没有可能去当演员。可事实上可以。他对形体的训练也是这样。格洛托夫斯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他从来不满足于自己某时某刻的所谓成果和结果,一生都在寻找变化。只要感觉到了这个东西,需要变他就去做。
汪:你看过格洛托夫斯基的戏吗?
牟:按顺序说,接受格洛托夫斯基,最早是看他的书,后来1991年去美国访问,还在纽约的林肯戏剧图书中心看到了他的一个录像带,这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录像带,是《卫城》。然后办《彼岸》训练班的时侯,冯远征是在德国学习过他的方法,又开始教他的方法。但实际上格洛托夫斯基身体训练的一个主要的基础是以瑜珈的方法为主。我自己是从90年就开始瑜珈练习,所以很多东西到最后就通了。瑜珈它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而且它还强调缓慢地变化。你只要坚持就会感觉到,它强调身体内部的变化,开发身体内部能量的东西。我在今天依然在学习各种东西,因为很多不同的东西我有不同的感受。
汪:你训练演员是采用这些方法吗?
牟:我直接采用了请冯远征来教一些方法,还有铃木忠志的方法,我自己教大量的瑜珈形体练习,包括我在美国学的各种方法。到现在为止我教的各种方法,应该说都跟我们现行 的教学方法不一样,包括京剧的教学手段,包括我在纽约大学谢克纳的编导课上学 的东西。谢克纳的课是开发脑力的。我上课时看到学生出来的东西简直是出乎意料 的。
汪:如果你将来有一个固定的剧团,就可以用你的方法训练演员了。
牟:那当然最好,但我可能在每一个戏的排练中都会借助训练。
汪:先用你的方法训练演员,然后再排演……
牟:对,同时的,这是一个同时的过程。那你说什么叫排练呢?说一个导演说戏,这个戏怎么能说出来?我见到很多导演排戏都在那儿说感觉,可是怎么完成,演员需要的是这个方法和这个动作性的东西,我是特别看重这个东西的。我觉得某一些人误解了我的戏剧主张,好象不是演员只要是真实的人上台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只是我的一部分,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技术性问题,这非常重要,这是戏剧区别于会议的地方。因为开会也是这样,上台去讲话,那为什么不叫戏剧呢?我去年特别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格洛托夫斯基,《零档案》在意大利佛塔拉戏剧节演出的时侯。佛塔拉戏剧节是欧洲4个最有名的前卫戏剧节之一,格洛托夫斯基在意大利的工作室就在佛塔拉城附近的一个山里,《零档案》剧组去了他的工作场地与他交谈,但因为我在日本排另外一个戏,没有见到他。(笑)以后我相信会有机会见到他的。
五
汪:《红鲱鱼》的演出是怎么回事?
牟:《红鲱鱼》就是我做的,我导演的。我在日本排了一个月。但是当时不能说,因为要在北京演出,日本人与中国方面怎么谈的我不知道,总之,不能说是我的导演才可以上演。
汪:与日本演员合作,感觉如何?
牟:95年8月我去日本东京排戏,日本演员使我特别感动。应该说与这5个演员的合作,证明了我有能力和真正的专业演员合作。5个演员来自日本的4个剧团,吃鱼的那个是有20多年演出经验的老演员,还有一个是剧作家也是演员(和泥的那个),高瘦的那个也是老演员。跟他们在一起工作非常愉快,而且让我在表演的感悟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都是用我的方法给他们训练。我觉得日本演员跟中国的专业演员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首先是作为人存在。日本人生活很艰苦,做戏剧的人更艰苦,赚不了很多钱,都是凭着喜欢和热爱,但他们在生活中干各种事情。所以他首先做为一个人存在。而在中国,这个人首先是演员,他有一个〃范儿〃,然后才是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别太重要了。象在《红鲱鱼》里,那个老演员每天晚上要讲一个半小时,都是他自己的。我给他做了相当长的训练,比如说我就给他两个字,让他坐好,我说我今天掐着表,让你讲一个小时。我的要求就是不许思考,不许停顿,我说我只给你出一个题目〃山〃。他觉得这是最难的题目。在东京的首演那天差点给忘了。因为我说在演出的当天我才告诉你今晚讲什么。首演前15分钟,他派一个人来问我,今天晚上我讲什么啊?我给忘了。川中,那个高的戴眼镜的男的,他是个同性恋。因为我明确,这个戏要向个人的隐私进攻,我说东方的道德是隐私不能对外,我说这是戏剧,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隐私,隐私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我从《红鲱鱼》开始,包括下面要做的戏,开始进入人的内心深处,用康拉德小说的话说是黑暗的内心深处。我跟他相处第3天就知道他是同性恋了,那人特别可爱。每天是8个小时疲惫的高强度的身体训练,他们生活得特别真实,还原自己没有很多的障碍。那个川中,有一天我就让他讲,让他自由地讲,整整半个小时,我把他的手绑起来,身体不能有任何动作地来讲。他已经45岁了,这半个小时他特别沉迷地讲他小时侯如何喜欢甜食,一有钱就买甜食,讲了半个小时。听完了我告诉他,我说我建议你去演李尔王,历来李尔王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威猛的国王的样子,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李尔王。我说我排李尔王,戏一开场就让他讲他小时侯喜欢吃的甜食,特别好。另外一个老的女演员,我问她如果让你选择,你最想演谁?她说她想演贝兰奇。贝兰奇是《欲望号街车》里的女主角,就是费雯丽曾经演过的,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具有悲剧感的美人儿才能演这个角色。可是她长得又矮又胖,脸上是娃娃那种喜气洋洋的样子。我问她你为什么喜欢贝兰奇,她说贝兰奇是一个有梦想的女人,而我也有梦想。哎呀把我感动得不得了,我说你一定能演贝兰奇。这非常好。我觉得人们对于戏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某类角色,李尔王应该由什么样的演员来演,贝兰奇一定要什么样的人来演,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日本演员给我的感受太深了。而且,他们从来没做过这么强体力的训练。那个老的女演员,她一直有一个自我保护自己身体的本能,所以有一天我就是要看看她忍耐力的极限,最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她开始骂人了,然后我就让郑义信上去做抚摸她的动作。后来我问她,她说我已经快要骂你了。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人的问题。我以后做戏剧对人的关注的最基本的点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时代永远是这样,就是伤害和自我保护,人类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互相调解的这么一个过程。伤害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毫无自觉的,而自我保护本能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在身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戏剧来信任自己,尽可能地减少人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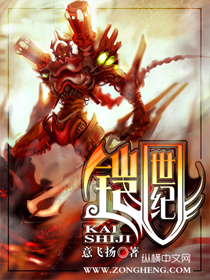
![[空间]重生2001封面](http://www.biku2.com/cover/2/263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