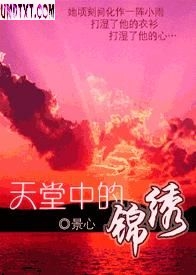天堂也有一双媚眼-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她也很夸张地跟我握握手,还腾出一只手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必过于激动,这是我应该做的。”
气得彭哥他们咬牙切齿。
我们越发得意了,双条腿像两条蛇一样的缠绕在一起。没有想到是,这种甜蜜的和谐很快被一件小事破坏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6
轮到去彭哥家开派对的那天,圣虹姐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奇。
彭哥的派对常是以音乐为主题的,这次改成了一顿诺曼底晚餐。
餐桌上特意还铺了一块红百菱形块格子桌布。所谓的诺曼底晚餐,是用小牛肉为主、用浓奶酪酱和苹果烧酒为辅的套餐,味道很地道,而且是圣虹姐一手操办的,连帮手都没用。
圣虹姐提前给我们打了电话,让我们穿着正式一点,怀着一颗上教堂做弥撒一样虔诚的心,前来赴宴。我们只好都打扮的像指挥家似的,个个人模狗样的。
“圣虹姐,今天一定是个特别的日子吧?”我问把光泽的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她。
她说她把一对濒临离婚的夫妇说服了,又和好如初了。桌上又嫩又新鲜的小牛肉就是那对夫妇送来的。
“很有成就感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当然了,这种成就感一点也不比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以后的那种成就感差多少。”圣虹姐笑盈盈地答道。
诺曼底晚餐的味道好极了,遗憾的是,我却难以全身心地来对付它。因为我总是惦记着铁木儿,她又约定要到我那里去过夜,一想到这个,我就不免心浮气躁。
“小牛肉要蘸着冰过的黄油,更可口。”圣虹姐说。
冰过的黄油切成方块,呈塔状摆在梅花形的碟子里。男人为了更舒适地享用这顿美味,早把西式外套脱掉了,不然浆得太硬的白领和黑领结硌得难受。每个人又恢复到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状态。圣虹姐也懒得管我们了。
“来,苏怀张嘴。”铃子夹了一块蘸了黄油的小牛肉喂给苏怀。
铃子的指甲涂了荧光的指甲油,特晃眼,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话,很可能会亲昵地拧一拧苏怀的嘴巴,搔一搔苏怀的耳朵或是做出别的什么“少儿不宜”的动作来。
梅梅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对铃子说:“嘿,适可而止吧。”
铃子慵懒地微笑了一下,又咕哝了一句什么。铃子笑得特别妩媚,所以就喜欢用笑容来自卫,抵御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趁大家品味土耳其咖啡的时候,我得以脱身,出了彭哥家,躲到一架废弃的马厩的阴影里,等铁木儿。
我深深呼吸着乡间夜晚苦涩湿润的空气。
不一会儿,彭哥和圣虹姐打着手电,把铁木儿送了出来,还嘱咐她两句。我恨不得马上向铁木儿扑过去,如果不这样的话,似乎一秒钟之后她就会从人间蒸发。我只能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铁木儿发动了车,开出去不远,拐个弯就停下了。
听见我的脚步声,她从车上走下来,冲着黑幕中的我问了一句:“口令?”
“面朝大海。”我答道,“回令?”
“春暖花开。”暗号对上了,都是自己人。
我们吻了几下,寒冷的夜风吹拂着我们滚烫的脸。我高兴地就像一个热情奔放的农村小伙子,亲热地把她举过了头顶。铁木儿吃吃地笑着,笑声宛如潺潺流水。
直到感觉出彻骨的寒意,我们才钻进车里,相拥着取暖,她还放一盘从三里屯酒吧录制的歌带让我听,很有现场感。
因为喝了不少苹果烧酒的缘故,她有一点醉态,我也是。我们的目光总是游戏似的相遇,又游戏似的移开,偶而也傻笑上几下。
回到我的房间时,已时午夜时分,院里冻僵了的灌木在簌簌发抖。
我生起了壁炉,让干燥的木材在炉膛里噼啪作响,而铁木儿俯在我窗口的天文望远镜跟前,眺望远方一颗最亮的如同初恋一般美好的淡蓝色星星。
我把床垫铺在壁炉跟前,躺上去很舒适地打了个滚。
“宝贝,快来,这里真暖和。”
铁木儿乖乖地脱去大衣,也光着脚丫爬到了床垫上,下巴枕在我的胸口上。
“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她喃喃地说。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7
我开始拥抱她,亲吻她松软的长发,把她柔弱的肩骨搂的咯咯作响,很快,我们就被黑暗所吞噬,进入到了一个见不到底的深渊,一时间,硝烟弥漫,仿佛大地也在富有弹性地颤抖。
各种艺术体操都让我们尝遍了,表演当中,我们得不时地微微直一直腰,以便让肺部吸进足够的空气。我们只能感到软茸茸的床垫爱抚着我们汗湿的皮肤,把冬天的寒冷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似乎完全沉没于茫茫的虚幻之中,这时候的她,显得过于文静了,她那长长的睫毛低垂着,双眉局促地耸动着,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每次Zuo爱她都是这样。
“你真的爱我吗?”这是她唯一说过的一句话,嘴角还咬着自己的一缕头发。
“傻瓜才会不爱你呢,你看我像个傻瓜吗?”我说。她吊在我的身上,紧紧箍着我的腰,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劳动强度。
不知怎么,我一骨碌翻了个身,铁木儿就跟我交换了场地,她到了上边……“不!”她突然尖叫了一声。
仿佛一阵冲刺跑到了终点,刹住脚,一下子松弛下来。我惊愣了,她似乎比我还惊愣。
“你无耻!”她虎视耽耽的目光投射在我的脸上,冷笑了一声,又说,“你们都那么无耻!”她站起身来,挺直了匀称漂亮的腰身,走到床边,将衣服穿上。我慌忙解除了灯火管制,让房间明亮起来。一边解开被汗水浸透的衬衣领扣,一边用疲惫的手点燃一支烟,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她铁青着脸,凉意袭人,没穿|乳罩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整体上看,她就像一座愤怒的中世纪城堡,耸立在乌云密布的峭壁下端,有点恐怖片的意思。
“你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就像一个在雷区用地雷探测器探雷的工兵,唯恐一不小心,踩到雷上,炸了。
“我怎么了,你知道!”她回答我的话,字字都跟拔出剑鞘的佩剑差不多,闪着锐利的寒光。
我一脸的无辜献媚似的走到她的跟前,把烟卷递给她,想让她吸一口,消消气。
“我烦你,”她一巴掌把烟打掉在地上,双唇威严地紧抿着,“我烦你们这些臭男人!”
我也有点恼,但我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懑,“说说吧,臭男人怎么惹着你了?”
“我懒得跟你说。”她的面色越来越惨白,蹙着眉头,明显是一种病态的敌意。
房间里一片寂静。我反思了半天,确实没发现自己犯过什么错误,确实没有。既然不是我的问题,那么就是她的责任了,她太怪僻了,真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可惜,我管不住自己的嘴,仿佛是为打破这种像是施了魔法的凝滞的宁静,这句话竟脱口而出。
“既然嫌我怪僻,从此别理我好了。”铁木儿仿佛一股热血一下子涌上了太阳|穴,腾地站起来,一双癫狂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转动着,同时发出阵阵痉挛似的喘息。火山爆发了。火山终于爆发了。
“不理就不理!”我说。脾气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她有,我也有。
“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
“我从来没有后悔的习惯。”
铁木儿舔了一下干涩的嘴唇,起身走了。
门扇“嘭”地响了一声,响得特深沉。
接下来,就是汽车发动的声音,那声音像撕心裂肺的恸哭,渐渐远去,直到再也听不到了,我的喉结才动了一下。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后悔了。
她一定会一边开车一边哭的,我想。
明知道她已走远,我还是追了出去,经过秀大妈房间的时候,我踮着脚,好像通过架在深渊上摇摇晃晃的独木桥,支楞着胳膊尽可能地保持着平衡。
“这么晚了,你还折腾什么?”黑暗处,秀大妈突然问道。
我吓了一跳,“没什么,您还没睡呢?”我含含糊糊地咕哝道。
秀大妈那双探究的眼光警惕地盯着我。
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身板笔直,面带微笑。
“去吧,早睡早起,身子骨才会好。”秀大妈嘱咐我一句。
“我知道。”我匆忙地点了一下头,就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打发漫漫长夜的惟一办法,恐怕就是看电视了。打开了电视,我骑在房间中央的旋转木马上,旋转木马是专门用来看电视的,累了,把宽大的马尾巴搬上来,可以靠着。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档老年节目。
这种时候,这种地点,以及这种心境,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点什么,以便转移视线。
我把电视调到闭音状态。屋内除了从百叶窗射进来的少许月光而外,几乎是死一般沉寂。地板上还随意丢着窗垫和床单什么的,仿佛是余热未尽。“一地鸡毛。”这个词像火花一样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铁木儿这时候大概已经回到她的咖啡馆了吧?冲过澡了吧?钻进鸭绒被里了吧……
也许我该给她打个电话吧?不,现在她的情绪还没稳定下来,打也白打,弄不好又得咆哮一通。
还是冷处理比较好。
对她我束手无策,她是个不按照逻辑去思维的女人,或者可以说是一头长着犄角的小山羊!
电视里的老人扭秧歌的也好,拉胡琴唱戏的也好,都是那么的平静而安详,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些慈善的老人当中,有多少人拿着棍棒刀枪参与过武斗,又有多少人揪着人家的头发揭发批判过谁呢?我知道,我的这个念头令人难以置信,同时,我也知道,我的这个念头绝对有它的合理性。我曾认识一个白发苍苍的邮递员,见谁都是一脸的笑,可和蔼了,后来,才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个造反派头头,杀人不眨眼呢!
看一阵电视,又胡思乱想一阵。
渐渐的,目光就变得浑浊了,我一头载到床垫上,呼呼睡了过去,给这一天画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8
()
一觉醒来,拉开百叶窗,清晨的空气弥漫着初冬的寒气。我把挂在墙上的木枪拿下来,光着脊梁,练了一通拼刺刀,算是做早操了。
一边练,一边唱:拼刺刀,看谁拼得好,保家卫祖国要练好这一招。
我穿衣服的时候,看见房三爷走出我的院子,秀大妈送他。我在水龙头跟前好歹洗了一把脸,腾腾地跑下楼去,十二月的阳光以锐不可挡之势,用一束束光筑起一道墙,我揉了揉眼睛,问秀大妈:“是房三爷来了吧?”
“是啊。”秀大妈用苦恼阴郁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此刻,她失却了以往的豁达和开朗。
“有什么事吗?”
“我家老头子求他来做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劝我回家去住。”秀大妈极度疲倦了似的走上台阶,嘴里嘟嘟囔囔地往她的房里走。我拦住了她的去路。
“秀大妈,我也纳闷,你为什么不搬回去跟老伴去住呢?”
秀大妈说:“我不爱我老伴了。”说完,哐地关上了她房间的门。
她的语气,她的声调,还有她的措辞,虽然是冷冰冰的透着一股子执拗,但还是把我给逗乐了。我冲着她的后背做了鬼脸,说道:“几十年的爱情,不会一步就走到尽头吧!”
“别理我,烦着呐。”她说。她的这句话是跟我学的。
看来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在折磨着我一个人。爱情太敏感了,仿佛电流,它能敏感地触及到每个人,无论男或女,也无论是老或少。多少人都企图紧紧地抓住爱情,因为没有爱情的地方,生命就像贫瘠的土地一样,冰封大地,白雪茫茫。
我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我想。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郁闷,甚至已经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了,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像阴影一样把自己团团包围起来。晚上,我决定去跟铁木儿讲和,既便她仍然是武装到牙齿的阵势,我也必须首先解除掉自己的武装,退一步,海阔天空,总会让她露出不可多得的微笑的。因为晚上要在原田家开派对,在那里,我就能跟她碰面了。
那天,我到的特早,所以原田说我:“整个一积极分子。”而且他是一脸的惊愕和诧异。
大概是因为独身的缘故,自由散漫惯了,参加集体活动时,迟到早退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偶尔,提前入场一把,反倒令人起疑。
“先喝一杯鸡尾酒。”梅梅一边说,一边用麦杆搅动浮在酒杯里的柠檬。
接过酒,我咕咚喝一口,然后说:“要是来一杯亚美尼亚酒才带劲呢。”梅梅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仿佛是在说:“你想得倒美。”梅梅在我们当中是惟一的一个远离酒精的人,因为她酒精过敏。好在我现在的兴奋点不在酒上,眼睛始终盯着门口,每次听见门铃声,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当发现进来的并不是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脸上就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等彭哥他们一一到场之后,铁木儿还没来。
她的路途比我们要远的多,来晚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不急,我不必急,我叮嘱自己说。
在笑声、歌声、吵闹声和插科打浑声中,我们结束了晚餐。这时候,还没见铁木儿的影子。
一个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并不那么简单,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件破坏了她的原计划,也许,很快她就会赶来的——我对她一直抱着一种天真的信赖态度。
原田今天晚上安排大家看的仍是帕索里尼的片子。据说是他最惊世骇俗的片子《萨罗,又名索多玛120天》。
“看帕索里尼的其他片子,看的是剪辑技术,看这部片子,看的是摄影角度,机位总是恰到好处。”原田说。
可是,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那些性虐待的场面就让人受不了了,纷纷提出抗议,圣虹姐差一点吐出来。表现得最为坦然的是梅梅,她习惯性地双手交叉在胸前,无动于衷。我猜,她的电影看得太多了,麻木了,多恶心,多变态,多恐怖的情节对她都是刀枪不入了。
原田终于禁不住舆论的压力,一边给大家鞠躬,一边赶紧换了一部库布里克的片子《全金属外壳》,总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始终不能静下心来,尽管放的是一部我喜欢的黑白片。
夜已很深了,铁木儿仍旧没有现身,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有点空虚,还有点烦人的孤独感。她的缺席,会不会是故意的?会不会是昨天夜里发生争执所产生的后遗症?会不会就是为了逃避我?
这中间,圣虹姐几次拍我的脑袋瓜。
“你是不是脑子开小差了?”
原来是圣虹姐想跟我聊一聊越战的话题,我却置若罔闻。
圣虹姐指了指正在放着的电影说:“最大的变态往往是战争上的变态,它扼杀的是人性,而帕索里尼的电影里的性变态,只是伤害人欲而已。”
她说着,含笑直视着我眼睛的目光温柔而亲切,酷似铁木儿在某种场合时常出现的表情。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话:微小的差别万岁。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的差别都是微小的。
()好看的txt电子书
我递给她一支烟,似乎是鼓励她说下去,事实上,我在力求把铁木儿的面部变化和眼前的圣虹姐的神态相比较,想从中找出一些“近似值”来。结果发现,除了一个皱纹多一点而另一个皱纹少一点之外,再无其他。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9
“咖啡馆么,请你帮我找一下铁木儿,让她接电话。”
从原田家布置得像电影院似的地方,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给铁木儿挂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不是她,是她雇佣的三个女服务生中的某一个,说话的声音很悦耳。有点像张韶涵,长相也是。
我听见“张韶涵”捂住话筒,跟别人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问我:“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哪位?”对方冒昧却又不失谦恭。背景音乐潺潺流水一般的隐约可闻。
我赶紧自报家门,告诉对方我是谁,那个黑黑的、瘦瘦的、带着一副镀铬眼睛的那个常客就是我。
沉默了一下,对方回答说铁木儿不在。
凭直觉,我猜铁木儿肯定在,就在“张韶涵”的旁边。她一边摇晃着酒杯里的白兰地,一边挂在嘴角一丝自持的微笑。
就是说,她还没有原谅我,就是说双边关系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问题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
我撂下电话,感到特疲惫,唉,一生中又过去了一个短促而漫长的昼夜。我斟了一杯酒,想跟谁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可惜连个对手都没有,就觉得没劲。
据说,古代人碰杯是为了让酒从一个杯溅到另一个杯里,为了证实里面有没有毒药。
由此可见,人与人永远是有戒心的。以前,我就没有,我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记得,那天铁木儿说她冷,我就捧起她的手,一边给她哈气,一边用舌尖舔她冰冷纤细的手指。
她呜咽了。她咬着嘴唇,眼睛也泪水模糊了。她像被火灼烧似的把手缩了回去。
紧接着,她又俯下身去,把我的头搁在她的膝盖上,抚摸着。
就是那一次,我对自己说:这个女人就是我要相伴一生的女人。
这些,恍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间,就像肥皂泡一样“叭”地破裂了。
闭幕了。我和她的一出情感剧就这么闭幕了,没有想到的是,居然会如此短暂!
一个人幸福的时候,才会产生害怕失去幸福的恐惧。好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么一想,一种坦然,像流星一样,带着刺骨的寒意和疼痛从心底一掠而过。
我躺倒就睡了,睡得比想像得要好,要踏实。
门铃把我叫醒的时候,冬日的太阳闪烁着,映照在左近的一座座田园式的红瓦屋顶上。
“闺女,怎么会是你呀。”我听见秀大妈说。
来的是花枝,一脸的纯真,仿佛随便插上一对翅膀就能成为一个天使似的。
“进来,快进来,看看你冻得彤红的小脸呦。”秀大妈牵着花枝进屋,坐下,用手暖着她的面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