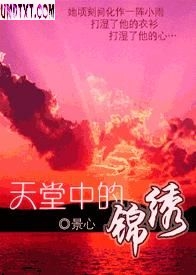天堂也有一双媚眼-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回来时,铁木儿已经煮好了咖啡,咖啡是特浓特浓的那种,点起了蜡烛,托着腮帮子在等,这样一来,她给这个夜晚赋予了缠绵悱恻的含义。
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0
我们又过了淡橘红色一般柔和的几天,铁木儿一直是笑着的,而且那笑只是给我一个人的。如果用温馨,用恬静,甚至用幸福一词来形容,都不过份,一点都不。
花枝住到我这里来的那天上午,她悄悄抻抻我的袖口,向铁木儿努了努嘴巴,问道,“柯本叔叔,你说,我该怎么称呼她才好?”“铁木儿阿姨呗,”我说。“可是奶奶说,让我问你,你说称呼啥我就称呼啥。”花枝这里所说的奶奶,当然指的是秀大妈。我抬眼看了坐在我对面的秀大妈一眼,秀大妈直冲我眨巴眼。
“你就叫她铁木儿阿姨,起码现在先这么叫着。”我对花枝说。
“嗳,知道了。”花枝懂事地答道。
那一天的白天,铁木儿一直叫花枝下围棋,我以顾问的身份左一边,基本做到了观棋不语。花枝确实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偶而还能把铁木儿弄得手忙脚乱。我推算,用不了多久,她要赢铁木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铁木儿却很不服气。
“我只是很久没有下了,生疏了。”她说。
“人家花枝还从来没有下过呢,岂不更生疏?”我说
铁木儿狠狠踩了我一脚,这是她的习惯动作,一般都是在她恼羞成怒的时候才这样。我当然要予以还击,别以为我是一盏省油的灯。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桌子底下悄悄进行的,绝对不能让花枝看见。
“歇一会儿吧,光下棋,多累心哪。”秀大妈端来了水果。
“那好,我们换一个节目,换一个不累心的。”我说。
铁木儿问:“说来听听,做什么?”
“朗诵,朗诵《旧日的保加利亚人》,一个叫卡拉维洛夫的人上上个世纪写的一部小说。”
“我听都没听说,不过也许会有那么一点意思。”铁木儿说。
我从阁楼上取来这本书,从花枝开始轮流转每人朗诵十页,正好可以把既是教师又是唱诗班唱诗的哈吉?耿巧的故事读完。在这之前,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了,里面涉及到的巴尔干的旧日风俗部分最为有趣。
“花枝,朗诵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情感,记住这是一篇讽喻小说。”
()
“知道,朗诵课文时,我们老师也这样要求来着。”花枝说。
铁木儿不耐烦了,“柯本,你就别罗嗦了,快开始吧。”
“好,开始。”
想不到花枝居然朗诵得这么好,很有天分,尤其在刻划人物时,抑扬顿挫,宛如鸟儿的啼啭。闭上眼睛去听,从她的声音里,能感觉到一切善良的和神圣的东西。这一点,跟铁木儿一样。跟她们一比,我就多少有点露怯,口吃没她们伶俐,嗓音也没有她们圆润,幸好,她们都已沉浸在书里头,谁也没顾得上来挑剔我。
一轮结束,花枝竟意犹未尽,还要接着朗诵,又是秀大妈出来阻挠。
“这个,一点也不累心。”花枝说。
“可是累眼。”秀大妈说,“一会儿客人就要来了,该准备晚餐了。”
“那好,一起动手,丰衣足食。”我把花枝拉进了厨房,让花枝穿上围裙做蜜饭给大家吃。花枝一个劲摇头说不会,我告诉她,蜜饭的配方就在刚读过的那本书里。
“是第五页,第一个自然段吗?”花枝问。
“对。我给你打下手。”我说。
于是,花枝淘米,然后再在米里拌上蜜,核桃泥、葡萄干、玉米粒,一尝,味道好极了。我们不禁击掌相庆起来。
“你们哪里像过日子,简直像是过家家。”秀大妈嗔怪似的说。
铁木儿也露了一手,是一道加了咸肉片和薯条的油煎鲱鱼,吃时,再浇上几滴芥末汁,吃得彭哥他们个个笑眯眯的。
那一天,都是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度过的,可是,到了晚上铁木儿却跟我翻脸了。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1
那是在谈理想的时候。原田说,假如让你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你将选择什么样的理想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回答,有人选择的是周游世界,也有人选择去当侦探,跟福尔摩斯干同一种行当,还有人选择到可可西里去当志愿者,保护那些可怜的藏羚羊。问道我,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坦白地告诉他们,我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图书馆,董桥早年就唱去那里读书。一时间,嘘声四起,普遍认为我的理想太平庸,基本可以算做碌碌无为,胸无大志。
“我就是这么想的,实话实说嘛,难道非得想去当联合国秘书长,舍得一身剐,敢把安南拉下马才算是理想吗?”我为自己辩解道。
他们则无话了。
铁木儿说她的理想是办一个牧场,养上大群的牛,养上大群的羊,赶到晴空万里的时候,就骑在牛背上晒太阳,吹得蒲公英满天飞。
“这理想也未免太小儿科了吧。”我说。
我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又不小心点燃了一颗导火索,因而会引起爆炸。
我要早一点发现到这个就好了,可惜,没有,等到稍微有感觉的时候,铁木儿已经像一只瞅着篱笆上啾啾唧唧的麻雀舔嘴巴上的猫,脸通红,仿佛随时都会扑过来,咬上我一口。
圣虹姐大概看出点苗头来,推了推铁木儿,“柯本是跟你开玩笑的。”
“跟我开玩笑?他也配!”她哼了一声说。
这个哼好像是一道划破天空的闪电,预示着快要打雷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狂风和暴雨。
我赶紧给自己的嘴巴贴上了封条。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铁木儿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一脸的沉重,仿佛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的受苦人等着她去解救呢。派对一结束,她第一个站起来,走了,拦也拦不住。
人都走了,客厅里立刻冷清下来,我也像是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了驿站,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让懊恼压得直不起腰来,我骂自己:我干嘛那么多嘴,纯粹是大脑进水了。留宿的花枝还紧着问铁木儿阿姨为什么也走了。我说人家都走了,她为什么不走?花枝说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我问她谁告诉你的,她说看也看得出来,再说了,地球人都知道。我怕花枝罗嗦起来没完,赶紧打开电视,调到凤凰卫视台,叫她跟秀大妈看“综艺大哥大”。
()好看的txt电子书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2
通常情况下,只要铁木儿跟我一进入冷战状态,就对我实行全封闭,这次也不例外,电话打不进去,电邮也一概退回,几次开车到她的咖啡馆去,转悠了几圈,没进去,我想,进去也肯定会吃到闭门羹何必呢?就在这时候,我开始怀疑我们的爱情了……
我有点难过,不是漠然的感觉,而是由于理论的推断——也许,铁木儿还在爱着她的那个新西兰男友,否则的话,她怎么会对他总是记忆犹新呢?随便一句话,就可能勾起她尘封的回想。
这个推断困扰着我,令我气馁,也令我无法安静下来,所以我就开着车兜圈子,我很想找一个人聊聊,聊什么都行,只要能聊就好,奇怪的是,想象中跟我聊天的那个人,也就是第一人选,不是彭哥他们,而是陆清,于是,仿佛受了诱惑似的,我再次来敲陆清的家门。
“对不起,我是不是打扰你了?”我对陆清说。
“别那么客气,”陆清笑一笑,“这个大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着的,尤其是你不太开心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我傻瓜似的问道。
“直觉,只是直觉而已。”陆清把我让进屋里,就去拿饮料,这就让我得以十分平静地观察她:我看见她已经不很丰润的脸上点缀着两个酒窝,头发很日常地披散着,脖子凹凸的曲线特古典……
我喝了一口她递过来的饮料,用手背抹抹嘴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件事一直让我觉得很好奇。”
“问吧。”她坦然地说。
“你对我一点不了解,而且似乎也不想深入了解,就跟我进行亲密接触,为什么?你觉得我值得你如此的信任吗?”我问道。
“有,肯定有。”陆清的语调多了些沉思的意味,“因为我坚信,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既使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起码要比不爱书的人好得多。这就是我信任的理由,难道还不够吗?”
她的感觉里透着一点天真。我反倒以为读过很多书的人,一旦坏起来要比没读多少书的人坏得多。当然,这并不是喜剧,而是悲剧,虽然一个人有时候会快乐,但片刻的快乐只不过是一个插曲,不是人生戏剧中的正文,悲剧才是。
也许是心境阴郁的缘故,我才这么灰心,平时未必总是这么想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他沉默了一会儿,苦笑道:“恰恰因为我太天真了,处处撞钉子,所以才情愿躲进书堆里,寻找些慰籍。”她的瞳仁是乌黑,从里面可以看到我的面影。那是一对仿佛从没有被尘世污染过的瞳仁。
“你不寂寞吗?”我问道,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脸,仿佛那张脸记录了她的全部历史。
“有时候会寂寞,”她踌躇地小声说,停了一歇,她跟我笑了一下,更准确地说,那不算是笑,而仅仅算是一个笑的形状。“不过,有你来陪我,我就不寂寞了。”她说。
“你说我吗?”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来无踪,去无影,来是连个招呼都不打,走时又像一阵风似的突然蒸发……”
“别这么说,”陆清摇了摇头,“我对你没有过多的要求,谈得来就已经很难得了,况且,我原本就没什么朋友。”她两只手垂在膝盖中间,显得特乏力。
不知为什么,她微微蹙起的眉竟让我怦然心动。
我拿起她的手,放到唇边吻了吻,像吻一朵水生的花一样。“我对你上一次可能过于鲁莽了,我原来以为自己是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的,现在看来,只是半瓶醋而已。”
“你恐怕想象不到,你几乎颠覆了我的生活,你来一次,就让我很久都不能平静。”她看了我一眼,又说,“不,我不是不欢迎你,却恰恰相反。”
我们的话题不知不觉变得沉重起来,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不免都觉得好笑。嘻嘻哈哈地就把刚才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打破了,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留意了一下,发现在陆清的房间里没有任何音响设备,能制造出动静来的怕只有那只座钟了,滴滴嗒嗒不停地响,我不禁问了一句,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在书堆里边翻来翻去,终于翻出一对音箱和一台老掉牙的录音机。“这不是,你要不提醒,我早把它们忘在脖子后面去了。”她掸掉手上的尘土说。
“你从来就不听音乐吗?”我问道。
“从来不听,”她很干脆地答道,“一是没时间,二是没心情。”
“那么好,趁你现在有时间,跟我走。”我拉着她到超市去,买了一个CD机和几张碟,回来,我对她说,“放着音乐读书,你就会有好心情,不信,你可以尝试一下。”
陆清仿佛神经麻痹了似的,站在那里很茫然。
“读菲兹杰拉德的小说时,你可以放诺拉?琼斯的带有爵士乐风格的歌;读亨利?米勒的书,则应该选听披头士;要是读《追忆逝水年华》,那么伴奏的就非得是法国的香颂歌曲不可了,”我说着把新买的一张碟放进CD里,接上音箱“比如这盘理查?马克斯的歌正好可以伴着哈代的这本《卡斯特桥市长》来读。”因为《卡斯特桥市长》恰好就在我手边。
陆清接过书随便掀了几页,惊奇地问道:“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呢!”
()免费TXT小说下载
我搂住她的肩膀,有舌头添了添她的耳垂,我还从来没有亲过女人的耳垂,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回忆。我说“也不是什么讲究,就是哄着自己玩,玩得高兴才是终极目标。”
“听起来,好象有几分道理。”她说。
“何止有几分道理,简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为什么要嗜爱书,还不是书能让我们高兴?”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这样读书的,我是说在音乐的伴奏下?”
“差不多是这样,久了,就成了一种习惯,一本书,一支曲子,再加上一杯咖啡,岂不是再惬意没有的了!”我说。
接下来,我们一起在理查?马克斯的歌声的陪伴下,重温了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为十九世纪英格兰一个叫伊丽莎白?杰恩的女孩的命运而担惊受怕半天。这本书是侍桁的老译本,竖排版,繁体字,看起来很舒服。
她读一页之后,我接着读另一页,也有时她读伊丽莎白?杰恩的段落,我来读伊丽莎白?杰恩继父那一部分。
读的时候,我们一直依偎着,相互牵着手。
跟她在一块,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起码,我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而这些,跟铁木儿相处的时候,却是不可能的。陆清的这间屋子,对我来说,就像一艘自由飘荡的方舟,逍遥而温暖的。这里之所以吸引我,就是因为这个。
读书读累了,我们就歇着,不知怎么,两对眼睛突然汇合到一道,触电一样的迸发出火花。
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面对着她的身体,我就像一位鉴赏家鉴赏一幅画似的,目光流连,突然说:“你记得劳伦斯在她的小说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吗?他说爱情之毛是最好看的毛,像一丛亮亮的金黄|色的槲寄生——”
“先生,你的着眼点太狭隘了。”她将我的下巴抬起来,让我的视线对着她的五官,仿佛她的五官写着她的命运一样。
“这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啊。”我调侃了一句。然后就跟她吻在了一起。
从窗口射进一片黄|色的眼光,那是夕阳,给陆清罩上一层梦幻般的神秘感。我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支唇膏,在她的胸|乳间描画出一支剑射中了一颗心的的图案,画完之后,又觉得有点俗,想擦掉,陆清欠起身,抚摸着那个图案,轻轻的小心翼翼的,就像抚摸别在衣襟上的一枚钻石胸针,“你提我吻吻它好吗?我自己够不着。”她颤颤巍巍地说。我照着她的吩咐去做了,我的唇所到之处,都使她不由自主地一阵阵抽搐。我贴近她胸|乳的时候,能清晰地听见她的心跳声,她的心跳犹如一把把竖琴的叮咚声,深沉而急速。
历经一次毁灭性的肉搏之后,陆清胸|乳间的图案也印在了我的胸口上,不过,颜色淡了些,朦胧了些,轮廓也稍微有点变形,像彩虹桥一样的呈椭圆状。
“我应该把图案纹在身上,就永远也掉不了啦。”她说。
我刚想逗她一句,我衣兜里的手机响了,我没去理它,谁叫它响得不是时候来着。
我仍旧拥着陆清,用脸颊摩擦着她的额。记得,第一次拥抱柔顺的她的时候,隐隐地还产生过一个怪诞的念头:我所希望的,我得不到;我所得到的,却不是我最希望得到的。现在则不同了,她似乎有这么一种魔力,可是她自己却意识不到。跟她在一起,很容易放松,只有在她流露出某些与铁木儿相似的言行时是例外,那样会让我焦虑和惶惑,甚至无所适从。
打电话的那个显然是个有耐性的人,一遍又一遍,也不嫌累得慌。铃声叫得像隆冬的北风,凛冽极了。陆清笑着推了推我,“我看,你最好还是去接吧,不然它会响上一夜的。”
我只好下地,从丢在地板上的裤子的兜里摸出电话,我首先听到的不是问话,而是哭声,确切地说,是梅梅的哭声。
“怎么了?”我忐忑地问道。
“原田住院了,现在正在手术室抢救呢。”梅梅泣不成声地说。
“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彭哥他们呢?”
“他们都到北京听蔡琴演唱会去了。”
“现在,你们在哪所医院?”
“县医院,你知道要去省城得一小时的行程,而县医院只花二十分钟就够了。”
()免费TXT小说下载
“等着,我马上去。”我没跟梅梅说,我此时此刻就在省城,怕她着急。我只有拼命赶路,尽可能地抢时间了。
我的神色一定十分紧张,让陆清很担心,她过来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对不起,我又得匆匆离去了。”我抱歉地说。
陆清给自己披上了一件睡衣,用手心抚抚我的眼睑,豁达地说,“有事,你就去忙吧。”嘴上这么说,脸上却不免露出萧瑟的神色。
吻了她一下,就要走。
她又说:“后天是我的生日。以往我从没过过生日,这一次过不过也无所谓,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过还是不过?”
我说:“过,当然要过,后天我一定过来,如果还有其他朋友的话,也一起叫上,我们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
“不必,人多就闹得慌了。”她淡然地说,我却还是从她的眼睛看出一抹欣喜一掠而过。她又说,“有你,我就很快乐了。”
我走出陆清的那间小屋,开着车,穿过大街,大街上刮着的风,把大街两侧的树吹得东摇西晃,跟我忐忑不安的心差不多。不知道原田究竟怎么了?人总是对未知的东西感到恐惧,因为它可以把人的思路引向无限广大的遐想之中,所有这些遐想足以让你心惊肉跳,越是最坏的境遇就越往那上面去想,而且偏执的令人无法扼制……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3
赶到医院里,原田恰好从手术室推出来,因为摘掉了眼镜,他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里,晦暗的要命——这可能是由于他一连数月闷在屋里给哪个混帐导演赶剧本的结果。我问过医生,医生告诉我,他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幸好手术做得很顺利,估计躺半个月就会痊愈。这才让我松了一口气。梅梅对我说,如果再迟些到医院,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不禁愧疚起来,愧疚自己在哥们儿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能冲在第一线。
“对不起,嫂子。”把原田送进了病房,我和梅梅坐在走廊上的长椅上。
“不怪你,他是自己累的。”梅梅惊魂未定似的,“我劝过他多少次了,不要再接剧本了,他不干,非要拿什么来证实自己。”
“你太疲劳了,回去休息吧。”我说,“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