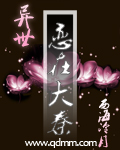大秦究竟多彪悍-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范雎坦然答道:“齐王以黄金十斤及牛、酒赐臣,臣不敢受,但来人四次非要强给,臣只留下了牛、酒。”
须贾又问:“赐给你这些东西是何故呢?”
范雎答:“臣不知,或者他们认为臣在大夫您左右,由于尊重大夫而惠及臣罢了。”
须贾不满意这个答案:“赐东西不给我,而独独给你,必是你与齐有隐情吧。”
范雎说:“齐王曾派人来,想留臣为客卿。臣严词拒绝。臣素以信义自律,岂敢有私?”
第十七章不大正常(3)
话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但须贾疑心却更重。从齐国出使归来,须贾就向相国魏齐汇报了此事,说很怀疑范雎在暗中将魏国的机密透露给了齐国,否则人家怎么又要给官做、又要给金子的。
魏齐大怒,派人去抓来范雎,又召集宾客聚会,即席审讯。审讯中,范雎还是那套话,拒不承认与齐国有私。
想那魏齐是何等人,当惯了大官儿的,脾气暴怒无常,对着范雎咆哮道:“卖国贼!既有牛、酒之赐,岂能事出无因?”于是招呼狱卒来,把范雎绑了去,用竹条抽脊背一百下,要逼出口供来。但范雎抵死不认。
魏齐更怒,叱道:“为我笞杀此奴!”
狱卒一顿鞭笞,打得范雎牙齿折断、血流满面。范雎受刑了也不服,只是喊冤。众宾客见相国发怒了,哪个敢劝?就这样,魏齐一面和大家用大碗喝酒,一面命狱卒使劲儿打。自辰至未(从早8时,到下午4时),打得范雎遍体皆伤、血肉横飞,最后“咔嚓”一声,肋骨被打断。范雎大叫一声,背过气去了。
这舍人的白饭,真不是好吃的,前有张仪被诬陷偷窃宝玉,现又有范雎“被卖国”——男儿之所以需要自强,就因为寄人篱下的苦楚,远不止受气而已。
左右的人看了看,报告说:“范雎气绝矣。”
魏齐亲自走下来看,见嫌犯断肋折齿、体无完肤,觉得还不解气,指着“尸体”骂道:“死得好!”随后,命狱卒用苇席卷了尸体,放在茅坑旁,让宾客撒尿于其上,卖国贼嘛,就得遗臭万年。
天黑之后,范雎命不该绝,死而复苏。他见狱卒还老实,就许诺以黄金数两买通了狱卒,让狱卒把自己偷偷背回家去。
狱卒趁着魏齐与宾客都喝得大醉,禀报说:“把死人埋了算了。”
魏齐命令:“把他扔到郊外,让老鹰饱餐一顿。”
监狱守卒便偷偷把范雎背到范家,范雎的妻子儿女见了,又惊又痛。范雎命家人拿出黄金来酬谢狱卒,又卸下苇席交给狱卒,嘱咐他扔到野外去。
范雎告诉家人,自己能逃得一命,是因为魏齐喝醉了,醒后一定会来查。范雎让家人通知铁哥们儿郑安平,来把自己接走,又嘱咐家人要假装哭丧,以迷惑外界,自己藏匿一个月后就会逃走,千万不要牵挂。
次日,魏齐果然起了疑心,怕范雎没死,派人去查看尸首。狱卒报告说:“扔到野外无人之处了,现在只剩苇席在,可能是被野狗叼去了。”
魏齐眼珠一转,叫人去监视范家,见到范家举哀戴孝,这才放了心。
这件事的处理,足以说明古代政治家之厉害,一是对下属宁可信其坏,不可信其好;二是搞人就要搞死。
可惜魏相国做事还是稍粗心了一些,第二条没做到,后面就有了报应。这个,我们稍后便知。
范雎藏匿在郑安平家,身体渐渐复元。两人就一起上了具茨山,隐居起来,范雎改名为张禄,外人皆不知他何许人也。这样过了半年,刚好碰见王稽奉秦昭襄王之命,出使魏国。郑安平就冒名顶替去当了驿卒,伏侍王稽。
郑安平应对敏捷,王稽对他很欣赏,私下里问他:“你们国家有贤人但又没当官的吗?”
郑安平说:“过去有一范雎者,其人乃智谋之士,可惜被相国给捶死了。”
王稽叹道:“惜哉!”
郑安平接着就说:“不过,臣的邻居中有一位张禄先生,其才智不亚于范雎,您想见见否?”
王稽很高兴,说马上就想见。郑安平说:“此人有仇家在国中,不敢昼行,只能晚上来见。”
到了深夜,范雎也扮做驿卒模样,跟郑安平一块儿到了公馆。王稽略问了问天下大势,这位假张禄侃侃而谈,无所不知。王稽大喜,当下邀请“张禄”赴秦,并约好日期相会。等到了辞别归国之日,王稽就偷偷把范雎、郑安平装到自己车上,给拉回秦国去了。
没走几天,就进入了秦界,到了湖关,忽然望见对面尘头起处,一队车骑自西而来。
范雎问道:“来者谁人?”
王稽认得仪仗,说:“此是丞相穰侯,代秦王巡视郡邑。”
范雎就说:“我听说穰侯专权,妒贤嫉能,最讨厌山东诸国的宾客,见了就要骂,我还是藏在车厢中避一避吧。’
不一会儿,穰侯魏冉到了,王稽下车迎谒,魏冉亦下车相见,两人互致寒暄。
魏冉目视车中,说:“先生没带诸侯宾客一块儿来吧,此辈仗口舌之能,游说别国,以取富贵,全无实用。”
王稽鞠躬道:“不敢。”
第十七章不大正常(4)
魏冉点点头,告别而去。范雎从车厢中爬出,便欲下车徒步行走。
王稽笑了:“丞相已去,先生可与我一同坐车。”
范雎说:“臣偷看穰侯之貌,眼多白而斜视,说明其人性疑而反应慢,刚才目视车中,就已有怀疑,他没有马上搜查,不久必悔,悔必复来。我还是避开比较安全。”于是招呼了郑安平也出来,一块儿步行。
王稽的车仗,就跟在他们后面几里地,走了大约10里,忽听背后有马铃声响,果然有20骑从东边如飞而来,赶上了王稽车仗。
为首的军士说:“吾等奉丞相之命,恐大夫带有游客,所以派我等再来查看,大夫勿怪。”
可是搜遍了车中,并无外国之人,一伙军士这才打马离去。王稽叹道:“张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于是催车前进,赶上了范雎、郑安平二人,把他们装上车,一起回到了咸阳。
这就是假张禄、真范雎的身世与来由。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固然有“一朝君王垂拂拭”的奇遇,但也可能有“被卖国”的无妄之灾,远不如今日之书生做得稳当。
那么,这位假张禄闲待了一年,为何忍不住要给昭襄王上书呢?
原来,有一日范雎走到街上,见到处都在征兵,说是丞相魏冉要发兵。
范雎就偷偷问别人:“丞相征兵,将伐何国?”
一老者说:“欲伐齐地刚、寿也!”
范雎纳闷了:“齐兵曾犯境乎?”
老者说:“没有啊。”
范雎就更不明白了:“秦与齐不接壤,中间隔有韩、魏,且齐不犯秦,秦为何要长途跋涉去远征?”
老者见这外乡人不开窍,就把范雎引到僻静处说:“伐齐,非秦王之意,因陶邑在丞相的封邑中,而刚、寿近于陶邑,所以丞相派武安君为将,要把这两块地拿下,以增加自己的封地。”
范雎一听,心里有数了,回到客舍就上书给秦王——他知道怎么能打动秦王了。
滔滔千年的历史,有时候命运就系于一卷尘封的帛书上。
秦昭襄王早把张禄忘了个一干二净,一见到这帛书,忽然触发了某种灵感,命人用车把“张禄先生”接到离宫召见。
范雎到了以后,秦王还没到。远远望见秦王的车骑来了,他佯作不知,故意快步走到巷子中央,宦官连忙来驱逐,说:“大王来了。”
范雎故作惊人语:“秦独有太后、穰侯,哪里有王?”一面说着,一面继续朝前走。
正在吵嚷间,昭襄王到了,听了宦官的汇报,他也不怒,遂将范雎迎进内宫,待之以上宾之礼。
昭襄王屏去左右,长跪而请求道:“先生有什么赐教于寡人的?”
范雎一抬头,作了个揖:“呵呵。”而后便无语。
过了一会儿,昭襄王又跪请一遍,范雎又客气了一下:“呵呵。”
如此三次,昭襄王忍不住了:“先生不赐教于寡人,莫非认为寡人不足以与您对话吗?”
范雎说:“臣哪里敢这样?臣所欲言者,皆秦国兴亡大计,或关系宗室骨肉之间的。不深言吧,则无助于秦;欲深言呢,则箕子、比干之祸就会随之而来。”
昭襄王一听就明白了,又跪请道:“事凡可言者,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尽言无隐。”
范雎这才放下心来,滔滔不绝,说出了一番石破惊天之语来。
他的这番话,决定了华夏后来的历史。是功是过,不易分辨,反正很多东西一直延续到现代。
——先秦人物的智慧,真是无可估量!
他说:“秦地之险,天下莫及,甲兵之强,天下也无敌;但兼并之谋无果,霸王之业不成,这不是秦之大臣脑筋不灵吗?”
一语击中软肋,昭襄王连忙问其原因。
范雎说:“臣听说穰侯想穿越韩、魏去攻齐,这计划不是太傻了吗!齐离秦甚远,有韩、魏隔在中间,出师的兵力要是少了,则不足以损齐;要是出师的兵力多了,则秦之负担太大;如果伐齐而不克,为秦大辱;就算伐齐而克,不也是白白便宜了韩、魏,于秦有何利呢?我为大王考虑,不如远交而近攻。远交是离间远近邻国的关系,近攻是扩展我之土地。如此由近而远,如蚕吃叶,天下就不难吃完呀!”
昭襄王听得入迷:“远交近攻?好。那么实施细则何如?”
范雎微微一笑:“远交齐楚,近攻韩魏。拿下了韩魏之后,齐楚还能独存吗?”
秦王豁然开朗,鼓掌叫好,旋即拜范雎为客卿,号为“张卿”,用他的计谋,实施东征韩、魏战略,并下令白起的伐齐之师停止开拔。
智者的一席话,可以左右千万人的命运。
风向变了,秦之黑旗的指向,也就要变了。
第十八章私人恩怨有时也能推进历史(1)
范雎受到赏识这一年,秦昭襄王执政刚好过了40年。40年的忍耐,终于像弹簧被压到了底,反弹起来后,力道将无比之大。
这时候,魏冉与白起在朝中已得意多年,忽然看到来了个张禄,一夜之间成了昭襄王的亲信,俩人都感到不大自在。
昭襄王则像久旱逢甘霖,一刻也离不开范雎了,每每半夜还把范雎召来议事,无所不谈。
范雎揣摩着,秦王对自己的恩宠已固,没有问题了,就请秦王找了个地方,屏去左右,神秘兮兮地说:“臣有安秦之计。”
昭襄王连忙又跪下,洗耳恭听。
范雎说:“臣从前居住在山东时,只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秦王。按理说,能管理国家的,那才叫王,现在太后恃国母之尊,擅专朝政四十余年;穰侯为秦相国,华阳君辅之,泾阳君、高陵君各立门户;他们生杀自由,私家之富十倍于公室,大王徒有空名,不亦危乎?现在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威,用兵则诸侯震恐,讲和则列国感恩。他还在大王左右遍布眼线,大王孤立无援,已不是一天了吧。怕是千秋万岁之后,掌控秦国的,就不是大王的子孙了!”
所谓专制之权,就在一人,即使老妈、老舅也不行——这番话,句句都是攻心术。昭襄王听了,不觉毛骨悚然,连连拜谢范雎。
第二天上朝,昭襄王立刻宣布,收穰侯魏冉的相印,请回封邑养老去。
古代政治的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如此。权臣如没有篡权准备,一把手只需一句话,权臣之权就顷刻丧失,全无反抗之力。
魏冉离开咸阳之时,从政府借了牛车运他的家财,竟有千乘之多,满载的奇珍异宝,全是王宫内库所没有的。
过了一天,昭襄王又宣布:放逐华阳、高陵、泾阳三君于关外,安置宣太后于深宫,不许他们参与政事。尔后,任命范雎为丞相,以应城为其封地,号为“应侯”。
就这样,范雎与昭襄王只是聊聊天、喝喝茶,就全面改革了秦国的内政外交。
可见,改革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决策者想不想改。想改,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搬掉了内政上最大的障碍,接下来对外战略的大戏,就看范雎与昭襄王如何放开手去演了。
对秦国所发生的变化,最为敏感的当然是“三晋”。当时魏昭王已死,儿子安厘王即位。风闻秦王起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禄为相,要讨伐魏国,安厘王慌了,急召群臣来商议。
安厘王的弟弟、“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说:“秦兵不来进犯魏国已有好几年了,如今无故兴师,明明是欺我不能与之抗衡,所以应严阵以待,他敢来就痛扁他!”
那位曾把范雎置于死地的相国魏齐,则表示反对:“不然,秦强魏弱,要打肯定是不能侥幸取胜的,咱们还是来软招子为好。我听说秦丞相张禄是我们魏国人,既是魏人,岂能无香火之情?如果派使者多带点钱财,先买通这位张相,后谒见秦王,许诺以公子为质讲和,可保魏国安然无事。”
安厘王是初即位的国君,从未经历过战伐之事,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战略战术,觉得还是相国的办法省事,于是就派中大夫须贾出使秦国,去忽悠一下。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很幽默了,仿佛《基督山恩仇记》的中国古代版。须贾傻头傻脑地领了命,直奔咸阳,下榻于馆驿。
这边范雎早已探之,窃喜道:“须贾至此,乃我报仇之日到了!”于是他换掉华丽衣裳,装作寒酸落魄之状,来到馆驿谒见须贾。
须贾一见,大吃一惊:“原来范叔没事哦?我还以为你被魏相打死了,怎么还留了条命在此?”
范雎说:“那时候把我的尸首扔到郊外,第二天早上才苏醒,恰好遇到有客商路过,听到呻吟声,怜而救之,我这才苟延一命。但不敢回家,专拣小路走,来到秦国。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大夫之面!”说着,似乎泪珠就要滚滚落下了。
须贾忙问:“范叔是想在这儿游说秦王吗?”
范雎可怜兮兮地说:“我昔日得罪魏国,亡命来此,能活着就不错了,还敢开口言事吗?”
须贾又问:“范叔在秦,何以为生?”
范雎这回眼泪真就掉了下来:“为人帮佣,糊口而已。”
须贾早先坑害范雎,不过是嫉妒加上“极左思维”。他本质上并非冷血之人,见范雎这副“犀利哥”的模样,不觉动了哀怜之意,连忙招呼他同坐,又吩咐手下端了酒食来,给范雎充饥。
时值寒天,范雎衣衫单薄,冻得瑟瑟发抖。须贾见了,叹道:“范叔怎么穷成这个样子?”于是又命左右,拿一件棉袍来给范雎穿。
第十八章私人恩怨有时也能推进历史(2)
范雎慌忙摆手:“大夫之衣,范某何敢当?”
须贾说:“故人何必过谦呢?”
范雎穿上袍子,再三再四称谢,然后问道:“大夫来秦国有何事?”
须贾说:“如今秦相张君正受重用,我想走走他的门路,但遗憾无人引见。先生你在秦国久了,是否有关系,能让我先跟这个张君勾兑勾兑呢?”
范雎说:“巧了,我的主人恰好与丞相关系不错,我也曾随主人到过相府,这个张丞相,特好谈论,言谈间我的主人答不上,我往往就要插上两句,张丞相认为我有辩才,常赐我酒食。跟他,我还算贴得上。先生您要想谒见张君,我当同往。”
须贾喜上眉梢:“既然如此,麻烦你预先订好日期。”
范雎说:“丞相事忙,今日正好闲暇,何不这就去?”
须贾当然愿意,不巧他的马车坏了,范雎就诈称自己主人的马车可以借出来,于是回到相府,赶着自己的马车出来,再到驿馆请须贾上车:“今儿我为先生赶车!”
世上的事情,如果巧得像个故事,那就肯定有假无疑。须贾居然丝毫不疑,欣然登车。
一路上,范雎牵着缰绳,摇着鞭子,像模像样。街市上的路人望见,都吃了一吓:“哦,今儿怎么丞相御车而来?”
众人肃然起敬,拱立两旁,也有吓得慌忙走避的。须贾见了,以为是秦人都敬畏自己,很是得意,万没想到大家怕的是他的车夫。
到了相府门前,范雎说:“大夫请在这儿稍等,我先进去,为大夫通报一下。”说罢,就径直进门去了。
须贾立于门外,候之良久,只听见府中有鸣鼓之声,有喧哗之声,都喊“丞相升堂咯……”随后属吏、舍人奔走不绝,但并不见范雎出来。他只好问守门人:“刚才有故人范叔,进去通报相国,久而不出,您能帮我叫一下吗?”
守门人问:“先生所言范叔,是何时进府的?”
须贾答:“刚才为我御车的就是啊。”
守门人哈哈大笑:“御车者?那就是丞相张君啊!他是微服到驿馆去访友的,哪里有什么范叔?”
须贾闻言,不禁愕然。
张禄——秦相——魏人——范雎……他脑袋转了半天,才如梦方醒:“吾为范雎所欺,死定了,死定了!”
想想没法,只得脱袍解带,免冠赤脚,跪于门外,托门子进去通报,只说是:“魏国罪人须贾,在外领死。”
过了好久,门内才准入。须贾哆哆嗦嗦,低头膝行,直至阶前,连连磕头称“死罪”。
范雎威风凛凛,坐于堂上,直视着这个家伙——又要搞人,又搞不死,不是自己在找死吗?于是问:“汝知罪吗?”
须贾汗流浃背,伏地答道:“拔我贾某的头发,以数我之罪,尚犹未足。”既然身陷绝境了,要保命,就先糟蹋自己吧。
范雎冷笑道:“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我来教你吧,你罪有三:我的先人庐墓在魏,所以不愿去齐国做官,你却以我私通齐国去告状,此罪一也;魏齐发怒之后,把我打得满地找牙,你却一点也不劝阻,此罪二也;到了我昏死过去,已弃厕中,你还率宾客尿我。过去孔子说‘不为已甚’,你怎么会如此忍心,此罪三也。今日至此,本该拧掉你的头,以报前恨,你之所以还死不了,是因刚才赠我棉袍,尚有故人之情,因此能苟全你的命!”
须贾叩头称谢不已,范雎挥挥手让他滚,须贾连忙匍匐而出。从这一天起,秦人才知道:威名赫赫的张禄丞相,原来是魏人范雎伪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