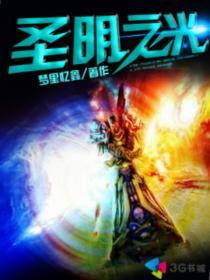八月之光-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这边来,丘普,”跟在女人后面的那个男人说。
“你在找谁,老兄?”那个黑人问。
“丘普,”女人中有人说道,她的声音略微高一些,“嘿,你过来。”
又隔了一会儿,两个一白一黑的头颅仿佛在黑暗中悬挂着,相持不让。然后从什么地方吹过一股凉风,黑人的头恍若漂流散去。克里斯默斯缓缓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消散、重新没入灰白的道路;他发现手里早已握着那柄剃刀。刀没有拉开。他这样做并非出于恐惧。“狗娘养的!”他大声骂道,“几个龟孙子!”
风刮起来了,暗淡而又冷凄,连那吹进他鞋子里的尘土也带着凉意。“他妈的,我怎么啦?”他心里纳闷。他把剃刀放回口袋,停下来点燃香烟。他舔了几下嘴唇才叼起烟卷。在火柴的光亮里他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这一切麻烦事,”他想,“他娘的这一切。”他骂出声来了,一面又开始举步。他仰望天空,天空里的繁星,心想:“现在准快十点了。”恰好这时,他听见从两英里外的法院大楼传来的钟声,悠悠缓缓,响亮地敲了十下。他边听边数,再次停在空寂的路上。“十点钟,”他想,“昨晚我也听见敲十点。还听见敲十一点,十二点。可是没有听见敲一点,说不定是风向变了。”
这天晚上,他听见敲十一点时正背靠着破门内的一棵树坐着,背后那幢楼房同样黑魆魆地隐没在草木丛中。今天晚上,他想的不是也许她也没睡着现在他什么也没想,心思还没开动,心里的种种声音也没有开始。他只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听见两英里外的时钟敲响十二点。这时他起身朝楼房走去,步子不快。这时他甚至没想就要出事,我就要肇事了。
六
记忆里积淀的必早于知晓的记忆,比能回忆的长远,甚至比记忆所想象的更久远。知晓的记忆相信有一条走廊,那是在一幢宽大长方的歪七扭八、冷浸浸回应有声的楼房里的一条走廊;这幢楼房的红砖墙已被它的烟囱,更多的是它四周的烟囱,熏得污黑暗淡;户外空地铺满炉渣,寸草不长;这幢房屋困在煤烟直冒的工厂中间,还被一道十英尺高的铁丝网包围起来,活像一座监狱或一个动物园;这儿偶尔也会腾起孩子们雀噪的声浪,在回忆里,那些身穿清一色粗棉布蓝制服的孤儿会不时浮现脑际,但在知晓中,这些孤儿同阴冷的墙壁、同那些无遮无蔽的窗户一样总是历历在目;遇到下雨天,雨水将窗边常年从四周烟囱飘落来的烟灰粘聚在一起,像是黑色的泪水滚滚下流。
在这条寂静空荡的走廊里,在正午之后的清静时刻,他像一个影子在那儿晃动;五岁了,个子还那么瘦小,不作声不出气的,跟影子一般无二。走廊里要是还有另一个人,那人准无法确切地说出他在什么时候、从哪儿悄然隐匿,钻进了哪扇门,进入了哪间房。可是此时此刻,走廊静悄悄空无一人。他知道这一点。自从他偶然发现营养师使用的牙膏那天起,将近一年时间他总在这个时候来到走廊。
一旦他钻进那房间,便赤着脚、不出声地端直走到梳洗台前,找到那管牙膏。他正看着粉红虫状的膏汁缓缓地凉爽细滑地溢上他羊皮纸般的黄色手指头,这时突然听见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接着听见说话声就在门外。也许他已辨别出营养师的话音。慌忙之间,还不等弄清他们是否只是打门前经过,他便抓起牙膏,赤着脚悄声悄气、仍像影子般横过房间,躲进遮掩屋角的一张布帘后面。他蹲在这儿,置身精致的鞋靴和悬挂的女人的细柔衣衫中间。他蜷伏在那儿,听见营养师和她的伙伴进入房内。
营养师在他心灵里还没有任何印象,除了与吃饭、食品、食堂以及木桌边餐前的仪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她出没于他视线之内,在他脑海里没产生任何影响,只不过偶尔他会获得愉快的联想,看见她时会感到快活——她年轻,体态丰满,肌肤匀滑,白里透红,不禁使他的思维想起食堂,使他的嘴巴想起香喷喷黏糊糊的食品,而且还是粉红色的,有点神秘的。他最初在她房里发现牙膏的那天,他径自撞进房,从未听说过牙膏,只是仿佛知道她准会有些那一类的东西,他会在房里找到它。他能分辨出她伙伴的声音,一个从乡村医院来的年轻实习生,教区医生的助手,也是这幢房里的常客,而且迄今还说不上是个敌人。
他躲在帘子后面,现在安全了。他们走后,他会把牙膏放回原处,也要离开。于是他蹲在帘子背后,不经意地听见营养师紧张的轻声话语:“不!不行!别在这儿。现在不行。人家会抓住咱们的。会有人——不,查利!请别这样!”男人说的话他一个字也不懂,也放低了声音。那声音带着冷酷无情的意味,就像迄今他所听过的所有男人的声音,他还太年幼离不开女人的世界;可此刻他巴不得逃离,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离开,然后甘愿一直呆到死亡时刻。他还听到一些他并不理解的声响:脚被拽着划过地板的声音,钥匙在门里转动的声音。“不,查利!查利,行行好吧!请别这样,查利!”女人在轻声地乞告。他还听见别的声音,窸窸窣窣,咕咕哝哝,但不是话音。他无心听,只是等在那儿,既不好奇也不在意地想着:这个时刻上床睡觉真莫名其妙。透过薄薄的布帘又传来女人微弱的声息:“我害怕!快!快!”
他蹲在满是女人气味的柔软衣衫和鞋靴中间。他凭感觉发现原先圆鼓鼓的牙膏现在给糟蹋了。凭味觉而非视觉,他感到那条看不见的凉爽虫子,像蜷曲地溢在他手指头上那样爬进了他嘴里,挺涩嘴却又甜甜地直往里钻。平常他并不贪心,嘴里含上一口就行,就把牙膏放回原处离开房间。哪怕只有五岁,他也知道不能再贪多。也许是那条软虫在警告他,贪多会使他生病;也许是他做人的本性在警告他,贪多她会发现牙膏变少了。这是他第一次贪多过量。他藏在那儿等候,到这时他已经多吞了不少。凭感觉他仿佛看见渐渐挤光的牙膏。他开始冒汗。然后他发现汗水已经冒了好些时候,好长一段时间他只是呆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淌汗水。这时他完全听而不闻了。帘子外面要是放一枪,他多半也听不见。他的注意力仿佛转到了自身,眼看着自己流汗,看着自己将另一条膏虫往嘴里塞,而他的肚子却不愿接受。果然,它拒绝往下钻了。现在他一动不动,凝神静气,像位化学家躬身待在实验室里等待着反应。他不用等多久,吞下的牙膏很快在体内翻腾,竭力想退出来,回到凉爽的空气里。那感觉不再是甜甜的了。他恍恍惚惚地蹲在满是女人胭脂气味的帘后暗处,口边悬着粉红色的唾沫,静听着体内的动静,带着惊讶的宿命想法等待着那即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接着,真的发生了。他一败涂地,只好乖乖地投降,自言自语地说:“唉,我糟了。”
当帘子突然拉开时,他没有抬头。他正在呕吐,一双手粗暴地把他拽出来,他没有抵抗。他被一双手拽着,歪歪倒倒,垂着下巴,傻乎乎地看着一张不再粉红白嫩的面庞,面庞周围拂着散乱的头发,那些泡酥酥的发卷儿曾使他想起过糖果。“你这讨厌鬼!”一个愤怒而微弱的嘶声骂道。“小密探!敢来监视我!你这小黑杂种!”
营养师二十七岁了——满有理由去冒险闯闯春宫,但毕竟年纪尚轻,她更加关心的不是爱情而是会不会被人当场捉住。而且她还愚蠢透顶,竟相信一个五岁的孩子不仅能从听见的声音推断出她所干的事,还会像成年人那样把它张扬出去。因此,事后的整整两天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眼睛往何处瞧,她总感到那孩子带着动物的窥测本能以深沉的目光盯着她,她越想越觉得他像个成年人:她相信他不仅打算讲出去,而且此刻故意保持沉默,好让她多受折磨。她压根儿没想到那孩子会认为自己犯了罪过,而今迟迟未受处罚,心里惶恐不安;他有意出现在她面前,为了挨一顿鞭打,把罪过抵销,让事情了结,一笔勾掉。
第二天快过去了,她差不多陷入绝望境地。夜里她通宵不眠,大半时间神情紧张地躺着,咬牙切齿,紧捏拳头,又气愤又害怕;更糟糕的是,她感到悔恨:一股莫名的怒火使她恨不得将时间倒转,哪怕是一小时、一秒钟也好。这时,爱情全然被排除了。年轻的医生甚至比那小孩更不屑一顾,没给她任何帮助,只给她带来了灾难。她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最憎恨什么,甚至分不清自己睡着与醒来的时候,因为在她的眼皮下,在她的视网膜上,时时刻刻呈现出那张沉静严肃、无法躲避的死死盯着她的羊皮色面孔。
到了第三天,她挣脱了似睡若醒的昏迷状态,不像头两天那样,在白天与人一起的时候,要毫不松懈地摆出一副假面孔,把自己严实地掩盖起来。这一天她采取行动了。她毫不费事地找到他。那是在午饭后的清静时刻,在空荡的走廊里。他果然在那儿,什么事也没干。也许他一直跟在她后面。谁也说不准他是不是在那儿等候。所以她在那儿找到他,毫不奇怪,而他听见脚步声后便转过身来望着她,也一点儿不感到惊奇:两人面面相对,一张脸不再匀滑、白里透红,另一张却仍然严肃庄重,除了期待别无任何表示。“这下我可以把那事了啦,”他想。
“听着,”她说。说完,她停住脚步,凝视着他,仿佛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孩子等在那儿,屏息静气,一动不动。渐渐地,缓慢地,他背部的肌肉变得平板、僵硬、紧张起来,像块木板似的。“你要说出去吗?”她问。
他没回答。他相信谁都应当明白,他绝对不情愿谈起自己关于牙膏和呕吐的丑事。他没敢看她的脸,只注视着她的双手,等待惩罚。她一只手捏成拳头放在裙子口袋里,透过裙布他看见捏得很紧。他还从未被别人用拳头揍过,也没有经历过连等三天才受处罚的事。当他看见那只手从口袋伸出来时,他相信挨揍的时刻到了。然而她没揍他,那手仅在他眼皮下摊开,手心里露出闪亮的一枚银元。她的声音纤细、急切而又微弱,尽管走廊里就只有他们两人。“你用它可以买不少东西。整整一美元呢。”他知道那是什么,但从未亲眼见过一美元。他眼睁睁地看着它,渴望得到它就像渴望得到啤酒瓶上亮晶晶的盖子一样。可是他不敢相信她会给他,因为这东西要是他的,他准舍不得给她。他不明白她要他做什么事。他正等着挨一顿鞭打,然后被豁免了事。她又开口说道,急迫紧张,说得很快:“整整一元呢,看见了吗?能买许多东西哩。每天买吃的也够花一个星期。下个月说不定我还会给你一块钱。”
他站着不动也不吭气,像个泥塑木雕的大玩具:瘦小,沉静,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眼睛,穿一件罩衫。他仍然惊讶不已,目瞪口呆,感到羞耻。看着那块银元,他仿佛瞧见讨厌的牙膏像条软木棍不断往外伸,叫人毛骨悚然;他整个身躯突然蜷曲起来,显得反感嫌恶极了。“我绝不要,”他说。“我永远千万不那么干了,”他心想。
这时他简直不敢望她一眼。他能感到她站在面前,听得见她说话,一声漫长而颤栗的叹气。他闪过一个念头现在该挨揍了可是她甚至没有动他,只是紧紧地抓住他,连摇都未摇他一下,仿佛她的手也不知道往下该如何行动。她的面孔靠得那么近,他能感到她的气息冲上自己的面颊。他不用抬头便知道她此刻的面孔像什么模样。“讲吧!”她说,“那你就讲出去吧!你这小黑鬼!黑杂种!”
那是第三天的事。到了第四天,她变得十分冷静,但又怒不可遏。她不再费心盘算。这以后她按照某种预见采取行动,仿佛不得安宁的白昼和不能入睡的夜晚加剧了她冷静的面具背后的恐惧和愤怒,将她的心灵与女人对邪恶的自然敏悟连在一起了。
现在她很坦然,甚至暂时也显得不着急了。现在她似乎有了周密思考和筹划的时间。她掂量着那情形,把全部注意力、心思和考虑统统集中到那个坐在锅炉房门口的看门人。这既缺乏周密的论证,也未曾细心盘算。看起来她只是往外望望而已,像坐在车内晃眼望见行人,毫无惊异地看着那个瘦弱邋遢的看门人——他正坐在积满污垢的门边的一张藤椅里,透过钢架眼镜读着摆在膝上的一本书——这个人几乎像根木桩似的,她知道他已有五年了,却从未真正把他看在眼里。走在街上,她不会认出他,从他身边经过也会视而不见,尽管他也是一个人。她的生活此刻恍若一条走廊,笔直而又简明,他就坐在这条走廊的另一端。她立即朝他走去,还没意识到开步已经踏上那条污黑的小道。
他坐在门口的一张藤椅里,一本翻开的书摆在膝头。她走近时看清是本《圣经》,她只是看了一眼,犹如瞥见他腿上有只苍蝇。“你也恨他,”她说,“一直在监视他,我看出来了,别对我否认。”他抬起头看着她的面孔,眼镜掀在眉梢。他并不老,与他目前干的这份差事不相称。他是个严峻的人,正当壮年;他应当过一种更充实更有活力的生活,可偏偏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竟把一个四十五岁、具有健壮体魄和心智的人扔到了阴山背后,一个适合六十岁或六十五岁的人呆的地方。“你知道,”她说,“在别的孩子叫他黑鬼之前你就知道了。你跟他大致在同一时候来这儿的。圣诞节晚上查利在大门的台阶上发现他,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你才到这儿干活的。我说得对吧。”看门人的脸圆圆的,面皮有些松弛,极为污秽肮脏,没刮胡子,满脸胡茬。他的眼睛十分澄明,呈深灰颜色,非常冷峻却又非常狂暴。但是女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也许在她看来并不显得狂暴。于是两人在积满煤尘的门边面面相对,疯狂的目光直视着疯狂的目光,恶狠的声音与恶狠的声音相撞,但声音不高,声音平静安详,谈话简洁,活像两个密谋者在一起策划。“我观察你已经整整五年了,”她深信自己说的一点儿不假,“你就坐在这张藤椅里,一直在注视他。孩子们到户外的时候你才坐在这儿。每当他们出现,你就把椅子挪到门边,坐在你能观察到他们的地方。你注视他,听别的孩子叫他黑鬼。这就是你干的事。我知道。你来这儿就为这个,观察他,憎恨他。你做好了准备他才来的。也许就是你把他抱来扔在那边门前的台阶上。总之,你心里明白。而且我必须知道。他一旦说出去,我就会被解雇。查利说不定——会——告诉我。把真相摊出来,现在就告诉我。”
“噢,”看门人说,“我早就晓得他会在那儿抓住你们的,当上帝惩诫的时机到来。我早晓得。我知道谁叫他藏在那儿的,一个征兆,一个对淫荡的诅咒。”
“不错,他就藏在帘子背后。离得像你这样近。你现在给我讲清楚。你瞧他的时候我看清了你的眼神。我一直在注意你,整整五个年头了。”“我知道,”他说,“我明白啥叫邪恶。难道不是我让邪恶站起来在上帝的世界里行走?我让它像浊气一样游动在上帝面前。上帝绝不阻止它从小娃儿嘴里说出来。你听见过他们叫喊的。我从来没教他们那样喊,叫他本来该叫的名字,该受诅咒的名字。我从来没对他们说过。他们早就晓得。有人告诉了他们,可不是我。我只是等待,等待上帝选择好时机,当他认为该向他的众生世界揭露邪恶的时候。现在时候到了。这是一个征兆,再次表现在女人的淫荡犯罪上。”
“是这样。但我该咋办呢?告诉我。”
“等吧,像我这样等着。我等了整整五年,等待上帝采取行动,表明他的意志。他终于这样做了。你也等待吧。等他准备好了,他会向有权威的人表明他的意志的。”
“是,有权威的人。”他们彼此怒目而视,却很冷静,心平气和。
“女总管。上帝做好准备时就会向她透露他的意志的。”
“你是说,要是女总管知道了,她就会把他送走?对啦。可是我不能等。”
“同样,你不能催促上帝。我不是等了五年吗?”
她轻轻把两手拍合在一起。“可是,难道你不明白?这也许正是上帝的意志,让你告诉我,因为你知道。由你告诉我,再由我去对女总管讲,说不定这正是上帝的意志。”她疯狂的目光显得异常沉静,恶狠狠的声音表现出耐心和安宁,只是她的一双手老在不停地动着。
“你得等待,像我这样,”他说,“你已经掂到了上帝令人悔恨的手掌的分量,大约三天了吧。我在他令人悔恨的手掌下生活了五年,一面观察一面等待,等他认为合适的时机,因为我的罪过比你的更大。”虽然他直盯着她的面孔,但似乎全然没有看见她,他的眼睛没有注视她。那双眼像是视而不见的盲眼,睁得老大,冷冰冰的,似迷若狂。“比起我犯的罪和我为赎罪吃的苦头来,你所干的事和受的折磨算个啥,只不过是女人害怕受到脏话辱骂而已。我已经苦苦忍受了五年。你算老几,敢为你那女人的淫秽去催促全能的上帝?”
她立即转过身去。“好吧。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告不告诉我都一样。我老早就知道他是个混血的黑崽子。”她转身回楼房去。现在她走得不快了,而且呵欠连天。“我只消想出个办法让女总管相信就成。他不会告诉她,不会支持我。”她又打了个呵欠,又长又大的呵欠,她的面孔上除了打呵欠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连呵欠也销声敛迹。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这以前她干吗没有想到,可是她深信她早就心里明白,一直明白,因为这主意显得太妙了:他不仅会被打发走,还会为给她带来的恐惧和担忧受到惩罚。她想:“他会被送进黑人孤儿院。当然,人们非这样做不可。”
她甚至没有即刻去见女总管。她开始是要朝那儿去的,但并没有往办公室的门口去,而是看着自己走过办公室门口继续向前,走向楼梯口然后登楼。她仿佛在跟随自己,看自己要往哪儿去。一踏进走廊,这时走廊里清静无人,她如释重负地又打起呵欠来,尽情地舒气。她走进自己的房间,闩上门,解下衣服上床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