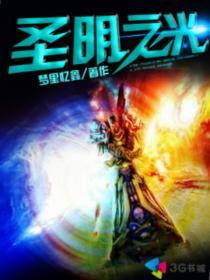八月之光-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住在那儿。”
“以前住在哪儿?他俩在那幢房子里住?”
“不,是在后面的一处黑人住的那种小木屋。三年前克里斯默斯把它收拾了出来。那以后他一直住在那儿,而乡亲们还猜不到他究竟在哪儿过夜呢。后来,他和布朗伙在一起,他便把布朗带去一块儿住了。”
“哦,”海托华说,“可是我不明白……要是他们在那儿住得挺自在,要是伯顿小姐不——”
“我看他们合得来。他们在贩卖威士忌,用那个老地方当窝子,作掩护。我想她不知道,不知道卖威士忌这事。起码,乡亲们闹不明白她是不是知道。他们说那是克里斯默斯三年前自己干起来的,只卖给几个互不相识的老主顾。可是他把布朗拉入伙以后,我猜是布朗想扩大生意的,他腰间带上酒,半品脱半品脱地出售,无论在哪条小巷逢人就卖。就是说贩卖他自己从不喝的东西。他们卖的威士忌来路不明,我看经不起查问,因为大约在布朗辞掉刨木厂的工作,成天驾着新汽车到处乱窜的两星期之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喝醉了,在闹市区的理发店里,向一堆人炫耀他和克里斯默斯某天晚上在孟菲斯或者那附近的路上所干的事,说到他们把新汽车隐藏在灌木丛里,克里斯默斯拿着手枪,还大吹特吹什么一辆卡车,一百多加仑的什么东西。他一直吹牛吹到克里斯默斯赶来,走到他面前把他从椅子里拽了出来。克里斯默斯开口了,用他那特有的平静的既说不上快活也说不上发火的声音说道:‘你小心点儿,别喝多了杰弗生镇产的这种烈酒。喝了要上头的。首先你会莫明其妙地豁了嘴漏风。’他一手搀住他,一手打他的耳光。看上去不像在狠狠揍他;可是当克里斯默斯抽打时拿开手的间歇,大伙儿看见布朗髭须下的面颊都给揍红了。‘你出来吸点儿新鲜空气,’克里斯默斯说,‘你在这儿让乡亲们没法做事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又说:“她就坐在那儿,坐在木板堆上,两眼望着我,我一个劲儿地把这一切告诉她,她眼睁睁地注视我。然后她问:‘他嘴角上是不是有一小块白伤疤?”’
“那么布朗就是她要找的人,”海托华说,他坐着一动不动,以一种静静的惊讶的神情看着拜伦,既不感情冲动,也不义愤填膺,好像在倾听另一个民族的人所做的事。“她的丈夫原来是个私酒贩子。唉,唉,唉。”然后,拜伦瞧见对方脸上有种隐伏的东西即将苏醒流露,而这连海托华自己都未意识到,仿佛他内心深处有样东西正竭力警告他或者让他有所准备。然而拜伦觉得那只不过是他自己已经有过的体验,而且他正要讲述出来。
“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把一切都告诉她了。即使在那个时候,在我认为那便是全部真相的时候,我也该稳住不说,哪怕把舌头咬成两段。”现在他不再瞧着对方。透过窗户,从远处教堂传来混合着风琴和歌唱的声音,声音越过静寂的夜晚,低微却很清晰。拜伦心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能听见。也许他老听,听得多了,时间久了,不再听见了,甚至不需要听了“我在干活的整个傍晚,她一直坐在那儿,对面的火焰终于渐渐消失了,我心里一直想着该对她说些什么呢,该叫她咋办呢。她当时就要去那儿,要我给她指路。我说那有两英里远呢,她听了只笑了笑,好像我是个孩子什么的。她说:‘从亚拉巴马州来的这一路都走过了,我还怕再走两英里不成。’然后我对她说……”他的话音停住了,两眼瞅着放脚的地板出神。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我撒了个谎,是的。不过,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不算是撒谎:因为我明白那儿会有许多人看热闹,她却要上那儿去找他。我自己没有把握,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去后会怎样,会有多么糟糕。于是我告诉她,他正忙着干他的活儿,最好六点钟后到城里去找他。这话倒也不假。我相信他的确把那种事,把怀里揣满冷冰冰的小瓶子叫作活儿的;要是广场上没有他,那他准是暂时钻进了某条小巷,或者稍稍迟了一步还没从小巷回来。所以我劝她别急,等等再说。她等在那儿,我一面干活一面琢磨该咋办。现在想来当时情况不明我是多么着急,而今我知道了全部情况,相比之下当时的着急算不了什么。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我要是能退回到昨天去,只有当时那点儿担心着急,那一切会容易得多。”
“我还是不明白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海托华说,“那个男人干那种事,她落到这个地步,都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了力,一个陌生人所能做的你都做到了,除非……”他也说到一半住口了。话音一断,正说的事便渐渐消散,不经意的思索变为推测,接着竟成了关切之类的东西。拜伦坐在对面没有任何动静,他垂着头,表情十分严肃;而坐在拜伦对面的海托华,还没有想到爱情上面去。他只记得拜伦还年轻,过着独身和勤劳的生活;从拜伦的谈话里,那个与他素不相识的女人或许具有某种令人动心之处,即便拜伦仍然相信那不过是怜悯而已。于是,他更密切地注视着拜伦,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满怀热情。与此同时,拜伦继续以平板的语调讲述:到了六点钟,他还不知道该咋办,甚至在他和莉娜走到了广场的时候,他仍然犹豫不决。当拜伦不动声色地谈到,他们到了广场以后他决定将莉娜领到比尔德太太家时,海托华迷惑不解的神情才开始有所触动,有了某种预感,想要退缩逃避。拜伦静静地谈着,边想边回味:当时像是有什么东西渗入了空气,进入了夜晚,使人们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他还没有听人说起,也不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弄明白是什么使他天真无知造成的困境显得十分幼稚;实际上他不用弄清事情的真相就知道不能让莉娜听到这一切。他不用别人明白地告诉他,便已确定无疑地发现了那溜掉的卢卡斯·伯奇。现在看来,他要再不明白就真是个愚昧无知的傻瓜蛋了。整整一天,命运,机遇,在空中竖起一道黄色烟柱,一个警告信号,而他太蠢,竟然没有能够领悟到。所以他得回避人们——旁边走过的人,回避周围尽在谈论这桩事的气氛,以免她得知真相。也许当时他明白,迟早她得知道,会听人说起,而且可以说她也有权利知道,但他似乎觉得只要领她走过广场,进入某个人家,他便尽到了责任。不是对那桩邪恶的责任,他的责任在于当她身无半文、长途跋涉三十天之后到达这儿,造化选择了他作为杰弗生镇的代表,在邪恶发生之际同她呆了一个下午。他没有回避这一责任的想法或愿望,只是为了让自己,也让她,有时间可以感受到惊讶和震动罢了。他静静地结结巴巴地谈着,低着头,始终是那平板的没有变化的声调,而坐在对面的海托华望着他,显出一副畏缩、不肯接受的神情。
他和莉娜终于走到他寄宿的住宅,走进了门。她好像也有某种预感似的,他俩站在门厅里,她望着他,首次开口问道:“街上的那些人想对你说什么?那幢被烧毁的房子是咋回事?”
“没啥,”他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话音听起来干巴巴的、轻飘飘的,“只是说伯顿小姐在这场火里烧伤了。”
“咋个烧伤的?伤得怎样?”
“我想不太糟糕。也许一点儿都没烧伤,乡亲们只是谈谈,像通常那样,他们总这样的。”他不敢看她,更不敢与她的目光相遇。可是他感到她在注视他,他仿佛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谈话声,镇里各处紧张的小声交谈,他匆匆领她走过的广场那儿的声音,人们在那儿相遇,在熟悉和安全的灯光下谈论。寄宿舍里也仿佛充满熟悉的声音,但更主要的是沉闷,难忍的拖延,他注视着昏暗的门厅,心想她为什么不出来,为什么不露面正在这时,比尔德太太出现了:一位神态怡然的女人,手臂红红的,一头散乱的花白头发。“这是伯奇太太,”他介绍说,瞪大了眼睛,显得迫不及待,强人所难似的,“她从亚拉巴马州来,刚到城里。她要在这儿见她丈夫。他还没来呢。所以我带她先到这儿,好让她在陷入城里这阵子的热闹事之前休息一下。她还没去镇上,还没同谁交谈过,我想你可以先给她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她免不了会听别人议论的,还有……”他的声音停住了,不再往下说,但语气概括了一切,急切的强求般的口气。这时他相信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后来他才知道,她没有把听到的事告诉她,并不是由于他的请求,而是她早已注意到她怀有身孕,认为最好避而不谈。她上上下下地打量莉娜,像四个星期来别的陌生女人常常做的那样。
“她打算在这儿住多久?”比尔德太太问。
“就一两夜,”拜伦说,“说不定只住今天晚上。她是来这儿见她丈夫的。她刚到,还来不及去问呀打听的——”他仍然简短扼要,话中有话。现在,比尔德太太打量起他来,他猜她还在努力领会他的意思。可是她却在注意他的吞吞吐吐的口吻,相信(或者即将相信)他这样支支吾吾另有原因,别有含义。于是,她再次打量莉娜,那眼神倒不一定冷漠,可也并不热情。
“我想她现在没必要马上去什么地方吧,”她说。
“我也这样想,”拜伦又快又急切地说,“她好久都没见过嘈杂和热闹,现在也许不得不忍受这一切……要是你这儿今晚很挤,我想她可以用我的房间。”
“那好,”比尔德太太马上答道,“反正过会儿你就要离开。你想让她住你的房间,住到你星期一早上回来?”
“今晚我不走了,”拜伦说,他并不转开目光,“这个星期去不了啦。”他直视着那双冷淡而且已经变得不信任的目光,看着她反过来又在观察他的神情,相信她领会了他的用意,而不是凭她自己的想象。人们常说:老练的骗子骗得了人。然而素有训练、一贯撒谎的骗子手常常只能骗自己,惟有一辈子都诚实可信的人撒了谎才会有人马上相信。
“嗯,”比尔德太太说,她又瞅了莉娜一眼,“杰弗生镇里她就没个熟人吗?”
“她在这儿一个人也不认识,”拜伦说,“离开了亚拉巴马州她没熟人。说不定伯奇先生明天早上就会露面。”
“那么,”比尔德太太说,“你到哪儿睡觉呢?”但她不等回答又说,“我想今晚我可以在我的房里给她搭个帆布床,要是她不反对的话。”
“好哇,”拜伦说,“那太好了。”
晚饭铃响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他找了个同比尔德太太谈话的机会。他从没有花过那么多时间去编造谎言。可后来证明这完全多余,他竭力掩盖的东西本身就是天然的保护。“男人们会在饭桌上谈论那件事的,”比尔德太太说,“我想,像她那样大着肚子的女人(而且还得找一个名叫伯奇的丈夫她带着冷嘲地想)犯不着再去听男人嚼舌头说怪话。你过阵子带她进来,等那些男人吃了以后。”拜伦这样做了。莉娜又一次吃得津津有味,但照样仪态庄重,彬彬有礼,几乎还没吃完饭便发困了。
“太累了,旅行真累人,”她解释说。
“你去客厅坐坐,我去替你搭帆布床,”比尔德太太说。
“我来帮一把,”莉娜说。但连拜伦也看得出来,她帮不了忙,已经瞌睡得要命。
“你去客厅坐着,”比尔德太太说,“我想邦奇先生会乐意陪你几分钟。”
“我不敢扔下她不管,”拜伦说。海托华坐在桌子对面,仍然没动弹。“于是我们坐在那儿等候。可就在这时候,城里警长的办公室里一切都抖出来了;这个时候布朗正在讲出那一切——关于他和克里斯默斯,还有威士忌以及所有的事情。不过威士忌对乡亲们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闻,布朗入伙以前人们就知道了。我猜大伙儿想知道的是,克里斯默斯干吗看中了布朗。也许因为他们是一路货色,臭味相投,想避也避不开。然而就算是一路货色,彼此还有不同之处。克里斯默斯敢于不顾法律去赚钱,可布朗不顾法律却是因为他糊里糊涂,蒙在鼓里盲目行动。就像那天晚上,他在理发店喝醉酒大吹牛皮,直到克里斯默斯几乎是跑进去把他拽走。马克西先生说:‘你认为他正要把他和另一个人干的什么事讲出来?’麦克伦登上尉说:‘我完全没想这个。’马克西先生说:‘你不认为他们实际上在抢劫别人运酒的车吗?’麦克伦登说:‘难道你会感到奇怪,当你听说克里斯默斯那家伙一辈子都在干同样的坏事?’
“那就是昨晚布朗招认的,可这些谁都知道。大家已经谈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该有人去告诉伯顿小姐。可是我想谁也不愿意去那儿告诉她,因为没人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看这儿出生的人中间还有不曾见过她的呢。我自己也不愿去那儿,到那幢老房子去;谁也没在那儿见过她,除了坐马车经过时偶尔见她站在院子里:长衣裙,遮阳帽,那式样就连有些黑人妇女也不愿穿戴,在她身上该像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不定她已经知道了这事。因为她是个北方佬,北方那一套也许她不介意。于是,去对她说,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她上床睡觉之前我不敢扔下她不管。昨晚我打算马上来见你的,但我不敢离开她。那儿住宿的男人在门厅里走来走去,我担心会有人偶然闯进去,一旦谈起来就会把所有事都给倒出来。我已经听见他们在走廊里谈论这事,当时她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又问起那场火的事。所以我不敢撇下她走开。我们坐在客厅里,她几乎睁不开眼睛,我告诉她没问题,会帮她找到他的,只是我得出来找一位认识的牧师,好帮助她去见他。她坐在那儿,闭上眼听我讲话,以为我不知道她和那家伙还没有结婚。她自以为把大家给蒙过去了。她问:我打算找谁去谈起她?我对她讲了,可她闭着眼坐在那儿。所以最后我说‘我讲的话你一个字也没听’,她这才稍微坐起身来,但眼睛还是没睁开,她问:‘他还可以帮人主持婚礼吗?’我说:‘什么?他还可以什么?’她说:‘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牧师,可以主持婚礼吗?’”
海托华仍然坐着不动。他端直地坐在桌对面,两条胳膊平行地放在椅子扶手上。他既未穿衬衣也没披外套,面孔瘦削而又松弛,看来仿佛是两张面孔,一张叠在另一张上;呆滞的目光从眼镜片后面向外望,苍白光秃的头颅四周,围了一圈灰白头发。由于老坐着不走动,身体发胖,肌肉松垮垮的;他露在桌面以上的躯体不成个体型,近乎畸形。他坐得笔直,脸上那副带有保留和捉摸不定的神情现在却变得明朗了。他说:“拜伦,拜伦,你究竟要对我说什么?”
拜伦住口了。他平静地看着对方,流露出同情和怜悯的神色。“我知道你还没听人说过,我早就知道该由我来告诉你。”
他们彼此望着。“什么事我还没听说过?”
“关于克里斯默斯的事。昨天发生的事和克里斯默斯的事。克里斯默斯是个混血儿。关于他、布朗和昨天发生的事。”
“混血儿,”海托华说。他的声音低微轻飘,像蓟毛扫帚倒了下去,没有任何重量,不出一丝声响。他坐着不动,隔了一阵还是一动不动。然后,退缩和拒绝的反应突然掠过他整个身躯,像是体内的各部分同他的面部五官一样可以活动;拜伦看见,那张呆滞松弛的宽大面孔上突然渗出了汗水。但他的声音低微平静,他问:“关于克里斯默斯、布朗和昨天的什么事?”
从远处教堂传来的音乐早已停止,屋里没有任何声息,除了拜伦单调的谈话和昆虫的从容不迫的唧唧尖鸣。海托华端坐在桌对面,两手掌心向下地平行摆放着,下半身被桌子遮住,那姿态活像一尊东方的偶像。“那是昨天上午,有一个乡下人和他的家人一道赶着马车进城,发现房屋着火的就是他。不,他是第二个去那儿的人,因为他说他破门进入后发现已经有一个人在那儿。他叙述了走近那幢住宅的情景;他对妻子说,那儿的厨房怎么直冒浓烟;马车往前走,他妻子说:‘那房子着火了。’我猜,他停住马车,先在车上坐着观望了一会儿,然后他说:‘看起来是那么回事。’我想是他妻子坚持叫他下车去看看的,她说:‘他们不知道房子着火了,你去告诉他们。’于是他下了马车,走上门廊,站在那儿‘喂喂’地叫唤了一阵。他说他能听见火在燃烧,就在屋内,于是用肩头撞开门进去,看见了第一个发现起火的人,那人就是布朗,但乡下人当时不知道。他只是说那人喝醉了,看来像是刚从楼梯上摔下来。当时他还没意识到那人醉到什么程度,他说:‘先生,你的房子着火了。’他告诉人们,那醉汉不停地说楼上没有人,而且说反正上面火势很大,用不着上去救什么东西了。
“可是乡下人明白,楼上不可能有什么大不了的火,因为烟火是从后面的厨房里冒出来的,何况那人醉成那样,怎么会知道呢。他告诉大家,从醉汉竭力阻止他上楼的情形看来,他怀疑楼上出了什么问题。于是他开始上楼,醉汉却竭力拖住他,他甩掉醉汉往楼上走时,醉汉还想跟上去,还一个劲儿地说楼上没什么;可等他从楼上下来,想起刚才的醉汉时,却不见人影了。可是我想,他准是隔了一会儿才想起布朗的,因为他上了楼梯,开始叫唤,一连打开几道门,才开了该开的一道,发现了她。”
他停了停。室内一片静寂,只有昆虫的鸣叫。窗户敞开着,户外昆虫扑打跳动,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种种声音。“发现了她,”海托华说,“他发现了伯顿小姐。”他坐着纹丝不动。拜伦没注视他,也许他一面讲述一面在看自己放在膝头的双手。
“她躺在地板上,脑袋差点儿被完全割断了。一位女士,头发刚刚花白。乡下人说,他站在那儿,能够听见哔哔剥剥的火势,他所在的房间也进烟了,像是跟着他灌进了室内。他不敢抱起她跑出屋外,因为他害怕那脑袋会掉下来。他说,于是他匆匆忙忙跑下楼,跑出楼外,甚至没留意到那醉汉已经不见了;他赶到路边,叫妻子赶紧催马去附近能打电话的地方,向警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