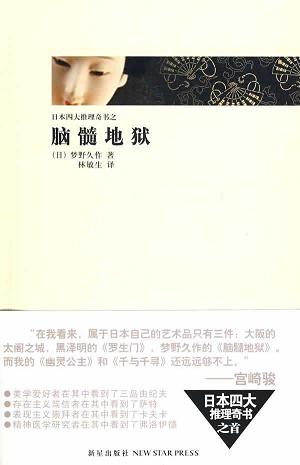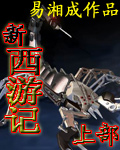大越狱-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浅坑,韦九终于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一屁股瘫坐在煤堆上,捏成拳头使劲地敲打自己的脑袋。
直到枪声响起,韦九这才惊醒过来,连忙跳下煤堆跑出夹弄,然后顺着车间的后墙朝东一路狂奔,一直跑到机械车间的后门口。
在水流的冷却下,铁门上蒸汽弥漫,黑洞洞的椭圆形洞口像一张巨嘴那样,边缘部分凝结着许多水珠状的金属悬挂物。
“别出来,钥匙没了!”韦九弯腰朝洞内大吼道。
“你说什么?”洞内的老鲁似乎没听明白。
“昨晚运来几十吨煤,钥匙被压在下面了。”韦九再次大叫。
这次里面的老鲁听明白了,洞内再无任何声息,恐怕都让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击晕了。韦九转过身来,顺原路飞快地返回夹弄,心里边空空荡荡,大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警报声一声响过一声,大批戒护队士兵在青木藤兵卫的率领下涌入工场,从铆焊车间的楼梯登上气楼,迅速扑向通往机械车间的那扇铁栅。月京未来站在机械车间前门边被捅破的玻璃窗前,铁青着脸色,将目力所及之处能看到的每个人的神色、姿态和所在位置全部观察一遍,以便尽早发现疑点。
“快开门!”月京未来狂吼起来。
李滋第一个从蹲着的角落里站起来,快步奔向前门,捡起地上的那根圆轴,猫下腰来将滑槽内的铁楔往反方向又敲又撬,不多时便将铁门重新打开。
被老鲁破坏掉的锁芯费了青木藤兵卫很多时间,枪托砸不到,用撬棍又不得力,最后不得不动用氧乙炔切割设备,从铆焊车间搬来氧气瓶和乙炔瓶,用气割枪将门搭扣切断。
老鲁和蒋亭虎首先被铐了起来,其他人则被枪兵赶拢到一堆,一律蹲下等候发落。
月京未来凑在门上的大洞前仔细端详,又钻出洞去察看外面的情况,甚至还跑到围墙边去查看北大门是否无恙。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勘查,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发现,唯一的疑点只有门边那根差不多已被烧焦的电线——漆桶和毛刷早就化为乌有——但是,仅仅只靠一根电线,哪来那么大的能量呢?
“不用查了,是我们俩干的!”蒋亭虎平静地对月京未来说道。“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可惜啊,还是没跑成。”老鲁大声叹息道。
“门上的洞是怎么烧出来的?”月京未来喝问道。“这件事为什么要到机械车间里来做?”
“用机油呗,一通电就烧起来了,”蒋亭虎随口胡说,“铸造车间里没机油,只能上这儿来啦。”
“你们准备用什么办法打开北大门?”月京未来一时吃不透机油通电后到底会不会燃烧。“还有,谁是你们的同谋?”
“当然是用撬棍啦。”老鲁翻了个白眼。“这么简单的事还用得着同谋?”
“混蛋!”月京未来即使用屁股想想也觉得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机械车间里谁帮过你们的忙?”
“这事谁敢帮忙?”蒋亭虎语气里带着讥讽。“别添乱就不错了。”
“谁要敢添乱,老子早就一棍敲上去了。”老鲁一下子把机械车间里的人全部撇清。
“你,你说,”月经未来突然指着地上的李滋叫道,“有没有别人帮忙?”
“没……没……没别人帮忙。”李滋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你,你说。”月经未来又一指郭松。
“他们一进车间就关门,手上又拿着铁棍,我们只能躲得远远的……”郭松连忙回答。
“你,你说。”月经未来挥手打断郭松,手指突然指向孟松胤。
“我们都躲在机床后面看,后来枪一响就赶紧趴下,什么都没搞明白。”孟松胤答道。
刚说到这里,野川所的最高长官野川少佐匆匆赶到,沉着脸先去察看门边的情况,但转来转去猜不出个究竟,只得下令先将老鲁和蒋亭虎押到审讯室去再说。
机械车间停工半天,所有的人被分成几组接受盘问,好在大家都把老鲁和蒋亭虎说过的话作为蓝本,颠来倒去只是重复,谁都没有露出破绽来,甚至包括李滋在内,也没敢吐露实情——现在日本人并无证据在手,一时不会危及自身,而一旦触犯难友,则致命的危险肯定就在眼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下午,北大门洞开,驶来了一辆装载砖头和水泥、黄沙的卡车,随后又来了几名外牢,在后门外砌起了一座厚厚的砖墙,椭圆形的大洞被严严实实地堵了起来。此外,厕所里的电灯和电线也被干脆剪除,另在北墙上高高地开了一只窗洞用来采光,尺寸小得恐怕连一只狗都钻不出去。
事后了解到,实际上所有车间的后门外都加了一堵墙,厕所里也一律剪除电线增开小窗,连热处理车间西侧那条通往后大门的夹弄,也被高高的砖墙封堵了起来,以后,包括运煤车在内的一切运输车辆,全部由野川所的正门进入工场——这就是说,韦九再也无法接近后门,手上的钥匙也成了废物。
日本人虽然暂时弄不明白门上的洞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但亡羊补牢和防患于未然的道理不会不懂。至于机油通电后是否真会燃烧的问题,最终并未深入研究下去,因为即使能够燃烧,又怎么可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呢?月京未来建议向上级报告,请专家来勘验现场,追查真相,但野川少佐并未采纳这一意见,原因非常简单:并不想让上司得知此事——号称固若金汤的野川所,居然在重兵把守之下依然捅出这么一个大窟窿来,除了说明主管人员的无能,对任何人的前途都没有好处。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撬开老鲁和蒋亭虎的口。
月京未来亲自负责审讯,在刑讯室内整整呆了一天,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作为一名具有一定经验的监狱管理人员,他深知对待面前这样的硬汉,家常便饭一样的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烫之类不会起任何作用,所以一开始就使用了类似于凌迟的毒刑。
凌迟是将肉割下来,而月京未来只是割皮,让医务室的一名台湾医官用细巧锋利的手术刀将人体的表皮割开,然后顺着一定的角度在表层切入,这样的结果是皮肉仍然相连,失血也不会很多,而痛楚却无与伦比。这一过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割割停停,停停割割,一旦晕过去便马上用盐水浇泼,直至受刑者的后背和大腿上如鱼鳞般挂满一块块破碎的表皮。
没有人知道老鲁和蒋亭虎是怎么熬过来的,尤其是蒋亭虎,由于腿上的枪伤失血较多,昏厥的次数特别多,到最后别说盐水泼不醒,连烙铁烫上去都没了反应。
傍晚时分,月京未来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下令将二人吊到广场上的旗杆上去。
放工之际,当人群排着队走回“羽”字号牢房的时候,全都看到了这样一幕令人心颤的场面:原本挂有日、汪旗帜的两根旗杆上,倒吊着两具全身赤裸、面目全非的人体,双臂柔软无力地下垂着,一些尚未干结的血水顺着十个手指慢慢滴落。
当天夜间,蒋亭虎停止了呼吸。
天亮以后,老鲁被放了下来,台湾医官过来看了看瞳孔,又摸了摸心跳,当场大表惊叹,说从来没见过生命力这么顽强的人,接着便给老鲁打了一针,并用绷带草草包裹躯体和大腿,让外牢用担架送往病栋。
“真是条好汉。”医官看着一声不吭的老鲁忍不住再次感叹。“真是条好汉哪。”
“是啊,不怕死没啥稀奇,硬硬头皮就行,谁都做得到,”抬担架的外牢也对老鲁佩服得五体投地,“要熬过这些折磨,真叫是生不如死,绝对不是人人做得到的。”
蒋亭虎的尸体,被直接送进了地下室中的硝镪池。
三十一、水之殇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邓一棍先生头上抹了许多香喷喷的刨花水,换上一身轻薄鲜丽的软缎春装,一路摇摇摆摆走进了镇夏镇。
邓一棍有个相好在镇上开糖果店,是个颇有三、四分姿色的半老徐娘,蔡大少爷今日兴冲冲前来,满心希望能成就一星半点如糖果般甜蜜的事体,没想到她家那做木匠的男人正好因为生意清淡而歇息在家。蔡大少爷与妇人隔着柜台四目相望,料想今日不可能有所斩获,真是巫山相隔远、大漠孤烟直,只得灰溜溜地无功而返。回家的路上,大少爷兀自气闷,寻思是不是找个地方喝上几口,途中正好碰见一名昔日的老友秦春狗,干脆一把拖住就近走进一家酒馆。
秦春狗在和平军中当差,还是个腰胯驳壳枪的中队长,这几年里和蔡三乐做了不少生意,以每发子弹一角钱的价钱暗中倒卖赢利,大挖大日本帝国的墙脚。
二人叫了酒菜慢慢吃喝,三杯下肚,不免聊起了男人间永远兴致勃勃的话题。邓一棍感叹道,最近明月湾来了一对小夫妻,那小娘们的长相别提多撩人了,老子一辈子花草堆里走过来走过去,还没见识过这等要人性命的美色。秦春狗说,别吹牛了,你小子天生一对桃花眼,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的。邓一棍说,骗你是丫头养的,他妈的城里女人硬是不一样,细皮嫩肉的赛过水豆腐。秦春狗问,你小子浑身都是本事,早弄上手了吧?邓一棍悻悻地说,屁,她家男人不是等闲之辈,手里还有一把德国撸子,不知道是什么来头。秦春狗一听来了精神,忙说手里有德国撸子的人确实不好惹,不过这样的人怎么会呆在明月湾呢?邓一棍说,我也正纳闷呢,估计里头大有隐情,而且那小娘们还想托我跟光福那边的共产党牵线搭桥,说是有一份……化……哦,化学的什么名堂要交给共产党。
秦春狗马上警觉起来,哦,要找共产党?
邓一棍说过便忘,秦春狗却将这事暗记在心,回去后立即上报大队长,稍作商量后觉得事情很不简单,极可能是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又一起赶往元山上报日本警护军方面。西山岛上虽然不通电话,但电报来去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仅仅半天功夫,来去了四、五个电报,苏州方面已经通过年龄长相和“德国撸子”、“鬼画符一样的化学名堂”等基本特征,将目标锁定在失踪已久的李匡仁和齐依萱身上。
苏州梅机关指示,万勿惊动,将派专人前来处理此事。
那边紧锣密鼓调兵遣将,这边却风平浪静、天下太平,李匡仁虽然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危险,但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在优哉游哉地品尝着现炒的碧螺春茶。事后回想起来,真是白受了那么多年的特务训练,连这点最基本的判断力和决策力都丧失了。怪只怪西山的风土人情太迷人,而且在这世外桃源与可人、可心的齐依萱日日相处,真有点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思。
不过,大黄狗一开始狂叫,李匡仁马上便惊醒过来。山坳里从来没有外人进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不为过,来到沈娘家后的这些日子里,还是头一次见到大黄狗这样狂暴的叫法。
齐依萱还在捧着茶碗品味甜滋滋的茶水,根本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靠近,李匡仁不打二话,一把拉住她的手,转身便往屋子里跑。身后,大黄狗已经蹿到了篱笆门外,连连狂吠着一声高过一声。齐依萱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一看李匡仁的神情,情知已至危急的地步,顿时吓得手足无措,唯有紧跟着直往灶屋后飞跑。
灶屋的北面有一扇后门,开出门去是一片长满野芦苇的小池塘,对岸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菜畦。池塘宽约六、七米,沈娘平时为了进出方便,在池塘中央泊着一条已经废弃的漏水破船,两头各搭一块三、四米长的跳板,可以直接去到对岸栽种、收割。李匡仁扶着齐依萱摇摇晃晃地走过跳板来到船上,顺便将跳板一脚踢下水去,走上对岸后,又将另一块跳板抽离,拉着齐依萱的手朝远处的一大片杨梅林狂奔而去。
大黄狗越叫越凶,似乎还在愤怒地扑咬,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狗叫声戛然而止。
“要是没有这条狗,我们今天都完蛋了。”李匡仁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
“来的……到底……是什么人?”齐依萱喘得话都连不成句。
“不知道,进门就开枪,应该不是好人。”李匡仁也拔枪在手。
“那支……钢笔……怎么办?”齐依萱脸都白了。
“那倒不要紧,我藏在茅房的砖缝里,谁也不会想到。”李匡仁答道。
“不行,我跑不动了。”齐依萱停下脚步,弯着腰拼命喘气。
“再坚持一下,先跑进杨梅林再说。”李匡仁挽着齐依萱的胳膊,一半是扶,一半是拖。
刚走出没几步,只听身后传来一声大叫:“站住!”
转身一看,好家伙,池塘对岸的灶屋门口站着一大群人,一个个持枪在手似凶神恶煞,甚至还有人已经做出举枪瞄准的动作。粗略看去,那十几个人中既有身穿黄绿色军服的日本兵,也有身穿灰黑色军服的和平军,还有几名身穿西服的年轻人。
“李匡仁,不要跑!”一名西服男子双手圈在嘴边大喊道。“跟我们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李匡仁定睛细看,只觉得那人有些面熟,姓什么叫什么记不大清,但肯定是苏州梅机关的人,以前曾一起在上海总部培训过。
“快走!”李匡仁拉起齐依萱急促地叫道。
齐依萱只得强行支撑起身体,跌跌撞撞地朝杨梅林继续奔跑。
“站住!再不站住开枪啦!”对岸的声音威胁道。
“弯腰!”李匡仁对齐依萱低声叫道,率先做出低首弯腰的样子。
后面果然开了枪,但似乎还是警告的意思,全部打在较远处的地上和树上,但还是把齐依萱吓得连声尖叫,腿软得几乎挪不开步。
李匡仁转身开了一枪摆明抵抗态度,继续拖拉着齐依萱往前跑,不多时,总算钻入了茂密的杨梅林。
“我实在……跑不动了。”齐依萱哭叫道,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跑不动也得跑啊!”李匡仁急得直跺脚。
“我们……能跑到哪里去呢?”齐依萱满脸都是绝望。
“往古码头跑。”李匡仁向四周稍作观望,马上作出了决定。“往山上跑绝对是死路一条,只有往湖里跑。”
齐依萱拼尽全身力气爬起身,再次艰难地迈动脚步,可恨这片四季常绿的杨梅林虽然能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但地势正好处于一片斜坡,越往上走越觉吃力。李匡仁回头观望,只见沈娘家后门口已经不见一人,可以想见,那帮家伙现在肯定正返回前院,准备绕过池塘一路追来。
“日本人实在太毒辣,千万不能落入他们手中,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姑娘,”李匡仁不停为她打气,“走,穿过这片杨梅林就是平地了,坚持一下。”
“那怎么办?”齐依萱一下子被吓懵了,干脆停住了脚步。
“还能怎么办?快跑啊,我的小姑奶奶。”李匡仁有点后悔刚才的话,连忙故作轻松地咧嘴一笑。“古码头那边经常停着几只小船,只要下了水就好办,一头钻进芦苇荡,管保谁也找不着,等天黑以后再出来想办法。”
这个计划听上去相当不错,齐依萱顿时有了些信心,抹抹眼泪,咬牙加快了脚步。所幸穿过杨梅林便是下坡路,绕过几座孤零零的野坟,终于走上了通往古码头的一条便道。
古码头宽约四、五米,长达五十余米,全部由花岗岩石条铺就,如一把宝剑直指湖心,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地方已经坍塌,现在已经基本废弃不用,平时只有几艘螺蛳船、放鸭船、鸬鹚船之类的轻舟停靠。李匡仁一马当先跑上空荡荡的码头,将系在码头边的几艘小船一一解开缆绳,由其慢慢飘离码头。
“他们追来了!”身后的齐依萱突然惊叫起来。
李匡仁回头一看,只见追兵果然已经出现在视野之中,连忙就近跳下一艘螺蛳船,飞快地解开缆绳。
“快跳下来。”李匡仁大叫道,搀扶着齐依萱跳下中舱,螺蛳船首尾都呈方形,因吃水较浅而十分灵活,大都为夫妻俩人漂在水上捞取螺蛳、蚬子所用,唯一特别之处在于中舱部位置有一只木盘,一般是男人站在船头上用两根竹竿上的耙和斗捞取水底的螺蛳,起水后倒入木盘,由坐在中舱的女人耐心挑拣,剔去泥污杂物后去镇上叫卖。
李匡仁摇动轻橹,小船打了个转,终于歪歪扭扭地朝湖心驶去。
时近黄昏,夕阳在水面上洒满了金鳞。远处的水平线上,一艘双桅渔船孤独地游弋着,搅动起满湖璀璨,使波光与绚丽的晚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水天一色的静谧画面。
“停船!”追兵边跑边喊。
李匡仁奋力摇橹,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啪”一声枪响,不远处的水面上溅起一片水花。
“快把木盘竖起来!”李匡仁对齐依萱大叫道。
齐依萱忙将中舱的木盘翻倒,自己弯腰躲在后面,虽然这一层木板根本无法阻挡子弹,但感觉上还是安全了不少。
追兵很快便涌上了码头,找到两条刚才李匡仁来不及解开缆绳的鸬鹚船,跳下四名黑狗子,先后掉转船头直追而来。
鸬鹚船上使的是双桨,俗话说“一橹能敌三桨”,所以速度上还是李匡仁的螺蛳船稍胜一筹。不过,黑狗子都是本地人,从小就惯会驶船,眼看着距离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李匡仁摸出枪来,稍一瞄准后连开两枪。
两枪都未命中,但把黑狗子吓得不轻,停下桨来趴在舱中不敢露头。
“开枪,把船打沉!”码头上穿西服的年轻人大声命令道。
黑狗子躲躲闪闪地趴在船头上,架着三八大盖开始射击。李匡仁连忙停下橹来,同样趴倒在船尾,拔出枪来连连回击。
连打了三枪,终于射中一名坐在船尾摇桨的家伙,那厮晃了几晃差点栽下水去。
这下火力更猛了,子弹嗖嗖乱飞,李匡仁只觉得肩膀一震,整条胳膊突然软了下来,低头一看,右肩已经渗出了一片鲜血。咬咬牙试着强抬手臂,在左手的帮助下勉强还能上举,似乎并未伤及骨骼。看来这小口径的三八大盖果然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精度高、速度低,弹头进入人体后不会翻滚,破坏范围较小。
“你受伤了吗?”身后的齐依萱惊恐地问道。
“这帮狗汉奸!”李匡仁愤怒地骂道。
“打在什么地方?”齐依萱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快趴下!”李匡仁扭头大喊,支撑着又开了一枪。
很不幸,德国鲁格手枪的装弹量为八发,来西山时弹盒里还剩六发,现在前后加起来已经开满五枪,只要再开一枪,这支精美的名枪将立即成为废铁。李匡仁扔下手枪,挣扎着扶起橹来继续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