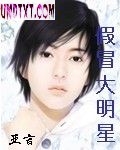大明官商-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杨一清冷笑道:“如何不敢?冯大人已收了信,张公公你想来也是非去不可的了。到那时,只怕一拿一个准。再有,那刘瑾如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有此非常之举,公公你说,他想做什么?”
“谋逆?!”
再看杨一清,面上一副“这可不是我说的”神情,却让张永哭笑不得。“你说,他刘瑾一个……那个,如今已是立皇帝,如何能做得皇帝,何苦要做此事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安化王谋反,打地名号可是清君侧。这个名号可不比寻常,当年成祖爷便是如此登基的。不管怎么说,皇上都得下旨彻查,给天下官民,给祖宗社稷一个交代。若是坐实了,逼反藩王这个罪名可是不轻。要不之前那刘瑾怎么尽遣锦衣卫四下查抄安化王檄文呢。可是此番公公领兵,这檄文么,难免不会落到公公手中。若是到了京师,献俘时公公将这檄文顺带往上这么一递,他刘瑾的大麻烦可就来了。既然如此,狗急跳墙也是在所难免了。故此,此番刘瑾若果真有何举动,第一个要杀的,便是公公你了!”
第二百五十二章 先下手为强
八月初九,张永所辖大军提前回京,第二天便押了安化王朱午门献俘,这一招大出刘瑾意料。// //这一天正是大朝之日,正德见着张永,龙颜大悦,好一顿夸奖。紧接着,正德便换了冯虞所献的那一身华胄,领了满朝文武,迫不及待地登上午门谯楼校,至于什么比谕旨所定之日早了八天,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一阵号炮之后,团营平叛大军一身崭新军装,气势磅礴地列队受阅。看团营将士,一个个精神抖擞,昂首挺胸。也难怪,此番出征一战没打,不过是武装巡游了一番,便能回京邀功受赏,士气能不高么。
正德看官军如此威武,自然欣喜,扭头朝着张永点了点头。张永叉手领命,上前一步,挥动令旗,转眼间便有数十辆囚车迤逦而来,打头那辆车上,一人身着污损不堪的明黄官袍,正是那志大才疏的安化王朱。囚车拉到午门城楼下,上百精壮兵丁一拥而上,两人夹一个,将身带重铐的一干叛军首脑干将押下囚车,强摁着跪在午门前。
此时,张永转身向正德施礼,“陛下,臣张永奉旨领军平叛,幸不辱命。现将叛贼头目押回京师交陛下发落,臣张永缴旨。”说罢,张永微微抬起头,得意地撇了一眼正德身边的刘瑾。
正德起身搀起张永,狠狠夸奖了一番,传旨厚赏张永及有功将士。
这一番节目演完,戏肉开演了。只见刑部尚书刘一脸肃穆登上城楼,三拜九叩之后,朗声奏道:“戾王朱,为人暴虐,阴怀异志,勾结匪类,横行不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兴兵作乱。残害忠良,涂炭地方,其心悖逆可诛,其罪十恶不赦。臣请旨,将此等逆贼正法,以肃朝纲,以告天下!”
正德点了点头,义正词严地说了一个字:“准。”颇有些惜墨如金的架势。
刘叩首领旨。长身而起。铆起全身气力大呼道:“圣上有旨,正国法!”
刘话音未落,正德身边军威凛凛的两名大汉将军应声复颂:“正国法”这呼喝之声转眼便一层层荡开来,音量越来越大,直至声震九门。在这震动九霄的声浪中。朱等一干囚徒给吓得瘫软在地。紧接着,便有锦衣校尉接管了囚犯,插上犯由牌(即民间所谓亡命牌),待刘下了城门亲笔勾名,便塞入囚车,押赴市曹正法。朱好歹是皇室,判绞刑,其他的可就倒霉了。一概凌迟。
了了这桩大事,正德心情大好,回头招呼刘瑾、张永二人:“今日大喜,朕高兴,走。陪朕吃酒去罢。”张永一边紧跟着正德脚步。不敢逾越一步,一边心里头小鼓擂个不停。当日大军回到京师。冯虞当晚便换装来访。到此刻为止,事态皆在当日冯虞所料之中。张永心中多少有些底气。不过,待会子酒席上才是大戏开锣,要说不紧张,那只能是瞪眼说瞎话了。幸好冯虞事先将今后谋划交了个底,如何行事,张永还是有数的。
想到这里,张永偷眼看向刘瑾,发觉这家伙也是满腹心事的模样。看来,此番加速回师以快制慢,确是打乱了刘瑾的布置。说实话,说刘瑾要冲自己下手,张永始终是半信半疑。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反正平素刘瑾拿自己不当回事,所谓先下手为强,这回也不能怪自己心狠了。
今日这顿酒,正德兴致极高。这一喝,从黄昏直喝到戌时。此时正德已有些微醺,他惊奇地发现,张永的兴致似乎比他还高,菜是一口接一口,酒是一杯接一杯,没完了。正德转念一想,军中禁酒,西北又没什么珍馐美味,也是难怪,今日干脆就让这位平乱功臣尽欢吧。可是身边地刘瑾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也不知是吃错了哪家的药方。
就在此时,一个小宦官,轻手轻脚进了屋子,伏在刘瑾耳旁嘀咕了几句,只见刘瑾脸色一变,匆匆起身对正德说道:“皇上,冯都护那边有要紧公务,老奴先行一步。”
往日但凡喝酒行乐,刘瑾总是想方设法闹出些乐子来,今日却无精打采,正德本有些不喜。看刘瑾告退,也不以为意。“自去料理便是。哦,完事了叫上冯虞过来,再叫上个乐户班子,咱们来个添酒回灯重开宴。”
刘瑾答应一声便急急离去。
看到这里,张永心中暗喜。冯虞说过,献俘后正德必会摆下庆功酒,到时候他张永能拖多久拖多久。待得刘瑾疲了,只说原先承诺之事有变,诓了刘瑾出去。接下来,就看张永如何行事了。
听得刘瑾走远,张永假借酒意,对正德说道:“皇上,臣此番平乱,在宁夏寻着一件有趣物事。”
“嗯?”正德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好玩的东西他是从来不愿错过的。“什么东西,可曾带来?”
张永笑道:“皇上稍安勿躁,臣正带在身边。”说罢,便从怀中掏出一张文告呈与正德。
正德接过来一看,却是那安化王起兵檄文!上头直书刘瑾十七条大罪,声言此番兴兵,全为阉宦所迫,只为清君侧、正朝纲。上上下下看了几回,正德面色是越来越难看。“张永,上头所写的,是真是假?”
“回皇上,所谓清君侧,自然是别有祸心,只是之前开列十七条,句句是实。尤其是迫反边军那一节。别个且不论,只说那宁夏巡抚安惟学,边军将士若是犯错,不但动辄严拷,甚至将妻儿一并拿来杖责折辱。三军将士岂能不恨之入骨,心存反意。”
正德听着,连连摇头,“贪些钱财也就罢了,怎能如此胡为!刘瑾负朕。”
张永看正德已信了八分,再接再厉。那晚冯虞又告诉他一桩秘辛,杀伤力还要强上百倍。“皇上,这十七条之外,还有更紧要的!”
“哦?你说。”
“皇上,前些时,焦芳致仕一事可还记得?”
“如何不记得,便在三个月前嘛。朕倒奇了。那焦芳尽人皆知是个官迷,素来是恋栈的。听说往年每遇升迁,便使尽手段,混泼耍赖。难道此番是转性了?”
“非是转性,是吓着了。据臣所知,那刘瑾已是位极人臣,本该尽忠竭力报效天恩,可惜他树敌过多,自然是惶惶终日,只怕不能善终。吏部尚书张彩是其心腹智囊,据臣探知,此人为刘瑾献计。妄言道,当今天子无子嗣,又好酒色,恐难长久。他教刘瑾早日留心,寻个年幼地宗室子弟,一旦有变则扶上皇位。如此则为长久之计。刘瑾便拿此事与那焦芳商议。焦芳那老狐狸听了这大逆不道之事,知道厉害,吓得不顾刘瑾再三挽留,次日便辞官致仕了。”
张永话音刚落,只听“啪”得一声,正德已将酒杯掼在地上,怒吼一声:“安敢如此!”
边上马永成、谷大用听了也是面如土色。要知道,擅议废立形同谋反,更何况刘瑾张彩二人话里话外还暗指正德命不长久。历代帝王自称万岁,哪个不愿自己寿比南山,这话简直就是往正德心窝里捅刀子!这下,刘瑾要倒霉了。
果不其然,正德怒发冲冠,在屋中走来走去,猛地立住脚步,转向马永成、谷大用二人。“你二人可知晓此事?”
马永成、谷大用略一迟疑,偷偷对视一眼,咬了咬牙,一齐跪倒。“回皇上,臣等知晓此事。”
正德更怒,“既然知道,如何不报?!”
马永成战战兢兢回话:“回皇上,兹事体大,我等又无佐证,不敢轻易上报,总要查实了才好。”
“屁话!”正德不依不饶,“你两个,一个督东厂一个督西厂,本就有风闻奏事之权责,又不曾让尔等当即拿人,如此大事,如何却要瞒报?”
谷大用心想,自从刘瑾建起内行厂,自家所督西厂就跟孙子一般,只有听使唤地份。有点什么事,还得拉下面子去求刘瑾,今日既然撕破脸,那就只能是鱼死网破了。想到这里,谷大用膝行两步,哭道:“皇上不知,刘瑾极有心计,整日里贴在皇上身旁,臣等如何能得上奏?此外,刘瑾对朝政把持极严,哪怕是东西厂密奏、前方军报也得先经他看过,允准的才能入皇上之眼。就如此番这檄文,刘瑾严令厂卫四下稽查,生怕落到皇上手中,有碍他前程。臣等几人是欲尽忠而不得啊!”
正德是越听越气。多年来,他视刘瑾为腹心依仗,军国大事尽行委付。之前正德也风闻刘瑾贪财,政略失当,不过始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着实是看中刘瑾能体察上意,加上自小又是刘瑾陪着玩大的,孰能无情?可是今日刘瑾所作所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德所能容忍的底线。
想了一阵,正德终于开口:“马永成、谷大用,连夜拿了刘瑾、张彩二人,再派人传焦芳即刻回京对质。”
哪知三人听了这话,异口同声叫道:“皇上,不可!”
第二百五十三章 雷霆之怒
正德听到三人如此回复,便是一愣。 //“如何不可?难道朕拿不得他?”
张永回道:“皇上,不是拿不得。而是东厂西厂拿不了。”
“这是怎么说的?”
“皇上您细想着,前几年,刘瑾之所以设内行厂,其中一条便是监管东西厂、锦衣卫。内行厂的人手,早先便是从这三处选调。这几年,内行厂又在东西厂、锦衣卫职属中大肆收买坐探,可说是耳目无数,若是动用这三处人马,难保不走漏风声,变生不测。”
正德问道:“那你说,如何行事才算妥当?”
张永笑道:“此刻,那刘瑾正在冯大人处。”
谷大用忙附和道:“张公公所言极是。如今内行厂、东西厂、锦衣卫靠不住,京营也在刘瑾手中,团营人马鱼龙混杂,惟有冯大人侍卫亲军靠得住,且又战力绝伦。皇上一道旨意,宣冯大人所部连夜入京,大局即可抵定。”
正德沉吟片刻,笑道:“你们这是不想脏了手,让人说你们自残同类。调冯国城不是不行,可是夜半如何入城?大军调动,惊天动地,若是刘瑾被惊动,出了岔子如何是好?”
张永不假思索答道:“这却不难。刘瑾此刻正在冯虞府上,皇上遣人飞马传旨,但凭冯大人府上亲兵便能成事。至于夜半入城,凭圣旨自然出入无碍。若是遣一重臣,率人盯在当场。想那五城兵马司也不敢造次。”
正德一想,是个办法,当即起身,自行取了笔墨,草草写就几封圣旨,取了随身所携印章盖印。“马永成。你即刻携了旨意往国城府上,拿住刘瑾及其亲随。哦,同时遣人召集手下亲信人马来宫中听用。张永,你辛苦一趟,往豹营调兵。同时,你调团营大军至京师城外听用。谷大用。你领了旨意带亲随至城门处给朕盯牢了,不必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只要开着城门就好。还有,今夜当值门军全给朕盯牢了,莫走了一人前去报讯。还有,你再派些得力可靠人手,分头将内行厂、锦衣卫、京营盯牢了,若有异动随时来报。”
三人见正德一改往日懒惫,精神抖擞。雷厉风行,且号令不乱,个个心头惊惕。忙不迭起身应命,领旨而去。
且说马永成,出了皇宫便命亲随回去召集心腹人马。自己揣着圣旨领了一干随从护卫直奔镇辽侯府而来。到了府门处一看,刘瑾车驾果然在此,随同跟班、侍卫都在边上候着了。守门兵丁看一大拨人上前拦住,行了个军礼问道:“请问这位公公,深夜到府上何事?”
马永成朝身后护卫丢了个眼色。让他们过去盯着刘瑾一干随从。自己冲那门军低声说道:“速去唤你们亲兵队长出来,圣上有密旨。”
那兵丁听了一激灵。不敢多问,扭头跑进府里。不多时。新任亲兵团长赖时亨脚步匆匆赶了出来,行礼问道:“不知公公如何称呼,有何吩咐?”
马永成正色道:“咱家便是东厂厂督马永成。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咱们进去说。”
此时,刘瑾与冯虞二人已在花厅内呆了有一阵子了。刘瑾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把玩着茶碗盖子,慢条斯理地说道:“京师产业,你自可留个信得过的慢慢料理。至于北上水师遇台风溃散之事,咱家却是帮不上了。再调船队赴京,一来一去又是一个月工夫。若是再出点什么差池,冯大人你莫非还打算在京师过年么?之前可是你说什么,咱家依什么,唯有这时限不能拖延。”
冯虞苦着脸说道:“公公说哪里话来。横竖是要南下,下官也不想这么没鼻子没脸地耗着。只是这老天爷难从人愿。皇上那边也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哪怕是真来不了船,那也得寻个说法交待不是。这个,别人没法子,于公公你来说,却是小事一桩。今日下官也是厚了脸皮求告,要么宽延些时日,要么,就得请公公美言几句了。”
刘瑾摇了摇头,笑道:“冯虞啊冯虞……”正待往下说,却听得有人叩门。“都护大人,宫里有旨意!”
听了这话,两人都是一愣。不过,冯虞地眼角却微微漾起一丝笑意。冯虞抬眼看了刘瑾一眼,待他微微点头,上前打开房门。外头站着的,正是马永成。两人对视一眼,会意一笑。
马永成手捧圣旨进屋,抬眼一看,刘瑾果然在此。“哟!刘兄,你也在此啊。”
刘瑾不明就里,随口答道:“哦,方才有些要事来寻冯大人商议。既然圣上有旨给冯大人,咱家先回避吧。”
马永成笑着摆摆手,“不必了。圣上这旨意也与刘兄你颇有关联,干脆一并接旨吧,省得小弟我传两回了。”
待二人跪好,马永成展开圣旨,尖声念道:“查刘瑾贪赃弄权,勾连宵小,谋乱萧墙,有负圣恩。着即拿下,钦此!”
话音未落,门外冲进来几名东厂番子,绳索齐上,没等刘瑾回过神来,转眼便将他捆翻在地,一名番子随手取了块手巾便将刘瑾的嘴给堵上了。此时,门外也传来一阵扭打声,随即,亲兵团长赖时亨迈步进屋,向着冯虞敬礼禀告:“报告,方才马督公向末将出示圣旨,指令末将率兵将那刘瑾部下一网打尽。现下门外几个刘瑾亲随已然拿获。府门外还有百十号随从,是否一并捉拿,赖时亨特来请命。”
“就按马公公部署去办。记着,手脚利索点,别闹出太大动静,更别让一个跑了。还有,门口那些眼线暗桩平日里让你们盯牢的,不管是什么出处,待会子一并先给我拿了。要是跑了一个,拿你试问。”
赖时亨双腿一并,“是!不管哪边跑了一个,末将提头来见!”
看着赖时亨跑步出屋,马永成不禁点头赞叹,“果然是训练有素。冯大人,麾下有能人啊。”
冯虞笑道,“东厂威名赫赫,宵小闻风丧胆,马公公又何尝不是驭下有方。来来来,且请稍坐,想来少时便有回报。”
果然,两人刚坐定,只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喧嚣,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屋外又归于沉寂。冯虞侧耳听了一阵,笑道:“成了。”
转眼间,赖时亨又匆匆进屋回报:“报告,方才职部已将刘瑾随从及府外各处眼线一扫而空。除格杀刘瑾侍卫三人外,余者束手就擒,我军无伤亡。俘虏如何处置,请大人训示。”
冯虞笑道:“捆牢了先丢场院里吧。空旷地方不好跑。看谁不老实当即斩了,不必请命,不必回报。”
“是!”
待赖时亨离去,冯虞转头冲马永成说道:“恭喜公公为国锄一巨奸。”
“过奖了。其中少不得也有侯爷你的功劳。”
“不敢贪功啊。对了,今晚皇上应该是不止这一路差遣吧?”
马永成点了点头,将之前正德的部署一一复述了一遍,感叹道:“今夜皇上杀伐决断,分明有太祖成祖遗风,大不同于往日啊。若不是如今天下承平,说不得又是个开创之君了。”
冯虞笑道:“承平之时便不能开创有为么?咱们这位皇上,不可小视啊。”说着瞥了一眼放翻在墙角地刘瑾,“此公便是吃了这个亏啊。”
马永成自然是连声附和,大赞了一番正德如何英明神武,转过头却不无忧心地说道:“京师里刘瑾爪牙甚重,京卫、京营、厂卫、五城兵马司都有党徒。万一给他们听了风声,连夜发难,却是极不好应付。现下只看亲军、团营能否尽早入城,控制大局了。”
冯虞却是信心满满。“公公不必着慌。此节虞早有布置。昨晚,我已奏明皇上,为防安化王余孽滋事,调亲军一师两万人马移驻京师北门外十里。此外,团营老营也在城外不远处,一呼即至。之前我还与留守豹房兵马打过招呼,务必枕戈待旦。豹房那边刘瑾党羽也没个跑。倒是皇上之前布置有一处疏漏,咱们得给补上。”
“怎么说?”
“皇上之前提过擒拿张彩,之后部署时却忘了发落此人。据我所知,这张彩不但是刘瑾心腹,还是智囊、总管。若是让此人得脱,四下煽风点火,京师必有大乱。马公公,你不妨遣几个得力部属,即刻去张彩府上拿人,不论死活,只是不能叫他逃脱。只要此人落网,刘瑾阵营群龙无首,自然难以发难了。”
马永成听了,一拍大腿,嚷道:“正该如此,怎的将此人忘了。我这就吩咐手下拿人。这厮若是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