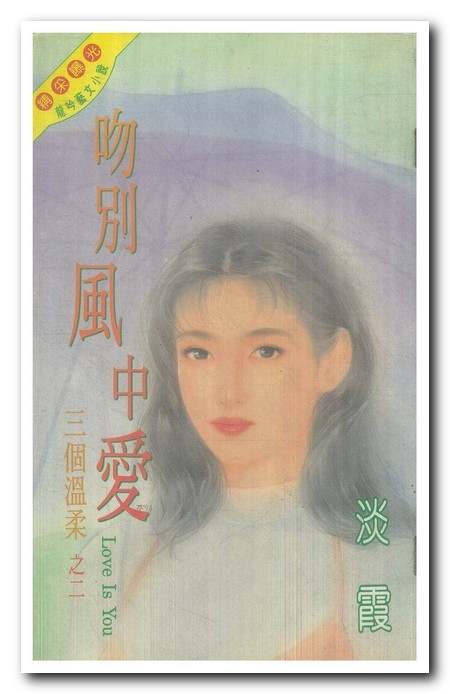the rainbow-虹(中文版)-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处奔跑着,一切全都毫无意义。他马上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
他看着厄休拉。她的脸上满是眼泪,可是非常光亮,仿佛在那通明的天光之中忽然变了一个样子。他用来给她擦去那热乎乎的闪着亮光的泪珠的手仿佛也不是他自己的了。他站在一边,一种残酷的、无能为力的感情压在他的心头。
慢慢地,在他心中出现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悲伤。可是他现在还在尽量和它进行斗争,他是为了自己的存亡问题在斗争着。他忽然变得非常沉静了,对他身边的一切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他仿佛是在等待着她对他的审判。
她考试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回到了诺丁汉。她必须到伦敦去。可是她不肯再和他一块儿住旅馆了。她要到大英博物馆旁边一家很安静的公寓里去住。
伦敦的这些安静的居住区对她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这儿一切都非常完备。在那里的那种宁静之中,她的思想似乎被禁锢起来了。谁会来把她解放出去呢?
在她的学位考试结束以后,那天傍晚,他同她一起到里奇蒙附近河边的一家饭店去吃饭。美丽的天空一片金黄色,黄色的水边是停留在杨柳树下的白色和红条纹的船上的篷帐和一片片蓝色的影子。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他声音急促但很随便地问她,仿佛这并非什么重大问题。
她观看着河上随时变换着的来去的游艇。他看着她的金色的惶惑的museau。他慢慢感到自己的喉咙哽住了。
“我不知道。”她说。
一种热辣辣的悲伤卡住了他的喉管。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愿意结婚吗?”他问她。
她慢慢把头转过去,她的惶惑的脸像一个孩子的脸,毫无表情,因为她现在看着他的脸,正在苦苦地思索。她看不见他,因为她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情。她一时说不清自己应该怎么说才好。
“我想我现在还不愿意结婚。”她说,她的天真、烦恼和惶惑的眼睛稍稍看了他一下,然后就向远处望去。她显然又去想她的心事去了。
“你是说永远,还是说暂时不结婚?”他问道。
他喉咙里的那个疙瘩变得越来越硬,他拉长着脸,仿佛他马上会给憋死了。
“我是说永远不结婚。”她说,仿佛是她的另一个遥远的自我代替她讲了这句话。
他的拉长的痛苦的脸对她看了一会儿,紧接着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她忽然一惊,立即清醒过来,恐惧地看着他。他的头奇怪地动了一下,下巴贴住了自己的喉咙,那奇怪的咕噜咕噜声又响起来,他的脸像发疯一样扭动着,他正在哭泣,盲目地扭动着身子在哭泣,仿佛原来控制他活动的一件什么东西现在忽然崩裂了。
“东尼———别这样,”她十分惊愕地叫道。
看到他那样子,她的每一根神经都似乎被撕裂了。他用手摸索着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他正无声地哭泣着,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的脸像一个假面具似的扭动着,眼泪从他脸上的深沟中一直往下流。他的脸永远像一个抽动着的面具一样让人感到非常可怕。他盲目地摸到他的帽子,摸着向阳台上走去。现在已经是八点钟,可是天色还相当的亮。有许多人转过脸来看着他。她又是非常激动,又是十分生气地留在后边,拿出半个金币付了饭钱,然后拿起她的纺绸外衣,跟在斯克里本斯基后面走去。
她看到他盲目地迈着碎步在河边一条小道上慢慢走着。从他的身体的那种奇怪的僵直的姿态来看,她知道他还在哭泣。她紧跑几步赶上去,挽起他的一只胳膊。
“东尼,”她叫着说,“别这样!你干吗要这样呢?你这是要干什么?别这样。这是不必要的。”
他听到了她的话,他的男人的性格被残酷地、冷漠地抹煞了。一切全没有用。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脸。他的脸,他的胸部都仿佛自动在那里凶猛地哭泣着。他的意志,他的知识和这一切都完全无关。他就是没有办法停住。
她挽着他的一只胳膊向前走着,愤怒、迷惑不解和痛苦的心情使她完全沉默着。他迈着一个盲人的不稳定的脚步,因为他的头脑由于哭泣已经盲目了。
“我们要不要回家去?要不要我去叫一辆马车?”她说。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她非常不安,非常激动地向着一辆慢慢跑过去的出租马车做了一个不很明确的手势。那马车夫一举手把车赶过来停下了。她拉开车门把斯克里本斯基推了进去,然后她自己也在车里坐下。她高扬着头,嘴唇紧闭着,样子看上去既凶狠、冷淡,又似乎有些羞怯。当马车夫向她伸过他的阴暗的红色的脸的时候,她止不住往后一躲。她看到他那张血红的脸上长着浓黑的眉毛和两撇剪得很短的浓黑的胡须。
“上哪儿,太太?”他说,露出了他的雪白的牙齿。她又犹豫了一会儿。
“鲁特兰广场路,第四十号。”她说。
他举手碰了一下帽檐,然后就稳稳地起动了马车。他似乎已和她商量好,对斯克里本斯基完全不予理睬。
斯克里本斯基好像被装进笼子里似的坐在那辆出租马车里,他的脸还不停地抽动着,有时猛地轻轻一动脑袋,似乎要甩掉脸上的眼泪。他始终也没有动一动他的双手。她看着他那样子简直无法忍耐。她坐在那里抬头看着窗外。
最后,她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于是又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已经安静多了。满是眼泪的脸不时还动几下,他的双手仍然一动也不动。可是他的眼神,现在却像雨后的天空一样显得安静多了,充满了淡淡的光亮,而且十分稳定,几乎有些阴森可怕。
在她的子宫里燃烧起了因他而引起的痛苦。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样伤了你的心,”她说,把她的一只手轻轻地试探着放在他的胳膊上。“那些话我连想都没想就那么随便说了。那都不过是随便瞎说说罢了,真的。”
他仍然十分安静地听着,但他脸色苍白,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她看着他,等待着,仿佛他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无法理解的动物。
“你别再哭了,你还会再哭吗,东尼?”
这个问题引起了他的羞惭和对她的强烈痛恨。她注意到他的胡须也完全被眼泪泡湿了,她拿出手绢来擦擦他的脸。那个车夫的厚重宽大的脊背始终对着他们,仿佛它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可是并不在意。斯克里本斯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听任厄休拉轻轻地、小心地,然而很笨拙地给他擦着脸。因为她显然没有他自己擦起来那么利索。
她的手绢很小,很快就完全湿透了。她从他口袋里掏出了他自己的手绢。然后,用这条大手绢她仔细地给他把脸擦干了。他一直仍然一动也不动。接着,她把他搂过来亲了亲他的脸,他的脸很凉。她心里感到很难受,她看到他的眼睛里很快又积满眼泪了。仿佛他是个小孩子,她又一次给他擦了眼泪。可是,现在她自己也忍不住要哭了。她用牙齿咬住了下嘴唇。
她安静地坐着,由于害怕自己也会哭起来,所以紧紧地挨着他,握住他的一只手,无限柔情地和他依偎在一起。这时那马车仍然向前奔跑着,柔和的仲夏的暮色越来越浓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她的手偶尔更紧地捏着他的手,表示一番爱抚,又慢慢松开了。
黑夜慢慢来临,远处出现了几星灯光。车夫把马车停下来,点上车灯。斯克里本斯基第一次动了一动,他向前倾过身子去,看看那车夫在干什么。他的脸仍然是那么宁静、清晰,仿佛带着一种冷淡的孩子的神态。
他们看到那车夫的奇怪的肥胖的黑色的脸紧皱着眉毛,正在朝灯里面观看。厄休拉不禁哆嗦了一下。这简直像是一头野兽的脸,然而这却是一头动作迅速的强大的机智的野兽,它不仅完全知道他们,而且几乎直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威力之下。她和斯克里本斯基靠得更紧了。
“我亲爱的,”她疑虑不安地对他说。这时那马车又开始全速前进了。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他让她抓住他的手,让她向前俯着身子,在那愈来愈浓的黑暗中吻着他的一动也不动的脸。哭泣已经过去了,他不会再哭了。他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下来,恢复了常态。
“我亲爱的,”她再次叫着说,极力想让他注意到她。可是他似乎还做不到。
他看着车外的马路。他们现在已跑过了肯辛顿花园。现在他第一次开口了。
“我们要不要下车到那公园里去呆一会儿?”他问道。
“那好哇,”她安静地回答说,弄不清他这是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取下了挂在木桩上的话筒。她看到那魁梧、强健和沉静的车夫,向他们这边歪过头来。
“在海德公园的拐角处停下吧。”
那个黑色的头点了点,马车仍照样往前跑着。
很快他们就停下了。斯克里本斯基拿钱付车费。厄休拉站在一边。她看到那车夫在接受小费的时候行了个礼,然后在驱动马车之前,先转过头来,用他那敏捷有力的野兽的眼神看了她一眼。他的眼光是那样的集中,白眼珠闪闪发亮。然后,他就驾起车走到人群中去了。他总算放开了她。她一直就感到很害怕。
斯克里本斯基和她一起进了公园。那里的乐队还在演奏着,公园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听了一会儿那悠扬的音乐,然后就走到旁边暗处的一张椅子前,手拉着手紧挨着坐下了。
最后,她终于打破沉默,犹犹豫豫地对他说:
“你到底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这时她的确感到难以理解。
“就因为你说你永远不肯跟我结婚了。”他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回答说。
“可是那怎么会使你那么难受呢?”她说,“对于我说的话,你完全不必那么认真。”
“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那样。”他谦恭而羞愧地说。
她热情地捏着他的手。他们紧挨着坐在那里,观看着一些士兵带着他们的情人走过去。无数的路灯沿着紧贴在花园边上的大道向远处伸展开去。
“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在意。”她也表现得十分谦卑地说。
“我也没想到。”他说,“我是冷不防自己栽了一个跟头———可是我在意———比什么都在意。”
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安静和丝毫不带感情,这使得她由于恐惧心都完全凉了。
“我亲爱的!”她说,把他更拉向自己的身边。可是,她这声喊叫完全是出于恐惧,而非出于爱情。
“我比什么都更在意———其他的一切我都不在乎———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他用同样那种安静的、毫无感情的真心实意的声调说。
“那你主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她低声喃喃说。
“就只是你———就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她又一次感到非常害怕。难道他就这样让人给征服了吗?她和他挨得更近一些,紧紧地偎着他。他们完全一动不动地坐着,倾听着那个城市的巨大的重浊的嘈杂声,倾听着走过的情人们的低语和士兵的脚步声。
她靠在他身上,不禁哆嗦起来。
“你冷吗?”他说。
“有一点。”
“我们去吃点晚饭吧。”
他现在一直都非常安静,因为主意已定,情绪更安定下来,所以也显得非常漂亮。他似乎有一种能够控制住她的奇怪的冷静的力量。
他们走进了一家饭馆,开始喝一种意大利酒。可是他的苍白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
“今天晚上不要离开我,”他最后看着她,请求地说。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奇怪和冷静,她又感到害怕了。
“可是,我那里的那些人。”她哆嗦着说。
“我会去对他们解释的———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订婚了。”
她脸色发白,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他等待着。
“咱们可以走了吧?”他最后说。
“上哪儿?”
“去找一家旅馆。”
她一切都豁出去了。她什么话也没说,站起来准备跟他走。可是她现在变得非常冷漠,简直是心不在焉了。不管怎样,她不能拒绝他,这仿佛是命里注定,是一种她无法逃避的命运。
他们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家意大利旅馆,租下了一间摆着一张大床的光线阴暗的房间。房间里很干净,可是非常阴暗。顶棚上,在床的上边,有一个很大的由花朵组成的圆形图案。她觉得那图案很漂亮。
他来到她身边,紧紧地搂着她,像钢铁一样死命紧搂着她。她的情欲被挑动起来。那情欲强烈而又冷淡。但今天夜里,他们的情欲可说是十分强烈、无比激动而又美妙。他紧搂着她,很快就睡着了。整个一夜他始终紧紧地搂着她。她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一切听之任之。可是她的睡眠一直都不很深沉,老是恍恍惚惚。
她清早一醒来就听到外面庭院里洒水的声音,并看到从窗格间射进来的阳光。她想着他现在是在外国的什么地方,斯克里本斯基像是趴在她身上的狐狸精。
她沉思着,安静地躺在那里,让他贴在她的身后,胳膊搂着她,头靠在她的肩膀上。两人身子贴着身子,他仍然睡得很熟。
她看到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照了进来;转眼之间,眼前的一切景象似乎又完全消失了。
她现在已经置身于另外一片土地上,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旧的制约已经消失,已经不复存在。一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不必怕别的人议论,不必那么小心,也不必随时防范着,而只是安静地过着无所顾忌的舒适生活。在一种迷惘的心情中,她似乎是自由自在地在一种银色的光辉中游荡着。人世的各种纽带已全部破除,英格兰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了。她听到下面院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叫喊着:
“奥基俄凡———奥———奥———奥———基俄凡!”
她现在知道,她是在一个新的国家,过着一种新的生活。这么安静地躺着,让自己的灵魂在另一个更简单、更接近自然的世界的银色的光辉之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游逛着,这实在是太美了。
可是,不知什么地方总有一种禁令在等待着她。她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了斯克里本斯基的存在。她知道他现在醒过来了。她必须为了他离开她那个更遥远的世界,而使自己的心灵受到折磨。
她知道他已经醒了。和他睡着时不一样,他用一种可以感知的安静,安静地躺着。接着,他的胳膊简直像痉挛似的更紧地搂住了她;他半似恐惧地说:
“你睡得好吗?”
“睡得很好。”
“我也是。”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爱我吗?”他问道。
她转过身来仔细地打量着他。他似乎和她毫无关系。
“我爱。”她说。
可是,她说这话完全出于应付,而且希望他不要再麻烦她了。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默的隔膜,这使他感到很害怕。
他们在床上躺到很晚,然后他摁铃要早饭。她希望起来之后,马上下楼去,离开这个地方。呆在这个房间里她感到很快乐,可是一想到到下面大厅去要见到许多人,便使她感到很不舒服。
一个出生在西西里的年轻的意大利人端着一个盘子进来了,他规规矩矩地穿着一身灰色的制服,黑黑的脸,微微有几颗麻子。他的脸上几乎有一种非洲人的十分冷漠的、被动的、难以理解的神态。
“简直像在意大利。”斯克里本斯基温和地对他说。一种近于恐惧的莫名其妙的神态出现在那人的脸上。他不懂他的话。
“这里很像是在意大利。”斯克里本斯基解释说。
那个意大利人的脸上闪过了一点表示不很理解的微笑,他放下盘子里的东西马上就走了。他不理解他的话,他什么也不愿意理解。他像一个还没有完全驯服的野兽一样从门口消失了。那个人的那种动作迅速、目光锐利、精神集中的动物性的表现,不免使厄休拉微微哆嗦了几下。
今天早晨,她觉得斯克里本斯基显得非常漂亮,他的脸由于痛苦和热恋变得更温柔更开朗了。他的举止也变得安静和柔和多了。在她看来,他显得很美,可是她却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得非常冷淡。她似乎总极力想缩短存在于他们俩之间的距离。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一点。那天早晨,他显得很开朗、很漂亮。她对他的一举一动,比方像他在蛋卷上涂蜂蜜,以及他倒咖啡的那种姿势,都感到很赞赏。
早饭之后,她倚在枕头上静躺着,让他先去梳洗打扮。她望着他,看着他用海绵擦洗,然后很快又用毛巾把身体擦干。他的身子很美,动作利索而迅速。她毫无保留地对他十分钦佩和赞赏。他现在似乎一切都已经完备。他在她心中引不起生儿育女的念头。他似乎一切已经结束,已经完结了。她对他已经全面了解,没有一个方面由于不了解还能引起她的好奇。她感到对他有一种强烈的,甚至是充满热情的赞赏,可是决没有那种可怕的惶惑感,决没有那种丰富的恐惧感,没有那种跟不可知的世界的联系,或者爱的尊重。但是今天早上,他似乎完全处于茫然的状态。他的身体宁静而满足,他的全身的血管都充满了满意的感觉,他感到幸福、完美。
她又回到了家里,可是这一次他也陪着她。他希望呆在她的身边。他希望她和他结婚。这时已经是七月了。九月初他就一定要出发到印度去了。要让他一个人走,这是不堪设想的,她必须和他一起走。所以他总尽量留在她的身边,神经一直非常紧张。
她的考试结束了,同时也就结束了她的大学生涯。现在她只能要么结婚,要么再去找工作做。她并没有寻找工作,那很显然她是要结婚了。印度对她也有吸引力———那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可是一想到加尔各答,或者孟买,或者西姆拉,以及那里的许多欧洲人,印度马上变得和诺丁汉一样对她毫无诱惑力了。
她的那次考试结果没有通过:她失败了,她没有得到她的学位。这对她是一个打击,这使她的心情十分恶劣。
“没有关系,”他说,“你有没有按照伦敦大学的标准获得学士学位,那对你有什么差别呢?你所学到的东西,你已经学到了。如果你做了斯克里本斯基太太,那学士学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话不仅没有使她感到安慰,相反的,却使她变得更冷淡,更暴躁不安了。她现在要和她自己的命运进行斗争。现在,得由她自己来做出选择,究竟自己是去当斯克里本斯基太太,或者甚至斯克里本斯基男爵夫人,去当一位皇家工兵上尉,或者如他所说的地老鼠的老婆,和别的许多欧洲人一起到印度去生活;或者还是做她的厄休拉·布兰文,当个老姑娘,去教一辈子书。由于她通过了中级学位考试,她现在完全具备了做教师的资格,她也许能够很容易在大学找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