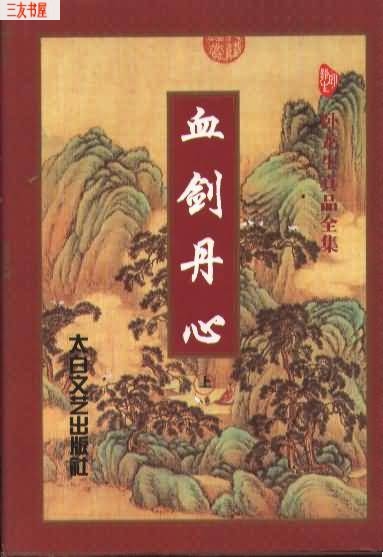赤胆丹心-第1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夫子这话何所见而云然,难道抚院有查究之命吗?果真如此,那倒不妨明白见示,兄弟才好答话,否则却不免稍嫌唐突了。”
韦文伟连忙站了起来,又一拱手道:“大人不必生气,晚生虽在抚幕,敝居停岂有对大人查究之理。便晚生也实无他意,只不过素性好奇,闻得川中三侠,均由大人罗致,意欲一见,却想不到因此转致开罪,既如此说,容晚生告辞便了。”
羹尧略一沉吟忙又道:“老夫子且请慢走,兄弟还有话说。”
韦文伟忙又坐了下来笑道:“大人只要不见罪,有话尽管吩咐,晚生恭候便了。”
羹尧也转笑容道:“老夫子方才说的川中三侠,究属何指,还望明说,否则你这样一走,那我更不明白了。”
韦文伟又哈哈大笑道:“大人何必明知故问?这川中三侠此间便三尺之童也会知道,难道大人竟未有所闻吗?”
接着又笑道:“这三位大侠便是罗老英雄天生,马老英雄镇山,还有一位玄门道长,静一道人,不全在大人罗致之中吗?”
羹尧又笑道:“原来老夫子指的是这三人,那位罗老英雄,倒确在敝署,但也只因他两位文郎在京曾与兄弟论交,才邀来一见。至于马老英雄却又因罗老英雄之介得以相见,如以技击而论,这两位确有过人之处,但却非游侠中人物,还有那位静一道长,兄弟却未见过,老夫子要见罗马二位这倒容易,改日只要他二位在此,便可相晤,那静一道人却连我也无法见到,那只好违命了。不过这两位一切无异常人,却算不得奇人异士咧。”
韦文伟又笑道:“大人是司空见惯,自然不以为奇,但在川中却是妇孺皆知的着名大侠咧。”
说着重又起身告辞,一面道:“晚生无知,多多冒犯,容再谢罪,这罗马二位既蒙金诺却必须介见咧。”
羹尧也不再挽留,便端茶送客,等他走后,忙回上房,将情形对中凤一说,一面令周再兴即刻去将布置在抚院的血滴子传来问话,中凤支颐沉思良久,忽然道:“照你方才这一说,此人这次来见的态度,不但不是巴结,反极傲慢放肆,大有咄咄逼人之概,那就一定有所使而来,要不然,焉有如此之说,这却非弄清楚不可,否则这以后,还真不好办咧。”
接着又笑道:“你曾称一称他的斤两没有?是不是也是一个练家子?这却也不可大意。”
羹尧忙又摇头道:“这却不知道,不过从他起坐行动看来,却是一位读书人,未必便曾练过。”
两人又揣测了一会,羹尧便去西花厅,来寻罗马二老,谁知全出去了,一个也不在家,转是周再兴转回来道:“那抚院布置的两名血滴子全已找到,少时便从后门进来,我在那刘秉恒家中已经约略问过,据他说,这位韦老爷是南边人,道道地地是一位绍兴师爷,过去和抚台并不认识,是由一位权要所荐,现在却相处极好,抚台大人对他极其尊敬,只称韦先生而不名,伙食全由小厨房开到他自己房里并不和其他各位师爷在一处用饭,平日除办奏折而外,便没有什么事,他也没有朋友,却每天全要出去逛上一趟,往往深夜才回来。”
羹尧点头,忙命将两名血滴子引向东花厅相见,不一会,那刘秉恒先到,他乃是抚院一位门稿大爷,在京之日本就和羹尧认识,见面叩头行礼之后,一问情形,果然和周再兴所言差不多。言所未及的,只有那韦文伟是江南中试的一名举人,并还工书善画,乃命随时留心行动,并将在外游赏的地方具报,来往信件地址人名也记下来,每日报上一次,等那刘秉恒走了之后,方将另外一人引进,一问却是一名专跑上房的小当差,姓黄名升,年纪才只二十来岁,所答也和刘秉恒大致无异,所不同的,是那韦文伟在外面尚有一处外室,便在衙门后面一条巷子里面,忙也命用心探报,并留意近日有无奏折专函发出。
等将黄升打发走了,恰好罗天生和马镇山二人也回来,忙到西花厅密室将情形一说,罗天生不由吃了一惊道:“如照这等说法,这其中定有主使的人,我与马兄无妨,那方老道却是名在海捕的要犯,今后却不宜再向此间出入,再说这人来历用意,也全非弄清不可,要不然还真不好办,老贤侄日内何妨去一见那巡抚,也许约略可以知道一点根底,此外此间各事,也须专函先告诉令亲一下,将脚步站稳。”
接着又掏出一张名单笑道:“川中各码头血滴子我和方马二兄已经计议好了,这张名单你过目之后,不妨也寄给他去,就便连允题私行出京约期比拼的话,也提上一提,在这时候,除我们的大计,和太阳庵的事而外,其余却不必瞒他。”
羹尧接过那名单一看,竟有二百多名,各县和重镇几乎是一个地方不空,忙向二人申谢,一面又提到沙丁诸人将来,和太阳庵筹设下院的事,罗天生大笑道:“我和方马二位老哥,连日便专为此事奔走相商,那下院决设青城山中,用赞普老番那撷翠山庄改建,一则地方幽僻,外人一时决找不着,二则他那里有一处秘径直通山腹,下及壑底,便不幸泄漏出去,也有一个退步,收徒上祭,更不怕外人看见,那方老道得力心腹弟子之中,便有苦干瓦木作巧匠,如今已经将人派了出去,和赞普夫妇会同办理,至多半年必可落成,这个下院,将来不妨请准老师父,作为统辖秦陇川诸省教务之用,那底下一步便是派出人去和那何老弟一同北上,与在京各人商定,请总坛派人前来举行开光大典,正式开山收徒,这事却无须再为磋商,只等丁沙各位一来,便可决定,目前要紧的,还是将这位姓韦的先摸清楚再说,要不然,各事便全放不开手去咧。”
羹尧方在点头,马镇山忙道:“这厮既有外室,我们从这个上着手,便不难明白,那巡抚衙门后面,我那无极教便有一处神坛,待我先去查看一下便了。”
羹尧忙道:“如得老前辈前往最好,但却不必打草惊蛇,让他知道,那就反而误事了。”
马镇山大笑道:“老弟你但放宽心,我这分坛本专为刺探抚院消息而设,那坛主玉美人王小巧,虽然是一个风流浪子,做事却极为精细,也颇有分寸,如今他也算是你这血滴子的一个分队长,我这一去,保管不出三五日便有确讯。”
说着,便告辞出了学政衙门,径向巡抚衙门后面而来,那王小巧原是破落户出身,除一身花拳绣腿而外,对于斗鸡走狗,无一不精,各项乐器无一不会,更生得非常俊俏,因此有玉美人之称,所居便在抚衙后面一条深巷内,原是一座一连三进的房子,东边还有一座小小跨院,只因年久失修,前面一进已经塌了,只剩一堆瓦砾,和短垣残壁,他便索性拆做一个大院落,将第三进做了神坛,第二进接待教中弟子,自己住到跨院里去,马镇山走到门前伸手一敲那门,半晌方听一个老佛婆出来开了门:“今天不是斋期,坛主也不在家,你有什么事,不妨晚上再来。”
马镇山不由寿眉微耸道:“我姓马,刚从川边来,找他有要紧的事,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那老佛婆将他上下一看,忙道:“他便在巷子外面小茶馆内坐着,这时也许摆上龙门阵咧,既有要紧的事,且待我去将他唤回来便了。”
说着,便将马镇山邀向厅上坐下,径自出去,半晌之后,忽听前面门声一响,一个清脆的喉咙娇笑道:“这小子真不是东西,怎么连门也虚掩着,便走了出去,我要不吓你一大跳才怪。”
说着便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妖妖娆娆的扭了进来,先向厅上略微一望,恰好马镇山坐在东边窗下,她并未望见有人,便径向跨院而去,马镇山本知王小巧是一个浪子,既没有成家,更无父母,心料必是姘妇之类,也未动问,仍旧坐在那里等着,又好半会,方见一个穿着褪色青绸长袍的少年走了进来,纳头便拜道:“弟子不知教主驾到,有失迎迓,还请恕罪。”
说着,大拜八拜方才起来侍立一边,马镇山再一细看,只见他瘦长身裁,长长的一张白净面皮,果然生得长眉俊眼,鼻如悬胆,唇若涂朱,只身上那件青绸长袍,不但已经褪色,有些地方已经破了,露出里面棉絮来,足上一双快鞋也破了,忙道:“你近来景况不大好吧,这里的教务如何?巡抚衙门对我们这无极教有什么消息吗?”
那王小巧连忙躬身道:“弟子不肖,本来家无恒产,近来因为教中须款又垫上了些,委实有点窘迫,至于巡抚衙门对我们这教虽未下令禁止,却也暗中正在查问,所好这里熟人多,弟子一时还能对付。”
马镇山一面笑着,一面掏出二十两一个川锭来道:“既然景况不宽,这里是二十两银子且拿去用,可不许吃酒赌钱去找女人,你如真的成家,我还可以成全。”
王小巧一手接过,又叩头谢了,马镇山忙道:“你不必如此,既系教下得力弟子,如有正用,我自不会着你受窘。”
说着又道:“我如今应学政年大人之邀,住在学台衙门,现在有一件事,关系本教极大,你须着意打听一下,果然办得好,我必设法调剂,让你得点好处,按月可以有几两银子,以后也好图个出身。”
王小巧忙又叩头道:“教主若能如此栽培,弟子终身感戴,决不敢有负教主这番盛意。
知有什么事着弟子去打听?”
马镇山忙将脸色一沉道:“这巡抚衙门有一个姓韦的文案,你知道吗?”
王小巧不由一怔道:“弟子知道,教主怎么忽然要打听起这人来?”
马镇山道:“你且不问这个,只将他出身来历先打听明白告诉我便行了。”
王小巧忙又躬身道:“这事不用打听,弟子早已知道,他是江南绍兴人,出身是一位乙榜举人,昔年曾在北京荣亲王府处馆,此番跟这巡抚大人入川是由宫中一位司礼太监所荐,所以巡抚大人非常看重,每月束修是三百银子,只办奏折,其他概不过问。”
马镇山不等说完便一捋修髯,大笑道:“你怎么知道得这等详细,却不可信口开河咧。”
王小巧忙又躬身道:“这个弟子怎么敢在教主面前撒谎,不信你老人家只管打听。”
马镇山二目微睁,两道奇光在他脸上一扫道:“既如此说,我还有事着你打听,只要能打听清楚,不但重重有赏,便方才我说的话,也必立即办到,不过这是机密大事,倘有虚诬不实不尽,或者泄漏出去,那便须领受我教下神刀贯顶,铁钻穿心的刑罚,你敢担当吗?”
王小巧忙又跪了下来道:“弟子既领教主之命,如有不实不尽,愿依教规处理,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马镇山忙又附耳说了一会,王小巧点头答应不迭,一面道:“教主放心,弟子多则五天少则三天,必能陈明实在。”
马镇山又嘱咐了几句,便出门回去,王小巧送出大门不由一脸高兴之色,口中哼着小曲,径向那跨院而来,那跨院之中,只有二间倒轩,他因为只有孤身一人,将西边两间做了客室,居然收拾得几净窗明非常雅洁,东边一间便做了卧室,原拟到卧室之中,换上一件衣服出去,但才一进房,那门后,忽然伸出一双嫩手将他双目掩上,接着便闻得一阵兰麝之香扑鼻,连忙笑着,一个转身,双手将那人一抱乘势先在脸上啧啧亲了两下,道:“那老家伙今天没来吗?你也该等到晚半天再来才是,怎么这个时候便来?当真便这等猴急,须知如果让他知道却不好咧。”
原来那藏在门后的,正是马镇山所见的妇人,闻言忙也将王小巧一把搂定,道:“他知道又怎样?老娘又不是他的老婆,我也不在乎他那一个月几两银子,好便好,不好各走各的路,抚台大人难道还能打我仰板,发交官买不成?”
说着却把一个酥胸贴紧了王小巧,双手按着脖子,将一条嫩舌直吐向王小巧口中来。
王小巧连忙一把推开笑道:“你且慢着些儿,那老佛婆已被差出去买点心,少时也许便回来咧。”
那妇人不由俏脸绯红,目光似火,浪笑道:“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偏在这个时候差她买点心去?要支使不会把她支使得远一些吗?”
接着又道:“反正我给过她不少好处,你去将门关上,她还能闯进来吗?”
王小巧摇头笑道:“那可不行,我们还得有事商量。”
那妇人忙道:“商量什么?是借钱吗?多没有,一二十两银子我还可以巴结,我不早和你说过,要短了钱,不妨和我说,你自不肯,那有什么法子?现在却打算拿我筋节,这怪得我吗?”
王小巧忙又笑道:“你全想得左咧,我虽不算什么正人君子,却还不至于要用女人的钱。”说着一手掏出那二十两银子,大笑道:“你瞧,我这是拿你筋节吗?”
那妇人忙又道:“那你有什么商量快说吧,我能依的全依你就是咧。”
王小巧又笑道:“你当真对那老家伙,就半点香火情没有吗?”
那妇人乜了他一眼也笑道:“这个时候,你平白又提这个做什么?那老家伙是化钱买乐儿,我是得钱消灾,一买一卖,这有什么交情可言?你难道还吃那老家伙的飞醋不成?我要对他真有交情,还不来找你咧。”
王小巧又笑道:“既如此说,这话便好说咧。”
说着一手搭向那妇人肩上双双就榻上坐了下来道:“如今那老家伙也许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他没法奈何你却打算找我的不是咧。”
那妇人忙道:“当真吗?你既不作贼又不为盗,办这神坛也是劝人为善,他到哪里找你不是去?”
王小巧摇头道:“我怕是怕不了他,不过有他在这里,我们的事总不方便,你以后还是少来,便今天也宜就此回去,要不然可不太好。”
说着,那只手却不老实起来,那妇人本来挟着一腔欲火而来,那禁得一再挑逗,闻言忙道:“好人,你别捉弄我,要我不来,那除非杀了我,他真要找你不是,我们索性离开这里,你没父母,我也没亲人,我们什么地方不能过起一份日子来?我和他既不是夫妻,又不是他的小老婆,他除了倚官仗势,还凭什么能找我们?”
王小巧又叹了一口气道:“不怕官,只怕管,闻得这老家伙,连巡抚大人全让他三分,就是要走,我们也该摸清他的来头才好。”
那妇人忙又把一张脸全偎向王小巧怀中道:“他的来历,我不早告诉过你吗?怎又问咧?”
王小巧摇头道:“你那话恐怕他是在骗你亦未可知,凭他只不过一个举人,抚台大人怎会对他这等恭敬信任,你还与我打听清楚才对。”
那妇人又笑道:“你原来为了这个,那容易得很,我包管不出三天连他的祖宗三代生辰八字全打听出来,你却不用怕咧。”
说着又浪笑道:“时候不早,快别耽误了,你还是快去将门关上,再迟那老佛婆便该回来咧。”
王小巧笑着去把门关上,匆匆回来又道:“我还忘记告诉你,我闻得有人说,这老家伙,没法奈何我,竟已经将我们这无极教,报了妖言惑众,打算造反咧,你也得再打听一下才好。”
接着又道:“他在你住的地方,有时候也批文书写什么吗?”
那妇人脸上红扑扑的嗔道:“你今天哪来的这许多话?他写东西倒是常写,可是我又不识字,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咧?你一定要知道,那我也有法子,他每一次到我那里去,虽然全非回去不可,总须脱掉衣服睡上一觉,你只藏在我那厨房里,等他睡着了,他如写什么,我偷着给你看一下不也就明白了?”
说着,竟来了个严阵以待,王小巧本也冷战已久,话既说完,也不再坐视,只苦了那个老佛婆,买了点心回来,却不得其门而入,敲唤了一阵也不见内面答应,直把一盘点心等得冷了,方见王小巧开门,再看时只见他敞披着长衣,脸上红红的,额上汗犹未干,忙道:
“你又在后面练功夫吗?怎我敲了半天门不见答应?那位老人家咧?点心全冷了,这却不能怪我。”
王小巧连忙支吾道:“他已走了,我方才睡了一觉,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那老佛婆正色道:“这冷的天气,你为什么睡觉,睡出一头汗来?”
再看时,那妇人已经从角门里出来,不禁(炫)恍(书)然(网)大悟,不再说什么,那妇人却笑嘻嘻的道:
“我正想来烧炷香,不想坛主竟睡着了,一个人也没有,如今也该回去咧。”
接着又道:“你这件袄子又破了,也该换上一换才是,我那里尽有用不了的布和棉花,明天到我那里取去,老年人却受不得凉咧。”
那老佛婆谢了又谢,心中虽然明知是怎么一会事,但人家已经许了愿,那能再说什么,转搭讪着道:“花二娘,你才来怎么就走?且待我将点心热一下,吃上两个再回去不好吗?”
那妇人却红着脸摇头而去,原来这花二娘,原本是当地一个著名私娼,虽不公然出局陪酒,却艳名颇噪一时,和王小巧原旧相识,那韦文伟虽然年逾知非,却颇喜渔色,但又道貌岸然,以朱程自诩,三不知瞒了抚衙各人,竟也成了入幕之宾,本待娶以为妾,但又不肯坏声名,所以暗中说妥,按月给钱包了下来,又特为她买了一座密室,作为藏娇金屋,只是公然在外住宿又恐被人知道,仍旧不妥,却闹了个偷偷摸摸夜去明来,每日下午到那地方,至迟二更以后便回衙门歇宿,那花二娘,虽然打扮起来,看去不过二十来岁,实际已是三十出头,正当狼虎之年,怎耐得夜夜孤衾独宿,背地里却仍和王小巧藕断丝连,时续旧好,却只碍着韦文伟,不敢公然留住香巢,转不时移樽就教,她那所居,是一座小楼,虽然楼上下才只四间房子,却独门独院,只住着花二娘一人,和一个仆妇,别无外人,这天从神坛回去,那神坛和居所,相隔不过一条巷子,还不到三五十步,不消片刻便到,方欲入门上楼,一看天色,不由暗中叫声啊哟,原来外面已是未末申初,正是韦文伟来的时候,方一敲门,那仆妇迎了出来悄声道:“老爷来了已经有一会,正在楼上咧。”
接着一看她脸上又悄声道:“奶奶,你这样子上去不得,且到我那房里稍待梳洗一下再说。”
原来那仆妇方妈久侍花二娘,原也是烟花巷陌积年人物,花二娘心知一定留下了破绽,连忙蹑着脚,随了方妈,走向楼下下房之中,取过一面镜子一照,只见一头头发全蓬着,眼圈儿发青之外,嘴唇下胭脂只剩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