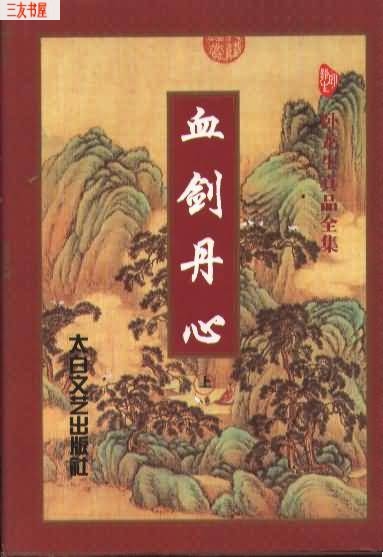赤胆丹心-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羹尧忙从床上坐了起来一掀布帷道:“您别瞒我,到底有无妨碍,要不然,治一经损一经却要不得咧。”
小香连忙赶前一步道:“您先别问这个,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倒是您的瘀血才下却折腾不得,还请睡好为是。”
说着忙就榻前又扶着羹尧,仍令睡下,一面长叹一声道:“可惜老师父和哑大师全不在这里,否则能有一粒回天再造丸,或者秘制百草还阳丹,便全好了。”
中凤忙道:“那回天再造九我倒有过一粒,可惜已经送人了,我想了因大师伯和周叔身边也许有,果然非此不行,那便只有打发人回京去求上两粒咧。”
小香不由跺了一脚道:“你这人,这种赎命至宝,怎么拿它送起人来,此刻只有一粒我和二爷分用,便全可随时复原,这一来不是不能好,却须假以时日了。”
中凤忙道:“既如此说,那只有赶快着人回京去求各位尊长,别人或许不会有,了因大师和周师叔身边总该有,能求上两粒来不也就行了。”
小香忙道:“亏你还是两位老人家的入室弟子,怎么就讲得这样容易,须知这种灵丹,不但要用若干可遇而不可求的圣药,天时人事非全备不行,就是知道方子制炼之法,也往往数十年不易配齐,一料也不过数十粒而已,这就在两位大师本人,也不敢必其便有存药,你能料定在京各人身边必有吗?如果徒劳往返,倒不如稍假时日让他慢慢恢复了。”
中凤不由半晌不语,羹尧忙道:“既有此药,何妨再请周再兴贤弟一行,反正我们有一匹千里良驹,往返极快,如能求得不好吗?”
正说着忽听那前面一阵人声噪杂,中凤连忙出房命人查问,天雄已从前进赶来道:“年兄好些吗?外面好多人求见,我一概挡掉,但那太湖谢老前辈一则远道而来,不便相拒,二则她说还有一件大事,不得不当面说明,这却无法不见咧。”
中凤忙道:“太湖那位谢老前辈忽然来此,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咧?”
天雄忙将谢五娘身世和所托说了,羹尧在榻上已经听见,忙又坐了起来道:“既如此说,马兄快请这位老前辈进来,容我穿衣拜见便了。”
小香在旁忙道:“二爷瘀血才下不宜劳动,那位老前辈既然也是一位女的,由云姐接待不也好吗?”
羹尧摇头道:“人家是老前辈,既然是为了那匹马指名要见我,怎么能不撑了起来。”
说着,便唤二婢取衣来穿,一面又催天雄相请,小香不由着急,中凤也赶进房来拦着道:
“您先别忙,那谢老前辈虽然要见你,你已受重伤却是真的,先由我来代见,她老人家也未必要一定见怪,真的要硬撑着起来,再折腾一下如有反复,别的不说,您对得起马姐吗?再说现在那回天再造丸还不知能否找到,万一再有差错,那便难说咧。”
羹尧不由默然又躺了下去,天雄在房外忙也道:“年兄放心,那位谢老前辈说来也是自己人,您但躺着无妨,且待我说明,请她进来便了。”
说罢径去,中凤和小香又一再劝阻,不一会,忽听前进一个苍老的女声道:“我早知道年二公子已被那老贼暗算咧,此来一则为了看一看我那小墨龙下一代的主人,二来便也为稍尽绵薄,既如此说,我倒放心了,马爷赶快请他不必起来,好在他那位云夫人也是老师父爱徒,我先和她谈一谈也是一样。”
中凤闻言,走出房来一看,只见天雄已经陪了个白发盈额,满脸皱纹,一身青布衣裙的老妇人进来,看那年岁,分明已在八十以上,却步履异常利落,二目更觉炯炯有神,连忙迎着拜道:“弟子云中凤不知谢老前辈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外子年羹尧因被侯威老贼阴手所伤,目前瘀血方下,未能起床,并请恕过。”
那谢五娘连忙扶着,先将中凤上下一看笑道:“久闻老师父所收几位弟子,全是出色人材,那鱼翠娘我已见过,确实名不虚传,却想不到竟是一个胜似一个,只可惜我这老婆子早生了几十年,如今到了这些年纪却无法订交了。”
说着又笑道:“我们且慢谈这个,那侯威老贼,所练阴手端的厉害,年公子既然中他一指,虽然那位马爷已经告诉我,伤已发出瘀血也下来,但稍一不慎,他年留下病根,却极可虑,能先赐我一看吗?”
中凤一面逊谢,一面肃客就座,将经过和小香治法一说,谢五娘点头笑道:“我道这伤为何发得这快,原来却由人用内功吊出,那武当少林的两种灵药我虽没有,却另有一项自制秘剂可以用得,既然伤发瘀下那便容易了,不过事不宜迟,还望容我先看伤势再行下药如何?”
中凤正说:“待我扶他出来拜见,再请老前辈看伤赐药。”
谢五娘连忙摇手道:“这却使不得,这瘀血一下,更比伤发之前更要紧,稍一大意病根便中,千万不可勉强起来,还是我来看他,比较妥当。”
说着便站了起来,携着中凤的手悄声道:“我也皈依太阳门下,却不是外人咧。”
中凤连忙又陪着,一同进了东间,羹尧便要起身也来不及,只有由小香挂上布帷,伏枕叩谢,谢五娘含笑道:“我在太湖,便闻得公子英名远播,此次北来,一路之上更是口碑载道,不过公子一身所系极重,前日所为虽属老贼见逼,不容袖手,但明珠弹雀,老妇却以为在所不取,以后还望珍重才好。”
羹尧不禁悚然,忙又谢过,五娘笑道:“老妇只因所望者大,出言不免憨直,还请不必介意。”
说着,一面走近榻前,一看脉象,又命解开衣服,微按伤处又笑道:“公子不但骨格非凡,先天禀赋特异,便内家功夫也到了火候,如以现在情形而论,便无药饵,也不过运用内功三五日内,便可无害,只忌用力而已,如再服我那归元散,自己运行一周天便可一切如常了。”
说罢,便取出一个绿玉小瓶来道:“此乃老妇昔年所配归元散,虽不能与回天再造丸、百草还阳丹相比,但也极具灵敏,只用七厘服下便行,余药我亦无所用之,便以相赠,以备救人,只非内伤极险,不必多用,否则如果用完,便一时无法再配了。”
羹尧忙道:“弟子只须一服已足,不过这位马姐却因运用内功救我,以致也大损真气,这药也能治吗?”
谢五娘把头一抬看了小香一眼微讶道:“公子这伤,便由姑娘用内功吊出吗?但既精此道,又为什么会因此伤及真气咧。”
小香不由含羞道:“那是弟子一时为了救人心切,自己又功力不够所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真气失调,稍一勉强运行,便竟胸隔作涨而已。”
谢五娘忙道:“这就奇了,你既能用内功将他伤吊了出来,怎么会把一口气运岔了,幸而我正好赶来,否则时日一长,轻则成为患疾,重则说不定会得半身不遂之症,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
小香猛忆运气治伤之初,微闻羹尧有拒婚之意,心下正又急又恨,真气一岔,便觉不能运动自如,起初还当功力不够,勉强从事,才有这等现象,现在经谢五娘一提,这才(炫)恍(书)然(网)大悟,连忙红着脸道:“弟子果然一时大意,这却如何是好咧,还望老前辈指点才好,要不然死却无妨,如果落上一个残疾,那便真受不了咧。”
羹尧中凤也一齐道:“既然老前辈有法可治,还望从速说明才好,否则不但小香姐难受,使我们也内疚终身了。”
谢五娘笑道:“说来也是缘,我足迹不离太湖已经多年,想不到此次北来,忽然遇上这位姑娘,这引气归元之法,并不太难,只我恩师朗月大师昔年曾有此系‘道家丹诀,非人莫传’之戒,姑娘能守我门中戒律吗?如果愿意,我这老婆子自当将本门心法倾囊相赠,否则也可由我推行气血过宫,也是一样,这个我却不愿强人所难咧。”
小香慌忙叩拜在地道:“如蒙老前辈不弃,肯以心法传授,弟子自当恪遵戒律,焉有不愿之理。”
谢五娘一面扶着,一面又笑道:“我这戒律看去极易遵守,不过其中一条却与寻常宗派不同,你还须三思才好。”
说着引向室外附耳数语,然后又正色道:“你能守得吗?”
小香毅然道:“弟子守得,如有一念破戒,但凭处置。”
说罢,便又就地拜了下去道:“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这次谢五娘却不再扶,等小香拜罢方道:“本门一切心法与誓言戒律并重,除上对师尊下对弟子而外,决不许轻泄,便属家人父子同门姐妹,也不能相告,否则便算违戒,此点还须记牢。”
说着又笑道:“本来我只打算在将那年二公子内伤治好,便行南归,既收下你这个徒弟,那便不得不随你西行一段路程,等你将本门心法学会再行回去了。”
说罢又相携入室向羹尧笑道:“二公子但放宽心,如今这马姑娘,已经算是我的门人,她这口运岔的真气,自有我来设法复原,至于你只将我那归元散服下,依言行功也便无碍,明日便可登程,不过我须随行一段路,等她将本门心法学会,方可回去,沿途打尖歇宿,还望另借净室一间,这使得吗?”
羹尧忙道:“老前辈说哪里话来,既蒙枉顾随行自当侍奉,何况马姐已拜在门下,又蒙赐药加惠咧。”
接着又笑道:“老前辈如果江南无什么要事,何妨一同入川小住,一览峨眉青城之胜,弟子也好随时恭请教益,那不更好吗?”
谢五娘略一沉吟又笑道:“那也再看罢,天下事无非一个缘法,时至则缘生,缘尽则身退,这便连我也做不得主咧。”
接着,亲取玉瓶,索过一张净纸,倾好一服归元散,命羹尧服下,将瓶交中凤收好,看看小香道:“你住在哪一间屋子里,我先传你这引火归元要诀将真气调摄还元好吗?”
小香忙道:“我便住在对面房里,恩师请随我来便了。”
说罢便向羹尧中凤告辞,将五娘请入西间,又拜了下去,五娘扶着笑道:“适才已经拜过,无须再如此,我先传你本门吐纳功夫和导引要诀便了。”
说着,一面密传要诀,又用推血过宫之法,将那一口运岔的真气复元,一面愀然道:
“我本烟花贱质,自幼即身陷娼门,幸而得遇恩师,授以本门心法,和武技剑诀,虽然游戏风尘,此身尚保清白,这十年来只有情关难勘,和始终未忘报国,如今昔年旧侣,业已先我西归,所剩下的,只差未见日月重光,其他人间恩怨,久已与我无关,但我那恩师,因系辽东人氏,曾有遗命,一旦王师北指,收复故土,必须设灵祭告,如今却想不到我已鸡皮鹤发,这大好河山还在满人手中,眼见此愿,已是难偿,你既传我这点末技,他日还须代了此愿才好。”
小香忙道:“恩师放心,弟子身世也极惨痛,此番随年二爷和云姐西行,便也打算一省祖宗邱墓,并谋驱除鞑虏,复我河山,既师祖有此遗言,他日得偿夙愿必随恩师之后设灵祭告,以慰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五娘慨然道:“你那身世我已略知一二,老实说,不因为你是这样一个出身,资质心地又均极可取,我还不急急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咧。”
接着又道:“你知道这西行不易,来日大难吗?”
小香悄声道:“难道恩师已经得讯,除那侯威之外,还另有能手不成?”
五娘道:“侯威和那毕五不过算是第一批而已,如今那几个鞑王对年二公子全看成雍王允祯的左右手,深知此番入川必有布置,以为夺嫡张本,纷纷派出人来,沿途邀截,如果得手便作盗劫被戕具报咧。”
小香道:“这个弟子已经知道,昨夜那毕五便说奉了八王允搪之命而来,恩师怎么会知道,是另外还有消息吗?”
五娘道:“你先别嚷,我也是前几天无意中,在邯郸一家旅店之内听见两个江湖女人互相谈说才知道,不但八王六王派了人出来,便连十四王爷也派有人跟了下来,除秦岭群贼而外,竟还打算激动天山派出面为难,此外又四出约人,秦岭群贼无妨,那天山派却难缠,何况此外又不知道他们约的是谁咧。”
接着又道:“目前那年二公子还不宜多劳,你且先别提,最好等天黑以后再告诉他,方可无碍。”
说罢便令盘膝趺坐行功不提。在另一方面,羹尧服药之后,到了薄暮,除了伤处仍然一片青紫而外,果然行动自如精神也好得多,那北京城里,却赶下两起人来,这第一起是何松林,一身劲装活像一个镖行趟子手,一进店门闻得中途出事,羹尧受伤,便大惊失色,直趋东跨院求见,匆匆一问经过,不由顿足道:“周师叔正因闻得各鞑王有派人暗中行刺消息,诚恐侯威老贼鬼手阴毒,贤弟疏于防范,特命我连夜赶来送信,却想不到你已遭毒手,如非马师妹随行,又有谢老前辈在此,那便真险得很,如今事虽过去,但允祀允搪兄弟贼心不死,前途还难免有伏击,你还须格外当心才好。”
羹尧正问详细情形,接着张杰也奉雍王和云霄之命飞马赶来,并携了雍王一封长函投递,羹尧一看,除诸王所派出的人竟有四五起之多,最奇的是侯威毕五竟是最后一起,前数起全未露面,方一沉吟,那张杰又请安道:“除王爷亲笔书信而外,那李大奶奶也有信给姑爷和姑奶奶,这是由李大姑娘面交小人的。”
说着又掏出一张油纸包好的信件呈上,这时不但中凤和小香全在场,便天雄和周再兴也都在一旁,羹尧再看那信,除问候而外,却说明程子云也在羹尧动身之后匹马出京,虽然不知何往,但事前曾向六八两王府商谈,并说近日因为翠娘一去不归,辞行之际又故意在权贵之前露出行藏,程子云对自己更加起疑,所做诸事竟避不与闻,一切还望加意防范,以免暗算等语,不由笑道:“照这么一说,那嵩山毕五的话又靠不住了。”
天雄忙道:“昨夜我原说过,这厮品格不高,您怎么竟会信之不疑,须知他虽说得极其光棍,却未必尽然咧,既有程子云从中作祟,我猜这一切布置也许就是那怪物主谋亦未可知。”
张杰又向中凤道:“姑奶奶对我们在这一带的人还须切实整顿一下才好,这次事情出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已是丢人,他们事前事后竟一点也查不出头绪来,显见老少几位山主和您一走,简直吃粮不管事咧,方才小人已经问过他们,姑老爷和您虽然已经严饬查明来的贼人下落,他们却一无所知,还要这些人有什么用处。”
中凤秀眉微耸道:“这倒不能全怪他们,来的本来全是老江湖,哪会有形迹落在他们眼中,不过此风不可长,如今就着你在此间稍住上两天,严加整顿,回去再向老山主禀明处置便了。”
接着天雄也道:“便我们派驻此地的那队血滴子,也不一定得力,尤其是那个领队,方才据报他已到李飞龙故居、张桂香前开小店去过,不但未见毕五鲍玉两人,竟连这两人是否去过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下去,不也直等虚设吗?”
羹尧略一沉吟道:“此事本应严惩,但那毕五的话既不可靠,也许他们根本就未住在那地方亦未可知,不妨也由张提调查明,就地切实整顿便了。”
正说着,忽见谢五娘掀帘而入道:“本来我因恐二公子重伤新愈,不宜多所劳虑,所以还有些话未说,如今京中既已专人前来,公子体力也早已复原,便不妨咧。”
说着,忙也将在邯郸旅店,无心听见两个江湖女人所谈说了。
中凤一问那两个女人面目,五娘道:“这两个女人一个一身重孝,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长长一个脸,倒长得极俊,另一个年纪也才二十出头,长得也不错,只是鼻子上贴着老大一张膏药,说话却不十分清楚,看去不是被人将鼻子削去受了重伤,便是染上恶疾,诸位知道这两人来历吗?”
中凤道:“如依老前辈所说年貌,这两人那穿孝的必是李元豹之妻林琼仙,那鼻子上贴膏药的,显然是被鱼师姐削去鼻子的余媚珠无疑,这二人如果打算弄鬼那倒怕不了她,不过她们如向天山搬弄是非,却也可虑,好在那闻天声我们对他过节还不算错,此事还须烦何师兄,赶紧回京着他自己说明才好。”
小香笑道:“这事也怕不了他,不但那小道士活口具在,便我对丁真人也可当面说明,他们打算挑拨是非,那是枉然。”
五娘笑道:“我倒忘了,那天山派和你姑父的渊源,既如此说,那便又少一层顾虑咧。”
说着又道:“除了天山派下诸长老而外,其余群贼虽不足虑,但他们既然四出邀约能手,夜长难免梦多,那秦岭老巢一关,尤其讨厌,公子伤势既愈,还宜速行,此地却不宜久呆咧。”
羹尧点头,忙命张杰处理当地各事,一面写好两封回信,分致雍王和各尊长,等张杰出去之后,又细问京中情形,留何松林一同用晚饭。第二天打发了二人之后,便又登程赶路。
这一路更是小心翼翼日夜提防意外,连邯郸也未多留,谁知始终并未见动静,只晓行夜宿,不免辛劳而已,众人不由倒反奇怪。这天已经将近宝鸡,仍无所见,羹尧在马上方笑说:
“这些贼奴既以秦岭为号召,该到老巢已久,为何却不见露面,难道因为侯威老贼未能将我置之死地,便已胆寒不敢再来吗?那倒算是便宜他们咧。”
费虎跟在马后忙道:“二爷有所不知,那贼人老巢,名在秦岭,实际却在甘肃和川陕交界的深山之中,为的是那地方三不管,才易藏身,一过宝鸡各地才有他们下的卡子,在这一带也许是不会露面的。”
正说着,忽见一匹青鬃马,从驿路上疾驰而来,那马上端坐一个三十上下的精壮汉子,上身敞披青绸大衫,下面青绸丢档马裤,足下薄底快靴,一手控马,一手扬鞭,背后却斜插着一口单刀,一望而知便是一个武行朋友,一见车仗人马,不由注视一下,哈哈一笑,横鞭马头,勒住缰绳道:“来的是新任四川学政年大人吗?我们掌门孟老太太候驾已久,想不到今日才到此处,这里现有名帖一张你且接了。”
说着猛一伸手,飞来一张大红帖子。
羹尧正待伸手来接,那费虎却一拍马股大喝道:“黄蜂洪五,竟敢用吹针行刺,这一来,你就死得快咧。”
那马一下冲出丈余,日光之下,果见随着红帖有三根蓝莹莹的毒针飞落,那马上汉子,一见费虎,忙又喝道:“原来你这小鬼竟敢吃里扒外,投了姓年的,你且不要慌,一到褒城就有你的乐子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