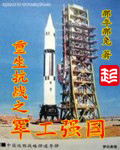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白骨精-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萧昂话一出口,白饶两只眼睛瞪得跟球那么大,猛地吞了一口口水,用手指了指白顾靖,又指了指萧姗,苦笑两下。
“怎么,白将军,萧某说得不是嘛?”
“哪里哪里,萧相爷言之有理。顾靖,你不能太放纵,知道吗?”
白顾靖无奈的回应,天地良心,白顾靖是抱过萧姗,搂过萧姗,亲过萧姗,可是那事儿,绝对没做过。这又是不能解释的事情,萧姗的病因,早晚会水落石出。
“嗯,白将军果然是我朝大将,甚明事理。昨天顾靖来我府上,还说姗儿是中毒了,萧某与外甥都很惊讶。今日一见,便知这毒,就是顾靖你自己啊。”
萧昂越说越离谱,白顾靖想要辩解,被白饶给生生瞪回去了。倒是萧姗,羞得桃花一样,微嗔,“爹,您说什么呢?”
“爹说的不对吗?你表哥夏威,陪着顾靖,还到你房里去找什么毒物了呢。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便不再说了。萧某还有事,白将军,萧某就此告辞。”
白饶送萧昂去了,留白顾靖和小桃照顾萧姗。等两位老人走远了,白顾靖便找了一张凳子,坐下来。方才萧姗听到夏威名字的时候,眼睛都亮了,只是那一下,就隔得白顾靖心疼。白顾靖自问,从几时开始,心眼竟是也跟着缩水了呢。
小桃不懂白顾靖的心思,凑到萧姗旁边,聊起关于夏威的事情。
“小姐,表少爷人真好,您不在府里的这段日子,表少爷经常到府里去,陪着老爷下棋,对诗,聊天。”
“嗯,表哥一向心细,这段日子也是亏得有他陪着爹……”
“噹”,白顾靖用力将茶盏蹲到桌子上,常舒一口气,提起笔,愣是半天没有下笔,心口堵着一块大石头,越听萧姗夸耀夏威,心里越不是滋味。白顾靖深知,自己是女人,萧姗也是女人,而且是个封建保守的女人,要让她突破那层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如果是直人,最好不要掰弯她……这话不是白顾靖说的,是她在看某个剧的梗概的时候看到的。
小桃冷了一下,自当是杯子没有放好,继续与萧姗谈论夏威,“小姐,说来也奇怪,您都已经和姑爷成亲了,表少爷还未娶亲。您说像表少爷那样的谦谦君子,长相俊朗,一表人才,怎么就没有说得一门亲事呢?”
萧姗听着小桃说着,眼睛看向桌边的白顾靖,就见紧握着的笔杆,颤抖两下,跟着在宣纸上,写画着什么。夏威不婚的原因,在于萧姗。自小定的娃娃亲,萧姗与夏威都已在两家人心里,成了那种关系。特别是萧姗母亲去世以后,夏家人对萧姗更是关爱有加,夏威对萧姗也是疼爱非常。圣上赐婚的时候,萧姗自知如若成亲,便将辜负夏威,然如若拒绝赐婚,虽可与夏威一起,却是要影响父亲的仕途与生活,甚至连累整个萧家。权衡后,萧姗终是选择了接受,即便对方是那个混世小魔王。
萧姗对夏威是有愧的。现在夏威又代萧姗,照顾萧昂,陪伴萧昂,亦是代萧姗尽孝道。萧姗如何不去感激夏威,如何不去增加心中的愧疚。然而,萧姗也知道,她是白顾靖的妻子,只此一生,便是白顾靖的人,心中纵然有对夏威的愧疚和感激,要偿还,也不单单是作为萧姗自己,更多的是要用白顾靖之妻的身份,来回馈。
白顾靖的举动,出卖了白顾靖的情绪,萧姗叫小桃去帮自己取煎服的药,将小桃支开。扶着床边,莲步微移,才走了五步,额头就已经沁出汗来,萧姗咬着牙,心里翻腾的难受。
白顾靖听着身后有动静,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想要回头,又忍住不看,手上毛笔,提起落下,也没法继续往下好好的誊抄,放下笔,转过身,就见萧姗低着头,抱着膝盖,蹲在地上。白顾靖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抱起萧姗,蹙着眉,摇了摇头,有些生气,却是极温柔的说道,“才好,就乱动。谁让你下床的!”
萧姗难受,看着白顾靖偶有的凶煞眼神,抿着唇。不知是什么时候,白顾靖掉落了一根头发,粘在衣领处,萧姗小心的抬手,捏起那根青丝,却是无力放下。
白顾靖将萧姗放到床上,替她拖下鞋子,盖好被子。
“姗儿,你是大家闺秀,平日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我白府,吃住与我一般,在萧府,也随萧相爷一起。旁人未能近你身,你嫁来我白府,便开始有呕吐昏迷迹象。郎中断言,你这是中毒之相,然毒从口入,你可曾记得误食过什么,或是有过什么异样?”
萧姗眼神闪烁,白顾靖眯了眯眼睛,将这一幕恰巧捕捉。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
☆、说·情
书上记载,将几味药材研磨成粉末,加蜜搅拌,成黑褐色,待混合充分,用手揉捏成丸状,味香稍苦,有毒。少量误食,脾胃胀气,头晕口干;过量食用,可致命。此毒性慢,连续多日,少量服用,毒性将在体内沉淀聚积,亦如过量食用之效果。若少量误食,克服用绿豆清汤解毒,或扣喉将毒物呕出……
萧姗的血液中,正是混着这种毒汁,在她的身体里,循环往复的流转着。那是一种有色有味有形的毒药,再马虎的投毒人也不会使用的毒药。就是这样的一种毒,在萧姗体内,使她疼痛,使她昏迷,使她不断的损耗精元,毫无力气。
“没有什么异常。”萧姗回应着,窝在白顾靖怀里,体会着温暖,如此她的心才能得到一些安宁,看着白顾靖的眼睛,弯弯的眯了眯,“靖儿,不高兴了。”
萧姗一语中的,白顾靖愣了愣,听着那声靖儿,有些恍惚。那一句靖儿,唤得轻柔,那一句不高兴了,似是有些慰藉。一颗炽热红心,微微收缩,拧动着,似痒似痛,复杂的心绪,难宁。
“爹爹,他有嘴无心的。你别往心里去。”萧姗说。
白顾靖望望萧姗,不作答。她哪里是为了岳父的几句话不悦,她那是因为吃了夏威的生醋,酸过了头。
见白顾靖不说话,萧姗眨眨眼睛,笑着讲起故事。
“靖儿,你别和爹爹计较。爹爹只是太紧张我了。记得有一次,表哥带我到池塘看小鱼,有条鱼不知怎么着,肚皮朝天,表哥说那鱼死了,我听了哭起来。爹爹来寻我们,见着我泪流满面,便教训表哥。表哥就这么吃了哑巴亏。”
萧姗的笑话,听在白顾靖的耳朵里,不是欢乐,反倒是一种悲伤。眼帘轻垂,白顾靖向外撤了撤,让萧姗躺好,为她盖好被子。说了一句,“别说话了,不舒服,就好好休息。”
白顾靖的情绪有些低,夏威的名字或是明显的,或是隐晦的,反反复复出现,那种感觉糟糕透了。先前在公司的时候,就算是在厉害的竞争对手,白顾靖也没有感到过厌恶,唯有这一次,感觉很不一样。或许,白顾靖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亦或者,白顾靖太过尊重萧姗,甚至有些违背自己的心意。
萧姗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从白顾靖的香怀里,重新躺到梆硬的床板上,看着白顾靖的方向,继续说。
“娘离开我们以后,爹爹的脾气,就不若以前温和了,”萧姗的声音有些哽咽,母亲是一道伤,在心里的疤还未结痂,能不触碰,就不去碰,像是今天这样自己解开伤口,也唯有对着白顾靖才会有吧,顾靖说过,不可以隐瞒心思,然而靖儿自己却违背了这规则,“爹很爱我娘,爹总是在书房看着母亲的自画像发呆,有时候也会偷偷落泪。有一次,我和表哥玩捉迷藏,不小心打翻了一盏茶,将爹爹藏在抽屉里的画浸湿了,画像模糊得再看不清模样。那时候,我很害怕,我怕爹爹会生气,会伤心,不敢告诉爹爹。害怕的大哭起来,爹闻声赶来,看我坐在地上哭,忙着把我抱在怀里,一边替我擦眼泪,一边安慰我,问我为什么哭,是磕着了,还是碰着了,还是有人欺负我。我摇着头,哭得更凶,我知道那是母亲唯一留下的画像,除此便再无其他。我指着画像,泣不成声。父亲抱着我,笑着看着我,眼睛里也有泪光闪烁,他说那是天意,是母亲想要爹爹照顾好我,不叫他再与过往纠缠。我信以为真,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怕我哭坏身子的说辞。父亲请修画的工匠到府里看过那幅画,工匠们都束手无策。纸上一幅画,浸了水,颜色都晕开了,如何还能恢复呢。父亲便趁我晚上睡熟,一个人到书房,凭着记忆,画着母亲的画像。没有一次能够画好的,爹却从不放弃。从那以后,如果我受伤了,或者落泪了,父亲便会想起那副画来。爹,这一生不容易。”
萧姗的声音,轻柔好听,带着感情的讲述,眼神氤氲,声音也有些呜咽。白顾靖仿佛见到一个哭泣的小女孩,面前有一张墨迹斑驳的画卷,一个英朗男子进来,抱起小孩子,轻轻的顺着她的背,看着那幅画卷,眼中是说不出的遗憾和伤感。
“知道爹不容易,你还招惹他老人家,”白顾靖轻轻的刮了刮萧姗的鼻尖,眼中带笑,“我没有不高兴,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透,过会就好了,没事。”
“是,表哥吗?”萧姗说,一双水润的黑晶石眸子望着,敏感如萧姗,她到底还是了解白顾靖的,从他微动的红唇就可以知晓,那件想不通透的事情,便是夏威无疑了。
“爹是朝中重臣,平日公务繁忙,在府里就我一个小主人。起初,家丁都还算本分,爹爹上朝的时间,他们也勤勤恳恳的工作,对我也是尊敬的。日子久了,爹仍旧一个人,忙着公务,很少照顾到我,府里的家丁,有了小心思。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便不再勤奋,有的还欺负我,说我是没娘的孩子……”说道这的时候,萧姗顿了顿,抿抿唇,接着说,“我很难过,回到房里就哭,等到父亲回来的时候,也不敢对父亲说,怕父亲生气,更怕父亲伤心。那时候小桃已经陪在我身边了,家丁说的话,小桃都记得。父亲见我眼睛红肿,问我是否受了委屈,我不说,父亲就又问小桃。小桃小,如实对父亲说了。父亲雷霆大怒,当即叫王伯将家丁如数召集到院子里,叫小桃指认欺负我的人。当天便将那几个家丁轰出萧府,爹担心我再受欺负,便将我送至外婆家。表哥就是在外婆家见到的,表哥的娘与我娘是同胞姐妹,知道我娘去世了,便视我如己处。还叫表哥待我如妹妹般,好好照顾。我自小就跟在表哥后面,与表哥一同习字读书。父亲请表哥来我家作伴,父亲不在的时候,就是表哥陪着我,读书写字玩耍。在母亲诞下我的时候,姨娘便与我娘商议着,订上一门娃娃亲。”
萧姗将与夏威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对白顾靖讲了。白顾靖听得仔细,这样的青梅竹马,果真显得自己倒像是外来户一样,横刀夺人所爱了。
“你与我说这些作甚,与我又不相干。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才刚好,要多休息。”
萧姗噗嗤一笑,那人口是心非的模样,竟也可以这般正经,“靖儿是个明事理的人,别在烦闷了。”
白顾靖抱着臂,看着人精一样的萧姗,这人倒是尤物,挑不出半点毛病来,“说得轻巧,姗儿还是好好想想,是何物之毒才好,早解早好。我不再这守着你俩,等下叫小桃陪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在这,你反倒休息不好。”
“去哪?”经历了几日昏迷,萧姗越加珍惜与白顾靖在一起的时间,待一天少一天,见一面便少一面。
白顾靖念起刺客的说辞,这个若兰还是得见上一面,这个若兰似乎对白顾靖有着不小的影响,她到底在白顾靖的圈子里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还需要在一探究竟,“有个朋友约了见面,约了几次都没见,今天再不去,情理上也说不过去,我便去会一会。你好生休息。”
白顾靖让白福叫小桃来陪着萧姗,自己带着白福,一同出门去了。萧姗的眼中,掠过一丝灰色,无人能懂。
☆、心事
“小姐,您不告诉姑爷吗?”
萧姗摇摇头,看着那扇打开的窗,一片蔚蓝的天空,一树泛黄的叶子,随着风摇摇欲坠。
“让他担心吗?还是不要了。按着我写的方子去抓药,回来吃上几次就好了。”萧姗说着放下笔,将一张写好的药方,折好交给小桃。
小桃接过方子,犹豫着看着萧姗,“小姐,这行吗?”
“有何不可?莫不是你不相信我的医术?”
“小桃不敢。只是这性命有关……小姐还是谨慎些的好。”
“我自有分寸,你且去抓药吧。”
小桃自知说不过萧姗,虽是不情愿,也只好将那方子收进袖口,跟着拿了银子,去药铺捉药。见小桃出了门,萧姗长吁,眼角也跟着往下垂了垂。已经昏厥两回,这次时间较长,昏迷间意识迷离,却是见到母亲身影。母亲还若当年那般年轻,漂亮,微微笑着看着自己的方向,母亲没有说话,只是远远的站在桌边,看着自己的方向,萧姗想要下床去与母亲说说话,还不待靠近,母亲就朝着自己的方向摆手,跟着离开房间。跟着听到白顾靖和那女人的对话,萧姗睁开眼睛,母亲早已不再。那种感觉似幻非幻,萧姗是相信轮回转世,鬼神之说的,那或许是母亲的魂或魄,萧姗如是想。
萧姗又一次想起母亲离开时的场景,那一幕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这么沉淀到心底,也会像是这般被重新提起,重现脑海。萧姗清楚的记得,那时候自己只有几岁大,那天天气很好,天很蓝,云很白,母亲第一次答应父亲,一家三口,到郊外去游山玩水,父亲还特意带着自己到书房扎风筝。蝴蝶样式的风筝,父亲手巧,做得很快,母亲在一旁为父亲递工具,调颜色,两个人一起为那只风筝上色,父亲抱着自己,有母亲送上一只笔,为蝴蝶画上黑色的眼睛。那天萧姗很开心,像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母亲蹭蹭萧姗的脸颊,告诉萧姗,不要太骄傲,要做水一样的女子,那样最美。
那时候萧昂已经身居要职,具体的职务,萧姗已经不记得了。家丁将这一家三口送出城门,萧昂就让家丁先回去了,自己赶着马车,带着妻儿一同往外走。萧昂已经有些念头,没有好好的陪陪这对母女了,特别是妻子夏静。萧姗的性子,像夏静的地方多一些,温柔少言,一双水一样的眸子,总是笑盈盈的。城外的树木更高更密,少有人声,多得是鸟雀鸣叫,还有些见识不到的野草野花,那花开得很灿烂,颜色也很鲜艳。夏静折下一朵花儿,别再萧姗耳边,母女俩相视而笑,萧姗的笑声像是一串银铃,清脆好听,夏静的笑恬静温和。
儿时的萧姗,一样有着别人家孩子的童真,也会撒娇,一样活泼,偶尔调皮。萧姗缠着萧昂放风筝,想要看到那只漂亮的蝴蝶,在天上翩翩飞舞的样子,萧昂敌不过小萧姗的要求,无奈的摇头,看着夏静幸福的笑。萧昂叫萧姗扶着蝴蝶翅膀,站在原地不要动,自己扯着风筝线,到远处去,等到风筝线绷紧,萧昂叫萧姗送了手,又跑了两步,将蝴蝶带起来。小萧姗见着风筝飞起来了,开心的笑着,追着萧昂的步子往前跑。父女俩人开心的笑着跑着,夏静守着马车,看着他们,脸上带着笑。
“再高点,再高点,爹爹,哎呀,”只顾着看着风筝往前跑的小女孩,没有注意到脚下凸起的树根,一下子被绊倒,跪倒地上,磕破了双膝,还有额头。
夏静忙着跑过来,萧昂仍旧按着女儿的要求放着风筝,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事情。夏静抱起萧姗,蹲下来,为女儿掸去身上的土,手帕在萧姗额头轻轻的擦了擦。
“我的好闺女,娘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夏静当真对着萧姗的额头,轻轻的吹了两下。
也不知道是心里作用,还真是吹的作用,疼痛的感觉,渐渐弱了下来,几乎也不怎么疼了。萧姗窝在母亲怀里,不再往前走,抬头看着飞得更高的风筝。萧昂看不到女儿,有些着急的唤着萧姗的名字。窝在母亲怀里的萧姗,舍不得离开母亲的怀抱,又不想失去与父亲一同放风筝的喜悦,就要母亲抱着自己往父亲的方向去。
夏静笑着抱着萧姗往前走,萧姗觉得夏静走的慢,半路就要求下来,自己往前跑。还不待萧姗跑到萧昂身边,父女两个就被夏静叫了回去。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母亲,或许就已经察觉到什么了吧。说好的一日之游,变成半天的休闲。萧昂收了风筝,还未尽兴的萧姗嘟着嘴,夏静抱着萧姗坐进车里。
萧姗清楚的记得,母亲对父亲说,官场如战场,万事还要多加小心。当天下午,萧姗像往常一样,被父亲要求在书房里习字,父亲一个人在院子里为花草浇水。听得嗖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飞进院子里,跟着就听到托盘与茶碗摔倒地上的声音,萧姗跑出来,就见着父亲怀里抱着母亲,母亲的身体被一只长箭刺穿胸膛,身前一片鲜红。父亲叫着母亲的名字,眼里满是泪水。萧姗跑出来,哭着喊娘,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见着母亲流血了,就学着母亲的样子,在那伤口吹了吹,哭着说,“娘,姗儿给娘吹吹,吹吹就不疼了。”
夏静疼得脸色惨白,嘴唇也跟着紫起来,即便是这样,仍旧努力得弯弯嘴角,摸摸萧姗的头,微微开口,气息却再不连贯,“姗儿乖。要听爹爹的话,娘不能陪再姗儿身边,看着姗儿长大嫁人,姗儿……答应娘,不要怪娘……好不好?”
“姗儿不要,姗儿不要,姗儿要娘陪着姗儿,姗儿不要娘不在姗儿身边。”
一颗泪划过面颊,夏静的身子已经有些微凉,她用尽最后力气,吻了吻萧昂,“新愁旧怨,如此作罢。此生夏静亏欠萧郎的,一笔勾销。”一只手垂落,夏静眼帘轻垂……
念至此处,不自觉的泪如雨下,萧姗像是个泪人儿一样。唯一能够睹物思人的画卷,也为自己年幼无知,毁掉了。萧姗清楚的记得,有个算命先生,说自己是克父母克夫君的硬命,就是因着如此命运,才使得夏静遭遇不测,萧昂久病缠身。萧昂叫人把那算命的先生轰了出去,又哄着萧姗叫她不要多想。萧姗嘴上答应,心里有了自己的主意。当皇帝赐婚,萧昂再受牵连的时候,萧姗便又坚定了那想法。不愿再连累任何人,她要用无人察觉,不被责备的方式,选择自己的去留。
白顾靖离开府上,就到那处熟悉又陌生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