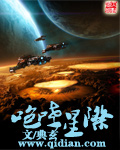星际战舰玛洛斯号-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段子。有人说伊斯特玩世不恭,而孔真觉得恰恰相反,伊斯特绝对是极为严肃认真、全身心投入地,把生活当成笑话来过。
伊斯特抱大腿不成,看孔真的神色却仍是殷殷切切,“阿真,你还恼不恼?”
孔真叹口气,“你为了和我讲道理,不惜把你自己和司徒的形象毁成了渣——”
“我们本来就是很渣的……”
“——你别打岔。……你下这么大力气讲给我的道理,我若是再听不进去,就当真是榆木脑袋了,食古不化了。
“我也想明白了——你想告诉我的是,每一对爱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相处之道,人们不应该按照既定俗成的道德标准,来对他们的相处方式横加评判;而在处理自身的情感问题时,应该把彼此之间感情的稳定和长远放在第一位,而不应该生活在外人批判的眼光之中,对吗?”
粗人兵痞伊斯特望着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博士生,表情又是艳羡,又是自惭。
“有文化真好呀。”伊斯特喃喃,“我脑中这团猥琐的浆糊,竟也可以被你说得这么有逻辑条理,这么有学院范儿。——孔教授,我被励志了,我也要读书!”
孔真推了敲了她一记,学着伊斯特的英国口音背起台词来,“以下是梅弗儿小姐说的原话:‘所谓‘唯一的心灵伴侣’一说,纯属虚构。 一个人对伴侣的爱,其实上是人类本能之中,对异性的生理需求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因为对伴侣一对一的承诺,而压抑了其它异性对自己产生的吸引,这实际上是压抑了人类爱的本能——如果爱的本能整体上被压抑了,那么对伴侣的爱,自然也会消减。’——梅,说老实话,我那些学人类学的同事,都不见得比你讲得更一针见血。”
伊斯特红了脸,吐吐舌头,“其实也不是人人都是我说的这种渣人。——世上有未进化完全的野蛮人,比如我,比如阿晋;也有进化得好一些的文明人,比如阿真你,比如元亨。野蛮人和野蛮人在一起,可以用野蛮的方式过得很好;而文明人和文明人在一起,可以用文明的方式过得很好。世界上的最大的悲剧,不在于有野蛮人和文明人之分,而在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搞在了一起。”
孔真扑哧一声,“看来我和元亨就是野蛮人和文明人搞在一起的悲剧。”
伊斯特也乐,“你说元亨野蛮,我代表我和阿晋表示反对。——当年上学的时候,那可是他谢大圣人每天都试图用锋利的眼神杀死我们这两个可耻的流氓。——不是我替他说话,他这次真是老实人一时糊涂。看在他认罪态度端正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好不好?”
孔真哼了一声。
伊斯特搂着闺蜜的肩膀,“对,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你到我那里去住几天,他若是不拿八抬大轿来抬,你就绝不回去。咱们得给他点教训,让他以后绝不敢再犯。”
孔真一脸阴狠地点头。
******
19:30。十九层甲板,飞行员住宿区。
离开图书馆回到宿舍,泥猴子伊斯特就被孔真一脚踢去洗澡。洗完澡出来,伊斯特说一起去唐人街吃饭吧,孔真却说不饿,提议伊斯特不如自己去卡玛卡尔餐吧的光棍节趴踢玩玩,顺便也弄点免费的吃的。
伊斯特早过了趴踢狂欢的年纪,但想到近来自己被软禁的传言,再加上洛曼诺的一再邀约,还是觉得去露个脸为好。——今天上演的狗血戏码太多,伊斯特也实在觉得应该喝杯酒,压压惊。
换上在军校常穿的那件正面印着“教官来了”,背面印着“教官走了”的旧T恤,伊斯特扭扭达达出了门,坐电梯下到地四十九层甲板。
卡玛卡尔餐吧里光影交错,人声鼎沸。虽然眼睛还没适应幽暗的光线,伊斯特却隐约看见前来趴踢的光棍们一个个衣装笔挺,竟都穿了最为正式的军礼服。穿着破T恤牛仔裤的伊斯特正一边感叹着现在的年轻人果然重口,一边准备直接转身遁走,却听身边响起一阵“教官来了”“教官来了”的喊声,紧接着她就被一束追光直直罩住。
伊斯特呆呆立在当地。原本喧闹的酒吧,此时竟一片安静。
伊斯特估摸着这又是对着装错误的土货的恶作剧,摸摸鼻子,正要说句撑场面的话,却见灯火忽然大亮,在掀破房顶的欢呼声中,五颜六色的彩带花片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撒向伊斯特,而在餐吧中央的半空中,一条大横幅徐徐展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梅弗儿?伊斯特:从军十二年,辉煌十二载。”
十二年前的今天,公元2948年11月11日,正是她从西点军校不光荣地延期毕业,勉强加入合众国海军的日子。
伊斯特目光略略向四周一扫,看见此时聚在卡玛卡尔餐吧的人中,一大半都是在几年来从她手下毕业的军校学生,而剩下的人,也多半是熟脸。在上百号人的欢呼和祝贺声中,军装笔挺的阿莱索?洛曼诺越众而出。高大英俊的金发通讯官手托一块圆圆白白的奶油蛋糕,上面数字“12”形状的蜡烛,火光摇曳。
洛曼诺将蛋糕托到伊斯特面前。伊斯特乖顺地吹灭蜡烛,众人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洛曼诺低头望着伊斯特,目光真挚地向她道恭喜。伊斯特心中感动,正要微笑道谢,却见洛曼诺飞快地拔下蜡烛,毫不犹豫地把蛋糕完完整整地扣在了伊斯特的脸上。
众人的哄笑鼓掌声,又一次掀翻了卡玛卡尔餐吧的顶棚。
☆、旧影
11月11日。
20:00。
卡玛卡尔酒吧,光棍节+伊斯特入伍十二周年庆祝会进行中。
伊斯特把糊在脸上的蛋糕抠下来的时候,参加庆祝的人群已自发在场地中间让出一片十数平方尺大小的空场。随着酒吧里灯光重又变得昏暗,在这片空场上播映的全息图景变得逐渐清晰。
首先放映的那张全息照片,是辽阔荒芜的西非大草原。一架型号极为老旧的军用直升机前,十数名身着脏兮兮野战军服的大兵在飞机前面勾肩搭背、龇牙咧嘴地合影。数尺之外,孤零零站着一个穿飞行夹克的细巧身影。照片里的伊斯特,一头黑色短发在风中飞扬凌乱,模样年轻得令人不可置信。然而相比于照片中其他人轻松惬意的神态,伊斯特那瞪大了的眼睛和微颦的眉峰,却约略显出这个年轻飞行员心中的无措与张皇。照片上标注的日期,是十二年前。
几秒之后画面一转,又成了穹顶林立的中亚风情。仍是十几个人同老旧飞机的大合影,这一次伊斯特却没有孤立于人群之外。她仍穿着飞行服,脖子上却围了一条极具异域风情的大围巾。此时她的头发已经留长,唇边抿着一痕笑容,神情平淡自若,气色却比上一张显得病态苍白。照片上的日期,是十一年前。
画面再一变,却又成了葱翠茂密的南美热带雨林。照片显然是拍于炎夏,照片里的几位军人似乎在进行午间休整。照片的一侧,伊斯特穿着一件汗湿了的白背心,头发清凉地束在脑后,颈上却累赘地系了一条颈巾。她斜倚着一棵榕树,神色轻松,正和一位高大的金发军官笑谈。那军官额头饱满,鼻梁挺直,面部线条如希腊雕塑般精致完美。照片上的日期,是十年前。
在这帧图像放出的时候,酒吧里的人群一阵私语,
“那是威廉?罗斯托!”
“那个年入百万的退役军官、畅销书作家?”
“他那时候看起来好年轻。”
“嘿,原来他年轻时候鼻子不是歪的……”
随着下一张图片的放映,酒吧里的私语声才渐渐减弱。这张照片拍摄于黑沉沉的地下矿区,站在一排黝黑强壮的矿工中间,身穿高领工作服的伊斯特显得更加纤细。照片里的伊斯特咧着嘴无忧地笑,脸上黑漆漆的煤灰,更显得她两排牙齿白得吓人。照片上的日期,是九年前。
随后放映的,却是一段DV,上面显示的日期是七年之前。从画面上看,DV的主人一边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一边解说,一边试图把每一个人都纳入镜头,
“大家看到的是拉格朗日号远洋科考船公元2952年万圣节化妆舞会实况!我是力学实验室的麦克雷博士,我今天扮装的是牛顿!……这是爱因斯坦,由谢国辉院士扮装!洛伦兹,由派瑞教授扮装!普朗克,由何家华教授扮装!”
面对镜头,被点到的大科学家们拘谨地招手微笑。却见镜头一转,捕捉到了一个烈焰红唇、身着白色复古高腰裙的俏丽身影。女郎风骚地向镜头献出飞吻,接着妖娆地走到空调出风口前,摆出一个翘臀掩裙的经典pose。不想她连换数个姿势,DV的主人却仍然没头绪地嗫嚅,“这应该是……应该是……”
那女郎的表情慢慢地由期待转到败兴,“我是飞行护航编队梅弗儿?伊斯特中尉,我扮装的自然是居里夫人。”
在众人哄笑声中,影像一转,又变成了一段新闻视频,正是六年前同天狼星系爆发热战时的战况报道。影像中显示的是一架歼击机冒着猛烈的近战炮火起飞的画面,眼尖的人可以看见歼击机上隐隐约约的锯鲨涂装。影像再次变幻,显示的却是庄严肃穆的合众国海军大授勋厅。在数千名海军军官的注视下,身着军礼服的伊斯特走上授勋台,目光明亮,军容严整。鬓发斑白的海军总司令向伊斯特肃然敬礼,亲手为她佩上象征合众国海军最高荣誉的紫罗兰之心。
下一段影像显示的则是伊斯特在西点军校担任教官时的场景。这段影像剪辑颇为精致,短短数分钟就涵盖了伊斯特在西点军校从下级教官升至总教官长的六年时光。由于在场的多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这段影像引起了他们最大的共鸣,整个酒吧里笑声、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整部影片的最高/潮在结尾处产生——那是两年前一个万里无云的秋日,西点军校58届军校生毕业典礼当天。军校的中央广场被临时改建成硕大的露天礼堂,年轻的毕业生们军装笔挺,脸上的神情满是欢欣鼓舞。中央主席台前,教官长梅弗儿?伊斯特身着满佩勋章的军礼服,她向军校生们发表的毕业致辞已接近尾声。
伊斯特背后是寥入九霄的秋日晴空。硕大威武的杏坛号战舰游弋在半空,让人振奋,又给人威压。秋日的阳光,将伊斯特的身影镶上了一抹金色的光晕,映得她烟水晶色的眸子波光重重,更显得温和真挚,
“……我愿你们高歌猛进,永不遭挫折阻碍;我愿你们壮志凌云,永不遇雨雾阴霾。但人生并不总是如此。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只要努力争取,就能够得到的东西,在这世界上实在少之又少。——因此,若是有幸遇到,就请千万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影片终了。昏暗的光影下,酒吧里一片静默。全息影像中那神色殷殷的伊斯特逐渐模糊淡去,空气中只剩下一片微微闪烁的荧光;而她的话语却在每个人耳边萦绕不去——当年毕业典礼上初次听到时,她的话只让人觉得热血沸腾;而今日在影片中回顾了伊斯特的半生遭际之后,再听这番话时,却听出了刻骨的沉重与悲凉。
但大家毕竟是不识愁为何物的年轻人,当灯光渐亮的时候,看到一脸奶油、模样滑稽的伊斯特,酒吧的气氛又重回欢乐——特别是在伊斯特说了几个令人捧腹的笑话段子之后。
周年庆祝会走的永远是老套路。开场回顾影片之后,自然是伊斯特的学生同事、故交旧友一一致辞。军校生兔宝宝们也就罢了,令伊斯特颇为惊讶的,是她在维和部队时期、在给科考船和采矿船护航时期曾合作过同事中,居然有几位现正在玛洛斯号执勤服役。这一次,他们也被请到了庆祝会场。时隔多年,虽然原来的小飞行员、小修理工和小技术员,此时早已成长为教官长、总机械师和首席科学家。对着见证了彼此苦逼青春的老同事,他们谁也端不起架子来。几个人强拉住伊斯特荤素不忌地划拳拼酒,相互出糗揭短,玩得不亦乐乎。
伊斯特借口尿遁,好不容易逃离了这一干人的魔爪。终是多喝了几杯酒,那些被她深埋心底的陈年旧事,此时压制不住地翻江倒海做起怪来。在洗手间里擦了把脸,她坐在洗手池那冰凉的大理石台面上,觉得自己需要先好好缓口气,然后才能打起精神,带着笑容重回到旧人旧事之中去。
洛曼诺推门而入时,看到的正是伊斯特翘脚坐在高高的洗漱台上,蹙眉咬唇,若有所思的模样。她两颊略带着酒气熏染的桃红,眼波流转,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台面,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复杂难解的事情,也好像在说服自己做一个决定。人们或欣赏伊斯特的行止合矩、动静得宜的风度,或艳羡她恬淡风趣、宠辱不惊的气质,而洛曼诺却为她此时这个苦恼纠结的小儿女情态而心漏跳了两拍。
抬头看到金发通讯官扶着门把手呆呆愣愣的样子,伊斯特哧地一笑,翘起兰花指,点点隔壁,意思是那边厢才是大官人你要找的男厕。
洛曼诺却摇摇头,推门而入,“刚才见你多喝了两杯酒,所以来看看是不是一切还好。”
伊斯特嘁地一声,“小看我。你不知道伊斯特少校她老人家是千杯不醉的。”说是这样说,她的声线中却明显带了两份酒意。伸手拍拍洛曼诺的手臂,伊斯特接着笑道,“你有心了,阿莱索。——我是说今天这个惊喜趴踢。”
洛曼诺耳根微红,“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
“随你怎么说,幕后主谋大人。” 伊斯特笑着耸耸肩。
看着她的粼粼眼波,温软笑容,洛曼诺心中忽然生出前所未有的勇气。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
伊斯特挑起眉毛,等他从实招来。
洛曼诺深吸一口气,低头直视她的双眼,“伊斯特,我想约你。”
伊斯特瞪大了眼睛盯着洛曼诺半晌,终是撑不住哧地一声笑出来。
洛曼诺天蓝色的眼睛里尽是沮丧懊恼,“我早料到你会是这种反应。”
伊斯特摊手,“你跑到女厕所来钓姑娘,还能指望人家有什么反应?”
洛曼诺也乐了,“你放心,我求婚的时候一定不挑这么重口味的地方。”
伊斯特神色仍是温和带笑,但洛曼诺知道自己最后一句话是说错了。——太久远的未来和太笃定的承诺,只会让眼前的人不回头地远远逃遁。但久藏的心事既已出口,洛曼诺倒宁愿延颈受她痛快一刀,也胜过日日夜夜焦灼无望的煎熬。
“那我若是在帝国大厦的天台,或者是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说我要约你呢?”
伊斯特的眸光有瞬间的沉黯。
望着洛曼诺真挚灼然的目光,半晌,伊斯特终是给了他一个半是安抚,半是无奈的苦涩微笑,
“阿莱索,和我在一起的下场会很悲剧的。”
洛曼诺示意她继续说下去。对于今天这通表白,洛曼诺在心中早已打了几百次的腹稿。因而,无论伊斯特说他俩年龄相差太大,还是他们的前师生关系太尴尬,这位能言善辩的通讯官都相信自己有办法说得她心意回转。
可伊斯特接下来说的却是,
“从以往的经验来讲,和我在一起的下场只有一个——我会伤透你的心,而司徒文晋会打断你的鼻子。”
☆、心魔
西非尼日利亚自治领。
百年不遇的旱灾,彻底毁掉了原本葱茏繁茂的西非大草原。苍黄龟裂的土地延展到天际,远近几棵焦枯的乔木,更衬得这片天地无比的荒凉颓败,死气沉沉。
百里之内唯一的小村庄的村口,停着几架喷涂着合众国纹样的飞机,数十名面黄肌瘦的村民,正在奋力争抢工作人员手中为数不多的救济粮和饮用水,场面一片拥挤混乱。
在歹毒日头的炙烤下,那维持秩序的扑克脸青年飞行员嘴唇早已干裂出血,汗水更是湿透了他厚重的野战军装。眼见食物饮水即将告罄,尚未拿到救济的灾民情绪激动,将一腔愤懑全都发泄他在身上。然而面对灾民们的推搡踢打,恶言相加,那黑发青年仍是不急不火,温言相劝,却守住位置一步不让。
人群最前方一个怀抱瘦弱婴儿的羸弱妇女,眼见自己的孩子日渐病弱消瘦,不知还能支撑几日,痛怒交加之下,上前一口就啐在他脸上,
“什么平等,什么均富,什么合众国,我呸!假惺惺地说什么现代化,说什么发展,说到底还不是眼里只有臭铜子的殖民者!你们掠夺我们的资源,压榨我们的百姓,到头来却连口残羹冷炙都不肯施舍一口!若是我的孩子今日死了,你这合众国的走狗也别想多活一天!我只盼你现在就下十八层地狱,也尝尝我们今日痛苦煎熬的滋味!”
人群中一片叫好喊打声,更有几个村民气势汹汹地手持锄头大棒,眼看着就要招呼在那青年的身上。伊斯特大声惊呼,就要冲上前去护持,却惊惶地发现自己既发不出声音,又迈不开手脚。
画面忽然一变,又成了肮脏潮湿的暗室。几名头戴黑面具的大汉手持足有两尺长的利刃,向那手脚被缚、委顿于暗室中央的俘虏走近。那俘虏的军装上斑斑点点尽是凝固了的黑红血污,一张清冷的扑克脸上也布满了青紫瘀伤。
那为首的大汉上前踹了那俘虏一脚,狞笑道,
“等我割下你的狗头挑在大营的旗杆上,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些肮脏的殖民狗吓得滚出我们的家乡!”
那大汉说着便一把抓起那青年的黑发,拿出一个黑布口袋便套在他头上,随即抽紧袋口的绳子。将青年踢倒在地,大汉用膝盖抵住他被黑布罩住的头,操起利刃便向他脖颈处割了下去。伊斯特大声哭喊着“阿晋!阿晋!”,手脚却被什么牢牢抓住,不能挪动分毫,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