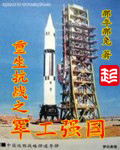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少爷作了什么孽-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边花落顺手捞起沈仙的灵位,转身就要朝外走。沈将军执刀一拦:“放下我儿子!”
匆忙赶来的沈夫人跑得气喘吁吁,被将军拦在外面,她急的带了哭腔:“你已经把我儿子杀了,如今你又来干什么,难道你让他在地下也不得好过吗?”
“胡说!我们庄主今日是来与公子成亲的,公子地下有灵,应是高兴得很,怎么会不好过!”几个红衣女子跟了进来,不知府门被大开了还是怎的,十来个喜娘也挤进来瞧热闹:“如此甚好!甚好!将军与夫人到齐了,拜堂行礼了!”
被掳上山后,庄中给信儿,礼成,才放人。
“行大礼!行大礼!”众人巴不得赶忙逃离花落魔爪。阿夏不知打哪里冒出来,手中托盘上竟还置有三杯酒。
花落拿起一杯朝将军同夫人两人抬抬:“爹,娘。”一口饮尽。
将军神色迟疑,夫人却顿足气得哭起来:“作孽!真是作孽!”
花落将手中酒杯朝地上一掼,顺手抽出剑来,额间红光一闪,剑身铮然有声:“今儿这酒,你们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怕她伤及爹娘,沈仙急得差点就走了出去。沈将军关键时刻分清主次,不就是跟个灵牌结婚么!有什么大不了!结!
将军一把捞起酒喝了。
花落满意一笑,接着看将军又拿起那杯,递到沈夫人嘴边,哄着她慢慢饮了。
“礼成!”花落收了剑,红影一闪,人已走远。
66、沈大少死得好冤(八)
那夜,花落抱着灵牌;一句话不说;喝了不少酒。
后来醉了,东倒西歪;阿夏几人搀着也起不来;最后被人七手八脚挪上床榻,她还牢牢抱着他;不肯撒手。嘴里嘀咕着,好歹也算大婚;圆个房。
满屋酒味儿。见她那架势;原以为要醉到不行;谁想第二天;又一早瞧着那小小身影坐在院中;迎着初升的太阳,懒懒盯着院中众人练武。
有几个姑娘练得不错,一招一式已渐成气候。
“庄主,昨儿又有一拨五人闯上了山,按您吩咐,已给排上了号,移到厢房安置着。”
花落点点头,按着太阳穴轻揉。
“多少个了?”
“从一一到十七了。”
好家伙,来翻墙灭庄的小混混们好多啊。
自打新庄建成,每天总有几个不怕死的,来找花落报仇。报什么仇?来给他们的父兄要解药呗,年年供奉,任是哪个散匪庄子也不愿意啊,吃到嘴的骨头,谁愿意吐肉。
更别提,这回新宫主一上任,就让他们先孝敬银两建庄子,孝敬少了的那几家,纷纷晚给了一个月的药,疼得小匪头死去活来。
以前的忘忧宫不好找,这回的花云庄可就在宋城边儿上,原来里面都是娘们,听说庄主还是个不大点儿的小姑娘,一定好拿捏!
于是就有这么一批不怕死的赶着来送死。
“挑年轻相貌好的留着,其余的劝几句,废了武功,好好送下山。”
年轻……相貌好……这是要干什么?
“自然是当我的男宠。”花落打了个哈欠,眼都不眨:“点了大穴,多喂药,好好养着。等攒到二十个,我统一过过目。”
说这话的第二天,二十个就攒到了,还反超了四个。
两打男宠,人人被逼着穿上了一身粉衣服,好吃好喝好伺候,面容白净,亭亭玉立。都是挑的长得好的。阿夏说,要不挑,人数早就破百了。
男宠们这是第一次见着传说中的庄主,没想到这样漂亮,一身红衣,霸气又妩媚。有几个甚至脸红了。更有几个色眯眯的,心中荡漾,由于武功不敌,只好收敛些许。
花落将他们一个个从头看到脚,有个胆大的忍不住开口:“那个什么,庄主,我们哥儿几个来也来了,不敌你们,被抓也认了,你到底是想干什么?难道要将我们关一辈子?”
花落瞟了瞟那个先说话的,不语。
阿夏朗声上前:“十三,不得无礼!你们是庄主选的男宠!以后就是庄主的人!每日里就负责貌美如花,好生将养,庄主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少说话!庄主最讨厌话多的人!”
听了她的话,下面众女子皆掩面而笑。庄主早同她们说过,这灵雀剑谱练到最后一步,要找男人帮忙。现今挑了这多男子让她们选,还都一个个长得不错,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男宠?
听了这话,从一一到二十四,面上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其中有人偷偷看了看花落,甚至春心荡漾,恨不得自己现在就赶快受了她的宠。
嗯,虽说男宠这两个字有些难听,可是既然对方是这么一个漂亮女子……也不是不能忍……不!是绝对不能忍!必须让她宠!
“庄主。”门外阿春走进:“安大公子带着一个女子来了。”
哦,大哥。带着大嫂,是来恭贺我新婚大喜的吗?
瞧见两人进门,花落好奇的打量起那个一身绿衣的女子。怎么,不是大嫂?
安怀瞧着满堂的粉衣男子,微微蹙眉:“这都是……”
“我的男宠。”花落似乎特别满意“男宠”的称呼:“大哥,你来是为了喝我的喜酒的吗?你瞧,爹爹去了,我也没赶回去哭上一场。这会儿还办红事,真是不孝。”
宋城那场喜事,办得轰轰烈烈,街闻巷知。死了的沈大少,被活人抱着灵牌,成了亲。据说还是抢亲,跟他成亲的,就是将他刺死的。这……这都什么事儿啊。
“落落。我早说过,绿衣有错,我带她来,任你处置。”
听闻安怀的话,那女子凄然一笑,并不看花落,情意绵绵死死盯着安怀,安怀不为所动,也不朝她看上一眼,抬头看着花落:“落落,这是绿衣。”
花落“哦”了一声,仿佛在细细琢磨什么,片刻问:“听说你会模仿众人之声?”
“是。”绿衣这会儿转过头来,抬眸看着花落。
自己要是她,该有多好。
只可惜,这辈子,不能够了。
她的眼中蓄满泪水,影影婆娑,望着高高在上的花落。
花落并未在意,仿佛关注点在另外一件事上:“你害我九叔的时候,说什么来的?”
绿衣想了想,说:“我在屋外,用沈仙的声音交代下人,说务要斩草除根,不留疑点,免她怀疑。”
“你说。”
说什么?绿衣不解,想了想,终于明白,开口:“务要斩草除根,不留疑点,免她怀疑。”
沈仙的声音自她口中说出,真正一点不差。花落心头一动,默然不语。片刻,又轻声说:“叫落落。”
绿衣得意的望向身边的安怀,他只望着花落,眼中说不清是繁杂,还是伤痛。绿衣心中宣泄出一种报复的快感,用沈仙最深情的声音,一遍遍叫着:“落落,落落,落落……”
众人眼见着一个女子竟出男人之声,稀奇万分,纷纷朝绿衣看。猛然间红光一间,一个鬼魅似的身影带着杀气逼近,绿影一闪,白光又一闪,“啊”的一声尖叫。
再看时,安怀脸色发白,绿衣慌忙捂着他的一支胳膊,手上已被他流出的血染红。她不知是吓的还是怎的,脸更是白得骇人,一双眼睛却发着炙热的光。
花落仍坐上位,轻轻掸掸身上的大红喜服。
众人悄悄打量她神色,她若有所思。自打那女子学了什么沈仙说话,庄主就仿佛进入一个游离状态,特别的心不在焉。不然,凭庄主出手,这一剑怎么还会让人躲过。
绿衣撕开自己衣服,帮安怀缠着受伤的手臂,一双手动作利索,又抖得频繁:“你……你为什么救我?”她问。眼泪先下来。
“你是我属下。做错了事,我自然要罚你。”这一剑刺得不轻,安怀微微蹙眉:“可是若要杀你,别人也杀不得。”
绿衣“哇”的一声大哭,身子如风中枯叶一般抖得厉害:“我……我没想这样的……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那天骗了你,我也不是就想代替她……我想尽法子,想让她回到你身边……只要你高兴,我就……”
“我知道。”安怀轻轻拉住她的手臂:“我都知道。”话没说完,绿衣向地上栽去。
见她无力至此,嘴角鲜血流出,安怀大异,将她头搂起,让她半躺在自己怀中,封住她周身要穴,将真气朝她背后灌去:“傻子,你服了什么药?”
“我就想问问你……那晚……你后来,后悔……后悔不后悔?”绿衣眼见着不行,她睁大双眼,看着安怀。
“不后悔。我不后悔。”安怀收了力,将她轻轻搂在怀中。
多年前,这个小姑娘,穿着一身破烂的绿色衣服,在街边模仿着各种动物叫,面前放着一个瓦罐,里面,零零散散,稀疏几个铜子儿。
后来,小姑娘长大了,一招一式刻苦练武,说,楼主,我要当楼里最好的刺客,给你赚多多的钱。
绿衣,绿衣。
他轻轻唤她。
绿衣含着一缕笑,慢慢合了眼。
能死在他怀里,这样真好。
大厅中一片寂然,花云庄中皆是女子,瞧见绿衣为情所致,不免唏嘘。
不过……新庄刚建成就有人死于厅中……庄主一定大怒……所有人向花落看去。
花落眼神飘渺,还是那样心不在焉。
后来,望着安怀抱着绿衣走远的背影,她终于出声:“真叫人伤感。”
第二天,花落带着沈仙的灵牌,下了山。她说,两个人去故地重游,回忆一番。阿夏问她去哪儿,她也不说,只说,看着姑娘们好好练武,照顾好我的男宠们。
三个月后,花落回庄。周身干净清爽,那块灵牌也怎么去的,怎么回来,连个磕碰都没有。谁也不知她去了哪儿,只见她带了好些茶叶回来,还带了……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看起来相当桀骜不驯,翻身下马,便朝庄主大声嚷嚷:“你别以为你这样,我就领你的情!”
“我也没叫你领情啊,表姐。”花落朝自己屋里走,对着阿夏指指后面的女子:“这是我表姐,好好伺候,什么要求都答应。”
被带来的是秦双。
被发放去守灵,虽比死强,可也太吓人了。还只许带两个丫鬟,那样大的一片陵园,虽说都是家人,可一到晚上,阴风恻恻,鬼火麟麟,秦双每晚都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睡也睡不好。还总梦见太子,太子掐着她的脖子,弄得她喘不过气,一遍遍恨声问她,你为什么害我,为什么害我,你为什么把龙袍偷偷缝进我的朝服中!为什么!
大喘着气醒来,秦双将头探出被子,正是那天,花落鬼一般的降临在她屋中。秦双将醒未醒,吓得一声尖叫,估计都要把地下沉睡的爹娘,吓得蹦起来。
“表姐,别怕,我是你表妹。”花落轻轻点起一支蜡烛,有了烛光,屋里见了人气儿,没那么吓人了。可是……干嘛……她还抱个灵牌?
看清是花落,秦双觉得自己死定了。这人,连未婚夫婿都敢杀,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她又来抽她巴掌了?
“别怕,表姐。我的亲人好友全死了,人都说,像我这样的叫天煞孤星,死后没好报。”花落自嘲般一笑:“表姐,我瞧着你也是这样。咱俩……搭个伴儿吧。”
67、沈大少死得好冤(九)
皇上病重,举国不敢有娱乐活动;各家各院都关了门;戏楼茶馆赚不着钱,愁得真搓手。
关了门的戏楼;有顾客上了门;拉着满楼的青衣小旦,进了花云庄。
据说庄子里的庄主爱听戏;还偏爱听几年前唱过的老戏。
花云庄奇大无比,占了整座山头;单独辟开一所院子;给戏班住。
夏至;庄中的大荷花池上搭了一个大戏台;凉风习习;每日不管有人看没人看,流水戏一直从早唱到晚。
自打来了戏班,庄主便常来听戏,往往她身边还有一个姑娘,瞪着大眼睛不住的挑刺儿。看什么都不顺眼。
这日,秦双又对着台上指指点点,一会儿说唱得不在点儿上,一会儿说脚步乱了方位,和几个男宠们争得不可开交,后来吵吵得戏里唱的是什么都听不清了。花落从塌上起身,绕着湖边慢慢走。
午后的阳光照在新绿的树芽上,园子里的热闹声渐渐远去,不时身边跑过几个带着银铃般笑声的姑娘,见着花落恭敬的问声好,接着又蹦跳着向前跑去。
阿夏在身后慢慢跟着,见光头照得足,怕晒着花落,问:“庄主,去前边找个阴凉处坐坐吧?前边花园里都是她们闹着玩儿时弄的小玩意儿,秋千、藤床、水席子什么的,这会儿她们都去听戏玩乐呢,里面清净。”
花云庄的花园就是姑娘们自己的小乐园,闲来无事,好美的姑娘们将里面打点得异常温馨,大树下挂了七八个秋千,绳上都有藤蔓花朵缠着,花落找着棵最高的大树,试了试绳子,正想坐,见着那块木板子,迟疑片刻。
庄主这几日怕凉。阿夏忙说:“我去取个厚毡垫来。”
花落绕着秋千等了半天,也没见阿夏回来,索性一跳蹦到了上面,站着悠。她小时从没玩过,这会儿异常新奇,越悠越高,晃来晃去,美得几乎要笑出来。
与此同时,身后真的有人笑出来:“庄主再使使劲,那树杈就要断了。”
花落没想自己偷玩秋千的事被人发现,觉得有些没面子,堂堂一庄之主,如同个孩子,甚为不威严。此时便暗中使力,待秋千稳稳停下,方回头去看。
树下,一个粉色的身影立在阴影中,说话的那名男子,一双狭长的凤眸,微微向上挑着,嘴边含着笑:“庄主今日好兴致。”
“你怎么没同他们去听戏?”花落若无其事的跳下秋千,淡淡问。
“我刚去了茶园,茶苗冒头了。”
茶园?花云庄何时有的茶园?见花落眼中满是不解,那男子做了个请的手势:“庄主,让二十二给您带路,去瞧瞧新鲜。”
院子东南角的一处三角地带,本是一块被废弃长满杂草的小荒地,眼下被规整得十分井井有条,墙边角下一排爬山虎,可想而知,再过几十日,盛夏时分,必定能爬了满墙。墙下的杂草被整齐规矩的几条茶苗所替代,刚翻的土还带有青草香气,一溜溜儿刚冒着头的小茶苗,刚刚破土而出,稚嫩的身躯,柔软又干净。
“这是你种的?”花落问。
“上次见庄主从外面回来,带了好多新茶,想必庄主是爱茶之人,若是庄子里有个自己的茶园,便不用再去远处寻觅。”那人答。
“哦,原来你是为了讨好我。”花落淡淡看了他一眼,不知怎的,和他的眸子一对上,花落觉得竟然心中有些忐忑,可能这男宠的身份,花落自己还不太适应。
“其实我也没多爱喝茶,不过是旧地重游,带些东西权当念想而已。你费心了。往后,该吃吃,该睡睡,没意思的时候去听戏,别将心思,浪费在用不着的地方。”说完,她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些男宠们,都养刁了。刚开始还七个不服八个不愤的,吵吵着要回去,有几个搞暗杀不成功,还作死上过吊。这会儿看出好了,有吃有喝有姑娘陪,竟然还敢把主意打到她头上。一个个换着花样儿的想来争宠!
是得给他们找点儿事儿干了。
“什么?造船?”
“庄主说了,湖中的荷花好看。于船上观花,午后阴凉,景色又美,限你们尽快造出一艘船来,不!两艘!庄主同秦双姑娘共赏!”
怎么?花云庄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废话,不是看你们天天闲得难受吗?
一日午后,秦双同花落一同吃饭。见桌上有一碟刚制出来的水晶酱牛肉,秦双要了壶酒,花落便也一同饮着,喝着喝着,两人又翻腾出了往事。
秦双恨恨,你他妈不是东西,当初何苦误我。
花落答,我就要抢你丈夫,你瞧,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秦双再怒,你为什么打我巴掌。
花落答,你还要炸了我呢。
两个人平素很少说话,一说话就打得生龙活虎,彼此都觉得特别爽快。
彼此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里,前尘往事都已知晓。末了秦双酒喝多了微有些醉,躺在塌上嘀咕:“这条命算是半路捡来的,没的再成天哀啊怨啊的,日后逮着一天算一天,我他妈要痛痛快快!哎,我说,你那些男宠有几个姿色不错,给老娘拨几个好的,快活快活。我瞧那个二十二就不错,将他给了我吧?”
没等花落答,秦双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花落将壶里的酒喝完,命人将她抬回屋去。听她提起了二十二,又想起那个小茶园,也不知,上次被自己打击一通,他还种不种了?
趁阿夏她们忙着去抬秦双收拾碗碟,花落一人走至园中。到后半程风一吹,头便有些晕,快步走到小茶园,见墙边又多了条木头板凳,正合心意,也顾不得看茶苗,摸着便坐了上去。
身后的墙上,满满的全是爬山虎,大片大片绿油油的叶子,靠上去还挺软和。太阳又晒得正好,靠着靠着,花落索性躺下了。
眯着眼怎么也睁不开,还哪有精神看什么茶苗,张了个哈欠,就睡了过去。
一梦梦到了长湘。
长湘的空气,总是湿湿润润的。清早,小路上人烟稀少,茶园里的茶叶上一滴滴都是露水,勤劳的茶农们天不亮就起床,去田中耕种。远山是绿的,茶园是绿的,空气是雾蔼蔼的。
整座小城都是清香的。
上个月,她刚和沈仙从长湘回来。沈家的那所小楼,人去楼空,桌椅上都积了厚厚一层土,她抱着他,从东面的那间屋里看了日出,又从西面的那间屋里看了日落,临走时,还闻见一楼大厅里,一股浓浓的黄酒味儿。
当初那些赌坊,早就被填平,盖起了新的房屋商铺,那间有桂花树的院子,桂花树还在,依旧高高大大,满树桂花,树下,新开了一家小铺子,里面的桂花糖,听说最地道。
花落买了一小包,在路上边走边吃,吃了许久,也觉不出甜。
谁是谁的如花美眷,谁又是谁的似水流年。
花落叹口气,徐徐睁开眼。眼前一个熟悉的背影让她愕然许久,分不清是梦非梦:“沈仙?”
那人回过身来,朝花落微微一笑:“庄主在叫谁?”
花落起身,将身上盖着的衣服还他,他接过,随意往身上一披:“看庄主睡着了,就没叫你。来,你瞧瞧,这排玉株长得真叫好。”
花落也分不清什么金株玉株,顺着他手望去,只见小小茶园热闹非凡,一排排的小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