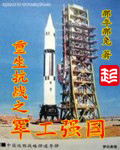误闯他的国-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当初能预料到现在的下场,自己是否还愿意陪他游戏人生?可是没有如果,无法重头再来。
从来没有预料过,分手会这样痛苦。没有经验,完全措手不及。一开始以为不走寻常路,逆道而行会好过一点,于是无所畏惧地一个人吃两个人吃过的冰激凌,一个人看两个人看过的CD,一个人睡两个人睡过的床,初衷是想借此麻痹自己,却每每吃朦胧了眼眶,看湿了眼睛,睡痛了心。原来,有些地方,有些记忆,有些禁区,真的碰不得。
冰激凌明明是甜的,却吃苦了嘴,以为是味觉出了问题,毫无理由地跑去拼命刷牙。电影明明是喜剧片,却看湿了一个抱枕,以为是自己笑得太厉害,却发现自己整个过程一直在哭。床被明明是温暖的,却感觉全身血液都被冻僵,以为自己躺在了冰窖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棉絮填充到再严实不过。
常常会半夜在梦里皱着眉醒来,下意识地去寻找他的怀抱,结果扑了空,最终彻夜无眠。连带着一起惧怕黑夜。
用了那么久,依然无法将他从心里连根拔起,还是留下了那么一大块伤疤,时不时地渗出鲜红伴着腥味的血丝。然后发现,只有将他埋藏在心的最深处,看不见摸不着,自己才能重生。
所以把所有跟他有关的东西收起藏入纸箱置于最不起眼的角落,连他曾经夸奖过的牡丹刺绣图也未放过。
上午十点下了课,下午都是空闲的。匆匆收拾好办公桌景安便直接打了车到盛柯大厦。在服务台得到消息,苏牧南还在22楼会议室开会。景安缓了口气,马不停蹄地赶到22层,看着会议室紧闭的门才松了口气。这会儿应该还没有开完会,所以他应该还在这里。
都还没有想好待会见面要说些什么,完全没有准备,只是听蔡释提到他会来这里和某个公司洽谈商务便决心一定要见他。问了一旁的一位工作人员,得知会议大概还要持续半个小时。
是有三年多没见过他了吧。算算苏禹瑾应该有五岁了。也不知道长多高了,有没有想妈妈,看到别的小朋友冲妈妈撒娇会不会羡慕。记忆力的小瑾那么乖巧可人,现在是不是依然如此?现在再见面会认得她么?还是用看陌生人的眼光打量她?很多情况都没有预想过,就这样一头热地跑了过来。
会议室门打开的时候景安就蜷缩着坐在地上,倚着墙下巴抵着膝盖盯着地面出神。逐渐逼近的脚步声将飘远的思绪拉回现实,抬头却看见一大群人异样地盯着自己。为首的两人眼神里透着万分的惊讶,却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心痛。
“安安?”苏牧南抑制不住的讶然,带着试探轻呼出声,以为从此都不可能再与景家有任何干系,根本没有想到景安会出现在眼前,也不敢确定她的目标是不是自己。
顾不得腿麻。忙挣扎着站起来,不敢望进他深沉的黑眸里。错开与他交汇的视线,转眼看向旁边的苏牧南,情急之下只记得最初的□裸的目的,说:“我想见孩子。”
听到这话江逸寒原本紧蹙的眉皱得更深,完成没有办法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可凭着苏牧南那句温柔不亚于他的昵称以及她开口的话,无法不引人那样猜测,他们有男女感情!
“我们换个地方谈好吗?”苏牧南几乎有些受宠若惊,不是亲眼所见,实在无法想象可以在商场呼风唤雨的人会对一个女人这般重视,甚至刻意逢迎地微笑。他转头与江逸寒交谈了几声,然后便听得他说“好了,我们走吧。”转身直到电梯门合上,景安都没有敢回头,每一步都走得艰辛,感觉如针芒在背。关于今天的相遇完全没有准备,没得来及设想见他应有的表情,是微笑或是继续擦肩而过,没有预习过,不能保证不会露馅让自己眼泪决堤。
有些回忆,明明很远,却感觉很近。有些记忆,明明很近,却恍惚地不真实。还记得那年,她和景乐快乐地陪着苏禹瑾玩耍,那轻松爽朗的笑声,小瑾稚嫩的童音,彷佛只在昨天。小孩儿虽小,认人却自有一套套路,无论她和景乐怎样试图迷惑他,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认出妈妈。看到景乐言溢于表的笑容,景安更加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有了禹瑾,景乐只会更加快乐。所以对未来的不确定她从没有往坏处设想过,对景乐偶尔的倾诉衷肠也不予理会,认为那是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景安的观念里,那么爱景乐的苏牧南根本不可能做出那样过分的事情,她相信苏牧南甚至要比相信同胞的景乐多得多。直到亲眼看到安详躺着面容安静的景乐,她才最终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残酷刽子手的事实。这更加让她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将爱自己的人亲手送上不归路,打着为她着想的名义,多么可笑!何其讽刺!
时间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充当最好的良药,它冲不淡景安永远无法释怀的负罪感。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将永远提醒她景乐是如何逝去的,她要忍受的不仅仅有失去亲人至爱的悲痛,还有间接成为谋杀者的自责和母亲痛失爱女转嫁过来的对她的痛恨。无法预言,是否某天她会不堪重负借死解脱。
自从景乐去世至今,苏牧南似乎都没有续弦的打算,这便让身为苏家独子的苏禹瑾更加受到苏母的溺爱和珍视。显赫如他,苏母当然容不得苏家断后,所以毫无理由地将景家列入假想敌,时时刻刻提防着,似乎哪一刻松懈了景家便会趁虚而入将苏禹瑾夺走。甚至连景家正常的探视权也剥夺了。作为爱女之子,她知道母亲对小瑾有多么挂念,所以她多次尝试希望能够见上小瑾一面,可都被苏母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和景乐长得像,苏母甚至不肯让她见他,即使他们只一墙之隔。苏牧南常年在外,况且在景安看来,他的立场会和苏母一样,因此对他也没抱太大希望。
没有想到这次如此顺利,苏牧南几乎没有做任何刁钻阻挠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受惯了苏母的冷言冷语,面对苏牧南友好而谦恭的态度,她突然觉得自己莫名而起的敌意实在显得有些小肚鸡肠。看得出来,景乐的死,苏牧南没有比她好过,甚至他受的伤害和煎熬远大于自己。这样的他,自己怎忍心再去责备?说到底,自己和他一样,都是罪人。以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她景安做不来。
给景寒去了电话,说过这几天能带小瑾回家。深层含义是希望他也能回去,一个人回去面对母亲,总会让她感觉紧张。想着母亲见到小瑾时惊喜的表情,心情也跟着好过一些。只是,免不了又会湿了衣襟吧?
姐夫
明天要和苏牧南一起去接机,于是她早早熄了灯休息,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断闪现过往的一幕幕,越来越清晰,神智越来越清醒。这样持续了两个小时,连脑袋都想痛了。她干脆坐起来,窗外月光流泻进来,整个房间显得神圣静谧。突然好想找个聆听着诉说自己的心声。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一辈子烂在心里,比如现在,就忽然泛起那么强烈的倾诉欲。
周围安静地连呼吸深浅都分辨得清,所以当门外传来窸窸窣窣地开锁声时,她整个人都戒备起来,心里怕得要命,却勉强壮起胆摸索着到客厅,随手拿起置在门边的雨伞,也没有来得及想这样的武器有没有杀伤力。门被打开,浓烈的酒味浸满整片空气,在她呆立的片刻,客厅灯被啪地打开。没有看她,他趔趄着撑到沙发上,他的酒量不会小,而现在连步子都踩不稳,可想而知喝过多少酒。
没来得及多想,她忙跑到厨房帮他煮了些醒酒姜汤。他不肯喝,她只能扶着他哄了他喝下去,这边心里却在天人交战。半卧在沙发上的他于她来说好似致命的鸦片,根本碰不得。可眼前憔悴的他让她根本无法抗拒,才几个小时没见,上午还精神抖擞的他何至于这样疲倦困乏?
这种状态能安全到这里已经算是幸运,肯定不可能就这样再回去。原本给自己竖起的警戒全被抛到了脑后,相对无言,她起身去给他放洗澡水,那放在角落许久未碰一见就疼的属于他的一切又重新被揭开。忘记了在戒掉他的那段日子里如何煎熬难耐,忘记了每次守着安静无声的手机如何心情失落,忘记了想起和他的点滴时心怎样滴着血,没有考虑过如果再来一次自己是否承受得住,就这样无条件接受了他的再次侵犯。
替他准备好浴袍试好水温,走出浴室他正闭着眼睛假寐,手无力地揉着太阳穴,眉头深锁。她走过去,轻声唤他,他睁开眼,冷冷地扫了她一眼,没有理她。半响后站起身,甩开她试图扶他的手,定了定神自己强撑着走向浴室。她尴尬地顿在原地,疑惑地看着他,不理解他何来的怒气。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她的地盘,他竟然生气地理直气壮。
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她却在外面坐立不安。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他。终于打定主意抱了床被子放在沙发上,看了看时钟他已经进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敢冒昧地冲进去,想敲门想起他刚才冰冷陌生的眼神又犹豫不决,在门口来回徘徊着踌躇不已。门突然被拉开,她半抬起的手差点落在他水珠未干的胸膛。发际大颗的水滴泛着灯光的光泽,合着浴室里冒出的热气熏得人缺氧眩晕,连带着意识模糊起来。
他用毛巾擦拭着发上的水珠,看到发愣的她微微吃了一惊。冲过澡整个人思路清晰了许多,还以为刚才的是梦境,却没想到自己真的又来了找她。明明记得自己是拉着裴时俊喝酒的,好像意识也一直停留在喝醉前的那刹那。裴时俊的话又在耳边回响起来,吵得他头痛欲裂。他说:“小子,你不会是爱上她了吧。看你的样子魂不守舍的,肯定是中爱情的毒了。”
他说:“个例不能代表全部。撇开你父母失败的婚姻,世界上不是还有那么多幸福美满的姻缘么。要自己试了才知道,能不能行别人说不准,连自己也算不好。”
他说:“你小子也是该定定性了。难道你一辈子游戏风尘不累?没有幻想过有一天下班回家有一个人用微笑为你退去整日的劳累,替你备好可口的饭菜,两人相濡以沫直一直到老,等你头发掉了牙齿松了也对你不离不弃和你挽手看夕阳?”
他说:“我说了这么多,你听的过程中在你交往过的那么多女人里面你想起了谁?”
然后她的样子渐渐清晰,让他近乎抓狂。和他交往过的那么多女人里面他唯一吃不准的就是她。她是会撒娇,会讨宠,会允许他看见真实的她。可更多时候她是冷静的,装在套子里的,疏离的。在他们的关系里,她永远是被动的,似乎他一直可有可无。就那天,她站在门外,朝他扯起嘴角,看上去是在笑,他却宁愿她那时什么表情都没有,甚至连哭都更好。他不奢求她会像其他女人一样向他要解释,可也不愿意她那样景乐式地对待他。
和她在一起那么久,他当然清楚她在何种情况下会用景乐的外衣伪装自己。原本以为自己在她心中可以是不一样的,可结果也不过如此。
况且现在还扯出一个苏牧南,看来她真的是不简单。
可即使这样,还是想听听她的解释,告诉自己是自己误解了,她和他其实什么关系也没有,是清白的。否则,自己已经付出的心要怎么收场?
依然是相对无声。喝了太多酒,现在头还痛得厉害。她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低头立在那里,半天不见抬头。
“ 能不能解释一下你和苏牧南的关系。”他开口,慵懒沙哑的声音透着疲倦,还有一丝的紧张,甚至伴着她察觉不到的卑微的乞求。连呼吸都变得微妙,神经紧绷着等待她的宣判。
“……他是我前姐夫。”
耳朵暂时性失聪,周围被抽成了真空,世界变成单调的黑白两色,只看得到她的唇一翕一合,耳边是嗡嗡的轰鸣声。好像过了一秒,又像过了一个世纪,一切再次恢复运转。敏感的神经迟钝地抓住她话的尾音,最后消化掉她整句话里的意思。瞬间,死寂的心活跃地五彩缤纷。
自己被她短短的一句话救赎了。
僵直的身体放松下来,陷进柔软成堆的抱枕里,原本被认作的世界末日顿时可爱地不像话。连几日来积压的怒气也不知道躲在了那个角落乘凉。什么都来不及思考,只听得心里最真实的声音说:不能再放过她!
他决定听从心声,不会再放过她。
以前的一切,他都可以不计较,包括她对他的不在意。只是以后,他一定要霸道地占据她的心,不管她愿不愿意。
他的表情柔和起来,低沉的气压也跟着缓和,让没有看他的她都感觉得到。
“那孩子也是他和景乐的吗?”语气里透着自己都未察觉到的抑制不住的失而复得的欣喜。
一切再次归于沉寂,他安静地熟睡着,浅浅均匀的呼吸让人无比心安。她却丝毫未受他的感染,仍然毫无睡意。
景乐
江逸寒一觉醒来的时候她还是保持着打量他的姿势,一动不动地连眼睛都不眨,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只是眼睛看着他思绪却不知飘到了何处,眼神空洞地不聚焦,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气。一觉醒来人要精神许多,他半坐起身,一连串动作终于将她惊醒,想换个姿势却发现全身都麻痹着,似浑身爬满了蚂蚁一般难受。不适感将她从自己的思绪里完全拉回现实。
“不睡么?”他拿起置在床头桌上的手表,看了一眼,已经凌晨一点。而且微凉的秋天她还穿着睡衣坐在床前。掀开被子示意她进来,她只坐着不动,僵持了一会儿感觉气氛周遭开始变得微妙,正不知所措间仿佛想起什么,抬头问他,“你的伤好全了么?”得到他的点头回应后便不再说话。关于那天出现的女人,其实还是很介意,虽然已经决定不再和他纠缠。
察觉出她的异样,他故意不点破,问她,“那天怎么不进来?不是来看我的么?”
“……”她低头窘地说不出话,半响试探着说,“那天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说话的。”声音低得像蚊子,也不确定他是否听得见。
关于“那天”他细想了一下,大概猜到她讲的是哪一件。可时隔那么久他的怒气早没了。况且她一下子惹出那么多值得他气恼的事,他根本气不过来。不过她提起这事算不算是另类的示弱?
这般想着觉得以前的什么气啊误会之类的都无所谓了,长期压抑的心情再次多云转晴。他没接话,放柔了语气哄她上床。再坐下去不能保证不会着凉。
孰料她立马跳起后退了几步,觉得自己反应有些过分,她抱歉地笑笑,转身从衣橱里拿出外套披上。以为她还在介意那天所见的事,他叹口气,起身下床,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解释,“那天你看到的女人是公司的职员。因为我受伤了,有份企划案耽误不得,就是上午和苏牧南公司合作的那份。因此只能叫了他们来家里开会。那天除了她还有其他几个员工。真的。”他急切地语气似乎晚了一秒她便不会相信,“不信你可以问她的。”说着便拿起手机认真翻找起来,也不考虑时间是否妥当。
以前他断然是不会这样多费口舌向谁就某事多做解释,可现在,众人该经历的他在她这里都领略了。人生,不能少的果然都不会少。
手机被她一把夺过,看她也没有再对此纠缠,舒了口气,从后面抱着她,熟悉的独属于她的清香再一次扑鼻而来,他将下巴抵在她肩头,贪婪地深吸一口气,蛊惑的嗓音响起,“以后我们不要闹别扭了好不好?”
话语温馨地令人不忍心说不。所有的坚持都决堤崩溃。
辗转多次还是睡不着。有些事必须说清楚,否则心无法安定。
她开了灯坐起直身,他也跟着半坐起。几次想要开口,却不知道怎么说清楚,这样的话,说出来现在的一切都会化成泡影,连带之前两人的心里挣扎也会变成徒劳。却,不得不说。甚至迫在眉睫。
才刚刚说过要好好过,不吵闹。现在却立马变卦了,他肯定会生气。想了下,她换了种方式。
“我跟你讲讲景乐好不好?”
“嗯。”他轻轻点头,帮她放好枕头。
时钟滴答走过三点,落地窗前高大的男人背影借着窗外变幻闪烁的灯光不断往后延伸拉长又左右变短,指尖烟火燃尽,他却丝毫未感觉到灼痛。巨大无边的黑暗里最真实的自己显现出来,脑子里全是景乐的音容笑貌。曾经他以为她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如今发现原来事实并不是那样,那么现在的自己该悲还是喜?
景安镇定地说:“姐姐她爱过你,从嫁给你的那一刻就在开始爱你。等发现爱一个人是那样痛苦的时候她打了退堂鼓,却终是不得脱身。她为你哭过,几乎伤心欲绝。只是这些她都没有让你看到。她外表是柔弱的,却在骨子里有自己的骄傲。你爱她,却用错了方式,她又何尝不是。”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
这样触不到的爱情是一种遗憾。
而他们,生在同时代,甚至已经结为连理,却在爱情的表达方式上输得一塌糊涂,比起那样柏拉图式的纯美爱情是否让人在感叹遗憾之余又禁不住泛起凄凉之感?
那么那时爱着自己的她是不是已经完全对自己绝望,哀莫大于心死,她的心被自己伤到麻木最后尘封了吧。
流产
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有着家,因为景乐的缘故他和家里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糟糕。每次踏进家门话不出三句母亲一定会将话题牵引到婚姻上去,他讨厌那样的谈话,排斥任何一个想走近他内心的女人,只因为,那里这辈子只属于一个人。不管这样的坚持有没有意义,他只知道,只有这样,自己才会好过一点。
认识景乐完全是出于偶然。看见她的第一眼便感觉全身电流穿过,好似四周春暖花开。后来才知道那叫一见钟情。可不幸的,景乐对被誉为少女杀手的他毫不感冒。她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对他的追求视而不见。
男人都是有征服欲的动物,钟情于胜利后的快感。景乐的拒绝只会更加坚定他要将她追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