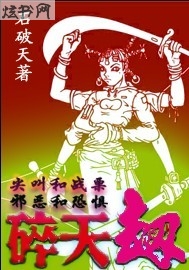花魁劫-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真难。
敬生去世后,整个生活都沉闷下来。
从前,老是要一早就爬起身来,打点他的衣服,或到大宅去吃早餐,或在家弄点粥面,就算有佣仆,我还是要在旁关照,很有点事做。不时,又会陪敬生上马会或到其它会所去饮杯茶,才送他上班。
这下来,我上美容院去做做头发,到银行或邮局去一趟,便是午饭时间,敬生除非跟生客见面,否则多把我带在身边。
这些年,下午三点半一收市,敬生便要跟我到文华或置地去钦下午茶,稍稍舒缓一下他的紧张情绪。然后,陪着他去几个酒会,就是晚饭时间。
若是晚间有隆重应酬,黄昏时的准备功夫就更教我忙乱。
一夜的时光转瞬便在灯红酒绿之中度过。
有一个伴,时光的打发是最容易的。
现今呢,几点起床也无所谓。有时转醒过来,赖在床上,甚至想,永远起不了床又如何?天下间不见得有多少个人会伤心呢?
心就直往下沉,益发在床上白白虚耗光阴。
打扮自己就更谈不上了,连午饭,我都很马虎的在家里胡乱吃过就算。都不打算见什么人,亦无人可见,费神在装修自己上头,未免更易生惘怅。
有时下午实在闷得慌,着司机开车送我去芬姐西环的生果摊铺上坐。
她是热情招呼,又是茶又是水果的扰攘一番,那几个伙记就像舞台上的跑龙套,在我们身边团团转,问长问短,什么都要芬姐拿主意。
看得出来,她是忙碌的人,我也就不好意思搁在那儿不走。
从前,我的身份是贺敬生如夫人,香江之内的所有大小出色场合,都有我的份儿,因有敬生份儿之故。
现今,一应酒会晚宴,人家巴巴的来招呼个寡妇干什么叫呢?既非亲友故旧,又没有生意援引,于是门庭冷落,深院寂静,永无休止地一夜又一夜的过。
没有了床头的那叠书房内的彩色电视机,我就更难捱了。
不是我醉心酬酢,实在百无聊而已。
刻板呆滞的生活,把整个人都蛀蚀得发霉发烂似,真有点寒心。
于是,可以这么说,日中最有生气,令我的神经稍微有刺激的,竟然是潘浩元的电话。
想着,也不觉震惊。
正呆呆的坐在房中那高背梳化上,看着金鱼缸里的锦鲤出神,身旁的电话铃声就响起来,我的心也随之而加速跳运。
“是三姨吗?”
不是潘浩元,是贺智。
“今儿个晚上,我把潘叔叔与潘光中都带到你家来吃晚饭好吗?还有,我且叫光中也把欣荣叔请一请,看能否大伙儿叙一叙。”
“啊!是有什么事吗?”我问。
“没有哇!跟潘叔叔谈起,他说一直叫你出来走动走动,吃顿饭,你总是不情不愿,这样子是要郁出病的,故此,我们来陪陪你。”
“怎么不上大宅那边去呢?我也可以过去……”
“三姨!”贺智截我的话。
她的语气是嗔怨,我当即明白过来了。
这是为关心我,也为贺智的方便。
“好,让我准备准备,喜欢吃些什么菜呢?”
“随随便便的晚饭就可以了,光中说,他还未试过家乡菜!”
“家乡菜是粗菜而已,怎么款客?”我答。
“他还少吃了珍馐百味吗?且都不算是客。”
贺智说这话时,声音甜得有点腻上咙喉似。
唉,什么女强人,一沾情爱,还不是那副样子。
也真亏贺智这个安排,我立即精神抖擞地忙足一整日。
整间房子都有了生气似。
我还赶着去买了满屋的鲜花回来。
菜原本是由厨子动手做的,我也因着贺智那番话,便亲自下了厨,做了两个地道家乡菜式,不管是不是正牌货,反正从前在乡下是常吃的。
熏了一脸的油烟,又忙着回房里去泡浴洗头,从新穿好旗袍,挽好了发髻,门铃就已经响起来了。
自敬生亡故以来,数这晚最热闹。
一行四人,连宋欣荣都来了。
“细嫂!”宋欣荣冲前来跟我握手,他一直对我很尊重,因是尊重敬生的原故,这我是知道的。
“荣叔!”我喜孜孜地,一直跟孩子一般称呼他。
从前贺杰小时,他父亲就是宠他,若是在暑假寒假,吃过早点,就把小儿子带上贺氏办公大楼,由着他在公司内胡乱转来转去,杰儿最爱转到荣叔身边。
宋欣荣就是跟他有缘份,老是抱着贺杰在膝上,两只手还是忙乱地拿着电话,跟在交易所出市的职员联系,气氛紧张得不得了,总要拔直咙喉的喊:“四元五角入汇丰,十万股!”
“三元七,沽,置地二十万股!覆盆覆盆!”
杰杰两只眼珠子转来转去,非常的习惯,绝对不骚扰荣叔。坐得累了,无聊时,喊荣叔一声,宋欣荣就摸出一颗瑞士糖来,塞到杰儿短短肥肥的小手上,他便又静静地把玩一会,才往嘴里送。
贺氏的同僚都爱贺杰,常说:“杰杰出来的那一天,必然是开红盆。”
都不知是真是假,敬生就是信以为真,老跟宋欣荣讲,这小儿子脚头好!又要把杰杰拜宋欣荣做干爹。
宋欣荣总是推,有日还特意向我解释说:“细嫂,生哥的好意我心领,其实我顶疼爱杰杰,只是不想高攀,反正心里头当他是儿子一般爱护就可以了,不尚形式。
细嫂是明白人,自然知道我的难处,谅解我的小家子气。“
我当然心领神会。
虽说是跟在敬生身边出身的老伙计,他本人的家当,亦已不差了,仍是无法跟贺家匹敌,差得太远了,无端攀上谊亲,别人不说什么,宋欣荣心里头也不好过。
其次,爱杰杰爱得如此出面了,有时已难免要看大宅那边人的面色。还实斧实凿地认上谊亲,就更不好说话。
我于是趁便时跟敬生解释过,才将此事搁置。
事实上,宋欣荣一直都对贺杰关心,对我也相当的友善。
他很紧张的打量我说:“听元哥一直说你这一阵子瘦多了,我还以为他形容夸张,怎么真的落了型,憔悴太甚了!细嫂,你要保重。”
“荣叔,你坐。也没有什么,敬生不在了,我就是不惯,过一阵子就好。”
“你跟贺聪是差不多年纪,抑或比他还小呢?现今看起来,像他的母亲!”宋欣荣惋惜地喊。
“论辈份身份,他的确是我儿子呢!”我倒无所谓,是老是颓,认了就是认了。
“依我看,贺伯母若是打扮打扮,我看要年轻得像贺智。”
潘光中说完这话,望住贺智,一股情意自眼神飘送出来,搅得贺智登时粉脸飞红。
恋爱的人,岂只神采飞扬,还真年青活泼。
我看贺智就真真突然青春得多,这跟衣着与打扮无关。
曾几何时,我望贺敬生一眼,或是敬生望我一眼,也还是贺智如今的那个模样,心上卜卜乱跳,通体热血沸腾,不知多兴奋、多舒服!
我是过来人,有什么看不出来。
贺智喜孜孜的走到我身边来:“我陪你去买几套西服好不好,别一天到晚的穿旗袍,还有,把头发剪短了,人就会精神清爽得多,别老是这种古古老老的发髻。”
我只是笑。心里头想,这还怎么得了?敬生才刚去世,我就扮起年轻相貌来了,惹人闲话。
贺智真聪明,鉴貌辨色,她就知道我的顾忌。于是摆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且扯了宋欣荣来主持公道,说:“荣叔,你算是长辈呢,来评评理,这个年头,三姨还是活在象牙塔里,老是船头慌鬼船尾惊贼,弄得自己整个人褪了颜色似,真叫人为她不值。”
宋欣荣看着我,语重深详地说:“细嫂,贺智的说话顶对。今时的确不同往日。
旧时呢,人言可畏。今日呢,人人都只顾自保。旁的人把你捧上天也不管用,你自己有多少实惠才最重要。细嫂,要是你还这样子活下去,如何捱得到贺杰成人长进,自立门户呢?“
这最后的几句话,叫我异常的心动。
是真要好好考虑,从详计议的。
总不能一天到晚孵在这房子里头,跟外界断了音讯似,将来怎么把江山交到儿子手上去呢?连江湖上黑白正邪都无法分析给下一代,未免敷衍塞责了。
社会上头,谁家子弟不是由父兄带着出身的?贺杰如果有日要碰得焦头烂额才得着一些经验与教训,我又舍得吗?
到那时候,做母亲的,站在一旁干著急,才惊觉自己没有本事,那就悔之已晚了。
晚饭在温暖而愉快的气氛之中渡过。
我一直留意到潘浩元吃得很多,却说得很少。
这也未尝不好。
饭后,宋欣荣要赶着走,连水果也不吃。
“加拿大的儿媳托朋友带了件毛衣回来送我,我好歹到酒店去会一会,也是礼貌。这就失陪了。”
“我嘱司机送你一程。”
我亲自陪荣叔走出大门。
上车前,他又握着我的手:“细嫂,真的今非昔比。从前有生哥,你可以安枕无忧,现今贺氏内半个心腹都没有,贺智到底是女孩儿家,将来有差池,只得她一把声主持公道也不成气候。你好歹要出来走走,不学多、也学少,别是被人家欺到头上去,也蒙然不知。”细嫂,宁可自己心知,放人一马,好过被受蒙蔽,死得冤枉。贺杰要靠你,就这几年光景要捱一捱罢了。“元哥是个老实正直的人,他提过,希望你到富华去行走,反正说话的只有元哥和我二人,人事顶简单,你就出来,看成上课也好,上班也好,当消闲也无所谓,一举可以几得,何必闷在家。”你不替自己拿定主意,只管什么人笑话的话,现今再行不通了。“
来欣荣拍拍我的手,才上车去。心思慎密的宋欣荣也如此说,就的确要注意了。
我走回小偏厅去时,只得潘浩元一人。
心里又不期然地抽动着,游目四顾,坐立不安。
“他们呢?光中与贺智呢?”我慌慌张张的问,甚而不见了群姐。
“是不是一定要找他们回来,你才安心?”潘浩元竟这样问。
我呆了一呆,若拿手往脸上一放,一定是烫热的。
我解释:“不是切开了一盆水果吗?他们吃了没有?”
潘浩元没有答我,只静静地睁着眼,看我在厅上团团转。
有点像斗兽场观众席上的皇侯贵宾胃,非常冷血而尊贵地望住场内那只将要作困兽斗的动物,心慌意乱地来往踱步,准备在下一分钟就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肉搏厮杀。
我的不得体与张惶,完全被对方看在眼内,心头更多焦躁。
“你坐下来!”潘浩元说,语音平定,且具权威性。
“坐下来,我给你说几句话。”
从前,敬生也是以这副类同的语调对我,我就总好象着了魔似,乖乖的如言照办。
如今,我也真的坐了下来,面对着潘浩元。
“敬生去世后,你适应得并不好。”他说。
怎么适应呢?
要我改嫁才叫适应得好吗?
念头飞快掠过心上,随即满头冷汗,只一忽儿功夫,那真丝旗袍就紧紧的贴在背上,只为汗出如浆之故。
我未免太离谱、太孟浪,怎么会想出这个念头来?
羞愧得两腮发热发烫,浑身僵直。
“这样子孤怜伶的过日子,是要令你胡思乱想的。”潘浩元竟说了这两句话。
“关心你,爱护你的人,只想你生活过得正常健康有建设性有前途,如此而已。”
潘浩元恳切地望住我。
“我的一番心意,你如果觉得并不单纯,并不可取,甚而并不可靠,我不怪你,我明白。但你身边对你好的人,无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向你介绍了一条你应走的道路。那些人包括宋欣荣、贺智、群姐、甚至潘光中、芬姐。他们是毫无机心,不求回报的希望你幸福,并有所成,你应该相信他们。”
我呆住了。
潘浩元这么说,就等于指责我好多心,以为他一直对我的关怀是别有用意的。
我真有这样想过吗?
是不是我作贼心虚?
抑或作贼心虚的是另有其人?
我看了潘浩元一眼,那健康的肤色上抹了一阵红光。
他其实也正在看我。
这叫不叫心照不宣呢?
“你的决定,我将永远尊重,绝不会以我的意愿为依归的,请放心。诚意地希望你跟在宋欣荣身边工作,因为这对你是好事,我其实并不常在富华,根本也不常常在本埠。”
话已说得相当露骨而明显了。
我只能答:“各人的好意,我非但心领,且会实实际际的筹算去。”
回到睡房去卸装,脱下了那袭旗袍,把发髻打散下来,在镜前站着。
身体还是如此的光洁粉白,肌肉依然是英挺在嫩滑的皮肤之内。
我伸手抚触着双肩、手臂,甚而沿胸膊,直下至腰际。
我宽松地叹一口气,感觉仍是滑不溜手。
当然才不过是一段短短的日子,今朝的人比黄花瘦,还落得一份凄迷的楚楚可怜,只怕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后。会把人整个都磨损得枯黄干瘪,神颓志丧。
我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下去。
躺在锦被之上,那种贴身的软棉棉感觉。益发令我想起了私情欲念,因而更念敬生。
不能再在潘浩元那番说话上钻牛角尖,由他怎样想当然吧,我必须谨记自己是贺家人,昨天是,今夜是。明朝亦是。
除了敬生,不可能再有别的人,此生也不作此想了。
然,总要把心神安顿,把体能虚耗,别是如此空荡荡的干折靡自己下去,以致于忽然间苍老,更令人惆怅。
贺智要陪我添置新装,我竟有一番兴奋,对她说:“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从乡下走出来,工厂工打不下去,便上大同酒家求职,那照顾我的同乡老表,就借我一套她最得体的衫裤穿在身上见工去。其后,还是预支头一个月的薪金,去缝了件旗袍,当成制服穿。那种感觉,现今跑回来了!“
贺智笑:“包保把你打扮得比那一次更满意。”
我以前很少逛名店,跟在贺智后头走,声势还是响亮的。
店员殷勤招呼,贺小姐前贺小姐后的,简直当她是宝。
贺智低声地对我说:“看,这就是外头世界,认钱不认人,我每月负责她们大量佣金,故而对我鞠躬尽瘁。等下你大手笔的买上几套,立即升价十倍。”
年轻女店员原本只着意招呼贺智,其后看我是试穿一套,买一套的样子,便忙不迭的围绕在我身旁,服侍得非常妥贴。
那些时款套装也真是方便,差不多每一套穿到我身上来都好看,舍不得放弃。
最难得的是整个人都变得年青,这感觉竟如此有效地影响着我,是始料不及的。
以往不是一直嚷,老了老了,好似一点都不在乎。
其实不然。
贺智也买了两套,其中一套黑色镶米白缎领的套装,贺智喜欢极了,就是那尺码太窄,腰身反而显得臃肿,坏了贺智甚是适中的身裁,诚是美中不足。
我说:“大一号就理想了。”
店员立即说:“请等一等。”
只钻到里头去一转眼的功夫就把另外一套大一码的西服取出来:“贺小姐,这一套合你的心意了。只是要待明天才能送上你办公室去。”
贺智点点头:“不相干,你们肯定别是穿用过的就成了。”
“贺小姐请放心,我们有专业道德。”
我忍不住插口:“怎不现在就一起包起来拿走呢?”
贺智把我拉到一旁,低声道:“他们要多赚一笔。”
然后,贺智细细的向我解释,这等名店也做一些娱乐或欢场中人的生意,电影电视艺员小姐们有空踱至名店,选定几套贵价货,然后把冤大头带来,签了信用咭了,服装才转一个圈,就自动送回店里来,物归原主,名店回佣百份之五十,衣服再重新安然无恙地卖出去。小姐呢是要现钞多于名牌服装,名店呢,多一条财路。
“刚才那一件定是什么人订下来,等有人认头找了数,再卖给我。”
贺智笑道:“我跟贺勇就不知多少次一齐为同一袭眼装付过钱!”
从前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真不是这样的。
别看轻我们酒家女。客人要多打赏小账,千多万谢,那是全层楼同事有份摊分的正当收人。
至于说,个别客人送礼物,我们还真不轻易肯收。收礼是真要对对方有好感,且是赏他面子,认定友谊的表示。
且收了人家的礼物了,就一定用。譬如说我认识了敬生有成年的日子,才肯收他一件衣料,还立即缝制了,穿出来,让敬生看,以示谢意。
怎么现在江湖行走的女人,真的面不改容、大小通杀。完全不怕流言、不顾面子,更不谈骨气了?
才出来买几件衣服,就上了新的一课。
外头的新人情、新道理,还真是大把大把的有得我慢慢学,好好学呢!
签完了信用咭,贺智看看表,对我说:“有个会议等着我去主持,迟不得。你先到发廊去,我给那发型师补个电话,招呼一声,他自会给你剪个好看的发型。”
我其实心上是十五十六,多买几套服装替换无所谓,要更改发型,真有太多诚惶诚恐,贺智这么一说,我乘机退缩下来,说:“那就改天吧!你忙你的。”
“三姨,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你这发髻怎么配时款西服?”
“我这就把头发束上去,用个发夹夹好了,不梳髻,不就成了!”
正扰攘之间,竟见走进来一位贵夫人。
我很自然的喊了一声:“大嫂!”
是贺聪的妻。
贺阮瑞芳跟我平日的关系不怎么样。
她看上是个淡淡漠漠、喜怒不大形于色的人。
常碍着了聂淑君和她母亲阮柳氏的身份和关系,我当然的不指望阮端芳会对我额外的友善。
因而,我们一直的保持了距离。
然,想深一层,我对阮端芳的印象还不是太差的。
只为有一次,一位表亲摸上门来,向聂淑君求借。
这种事对贺家来说呢,也是司空见惯了。
实实在在的,敬生年中就预定了一笔钱,无可避免的用在接济亲朋戚友上头。
敬生还自定一个规矩,凡是第一次开口求借的,除非数目太离谱,否则必定帮忙,然,下不为例。坚持旧债未还,新债免问。
我呢,心就比较软,事必问明问白借款的理由,如果觉得其情可悯,境况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