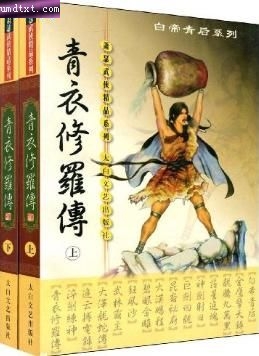大唐游侠传-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旭道:“只怕醉了写不好,教司马见笑。”崔宗之笑道:“你写草书也象李学士写诗一样,越醉了越好,何必客气。”
贺知章叫店家取了纸笔来,就在旁边一张空桌上铺好了纸,张旭选了一枝大号的狼毫笔,蘸满了墨,崔宗之念道: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二斗始朝天,路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街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伟前,醉中往往受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商谈雄辨惊四筵。
崔宗之念完大家便哄笑一场,贺知章道:“真是把咱们的醉态写得淋漓尽致!”张旭大笔挥舞,墨汁飞溅,写完了这首诗,他的面上,东黑一块,西黑一块,连胡须上也溅满了墨,旁边的人,衣裳上也是点点斑斑的墨迹,张旭哈哈大奖,挥笔笑道;“你们是醉态可掬,我却是丑态毕露了!”
贺知章道:“可借你不早些来长安,听说湖州乌程酒极佳,你就是为了乌程酒才去就湖州司马之职的,要是你在长安,老杜就应该写饮中八仙了。嗯,我忘了问你,你不在湖州任内,却上京来干什么?”
吴筠道:我是奉召进京述职的,来了五天,却尚未蒙皇上召见。”贺知章面有诧色,道:“皇上极少顾问政事,却怎的会突然召你进京述职?”沉吟半晌,忽地说道:“你可见过杨国忠没有?”吴筠道:“没有。”贺知章道:“你赶快各办一份名贵的礼物送他。”崔宗之笑道:“若是急切之间备办不来礼物,送金子更妙。我们这位宝贝相爷一见了黄澄澄的金子,就容易说话了。”
吴筠大笑道:“我为官数载,两袖清风,那来的金子?再说,我若有钱,自己不买酒吃么?为什么要送礼给杨国忠?”
贺知章道:“司马有所不知,自杨国忠专权之后,卖官晋爵,无所不为,州郡长官,若不是他的人,便陆续撤换。依我看来,召你入京述职,只怕是他的主意。他正在等着你送礼呢,谁知你却这样不懂人情世故。”笑了一笑,继续道:“要是你宦囊不便,咱们几位酒友给你凑一些如何?他大约因为你政声颇好!所以迟迟不敢换你,只是召你述职,想等你找上门来。你稍为给他一点好处,卖他一点面子,大约也就可以无事了。”
吴筠愤然说道:“小弟宁可丢了这项乌纱,也决不巴结权贵,送礼之事,再也休提。”
贺知章道:“吴兄廉洁自持,当然是好,可是你就不想想,要是湖州司马,换了一个贪鄙之人,岂不是苦了湖州百姓?我们不是劝你巴给扬国忠,而是想为湖州留一个好官。唉,现在天下的好官太少了,能留得一个就是一个。”
崔宗之道:“要是吴兄不肯送礼,还有一法,可以找李仆射给你讲讲情。他也是咱们酒友之一,杜甫‘饮中八仙歌’所说的那位‘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杨杯乐圣避称贤。’就是说他。李仆射虽然豪奢,人却还是正直的。”
吴筠叹口气道:“贺老大人劝我以湖州百姓为重。此心可感,只是如此官场,实在已令我心灰意冷,再说,纵使花钱打点,我却不是个同流合污之人,这个官又能做到几时?诸兄盛情心领,这项乌纱,能不能保,听天由命吧。”
贺知章等还想再劝,忽听得楼梯声响,跑堂的弯腰曲背,道:“伺候令狐大人,令狐都尉,今天你老来得迟了。”
吴筠问道:“什么官儿,这样威风。”贺知章笑道:“大约是羽林军(即彻林军)的军官专职护卫圣上的,你别瞧他们的品级不及咱们,可比咱们阔气得多呢。这班侍卫老爷多是这家酒楼的常客,堂倌当然要巴结他们。”一个官儿道:“官中的都尉来了。不知是不是皇上要召李学士入宫?”
说话之间,只见三个军官走上楼来,当前的一个穿着羽林军的服饰。十分神气,后面两个军官,身披驼绒军装,腰围金带,脚踏蛮靴(一种长统的马靴),看这装束,便知是边军的高级将领。
那羽林军军官道:“我给你们带来两位贵客,这位是田将军,这位是薛将军,快给我们找一副雅座。”堂倌连连的应诺。还忙去收拾一副临窗的座头。
跟在令孤都尉后面那个身体有点发胖的军官,用眼光一瞥,见李白伏在桌上呼呼噜噜的打鼾,鞋子帽子都给扔在一边,远远就闻得到他那股酒气,还有一个张旭,须子上墨汁淋漓,兀自在那里手舞足蹈,要和别人斗酒,那军官皱起眉头,道:“人家都说这是长安最有名气的一家酒楼,却怎么容得这些穷酸在这里撒野。”令狐都尉不待他的话说完,急忙拉着了他,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打瞌睡的那个人正是皇上所宠爱的李青篷车学士。”那个军官吓了一跳,连忙禁声,脸色尴尬之极,偷偷的朝李白张旭那两张桌子望去,见那些人闹酒的闹酒,谈天的谈天,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话,这才放心。
这时段珪璋已回到了他原来的座头。铁摩勒低声说道:“这两人就是安禄山手下的田承嗣和薛嵩。”段珪璋道:“沉住了气,不可闹出来。”
酒楼上有三张桌子,坐着的都是宫中的侍卫和羽林军军官,见了令狐都尉,纷纷起来招呼,那令狐都尉哈哈关道:“我给你们介绍两位好朋友,平卢军的田将军和薛将军,他们两位是安节度使的左右手。”在各路节度使中安禄山兵权最大,又是杨贵妃的干儿子,那些恃卫们和军官们对田薛二人纷纷趋奉。
段珪璋听他们的言语,知道那个令狐都尉名叫今狐达,在这群军官中似乎职位最高,那些人对他都很恭敬。他们则是护送安禄山人宫的,安禄山给杨贵妃留下了,要他们到晚上才去接他。
段珪璋心想:“这酒楼正对着明凤门,我今晚再来,在此守候,等这两家伙接安禄山回去之时,我暗地里跟踪他们。”铁摩勒那日在马蹄下救人,田薛二人虽然在安禄山的左右,但铁摩勒那日是个乡下少年,现在却打扮成硅家子弟的模样,田薛二人那里认得出来?何况他们的眼光都被李白的醉态吸引住了,更没有注意他们。
不过段珪璋却不敢大意,生怕给他们窥出行藏,已然得到了安禄山的消息,便想离开酒楼。
正待叫堂倌过来结帐,酒楼上又来了一个客人,一进来就大声问道:“李学士可是在此喝酒么?”
这人也是个武官装束,但与田薛二人却大大不同,他着得是一身粗布军装,严冬时分,仍然穿着草鞋,但他腰挂长刀,刀鞘却是名贵的犀牛角做的,样式古拙,刀鞘上还缠有铁丝,要不是他挂着这把名贵的宝刀,那就完全象一个穷大兵了。
段珪璋抬起头来,打量了这入一眼,不觉暗暗吃惊,这军官约有三十岁左右,双目炯炯有神,虬须加戟,满面风尘之极,却掩盖不住他的侠气雄风,段珪璋蓦然想起了一个人来,但却不敢断定是不是他。
令狐达喝道:“你这厮是什么人?李学士是你随便见得的么?”
那军官冷笑道;“我找李学士关你什么?要你出来多事?”
薛嵩道:“你大呼小叫好设规矩,李学士正在好睡,你胆敢吵醒他么?看你这粗野的样子,李学士就不会交你这样的朋友!”薛嵩刚才认不得李白,出言无状,甚感难为情,正好趁这个机会,一来为令狐达助威,二来讨好和李白同来饮酒的那班官儿,心中想道;“这回大约不至于看错人了吧,看来这厮最多不过是个边军的小军官,谅他怎能识得了李白。”
薛嵩拦着了去路,那军官大怒道:“你狗眼看人!”平掌一推,薛嵩冷笑道:“你耍打架么?”立即施展擒拿手法来扣他的脉门,想把他一下拿着,反扭过来,在众军官面前,博个哈哈一笑。那知他没有抓着人家,却反而给那个军官一掌推开,跄跄踉踉的几乎跌倒!
令狐达大吃一惊,要知薛嵩是个有名的青州剑客,以剑术、暗器与擒拿手称为三绝,而今他竟然一交手就吃了对方的亏,而且还令令狐达也看不出那个军官是怎样闪开薛嵩的擒拿手的。
薛嵩大怒,便想拔出剑来,贺知章上前调解道:“李学士结交遍天下,薛将军敬爱李学士之情可感,这位……”那军官道:“我姓南,东南西北的南。”贺知章继道:“这位南兄既然是李学士的相知,对薛将军的阻拦也不应见怪,李学士当真是多喝了几杯,现在已睡着了。”贺知章这番话说得婉转之极,薛嵩又知道他是个大官,只好忍住了气,不敢发作。那性南的军官游目四方,问道:“那位伏在桌上打瞌睡的人就是李学士吗?”
贺知章诧道:“不错,就是李学士。”薛嵩已冷笑道:“闹了半天,原来你是并不认识李学士的呀!”
那姓南的道:“我几时说过了我认识他,我不想谬托知己。”
贺知章道:“然则阁下找他何事?”那性南的道:“我不敢谬托知己,可是另有一位是李学士知己的人,托我稍一封信给他。”
贺知意道:“是那一位?”心想:“李白的知己朋友,说出来大约我即算不认识也总会听过名字。”那姓南的道:“是一位姓郭的朋友,这封信我得亲自交给学士,不便转托他人。”着情形是不愿说出这姓郭的名字。
贺知章心想道:“我可未曾听李白提过有姓郭的好朋友啊。”但他老于世故,别人不愿说,他也不便再问,当下说道:“李学士这觉不知要睡多少时候,可要我唤醒他么?”
那姓南的军官道:“不必,不必。我也就在这里喝酒等他醒来好了!”高声叫道:“打五斤好酒,切三斤牛肉来!”
薛嵩歪着眼睛,洋洋得意的说道:“如何,我这双眼着人还看得准吧?”言下之竟,即是说:“你看,我说李学士不会有这样的朋友,没有错吧?”那姓南的大盅大盅的喝酒,不理会他。薛诡又笑道:“这是长安最出名的一家酒楼,哈哈,却想不到有人把他当作路边酒肆了。”这是嘲笑那姓南的只知道叫路边酒肆所常卖的东西,这酒楼上有多少美味的菜式他不叫,却只叫白酒和切牛肉。
那姓南的把酒盅重重一顿,大声说道:“我吃什么东西,也要你管么?”
那酒盅是青铜做的,被他重重一顿,只听得“当”的一声,酒盅陷入桌内,与桌面相平,四座皆惊,薛嵩亦自有点气馁,但又不愿当众失了面子,退了一步,说道:“你真发横。这里不是打架的处所,有本事的,你敢与我约个地方比剑么?”口气已经软了许多。那姓南的军官冷笑道:“随你划出道儿,我一准奉陪便是。待我见过李学士之后,立刻便可赴约。”
段珪璋见了这人的身手,心里想道:“这一定是他了,想不到在此地相遇。”但酒楼上人多口杂,他虽然认出了这个人,却也只得暂时忍耐,不敢立即去招呼。
田承嗣与薛嵩同来,薛嵩与那性南的发生争斗,田承嗣却躲在一边,禁若寒蝉,段珪璋暗里留意,只见他的面色铁青,眼神注定那个娃南的军官,屡次手按刀柄,却始终不敢站出来,段珪璋暗暗奇怪,心道:“田承嗣和这个姓南的一定有什么过节,看来只怕好戏在后头。”
薛嵩心道:“你手上功夫虽然了得。比剑我未必会输给你。”正要与那姓南的订约,贺知章等人也正要出来调解,就在这乱哄哄之际,忽听得“当、当、当”三下锣声,有人高声报道:“圣旨到!”
酒楼上肃静无哗声,有品级的官儿都站了起来,避过两边,酒店的主人急忙上前迎接道;“迎中度使大人,不知圣旨宣召那位大人。”这样的事情在这酒楼上已发生过几次,主人也知道定然是宣召李白,但仍然不能不有此一问。
唐朝的太监奉目出差的尊称“中使”,但这次率领几个小太监出来找寻李白的人,本身却不是个太监,而是二个乐工,名叫李龟年,虽是乐工,但甚得皇上宠爱,授为“拿乐御奉”,身份不比寻常,贺知章等人都认得他。
李龟年上前高声说道:“奉圣旨立宣李学士至沉香亭见驾。”他背后一个小太监,手捧冠袍、玉带和象笏,便来找寻李白。
李龟年笑道:“李学士果然又喝醉了。皇上立即便要见他,这却如何是好?贺大人也在此,帮忙我一同唤醒了他吧。”
两人正在扶起李白,李白忽地双手一推,酒气喷人,哺喃念道:“我醉欲眠君且去。”头也不抬,又倒下去睡了。贸知章和李龟年给他一推,险险跌倒。李龟年苦笑道;“这次比上次醉得更厉害了,怎么办呢?”
小太监道:“咱们抬地走吧。”李龟年道:“总得让他换过朝衣。”叫道:“店家,打一盆水来。”
贺知章官居秘书少监,也是侍从皇帝的近臣,与李龟年又稔熟,李龟年已宣读了圣旨,彼此不必再拘什么礼节,贺知章问道:“皇上这次急於宣召李学士,为了何事?”
李龟年道:“今年扬州贡来了许多种牡丹,都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下。今日牡丹盛开,皇上命内侍设宴于亭中,同杨贵妃赏玩,命我引梨园中的一十六色子弟,各执乐器,前来承应。奏了几曲,不合上意。皇上便叫我停住,说道:“今日对妃子、赏名花,岂可复用旧乐?你即将朕所乘的玉花驰马,速往宜召李白学士前来,作一番新词庆赏!”你瞧,皇上的御马都牵来了,就等着李学士去呢,急不急煞人?”
说话之间,店主人已亲自把一盆冷水捧来,李龟年要了一条毛巾,也顾不得天寨地冻,亲自把手巾没了冷水,扭了两下,使往李白的额角敷去,又叫店家取来了四面屏风,围着李白,笑道:“幸而我熟知学土的脾气,预先到翰林院取了他的冠袍、玉带、家笏来,不出我之所料,他果然是一袭布衣,在此与诸公饮酒。”
李白等人被屏风遮住,段珪璋瞧不见内里情景,过了一会,只听得李白的声音说道:“真煞风景,我还未喝够呢,做什么诗?”李龟年唧唧咕咕,似乎是在耳边低声求恳,过了片刻。又听得李白笑道:“吓,扬州的名种牡丹都盛开了,大红、深紫、淡黄、淡红、通白各色各种都全,皇上又备了凉州美酒,等我去喝,哈,这倒对了我的口味了,瞧在扬州牡丹的份上,我就去一趟吧。”楼板冬冬作响,原来当他说到各种牡丹、凉州美酒之时,禁不住手舞足蹈。随着又听得悉悉索索的声音,敢请他已是脱下布泡,换上朝衣。
再过片刻,只见李白推开屏风,走了出来兀自脚步跟跄,朦胧醉眼,酒气熏人,几个太监前呼后拥,左右扶持,走过那姓南的军官座前,李白忽然停了下来,道:“好一位壮士,咦,你、你、你……”那姓南的道;“我给令公带了一封信来,正要见你。”话未说完,太监们早上前将他拉了开,喝道:“什么人,赶快滚开!”
李白怒道:“岂有此理,你们要赶走我的好朋友么?”双臂横伸,扶着他的那两个小太监,“扑通”一声,跌了个四脚朝天。
太监们大惊失色,旁边一个官儿好生诧异,小声问他的同伴道:“咦,刚才这人还不认得李学士呢,怎的却又忽然是他的好朋友了?”
李白推开了太监,东倒西歪。摇摇晃晃的踏上几步,指着那个姓南的军官哈哈笑道:“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你。你,你,你一定是南八兄,敢知荆轲胆如鼠,好呼南八是男儿!哈,哈,哈,见了南八,谁还理会什么贵妃娘娘,来,来,来,咱们再来喝酒!”
李龟年早就上前拉着南八,对他一揖,悄声说道:“皇上等看见李学士,你帮个忙!”
李白一步跨得太阔,身躯倾倒,扶着桌子叫道:“南八南八,你怎么不来喝酒,喂,喂!你刚才说什么?有什么阔气的老公公托你带东西给我呀?哈,哈,哈,你南八怎会是给人送礼的人呀?笑话,笑话。快来说清楚了!”李白尚未醉醒,又一心放在南八身上。竟未听清楚他说些什么,将他说的“郭令公”,当成了什么阔气的老公公了。
那性南的军官大笑道:“学士果然是我辈中人,但现在楼下就有御马等着你骑进宫去,你纵然陪我吃酒,我也喝得不痛快,不如待你今晚无事,我再去与你吃个通宵!”
李白道:“好,你说得也对!待我见皇帝老儿再去见见你,的确可以吃得舒服一些!”
贸知章忙道:“李学士住在我的家中,你问城西贺家就知道了。”那姓南的道:“你老先生是贺少监,我知道。”他知道贺知章的意思,是要他让李白快走,他一想托他的说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而李白又在醉中,在这样的情形下,那封信他也不方便在这个时候交出来了。
李龟年与那班大监急忙拥着李白下楼,李白那班酒友也都跟着散了。那姓南的军官摇了摇头,叹口气道:“玉门已自燃烽火,宫门沉沉醉歌舞……”蓦地拍案叫道:“可惜了李学士!”仰着脖子,将酒盅余酒,一倾而尽,掷了一锭银子在桌子上面,便要离开。
令狐达与薛嵩忽然走了过来,令狐达陪笑说道:“南兄且慢!”
那姓南的军官剑眉一坚,朗声说道:“什么地方。是不是现在就去?除了这个姓薛的之外,你是不是也想要凑上一份?”
令狐达笑道:“南人兄,不是约你比剑。”那姓南的圆睁双眼说道:“不是约我比剑,你留我作什么?”薛嵩上来抱拳说道:“方才不知吾兄,多有冒犯,还望南兄勿怪。”
南八肚里暗暗好笑,心中想道:“想是这厮见了李白如何待我的。故此马上便变了一副脸孔!”他是个豪爽的人,虽然看不起薛嵩,但别人既来陪罪,他便也哈哈笑道:“小小一点言语角逆(冲突之意)何足介怀?薛将军既是不必要我比剑,那就请容我先走一步吧。”
令狐达道;“不打不成相识,南八兄多坐片刻何妨?”南八道“不敢高攀!”令狐达笑道:“南八兄这样说,就是还有见怪之意了。”薛嵩也道:“彼此都是武林同道,令狐都尉又是最喜爱结交朋友的,南八兄何必这样吝于赐教。”
南八心道:“这两个人的武功还过得去,却偏生这么讨厌!”只得再坐下来,谈谈说道;“两位有何指教。”
令狐达笑道:“正是有件事要请问南兄,方才南兄所提到的郭令公可是九原郡守郭子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