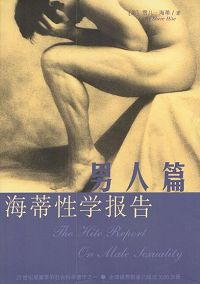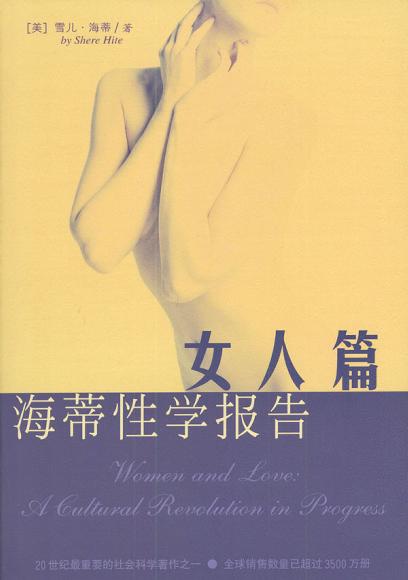报告政府-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吗?”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啊。”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小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成人吧……”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肯定是他。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事情不要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吗?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邪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她今天早上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任务重,要求高,一心要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干扰——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
“对不起,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被子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游,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啊。”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啊?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化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或者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吗?”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脸增添任何表情。学员只对柳老师抱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曲子里既有泥土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作为游戏之作,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竟是一支圆舞曲,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曲子,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但还是不够斯基也不够柯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嘿,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啊。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他发现有些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珈。用他的话来说,瑜珈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有饭吃了,大体上能吃饱了,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牲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