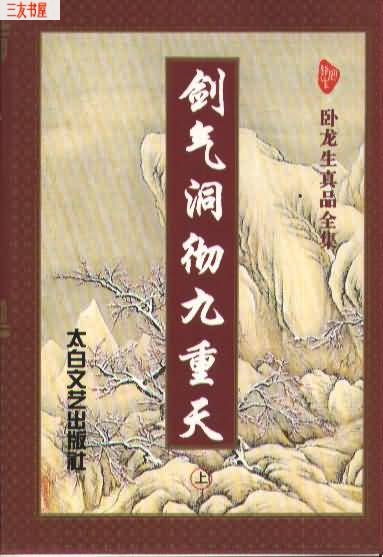九重恩怨-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单是江家一下子损失七亿以上,震撼力就足以使传媒穷迫不舍、使行内人津津乐道。
在还未有更新鲜吸引的市场资料转移众人视线之前,我还是谣言是非的对象目标,无法幸免。
只有脱离那班群众,才有呼吸一下自由自在空气的实在,今晚的机会也真是绝无仅有。
我不期然地对这些短暂的喘息与欢愉另眼相看。
“今晚想到吃些什么吗?”那庄尼间。
“什么都成,食物要最美味可口,地方要宁静舒适,好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明天才回到香港去。”
“要这两个条件都齐全,全多伦多只有一家。”
“那就去那家好了!”
庄尼皇我一眼,微微有点错愕。
我问:“有什么不对眼的地方?”
他慌忙解释:“没有,没有。只是我有点惊骇。”
“为什么?”
他终于腼腆地答:“东方人的面部轮廓很少有如此澄明清朗的线条,从侧面看,你仍是个好看的人儿。”
跟着他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个注脚。
“可惜,就算好看的人儿,也要闹夫恋。可想而知,人的福份并不因为天生有什么条件,或是后天作过何种努力,而定夺厚薄。”
我不能以为他的这番话只是冲着我而发。事实上,庄尼也是个漂亮的男人。
他的外在条件看上去,并不比我差。
我忽然地失笑了,谁个在今日碰上我俩,也许会认定是相当配衬的一对。
怎会想到都是被遗弃的可怜人?
“你笑什么?笑我胡乱讲人生哲学?”庄尼间。
“不,我只是一时间想起等下有顿好吃的,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这个借口未免牵强。然,不要紧,偶然拾得的一段相叙,彼此都没有在言行上斤斤计较的打算。
庄尼把车子直开到一条林荫道上,两旁的房子互相距离得相当远,中间是一大片的林地。
很明显地,这是个顶高尚的住宅区。
加拿大东岸的屋地普遍比西岸狭窄,年来价格突飞猛涨,使不少在多伦多定居的人,往西迁徙,也是为了西岸阳光充沛之外,房子还真价廉物美。
能像这一区,差不多每幢独立房子的屋地范围都占去半个街口位置的,实在绝无仅有。
庄尼把车驶进一条两旁种满了红白杜鹃花的小车路上,再停到一幢白色殖民地官邪式的房子门前。
“不骗你,全市最清静,最能供应色香味俱全食物的餐厅就在这里头。玛利亚,你现今可以作出一个决定,是否愿意到舍下作客,一尝我的厨艺,抑或,你信不过我,那就改道到一般的食肆去!”
信不信得过他呢?语带双关,这里头可能是另外一篇文童。
谁不是白白担了个圣洁的外表,而实际上做着满足私欲的种种劣行?
任何人目睹了当日社青云对我的那副脸孔,都会相信他纵非至情至圣,也必定忠诚正直。谁能料到他竟是好险狠毒,心如蛇蝎?
我已曾经沧海。
世上再恐怖不过的欺骗手段再加之于我身上,都不能跟我承受过的相提并论。
玛利亚今夜,何惧之有?真想不到庄尼竟有如此高雅壮丽的巨宅作居停。
坐到那宽敞的客厅去,享受着完全十九世纪英式的贵族家居布置,一种皇侯风范、泱泱气氛弥漫着空间,令人肃然起敬。
庄尼给我调校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说:“你随便浏览,我这几完全没有机关,也没有秘密,什么角落你都可以走,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翻。”
“你呢,你不在我身边陪我?”
“我到厨房去弄晚餐,只一会儿就来!”
我悠闲地在屋内逛着,客厅的左侧是个中式饭厅,一张足可坐二十人的大圆饭桌放在正中,跟垂下来的金澄澄欧式大吊灯互相配衬辉映,已经很气势如虹。
客厅的右侧,是两个相连的房间,一个是较小的西式饭厅,椭圆形的餐桌,伴以八张餐椅,都罩上大红的椅罩,在椅背后扎着一个大红蝴蝶结,宛如一个到舞会去跳宫廷舞的少女,正微微屈膝,回礼舞伴似的。加上墙上名贵缤纷的挂画,整间餐厅都出落得热闹而温馨,别具韵味。
另外一向是书房,三面墙都是高耸至天花板的书柜,整齐地徘满了书籍。驻足细看,竟是中英巨著,琳琅满目。
这庄尼那么能学贯中西?看不出来。
诚然,我应该知道看得出来的往往并非真相。
堂前的乙道螺旋形云石楼梯,向上一定是通往楼上的几间睡房,向下则一直带往地库。想地库也不外是那些游戏室,桑拿浴室之类,我都没有兴趣观赏了。
正想走到厨房去看看庄尼怎样弄我们的晚餐,他就出现眼前,一把拉起我的手,说“来,一切已经就绪,我们先饮杯酒,吃一点餐前的沙拉,醒醒胃!”
我们绕道自客厅的一扇抽木镶玻璃的双掩门,通到一个罗马式的室内泳池旁边。
泳池呈长方形,在弯位处竖立了一身布满线条的大圆柱,头顶是玻璃盖成的大天窗。已见一两颗疏落的星星,那么的由远而近,仿佛等一会就会掉进池中,微微溅起水花,添一点生气似的。
晚餐桌放在泳池旁,只有两个位置,除了精巧矜贵的餐具外,就是一大蓬优怨而瑰丽的艳红杜鹃,跟那插了六枝红色洋烛的纯银烛台,一齐霸在餐桌中央,那么的令人心旌摇荡。
白酒是顶上好的品种,人口一阵芬芳,真能齿颊留香。
连那凯撒沙拉,都其味无穷。做这菜最考功夫,一般不是调得稍咸而变得略带酸味,就是过淡。庄尼的手势肯定是恰到好处。
“每吃完一道菜,我们都慢条斯理地呷一会儿酒,庄尼才捧出另一度菜来。
那白菌煎鹅肝,和香蒜牛仔肉,都吃得我津津有味。
我不禁歪着头想,这么好条件的一个男孩子,怎么可能闹失恋。
随即我甩甩一头短发,一并把这个意念都抛到九霄云外。
庄尼的背景强得过我吗?
然,有目共睹,我如何地惨遭茶毒。
杜青云至兀不渝地爱着他那位青海竹马的陆湘灵,为她的被迫沦落风尘而讨回一个公道,事必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向当年害惨了陆家的江尚贤报复,因而要我承担了重罪。
很明显地,我纵有百般可爱,千种能干,万样德行,在杜青云心目中都不值一文。
还是那条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的道理。
一念至此,竟对眼前人生了怜悯同情的爱心。
真的,相逢不必曾相识,彼此能说着同一语言,心照不宣,就是天涯知己。
吃罢了那个可口的甜品,我的感慨更深。
问庄尼:“看过一个香港流行小说名作家亦舒的那本《喜宝》的小说吗?”
庄尼摇摇头,脸上写上问号。
“故事说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就愿意下厨为他悉心泡制一度美妙的甜品。”
庄尼凝神望住我,眼里荡漾着无限温情与温馨。
没想到吧?
说着这么一句具挑逗性说话的不是庄尼,而竟是我。
我正在逐步实现我预期的后果。
以一种温柔温驯的眼神,回应着庄尼。
他双颊泛着配红,竟有点口吃地对我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的问题?我……”
“那就不要回答好了!”
庄尼似在搜索枯肠,希望找出一组适合的辞句,对我们这番偶遇的感情作出交代。
第二章
显然地,他力不从心。反倒由我轻松他说出他心中的感受。
‘能以一个新人替代;新人,填补心中的遗缺,总是一种踏实的感觉。人要自救,因而不可轻率地放过这个机会,即使只能短暂性疗治痛楚,也还是值得恋栈、舍不得放弃的,是吗?是有这种感受吗?“
名副其实的红烛高烧,映红了的竟是庄尼的脸。
我却刻意地要保持平静。
庄尼的眼神开始灼热,像两朵小人焰,慢慢随着室内的温软气流烧到我的脸上来。
他站起来,步至我跟前,强大的身躯又像当初相逢时的模样,挡在我眼前,掩住了我的视线。
这一次的分别是,我还未及抬起头来,他已经伸手将我一把拉进他怀里。
女人在男人健壮有力的臂弯之中,一般都能产生莫名的安全快感。
我学习完全放松自己,让身子与心情,都像浮在碧波之上似的。绝不挣扎、绝不回顾、绝不紧张。微微的载浮载沉,好使我飘荡得至久至远至舒畅。
这是一个必须实习适应的过程。
并不需要躲在自己心爱人儿的怀抱之中,才感到幸福。
事实上,世间哪来这么多真情真义?
有的话,也未免表达得大恐怖,即如杜青云为了陆湘灵,而残害了我,就是活生生的现成实例,男女之间的相悦,自今日始,我应视作生活上一种可以争取的情趣,也同时是能够发挥特殊功能以达到个人目的之投资与手段。
这个意念,自杜青云串谋害得利通银行股份狂泻与发生挤提之日始,已在我心滋长。
于今,是我的些微幸运吧,遇到这么一个如此可喜的试练对象,怎容错过?
两颗寂寞的心,两个孤独的人,很自然地会彼此需要,互相利用。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是资产而非负累,能制造欢乐,能产生喜悦。
想着,想着,精神完全进入迷糊与迷离状态。我浑身松懈,有如一团海绵,尽情吸索与享受着男欢女爱的兴奋。
一点都没有困难!
好的开始往往是成功的一半。
当我静静地躺在庄尼的身边,看着他赤裸的肩膊,因着均匀的鼻息而甚有节奏地微微鼓动时,我睁着眼冷笑。
要完全站于不败的地步,只有一个秘诀。
务必将一件事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分析出来,然后选最坏的那个可能,作出预防与应变措施。
过往,我犯的最严重错误,就是大一厢情愿地将事件看得简单、将人性看得善良、将效果看得乐观。
拿我跟庄尼的这段一夜情缘作为实验吧!
首先分析整个相遇与结缘的过程。如果庄尼说话可信,那自然是他跟爱人开谈判,对方爽约,等于表示恩尽义绝,顿成陌路,庄尼在沮丧之余,偏巧遇上了我。
一个并不难看的女人,出现在情怀历乱,心绪不宁之际,很自然能起到相当的解慰作用。
当然,我不必高估庄尼的失意,那跟我的创伤固然是小巫见大巫,就算跟一般少男少女的所谓失恋比较,也还可能有一段相当距离,因而,我那么容易地扮演了替身的角色!
以上是正途而合理的推论,却失之于表面化。
换言之,往最坏的另一个方向分析和构思,得出的故事情节与画面,可以完全不同。
会不会是多伦多一个无聊的纨绔于弟、惨绿少年;手上大把光阴与金钱,日中忙不迭地寻求各类新刺激呢?
某日黄昏,路过大酒店酒吧,瞥见有个形貌不俗的单身女郎,在饮闷酒,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上前搭讪。
至于他的表现和藉口,更不必担心,真正唾手可得,俯拾皆是。
鱼儿上钩了,半个子儿不用花,就春宵共度,成全他一个凄迷美丽,如幻似真的爱情短篇,不知多爽畅多温馨。自编自导,免费合演,认真价廉物美。
这个推测未免对庄尼苛刻一点。
然,对他仁厚,寄予温情与信任,如果万一真相确然有将我愚弄的成分在内呢,仍是我要吃亏。
尤有甚者,这相貌堂堂、翩翩风度的庄尼,会不会老早沦为以色相赚安乐茶饭的舞男呢?准敢百分之一百抹煞了这可能性。
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处于下风,都要戒备、预防、甚至先下手为强。
这一夕的欢娱必须是我试练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功课。我完完全全不准备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客串娱乐。
单是为了获得这个保障,我就有理由进行我的把戏。
蓦地翻过身来,穿戴停当。
庄尼显然仍在熟睡之中。他刚才过分卖力,以致疲累不堪。
这也教训了我,千万在每事每物上留有余力,以防不测。
我冷笑。
打开了手袋,取出一支唇膏,写了两行大字在庄尼睡房的镜子上。
“风流岂会无价,欢迎成为我们的一员!”
写毕,差点没忍得住哈哈大笑,才扬长而去。
走在街上,天色只是微明。
淡淡的晨光透过街道两旁茂密的树木,稀疏而勉强地洒在灰白的石屎路上,令眼前景致凄清而迷惆。
一两只早起的小鸟与松鼠,奔窜街头,使画面更添了一分惶惑,带一点忙乱。又开始营营役役的一天了罢?
我走了一个街口,才看到一个公共电话亭,摇电话叫了一部计程车,将我带返酒店。
立即结了帐,提起简单行李,直出机场。
我改乘早班机先赴温哥华,留在西岸接机返香港。
坐在航机之上,处于蓝天臼云之间,我的心,还是冰冷。
从小到大,我其实很晓得自爱。
父亲虽如珠似主地呵护我,可从来都不作任何纵容。
他尤其害怕显赫的家势,丰厚的家资会成为我品格上的腐蚀剂,使我变得横蛮无理、独断独行。
我的确在非常填密、保守而且正面的教育方式下成长。
父亲让我看到的全部都是光明面。
在我生活圈子内出现的人物表面是身光颈靓、皮光肉滑、心朗气清,我以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由内而外地干净整洁澄明正直,一如我的父亲。
所不同者,只不过是一些人比较聪明好彩,一些人比较愚钝运滞,因而造成了社会阶层的高下与财富的厚薄,得出了气派、风采和相貌的贵贱,如此而已。
整体而言,人性是善良的。
当然,我看错了。
连自己看成神一般高贵万能的父亲,都完全不是那回事。
从一开始在故乡里出身,父亲就舍弃了一段情缘,以自己的婚姻,换取直上青云之路。
当年,他若不是娶了母亲,绝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外祖父在广州的利通银铺,为日后香港创业奠下基石。
南下后,再下意识地利用了爱恋自己的秘书张佩芬,把乡下的黄金偷运来港,作为雄厚资本,使他唾手而得了个价值连城的银行牌照,从此一帆风顺,风生水起,再下来,父亲分明地把握着任何一个时机,做着一宗又一宗可能损人而绝对利己的商场勾当,乐不可支,欲罢不能地扮演着好商的角色。
其中一宗罪行,想必是在六二年,当时股市如日中天,银行家因法例规定,不得同时成为证券经纪,于是父亲利用一同南逃香江的知交陆建通,着他出面开办股票行,既活跃于证券买卖,乘势赚取巨额佣金,兼自行投机。还埋没良心,把那么一间差下多只有空壳而无实质营运生意和盈利的伟力电讯上市,骗取公众资金。
直至七三年,股市狂泻,一下子措手不及,资金调度不灵,父亲再下肯以银行借贷作为陆建通的后盾,且面不改容,似是大公无私地向陆氏迫仓,以免坏了自己稳重保守、言而有信的银行家形象。
于是穷途末路的就只是轻信人言,把人性险恶破坏力低估了的陆建通。
投诉无门,身败名裂,甚而气愤填胸之际,陆氏只有自寓所的二十多层大厦耸身一跳,以求解脱。
事实上,近百年来,国际金融风暴,此起彼落。美国三十年代不景气之际,纽约财经界有个凄厉的笑话,说:“千万别走在华尔街,以免不测,死得冤枉。事关股票狂泻而致破产者众,纷纷自华尔街的金融大厦飞身而下,怕要压倒途人,殃及池鱼,一同归西。”
陆建通当时的了断,又岂是香江独一无二的惨案。
陆湘灵父仇不共戴天,再加上为了家变而被迫沦落风尘,致跟青梅竹马的杜青云生分了。这份心灵与肉体的长期折磨,更坚定了他俩日后携手对付我的决心。纵使不能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真真注定了人间的一场悲剧。
父亲原是菩萨面孔、魔鬼心肠。叱咤风云,金马玉堂的背后,是数之不尽、令人闻而胆丧的一宗又一宗忘恩负义,忘情弃爱。
他之所以有万世基业和万贯家财,无非是权术的表现与累积。
就算私生活里头,父亲对情爱的处理,也流于吝啬刻薄。在他生命上头出现的每一个女人,除了赋予他一份真情挚爱之外,一定还要向他献奉其他的利益,不论是性欲的发泄、精神的寄托、抑或其他有关商业的用途。总之,他的受益程度远超乎他的支出。
我已开始清醒,并不认为情爱不可能以实质去衡量。
父亲口中心上,如何深深爱恋他的女人,甚而包括了我那童年好友蒋帼眉在内,原只是他自顾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的事。
他有力挚爱的人做过什么事没有?
没有。无人在他的身上,可以获得稍微超值的金钱,稍为世人所共识的地位,甚至光明正大的认可身分。
爱情是这样的吗?
我恨杜青云是铁一般的事实。
然而,在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角度下看,父亲的情操更不如他,当然也比下上默默地、隐蔽地爱父亲一生的蒋帼眉。
只管接收权益,不图履行义务;只衡量本身得失,漠视对方为难感受者,根本没资格说自己如何爱人,父亲只不过是生前幸运,把他的孽债连遗产一并交我承担罢了。
我厉行自爱又如何?
命定的厄运,仍如期在我身上发生。
人下一定为了自己的罪行而终会身受其害。
人也不一定为自己的操守而必幸免于难。
三十年保持的冰清玉洁,毁于一旦,毁于上一代的、与我完全无关的恩仇之内。
我并不觉得跟杜青云,抑或那个庄尼的关系有何分别,都是一般的肮脏、污浊、低贱。
都是人间你虞我诈的一场短暂把戏。
又或者,我可以将这种男女关系看得轻松一点,只视为日中不妨出现的折子戏。
谁于昨夜跟谁抵死缠绵,轻怜浅爱,只须睡一觉,翌晨醒来,彻头彻尾地洗个澡,就什么都冲刷得一千二净了。
留有创痕的必不是我。
我想起那庄尼,应该失笑。
他现今转醒过来,看见我的留言,怕要吓个半死。
欧美在爱滋顽疾猖厥的今天,坊间经常传诵的谣言就是谁一觉醒来,发觉昨夜风流的伙伴,竟是身有恶疾的人,后悔无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