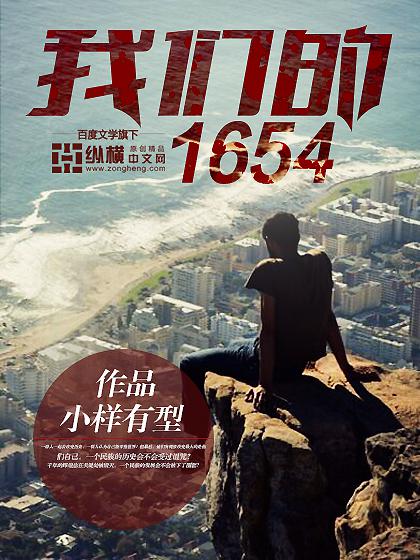假装我们在相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沙昔非蹙起眉,脑里刷不出任何印象。
她的确是不记得了,和她“谈情说爱”过的男人那么多,每张脸她看起来都差不多,一颗颗南瓜头,哪能一一记得那么多!况且,她也没有义务去记得哪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一成,拍拍屁股挥挥手,从此相忘于江湖,就甚么都不必多说了;更别说,她一向只认钱不认人的。
对他们这行的人来说,遗忘是最好的美德。
“我的确是不记得了。”她摇摇头,表示想不起来。“不过,你知道,我们这行的情形比较特殊,忘记了对方对彼此都好,少一些精神负担。”
“是吗?”卓晋生还是回答得平板没高低起伏。
从开始,他就一直是这种态度,语调平板、不愠不火,仿佛没甚么情绪,又像只是漠不相关的冷淡。
沙昔非无所谓地耸耸肩,很轻微,只是不以为意。她一向不做无谓的幻想,并不认为卓晋生这种谈不上太友好、热络的态度是针对她的;互不投机,当然是很正常的。
卓晋生侧头望望她,把嘴抿得薄薄的。
是吗?她不记得了——她不记得了,他倒是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他在张君开的餐听看见她时,她正和张君卿卿我我,无视一旁张君那个一度变心他去的女友的存在,惹得满心后悔想回头和张君重来的哪女人满脸泪痕地跑开。
而后,张君抬头看见他,对他招个手。然后交给她一纸信封袋,厚厚一叠。他走过去,她看都没看他,当着他的面,将信封袋凑到嘴边重重一吻,很满意地笑开脸,娇嫩如春花;亮亮的双眼,闪耀着贪婪的光焰。
他直觉把眉头一皱;但她甚至没在意他的存在,拐过地,揣着那封厚厚一叠的钞票离开。而后,张君才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印象,自然不会太模糊;而她,却甚么都不记得了。他掉开眼,语带讽刺,说:“我还以为,像你们这种行业的,记性会比较好。”车子转了个弯,在巷子口停下来。前面号志的红灯刚亮起来。
某种禁忌跟着燃烧起来。他真怀疑,像她这种混生活的女人,现实薄情、金钱第一,除了珠宝黄金和钞票,她还会记得甚么?
连“感情”都拿来当生意买卖、赚钱工具,以“扮演爱情”写生的女人,还有甚么可说的?
“所以喽,眼见为凭、耳听为实,道听途说都不太可靠。”沙昔非嘻笑着把话含混回去。一张狗腿脸,哈巴的表情。
卓晋生斜视她一眼,又把眼光掉回车前。
“我很好奇,像你这种扮演爱情为生的女孩,对感情有甚么观感?相信爱情吗?”问得极是无所谓,混带些微可有可无的试探。
“干嘛不相信?”沙昔非眨眨眼,眼神闪烁不定。惯性与职业性地嚼着谎,狡狯地反问。
会相信才有鬼!
关于爱情,纯粹的精神恋与痴守已消失不见,感官的气息与肉体的味道相煎成欲热的波潮,情爱的追逐在这股波潮覆掩下,只为舔舐色欲的乳汁。并且依附在现实的赤裸下。
没有人像她这么聪明,看得这么透彻。
爱情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没有钱,别谈甚么爱啊情的,连灵魂都是漂泊的。
钱为重,情可轻。
“是这样吗?”卓晋生敷衍式的轻笑一声,他本来就不期待听到多“可歌可泣”的回答。像她这种女孩,天生就是一个大骗子,对她的所言所行,自然不必太认真。
他实在受够了那些空有外表、虚荣肤浅,又现实拜金的女人。而这个女孩,大概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更糟糕——反正女人都一个样,思想、见识、气质就只有皮肤一层那么浅薄。只不过,这女孩最起码粗俗现实得很理直气壮,她的底细他一清二楚,不像那些女人,贪婪的嘴脸外,总要适遮掩掩地披上一层优雅、高贵、雍容,以及端秀纯洁和文丽的假皮;只有外表没有个性。
绿灯转亮,他慢慢踩动油门。车子刚开动,巷子旁突然斜窜出个女人挡在车子之前,然后抢到车旁。
“长得不错嘛!挺俊的!你好,我叫娜娜。”那女人倚着车窗,半个身子几乎探进车里来,冲着他勾量了几眼。而后,用着粗俗夹杂暧昧的语调,对沙昔非诡笑说:“这男人是没话说啦!看起来又有魅力又有个性,身材也十分结实,可这辆车子,未免太旧了点!阿非,你这么死要钱的,怎么会找上这么个穷小子?”她朝车内环显一眼,车里车外扫视一遍,皱鼻挑剔嫌弃。
显然,那女人是冲着沙昔非而来的。
卓晋生转头看看沙昔非。她一脸的不耐烦,眉颦额蹙;他把目光移向那女人,并未作任何的询问,那女人捂起涂得厚厚艳红的嘴唇,娇媚地对他送个秋波。
那是个浓色艳派的女人,高挑野丽,烫着一头松蓬的花拉头,一身七彩的紧身短迷你裙,充斥着挑逗的风情;白皙的皮肤如婴孩的细嫩,丰胸肥臀的身段却有着成熟女人的惹火性感,顾盼之间的那份妖媚是属于三十岁女人的性感挑逗,可那轻盈的体态,却宛如十数岁青春的少女。她那种柳细眉、勾魂眼、红艳欲滴的饱满唇,以及高耸肥厚的乳房和屁股,彷如掐得出水汁的鲜嫩,在在说明了其人饱藏男色的滋润,微微地泄露年轮的暗征;可是她那情态、模样和体态,却显着教人模糊不清的青春。
分明是张果结实的女人了,却直比沙昔非尚自含苞的花蕊。两人并立一起,那眉眼神韵气质,就好似姐妹一对。
沙昔非嫌恶地瞪那女人一眼,粗嘎说:“你少跟我扯这些无聊事!没看我有事要忙吗?少来烦我!”
这女人一出现,就准没好事;看到这女人,她就没好心情。她来找她,不会为旁的,士成十是被男人掏光了,又想来算计她辛苦攒的钱。
“我好一阵没见到你了。才一来,你就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也没个好脸色!”
“你来还会有甚么好事?”沙昔非嗤之以鼻。“少废话!你到底想干嘛?——我先吧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是来要钱的,没有。”
她不让女人开口,抢先吧话堵在前头。
那女人立刻哭丧起脸,表情歪变,变得哀愁又委屈。
“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阿非,我好歹是你的娘,辛辛苦苦生下你,把你拉拔长大,不知吃了多少苦——”
“停!”沙昔非不耐烦她老娘的哭哭啼啼。“你少跟我来这套!东尼前两天才给的那五万呢?钱呢?哪里去了?”
都说她那不知长得是圆是扁的老头是小有名气的小生——依她看,她这身靠着吃饭的戏子本事,根本都是遗传自她这个妈!看她老娘这哭哭啼啼的假造本事多高明,烦都烦死她!
沙娜娜愣了一下,随即恢复满腹的委屈,被冤枉了似睹咒喊道:“钱?哪来的钱?东尼跟你说了甚么是不是?天地良心,他那个吝啬鬼,一毛钱也蹦不出来。哪来的五万块借我?我可是一个子儿也没向东尼那死家伙拿着来的!”
“是吗?那就是钱自己长脚,从东尼的口袋爬出来跑到你那边去喽?”
“你别净是这样说话呕我!东尼那死家伙,不知跟你嚼了甚么舌根,看我不找他算账!”
“你跟他的账,的确该去算一算。你别又想把一屁股的烂债,赖在我头上。”
“阿非!”沙娜娜硬是死皮赖脸。“我好歹是你妈,你可不能不管我的死活。”
“你的死活干我甚么事?”沙昔非板着脸,不为所动。
“当然关你的事!”沙娜娜呼号起来。“我生你养你,把你拉拔得这么大,你不孝不顺,不奉养我也就算了,但你总不能狠心看我饿死在街头吧?”
这种话亏她妈还说得出口!沙昔非翻个白眼,回嘴说:“这种话亏你还敢说出口!你甚么时候管过我死活了?我长这么大,你可又甚么时候好好照显过我一天?就只会伸手向我要钱,把一屁股烂债赖在我头上,我又不是活该欠你的!亏你有脸说自己伟大,讨恩要情!”
“不管怎么说,我可是你的妈。你很心丢下我不管?”
“不然你想我怎么办?”沙昔非厌透了,皱紧眉。“我的钱都被你榨干了,你还想把我怎么样?你要跟那些没骨头的家伙瞎搅和,那是你的事,可没钱了别来找我,我可没义务帮着你养那些没出息的家伙!”
甚么嘛!就只会算计她的钱!她老娘若用讹诈她的这些精神和气力去对付男人的话,怕早不都可攒了几千几百万了!
“你居然说这种没有良心的话!”沙娜娜干脆撒泼。“如果没有我这个妈,还会有你吗?现在你居然要丢下我不管!我真是歹命啊!生个女儿不孝又不肖!”
沙昔非烦她不过,索性不睬她,对卓晋生说:“走吧!不必管她。”
沙娜娜霍然跳起来,横手拦住车子。
“不许走!”她扯着喉咙大叫。“停车!谁都不许走!”
她这样大叫大闹,惹得沙昔非更烦,咆哮说:“我说没钱就是没钱!有本事养男人,就要有本事自己去攒钱!”猛然挤身到晋生身上,抢过方向盘,用力踩下油门,朝前横冲直撞过去。
“你干甚么?这样很危险的!”卓晋生被她突如的举动吓了一跳,使劲地将她推开。
车子惊险的煞住,险险地就撞上横向马路上的来车。
“停车!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女孩!给我回来!”沙娜娜叫嚣个不停。“早知道,当初就把你卖了,还有一笔钱好赚,也不会留着今天来气我了!”
“开车!”沙昔非歪到卓晋生身上,又要去抢方向盘。
卓晋生挡住她,看了后视镜一眼,发动引擎,将沙娜娜近乎歇斯底里的鬼叫,远远抛在后头。
“那真的是你母亲?”他问道。
真不知那是怎么样的家庭!她们的态度、对话,以及生活型态,压根儿与甚么和乐、母慈子孝的“正常”家庭扯不上边。
沙昔非斜瞪他一眼,才撇撇嘴,答非所问道:“算你运气好,免费看了一场闹剧。”完全一副无所谓。对刚刚发生的事,也不当是一回事。
看来有其母必有其女。那做母亲的,千方百计想讹诈女儿的钱去养小白脸;然后那做女儿的,扮演爱情,拿感情当作赚钱的工具。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倒不奢望沙昔非会是多“正常”的女孩。像她们干这种畸零行业的女孩,想他知道,总有各方面的问题存在,却没想到会离谱到简直是夸张的地步。
他对她惊鸿一瞥,留下了奇特的印象,而触碰了禁忌的环套。那环套,可解可结,牢牢的一个捆绕。
破破的“台湾保时捷”几近半解体地停在那栋教人膛目结舌的大房子前。沙昔非先屏息几秒钟,然后回头望那一路树草县延,堪称是“热带小丛林”也似的广阔大院地。
这整个地方,倒说不上多富丽堂皇或奢华,就只是大——单那座大房子,占地的面积就有寻常双并公寓大厦的三倍有多;至于那庭地。扣掉车道,往两旁彷彿无限制地扩展而去,从这头根本看不到那头。更过份的是,车子从前头一路开进来时,居然还经过一座小石桥,小桥加流水,有林有水,彷倒自成了一处桃花源。
但仔细观察打量,卓家这个“深宅大院”,真的就是“大”而已;房子建有两层楼高,仿西式的洋房建筑,外表有点斑驳陈旧,怕不都盖了好几十年。总之,除了“大”、土地辽阔这一桩外,从外表是绝对看不出这座宅院有甚么烜赫辉煌的地方,更谈不上富丽豪华,一点都嗅不出豪门巨宅特有的那种金碧辉煌的鲜热味道。
“我先告诉你——”卓晋生也没先打个招呼,随着说话声,冷不防就凑到沙昔非身旁,脸贴得很近,俯在她鬓旁,像说悄悄话似的,嘴唇几乎贴在她耳畔上。
沙昔非猛被吓一跳,下意识地往后略为退开;卓晋生倾身凑得更近,将她逼到门边。
“你……要告诉我甚么?”沙昔非被逼得暂时停止呼吸,疑怯地望着卓晋生,用手指阻隔住他。“拜托你,能不能别靠我那么近?”
真是的!有话告诉她,直接说不就得了,非得靠这么近吗?那股压迫感简直逼得她不能呼吸!
卓晋生仍维持相同的姿势和倾身的角度,并没有将她的话听进去。用着慢板的声调说:“我的家庭是属于传统的家庭,家祖母的观念也比较守旧,所以,在这段期间,请你务必节制你的言行。你和令堂之间那种”开放式“的态度,在这里是种禁忌。我知道这要求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困难,但我想,你应该有那种能耐才对。”
他凝住呼吸!停了一会,然后才慢慢收回身子,恢复原来的表情和姿态。
“这我懂得,你不必特别提醒。”这时,沙昔非方才小心、慢慢地吸了一口气。
下了车,卓晋生绕到她身旁来,忽然想起甚么,冷不防又凑到她颊旁,将她逼靠到车身上,不急不徐地吐出一句:“我想,还是提醒你一下比较妥当。记得我们现在的”关系“。从现在起,可别再脱口叫我甚么卓先生——”
他说一句。沙昔非便点头一次。这家伙讲话时似乎有将人逼到角落墙边和凑到人身旁的习惯,总是教人冷不防、稍不留神便猛然被吓一跳。
“我晓得。”她伸出根指头点着他的肩头,使力将他推开。“你讲话都非得像这样凑到人身旁将人逼到墙边角落的吗?你这样,让我觉得有种压迫和威胁感,呼吸很困难。”
卓晋生微微挑了挑眉,显得意味深长地打量她一眼,要语不语。个性的一张古铜脸,雕得立体深隽,除了深显的轮廓,内藏的情绪不明。
从他找上沙昔非,到故作那一身弩俗土气大便色的装扮,就教人猜测不出他心里做的是怎样的打算。他受够了那些虚荣肤浅现实的女人,却又找上沙昔非这样一个拜金崇物、现实十足的“爱情戏子”,矛盾的情态,如同那环禁忌的环绕,教人费解,将人捆绕。
“进去吧!”他朝屋子偏倾头,挪挪下巴,示意沙昔非跟着他。
沙昔非自然地靠到他身旁,表情也跟着改变,粉凝的脸,变抹得端庄又飞扬。舞台的帘幕,开始慢慢地升起。
她这样顷刻间由神色、谈吐犹带流气的女孩,一变而为气质外显,既端庄又风采飞扬的文雅仕女,引得卓晋生不由得惊叹动容;他实在迷惑了,辨不清她真正的面貌。到底怎么样的气质风貌才是真正的她?突竟那流气粗俗与端庄飞扬之间的变换与差异,哪一个才是在“演戏”?
他竟无法对她定出一个绝对的定义!
“又怎么了?”他表情不可思议,使得沙昔非下意识里觉得自己是否哪里不对劲,低头看看自己。
她发现,某个程度上,卓晋生实在是个很会挑剔的男人。尽管他显示得耐性好,耐烦耐气,可也个性十足,踰越他容忍范围标准的,他绝对不会客气。好比在来时他在车上对她那种冷淡挑衅的语气就是一个例子。
尤其,他不是那种经常有求于人的男子,在“委屈自己”这方面上,他不怎么愿意妥协;这一点和她恰巧相反。打小她就看惯了各种脸色,也伺候惯了各种脸色,能屈能伸,能不坚持的就绝对不坚持,要银要钱,就是不要脸;当然,她有她的个性与脾气,只是,不到最后不得已的关头,她绝对不会跟白花花的银子过不去。
因为她是属于土的。属于士的女子,有一颗最现实固执的心。
卓晋生管听不答的,对她偏个头,迳自走进屋里去。她赶紧跟进去,牢牢挨在他后头。
客听里一片宁祥。西落的太阳,从西边的窗子洒照进来片片丝丝的暖金光芒,光彩一地参差对照着,满室蒸发着一股幽幽的古旧风情。
卓晋生大步走到光影中,立即地,光与影将他整个人偏分在明亮与幽暗的参差里。
“大哥!”楼上传下来一声不期然的惊喜。一个年纪和卓晋生相仿,大概两三岁之差的年轻男子快步下来。
他和卓晋生一样,晒了一身古铜的健康肌肤;唇齿眉眼,和突出深刻的轮廓,也与卓晋生有几分神似。乍看下,如同的一个知性加帅性加个性的魅力表征。
“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回来?我好过去接你!”他带着惊喜的笑脸,来到他们的面前。
那一双眼,晶灿得像珠光。同样是自体会发光,他的眼神却不若卓晋生那等会吞噬人似的燃烧般光热,而是一种明亮的照拂,缺乏了卓晋生那种个性不妥协的倔霸之气,却有着卓晋生所没有的温秀之贾;一个轰烈,一个低回情长。
沙昔非从听到声音传来开始。脸上就挂着浅浅的笑,并且一直保持它的柔和度,丝毫没有僵硬感。
她看看卓晋生,再看看那个男子。
他叫卓晋生“大哥”,自然就是那个“弟弟”了。凭着职业的本能,她嗅得出,这个男人绝对是上等货,不但英俊风采、体魄强健,而且多金多田,旁的且不算,光是这房子的土地,少说也值好几债。卓晋生看来不好应付,她倒可以把心力放在弟弟身上,同样地不愁吃穿。
“反正我自己开车回来也一样,不麻烦。”卓晋生一贯那平板的语调。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他居然还说不麻烦。
沙昔非不现甚么意味地侧头望他一眼。原来他那种没有高低起伏情感的平板语调,是他个性一种原始的元素;她原还以为,那或只是他另一款的面具。
“奶奶呢?英生!”卓晋生问道。
银生?沙昔非想着心事,没听仔细,自以为是,险些突兀地笑出来。金生、银生,这一家的男子倒都是啄着宝贝出生,难怪生来就是富贵命。
“奶奶在房里休息,爸妈和小瑶也在。我想他们应该也都听到声响,大概马上就会出来了。”卓英生边回答,边将眼光移到沙昔非身上。
“她叫沙昔非。”卓晋生会意,介绍说:“我的未婚妻。上回我跟你们提过了,今天特地带她回来见奶奶的。”
“未婚妻?大哥,你真的——”卓英生的反应没有应有的高兴与惊喜,反倒显得错愕。好像卓晋生做了甚么,而他却不相信他真的会那么做的事。
“当然是真的。从小,哪一次我说的话没做到过?只要我说出口的,言出必行。”卓晋生脸上流露着不妥协的神气。
沙昔非愉愉吊个白眼,在心头暗笑。甚么言出必行?说得跟真的一样!
“阿非,来,我跟你介绍——”卓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