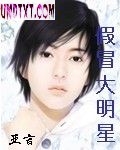大明王朝1566-第7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海瑞:“公文上直接写着下给你的吗?”
田有禄这回真的怔了,自己拿着那纸公文重新看了起来,不好说话了。
海瑞:“回话。”
田有禄:“公文当然是下给淳安县的……可巡抚衙门的上差却是亲手交给属下的。”
“咄咄怪事!”海瑞声音陡转严厉,“《大明会典》载有明文,现任官不管是调任还是辞任都必须见到吏部的回文。吏部现在并无回文免去我的淳安知县,巡抚衙门却把公文交给你,你竟也拿着公文擅行知县事。淳安正堂的大印现在就在这里,你是不是也要拿去?”
田有禄:“堂、堂尊,你自己不也跟属下说,叫属下…?”
“我跟你说了我是在待罪等候处置吗,”海瑞目光如刀紧盯着田有禄,“你跟衙门的公人到处散布,说我已经待罪了,请问,我待的什么罪?”
“待罪的话卑职可没有说!”田有禄一下子慌了,“谁敢如此挑拨县尊县丞!”
海瑞望向了差役班头王牢头:“田县丞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挑拨县尊县丞可不是轻罪。”
这就不得不为自己洗刷了。王牢头立刻抬起了头:“二老爷,你老可是说过海老爷在省里犯了错,正待罪在家。这话也不是一个两个人听见,怎么反说是小人们挑拨了。”说着望向了差役班头。
差役班头却比他油滑得多:“或许是二老爷听信了误传。”
海瑞不看他,只盯着田有禄:“是不是听信了误传?”
田有禄出汗了:“电、也许是误传……”
海瑞:“既是误传,那就是说我并没有待罪。省里的公文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看看了?”
田有禄连忙走过去将巡抚衙门那纸公文双手递给海瑞。海瑞飞快地看了,接着将目光向堂上所有的人扫了_逦,大声说道:“沈一石当时将粮运到淳安跟我说得明明白白,那些粮都是织造局奉了圣命赈济淳安灾民的粮。万民颂圣之声犹在,为何还要追讨皇上赈济灾民的粮?这纸公文于理不当于事不合,不能听从。”说到这里他竞当着满堂的人将那纸公文一撕两半,接着又撕成碎片向案前扔去!
望着蝶般飞舞飘落的碎纸片,所有的人眼睛都睁大了,愣在那里。
“堂尊。”田有禄终于省过神来,“擅自撕毁巡抚衙门的公文,这个罪我们可担不起。”
海瑞:“有我在,还轮不到你担罪。你的罪,我正要问你。”
田有禄擦了一把汗:“我、我有什么罪?”
“你的父亲接回家奉养了吗?”海瑞突然话锋一转,紧盯着田有禄。
田有禄哪想到他突然又会问这个事,立时怔在那里。
海瑞:“我大明朝以孝治天下。身为朝廷命官,虐待老父,忤逆不孝,这就是你的罪。身为淳安正堂,下属犯此忤逆之罪,才是我份所当管。参你的公文我已经想好了,写完后我会立即上呈都察院。你还有何话说?”
田有禄这才真慌了,腿一软跪了下去:“堂尊明鉴。卑职本已将家父接回家里奉养,无奈家父与儿媳不合,他、他老人家自己又搬出去了…”
海瑞:“与儿媳不台?你干什么的?”
田有禄:“堂尊明鉴。自从堂尊奉命去办钦案,淳安县的事都在卑职一人身上,忙得卑职焦头烂额,家里的事实在管不过来。”
海瑞一声冷笑:“自己的父亲管不过来,上司的儿子倒去孝敬。”
海瑞的厉害田有禄早就如芒刺在背,自他当这个知县以来,自己也不知已受了多少惊吓,郁闷憋屈自不用说,担惊受怕更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他要辞官了,原想终能伸直了腰拼命巴结一把上司,趁这个机会或许能接了淳安正堂。偏是几件事还没做完,就让他揪住了。现在竟然又追问胡部堂儿子这件事,牵涉到浙直总督也要追查,田有禄心里也有了气,心想在这件事上决不能服软。
田有禄抬起了头:“堂尊,卑职是县丞,礼敬堂尊是规矩,礼敬胡部堂更是规矩。
大明朝各府州县都是这个例子,卑职去接待一下胡部堂的公子,哪就说得上孝敬。堂尊这个话卑职万难接受。“
海瑞:“你是怎么接待的?”
田有禄:“他从我淳安县过,我们是主人,他是客人,自然以主待客之礼接待。”
海瑞:“二百两银子的饭食费,四百两银子的贽敬,是你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
田有禄又怔在那里。
海瑞:“一毫一厘均是民脂民膏。一家农户全年穿衣吃饭也不过五两银子,你一次出手就送丁六百两银子。张书吏,你管钱粮,你替我算算,六百两银子是庄户人家多少户一年的衣食钱?”
钱粮吏首一直缩站在一边,这时问到了他,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
海瑞盯向了他:“算不过来是吗?”
钱粮吏首只好答道:“回堂尊,是一百二十户百姓一年的衣食。”
海瑞:“好个以主待客之礼。一出手就送掉了一百二十户百姓一年的衣食银子,你这个主人当得真是大方。你说我大明朝各府州县都是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写在朝廷哪个条文上,你拿来我看。”
田有禄哪里还有话说,跪在那里不停地流汗。
海瑞紧盯着田有禄:“我再问你一句,胡部堂的儿子你以前见过吗?”
田有禄:“回堂尊,以前没、没见过。”
“这就是了。”海瑞站了起来,“我和胡部堂见过面,而且有过深谈。胡部堂本人就对搜刮民财耗费官帑以肥私囊深恶痛绝。真是他的儿子,就不会接受你这样的贽敬。
接受你的贽敬,就一定不是胡部堂的儿子。拿我的签,带着差役把这个人抓起来,你亲自送到胡部堂那儿去。“说着从签筒里抽出一支红头签扔在田有禄面前。
田有禄知道自己这是又倒了血霉了,再也顾不得面子当堂磕起头来:“堂、堂尊容禀,州里给卑职打的招呼,这个人确实是胡公子。再、再说,四百两贽敬的银票现在还在卑职身上,并没有给他。卑职怎么敢把胡公于押送到部堂大人那儿去。卑职万万不敢接这个差使。”
海瑞:“不接这个差使也可以,你就脱下官服官帽,等着杖四十,流三千里吧。”
田有禄眼睛睁得好大:“堂尊,卑职犯了什么罪,你要这般治卑职于死地?”
海瑞:“我没有叫你去死,我也不能治你于死地。我治你是按的《大明律》的条文。
为了巴结上司,拿官帑行贿朝廷大臣,治胡部堂以收受贿赂的恶名,其罪一。虐待亲生父亲忤逆不孝,其罪二。《大明律》你那里也有,翻翻看,犯了这两条,是不是杖四十,流三千里。“
田有禄知道这是来真的了,立刻说道:“堂尊,念在这几个月卑职侍候的份上,容卑职先把家父接回家奉养,再把胡公子…或许不是胡公子,就是那个人送到胡部堂那里去。”
海瑞见他惊惶失魄的样子又好气又可怜:“你的父亲我会安排人去接。你现在立刻把驿站的那个人送到胡部堂那里去。”
“卑职就去,卑职这就去。”田有禄都快要哭了,“卑职立刻带人把、把那个人送到胡部堂那儿去。”
海瑞:“去吧。”
田有禄站了起来,满脸的汗水把眼睛糊得都睁不开了,擦了擦眼睛,望向了差役班头:“你带人跟我去。”
那班头这时竞假装没听见,眼睛望着别处。海瑞历来深恶痛绝的就是赵班头这样的衙门差人。晚年他曾经用“贪恶欺滑顽”五个字概括这等衙门差人,称之五毒之人。此时见这赵班头兀自这副模样,动了真怒,猛地抓起惊堂木一拍:“跪下!”
赵班头刚才还装模作样,这时竟像弹簧般立刻跪倒了:“老、老爷有何吩咐?”
海瑞:“县丞派你差使,你没听到?”
“什、什么差使?”赵班头兀自装懵,待看到海瑞刀子般的目光又连忙改口,“听、听
到了,押送人。小的这就去。“磕了个头站起,立刻对几个差役:”走吧。“
“不用你去了。”海瑞又喝住了他。赵班头定在那里。
海瑞目光炯炯扫向堂上一干公人:“这个姓赵的班头,在街市上以为我待罪在家便视若不见,现在见田县丞有了干系又翻脸不理,可见这个人平时对小民百姓何等凶恶!常言道‘身在公门,手握人命’。要是你们都像他这样,淳安的百姓不知要遭多少罪孽!王牢头。”
王牢头连忙答道:“小人在。”
海瑞:“你不是抱怨牢里是空的吗?把这个姓赵的班头关进去,听候处置。”
“是。”王牢头哪敢犹豫,爬起来走到那个赵班头身边,“走吧。”
那赵班头:“大老爷,小的有错也不至坐牢。”
海瑞:“无视上命,凌虐百姓。你不坐牢,大明朝也不用设牢房了。带下去!”
王牢头向跪着的两个牢卒示了个眼色,两个牢卒爬起来,一边一个拉住赵班头的手臂把他扯了起来。王牢头:“走吧。”二个人押着那赵班头走了出去。
海瑞望向另外几个差人:“你们跟田县丞去驿站。”
几个差役大声齐应:“是!”田有禄在前,几个差役在后,慌忙走出了大堂。
钱粮吏首、刑名吏首还有剩下的一班差役牢卒都低着头站在堂上。
海瑞:“淳安今年全县被淹,家家百姓颗粒无存,好些人倒塌了房屋还住在窝棚里,全指着新产的那些生丝度过荒年,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居然四处抓人,夺民口中之食,各自互相看看,你们这样做还像个人吗!”
一千人的头更低了。
海瑞:“巡抚衙门追税的公文我已经撕了,请求朝廷免税的公文我也呈了上去。有人不想让淳安的百姓活,朝廷不会让淳安的百姓死。从今日起,任何人不得向百姓追讨税赋,尤其不许抓人。谁再敢抓人,就到牢里跟那个赵班头做伴去。都听到了吗!”
所有的人:“是。”这一句答得真是有气无力。
杭州原沈一石织坊
这里的上百架织机发出的声音依然是那样轰鸣。还是那些织机,还是那些织工,织出来的还是那些上等的丝绸。
这时赵贞吉身兼着织造局的差使,每日都要抽出时间来这里促织。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钦案明明结了,锦衣卫那个头儿和另一个锦衣卫仍不回京,也每日在几个织坊里转悠,这就明显表示出了皇上一直在盯着杭州这五十万匹丝绸。今天又是这样,五个徽商就跟在赵贞吉和那两个锦衣卫的身后,在通道上看着一架架织机上一根根蚕丝织成一片片丝绸,五个人的脸却都比盖死尸的布还难看。
画外音:“其实赵贞吉何尝想让治下的百姓去死?前方抗倭急需军饷,可沈一石织坊却因生丝日缺日日减产。还有最让赵贞吉头疼,也最让几个徽商揪心的是,丝绸在一架一架担机上织,本钱从徽商身上一两一两往外掏,最后沈一石这片产业属谁,名舟却仍髂唛味不明。赵贞吉簦的约是卖给了五个徽商,皇上的旨意里却说这些织坊从来就是江南织造局的徽商们急着要赵贞吉培个说法,赵贞吉身边日夜跟着皇上派来的人,哪里能向皇上去讨说法'”
“现在每天的织量是多少?”赵贞吉提高着嗓子问。
“眼下每天还能织一百匹。”那个年轻的徽商答道,“过几天只怕要停机了。”
赵贞吉站住了,先向两个锦衣卫望了一眼。两个锦衣卫却像没有听见,背着手踱着步走向一架织着蝴蝶花纹的织机前,假装在那里看着。
赵贞吉这才把目光望向几个徽商,放大了声音尽量让两个锦衣卫听见:“为什么停机?”
年老的徽商接言了,也尽量放开了嗓门:“不瞒中丞大人,我们的本钱也有限,实在拿不出钱来买丝了。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要开工钱。”
赵贞吉回以大声:“半价买丝你们都拿不出本钱?当时为什么签约书?告诉你们,耽误了朝廷的事,胡部堂也保不了你们。”
那年老徽商立刻激动起来:“做生意我们也不要谁保,只讲信用二字。赵中丞,你能担保按约书给我们兑现吗?
“谁说不按约书兑现!”赵贞吉脸一沉,又瞟了一眼两个锦衣卫,“织机一天也不能停,今年五十万匹丝绸一匹也不能少。你们谁敢停机,我不抓人,请你们的本家胡部堂派兵抓人。”说着大步向织坊外走去。
五个徽商被撂在那里,都想吐血了。两个锦衣卫这才慢悠悠地跟着赵贞吉也向织坊门外走去。一行还没有走到织坊门口,巡抚衙门一个书吏迎上来了:“禀中丞大人,淳安县丞田有禄来了,在衙门里急着候见中丞。”
赵贞吉的脸更难看了:“一个县丞也要见我,你们的差使真是当得好呀!”
那书吏连忙躬下腰:“中丞容禀,田有禄是带着胡部堂的公子来的。据说是那个海瑞叫他押送来的。”‘
赵贞吉这才一怔,不禁又望向了两个锦衣卫。两个锦衣卫这时不避他的目光了,
也与他对望了一眼,三个人一同走了出去。
浙江巡抚衙门签押房
赵贞吉没有先见胡公子,而是把田有禄叫进来了。
田有禄探头探脑进来后,见赵贞吉站在案边,靠窗的椅子上还坐着镇抚司的两个钦差,更是慌神了,在门边就趴跪了下来,不断地磕着头。
赵贞吉:“海知县已经递了辞呈,我说了淳安的事由你署理,又闹出什么了?”
田有禄头趴着回道:“中丞大人把追讨淳安百姓欠粮的差使交给卑职去干,卑职好不容易派了些人下去收丝,却被海知县都叫回来了。”
赵贞吉:“巡抚衙门的公文没给他看吗?
田有禄有意嗫嚅着不答。
赵贞吉转过了身子盯着他:“我问的话你没听见‘”
田有禄这才又吞吞吐吐地:“卑、卑职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中丞大人回话”
赵贞吉:“照实回话。”
田有禄:“海、海知县把巡抚衙门的公文扯了。”
赵贞吉眼睛一下子大了。两个锦农卫身子也动了一下,都望向趴在那里的田有禄。
田有禄:“海知县说,织造局那些粮是皇上赈给淳安灾民的赈灾粮,谁要追讨便是玷污圣名。还说淳安今年是重灾县,他已经呈文朝廷请求免去全县的赋税。”
赵贞吉那个气在胸巾沸腾翻滚,一时竞说不出话来。两个锦衣卫也都站起了。
锦衣卫头儿:“有这等事,”
田有禄:“回钦差大人的话,千真万确,这都是海知县所说所为。”
另一个锦衣卫望着锦衣卫头儿:“这个人或许真是脑子有病”
“什么病!”赵贞吉终于说出话了,声色惧厉,“就是对抗上司对抗朝廷的病!二位在这里都听到了,我要上疏参他,请二位也向宫里禀奏。”
锦衣卫头儿:“我们自然如实禀奏。”
赵贞吉又望向田有禄:“把胡部堂的公子也扯了进来,这是怎么回事?”
田有禄觉着有了底气,这时更是百般委屈地:“州里给卑职打了个招呼,说胡部堂公子到台州看望父亲,从淳安经过换船。卑职按照惯例,接待了一下,海知县却说卑职奉承上司,还说胡公于是假的,命卑职把他押送给胡部堂。卑职不按他说的做,他就要行文都察院参卑职的罪。中丞太人,卑职在淳安实在干不下去了,请中丞大人开恩,让卑职调、调个地方吧。”说到这里,他抹开了眼泪。
赵贞吉这个时候突然又沉默了下来,治丝愈棼,步步荆棘,田有禄的话突然提醒了他,头上还有个胡宗宪,送来的这个胡公子不正是一卸担肩的契机,他的脸平静了,向门外叫了一声:“来人。”当值的书吏连忙走了进来。
赵贞吉:“送给胡部堂军营的最后一批军需粮草什么时候起运?”
当值书吏:“回中丞,这一次是好几万人的军需,还有十几船今天下午才能到齐。
到齐后立刻起运。“
赵贞吉:“剿灭倭寇这是最后一仗,一粒粮一根草也不许短缺。再去催,到齐后三天必须运到。”
当值书吏:“是。小人这就去传令。”
“慢。”赵贞吉望了一眼趴跪在那里的田有禄,“把他还有海瑞抓的那个人一并带上,送到胡部堂那里去。”
当值书吏:“是。跟我走吧。”
田有禄还在那里发懵,半抬着头:“中丞大人。”
赵贞吉:“滚!”
台州军营中军大帐
海雨白茫茫一片蔽接苍穹时,天风便收了。海浪惊涛此时都安静地偃伏着,把撼地的吼声让给了连天的雨幕。
中军大帐的帷口巨石般站着齐大柱,在雨幕中手把着剑柄一动不动,大帐的两侧和四周几十个亲兵也在雨幕中巨石般挺立一动不动。
大帐内只有一只小炭炉在吐着青色的火苗,催沸着药罐里的药汤,白气直冲搁在两根筷子上的药盖,发出微弱的叩动声。
胡宗宪的亲兵队长就守在药罐前,这时揭开了药罐盖,轻轻吹散了笼冒的白气,接着用铁钳夹出了火炉中的几块红炭,再将药罐盖搁在两根竹筷上,让小火慢慢煎着药罐中的药汤。再接着,他向中军大案前方向望去。
大案前的躺椅上一床被子拥着胡宗宪半躺半坐在那里,他的面前是一只矮几,矮几上是一局己到中盘的围棋,围棋的对面笔直地坐着戚继光。轻轻地,胡宗宪将一枚黑子下在了棋盘上,戚继光望着那枚黑子苦苦地出神想着。
“这颗子不知道该怎么下了吧?”胡宗宪掩了掩半垫着躺椅半盖在身上的棉被,靠躺了下去:“好像我曾经跟你说过围棋的出典,还记得吗?”
戚继光本捏着一枚棋子望着棋盘在想,昕胡宗宪这一问,抬起了头望向他:“是。部堂曾经给属下说过,围棋是古人见了河图洛书,受到启示,想出来的。”
胡宗宪:“那就从河图洛书中想想,这步棋该怎么下。”
戚继光:“部堂这是取笑属下了。河图洛书,是上天出的题意,多少先圣贤哲都不能破解,属下一个军伍中人怎能从天书中找到想法。”
胡宗宪:“只要肯用心找,就能找到。世间万事万物都只有一个理,各人站的位置不同,看法不同而已。譬若看一条河的对岸,站在河的南边,北边就是对岸;站在河的北边,南边就是对岸。记得我曾在王阳明一则手记中见过,他就认为河图洛书不过是三代先人观测天象,对何时降雨,何时天旱的记载,用以驱牛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