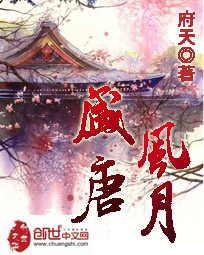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1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尴铝司挤荒谝患衣蒙帷4丝烫靤è已晚;九叔明ri还要去都督府点卯;我这就先告辞了。”
站起身的杜士仪见杜孚令杜黯之相送一程;而堂弟连声答应;面上却仿佛有些失望;他想了想刚刚杜黯之的请求;便开口说道:“二十一郎刚刚求过我看他的诗文;不若就让他跟我回去在旅舍暂住一夜。我此番毕竟是公于;不知道在幽州能停留多久;恐怕之后未必能抽出空来。”
“那是他的福分。”杜孚想也不想便连连点头;这才板着脸冲满脸狂喜的杜黯之说道;“你随你十九兄回去;务必恭敬请教。”
“是;父亲”
杜黯之完全没注意到嫡母那铁青的脸sè;等到送了杜士仪出门;又见家仆牵了马匹出来;他只觉得心情激荡;高兴得恨不得叫出声来。
第二百二十七章 大义之名
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是杜士仪向来做人的宗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若本来就对他无甚情意的人要想把他当成是软柿子;他一定会设法让人崩了牙
因而;今天晚上去拜会叔父杜孚一家人;他已经大约摸清楚了这一家人的xing子。杜孚倒还是要脸面的;至少场面上的客套热络做得齐全;可一个劲拐弯抹角打听他在京城和那些达官显贵的关系;以及杜思温对他如何等等;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差没明着说出来而已;至于婶娘韦氏;那便纯粹是个自以为是的无知妇人;当着他的面说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真把他当成是可以随意揉搓的晚辈了?
别说他如今有心仪的人;就算没有;又怎会容忍她指手画脚?
“十九兄;就是这家旅舍?”
听到耳畔传来这么一个声音;杜士仪这才回过神来。见旅舍里头已经有人闻讯出来迎接;他便跳下了马背;随手把缰绳丢了出去;这才带着杜黯之和田陌往里走去。才进餐堂;他就闻到了一股扑鼻而来的香气;再看到一方方食案上摆了羊肉胡饼等一应俱全;在杜家根本没吃饱的他顿时只觉得食指大动。而身边的杜黯之反应则是更直接;肚子又是不争气地叫了两声;一时引来了好些人侧目。众目睽睽之下;他顿时羞得脸sè通红;恨不得把钻进地缝里头去。
尽管杜孚和韦氏不招人待见;但杜士仪还不至于迁怒一个孩子;更何况此刻是他把杜黯之带了回来。此刻;他瞥了杜黯之一眼;见赤毕迎了上前;他便笑道:“这么晚你们还没吃晚饭?还是让人准备了夜宵?”
赤毕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陌生的杜黯之;因笑道:“是夜宵。这几天东奔西走;料想郎君回来十有腹中饥饿。再说;大家都是大肚汉;一顿晚饭还不顶饿。”
“那就正好了。”杜士仪对杜黯之略一颔首道;“二十一郎;索xing坐下再陪我吃完夜宵;我也考问一下你的功课
杜黯之想到今天已经是杜士仪第二次替自己遮掩这样的尴尬场面了;他不禁感激涕零;讷讷答应了之后;等杜士仪带他到角落的一席坐下后;他便低声说道:“十九兄;我……”
“没吃饱就先填饱肚子;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当初和你这么大的时候;成ri里在嵩山打兔子打野鸡;到最后那些狡猾的小家伙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躲得没影子了。”杜士仪用小刀割下了一大块羊肉;又送上了酱料碟放到杜黯之面前;这才说道;“一边吃一边说话;你这些年都读过什么书?”
杜黯之正要回答;可看到杜士仪已经毫不在意地蘸酱吃肉;他犹豫片刻也就照着吃了一口。杜孚官阶不高;职田俸禄都是有限的;再加上韦氏治家俭省到了极点;更何况他这个庶长子;上次吃到羊肉还是三月三的时候。一口鲜香可口的羊肉下肚;他只觉得腹中仿佛更加饥饿了;好一会儿方才醒悟到应该是答话的时候。
“读过《诗经》、《尚书》、《礼记》、《论语》。正在读《chun秋左氏传》。”
这若是放在平常的人家;读过这些已经算是不错了;但若是门荫出仕困难;需得从明经或是进士谋求出仕的世家子弟;那就远远不够了。杜士仪微微蹙了蹙眉;见杜黯之细嚼慢咽;吃相与其说是秀气;不如说是小心翼翼;他不禁回忆了起来;猛然间想到杜孚仿佛有一庶子在前;迎娶韦氏在后;心头便恍然大悟。略一思忖;他便又问道:“可拜过师?”
“是父亲亲自启蒙教的读书认字。”
这种事在如今是最平常不过了;可想到韦氏那xing子;杜孚还有公务;理应不可能有太大的功夫花在庶长子身上;杜士仪便从刚刚杜黯之所读过地那几本书中;随便抽取了几条经义;见其答得一板一眼;显然是真的花过苦功夫;但却无甚自己的见解;他少不得又问了其读《chun秋左氏传》的进度。等到要了杜黯之随身所带的那些诗文;他翻阅了几卷;抬头发现杜黯之紧张地看着自己;他便笑了起来:“好了;眼下不说这些;你先吃饱了再说。不过眼下晚了;荤腥吃太多太过油腻;喝一碗鲜汤;吃一块胡饼;余下的明天再说。”
杜黯之自然是杜士仪怎么说怎么做;当下再也不看那对自己诱惑不小的羊肉;胡饼和汤下肚;他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竟情不自禁又打了个饱嗝。从晚上到现在已经出了好几回丑;此刻他只能埋下了脑袋;等接过一旁不知是谁递来的软巾擦了油腻的嘴角;他方才微微抬头;却发现那不是别人;而是杜士仪这位堂兄。
“吃完东西不可久坐;跟我到院子里走走。”
把地方腾给刚刚不敢高声说话的赤毕等人;杜士仪又嘱咐田陌别大晚上去和店主磨叽什么本地特有作物和种子之类的话题;这才带着杜黯之出了餐堂。此刻的天sè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足足绕着院子走了一圈;他才头也不回地问道:“二十一郎;你今后是什么打算?”
杜黯之不想杜士仪突然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顿时愣住了。直到醒悟过来眼下不该发呆;他方才咬了咬牙说道:“我想学十九兄”
不止是杜黯之;杜士仪哪里不知道;如今京兆杜氏在杜思温的刻意宣扬下;那些长辈都在用自己当榜样鞭策下头那些子弟;可是;他自家人知自家事;能够有今天;卢鸿在他身上花费了莫大心血;而抄书后便能把内容铭刻在心的本事;亦是他最大的优势。须知这世上过目不忘的天才固然有;可短时的强行记忆不意味着终身就能铭记在心。再加上煞费苦心的一次次造势;jing通琵琶曲乐而结下的人脉;而这些很多都是不容易复制的。
“你知道京兆杜氏自当今圣人改元开元之后;这些年出过几个进士科及第的子弟?”见杜黯之摇了摇头;杜士仪方才举起一根食指道;“就只有我一个。”
杜黯之倒吸一口凉气;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动摇。而这时候;杜士仪方才继续说道:“你那些诗文我都看过了;文章中规中矩;诗赋亦是如此;这不怪你;因为九叔自己本就不长于此;你不得名师教授;能在启蒙之后有如此的底子;已经很不错了。”
倘若不是今天一时恻隐把杜黯之带了回来;又记起他是杜孚的庶长子;明显在家中无甚地位;心xing却上进而淳朴;杜士仪也不会多费唇舌。京兆杜氏如今是有杜思温竭力帮他;可家中单薄的他在宗族之中;也就是和杜士翰亲近一些;后者明显是从武不从文的;他不得不考虑在族中另外给自己打下一些根基;顺便也牵制一下杜孚这个叔父。此时此刻;见杜黯之并没有因为他那直截了当的评点而气馁;而是低头应是;他便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若是要应进士科;那今后这些年;先得读通帖经所需的所有大经;尤其是chun秋三传;然后苦练杂文;再接着便是广见识的策论;最后是关试必备的书判。光是这些基础打好;就要八年甚至十年;当然若有名师;应该可以减少一些时间。但是;科场之事;纵使才华横溢的才子也难免受挫;如今的京城中;便有十数载浸yin科场而求不得一个出身的。九叔和婶娘恐怕不会让你这样一年年反复折腾;所以我建议你;不妨专攻明经科。”
建议是建议;但杜氏更清楚;是否愿意做出取舍;还得看杜黯之的。顷刻之间;他就等到了杜黯之的回答:“我听十九兄的”
就算父亲;也只是让他用功读书;至于期望也好建议也好;什么都没有
“很好;但即便明经;也不能光是死记硬背;需得更加娴熟地通晓经义。幽州对于九叔来说;是仕途上迈了一个大台阶;但对于你来说却不是。这里武风兴盛;文风却寻常;所以你不妨回樊川去读书。你只要愿意;此事我会对九叔说。”
如今嵩山悬练峰的卢氏草堂人满为患;他可以把堂弟引介过去;但没有那个必要。这年头;那些进不去国子监之类官学的读书人;多半都得靠亲长启蒙读书;如卢鸿这样肯传道授业解惑的少之又少;私学并不发达。只看偌大的京兆杜氏;竟是没有一座宗学;就可以看出这种观念来。
京兆杜氏子弟中;那些家境富贵的;或者有长辈jing通经史的无所谓;可总有和从前的他那样家道中落或极其贫寒的;那么;他出钱;让杜思温拿出京兆公的面子来;专供族中贫寒子弟读书;也不用专请一位老师;而是可以挑那些名望卓著的作为“客座教授”;轮流前来讲课;岂不是一桩美谈?如此;除了此前那些才名;他又有了大义之名;作为杜家小字辈才算是真正站稳了
“多谢十九兄”
见杜黯之一躬到地;杜士仪便伸手把人扶了起来;却发现对方的眼眶里竟是泪珠直打转。想当初他自己虽说起头艰辛;可有十三娘这个妹妹襄助;而后又得良师益友;说起来比杜黯之幸运得多。想到这里;轻轻松松撬了杜孚墙角的他不禁笑了起来;又语重心长地吐出了一句话。
“总而言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发愤图强上进努力。须知此前的苏相国;还不是出身于微贱
第二百二十八章 送卿回京,与君惜别巡
一大清早;一行车马悄悄驶离了幽州开阳坊的一家客舍。坐在马车中;白姜频频悄悄偷眼去瞥自己的主人;见其手托下巴心不在焉;她终于忍不住低声说道:“娘子;真的就这么走了;也不和杜郎君打个招呼?”
“出城之后;我就让人去给他送信。他此次是奉旨观风;正事要紧。”
嘴里说得正气凛然;王容的双颊却不禁微微一红。前一天傍晚在蓟北楼上;她着实没料到杜士仪会真的把话说开了;这足以⊥她一个晚上辗转难眠。每年进士及第的人就那么几个;半数以上都是四五十开外的;年轻而尚未婚娶的屈指可数;更何况还是世家子弟?榜下挑女婿的公卿们想来都早已看上了杜士仪;之所以尚未下手;还不是杜士仪那奉旨观风之行。可以预想;杜士仪此前在并州之行中已经立下了不小的功勋;回京之后必定会被人趋之若鹜。
更何况;市井传言中;东都永丰里崔家对他极其看重;应有定下婚姻许配女儿的意思;须知清河崔氏位列五姓七望;头等名门望族;门前列戟;家名赫赫;将来必能相助他的仕途。
心里这么想;可随着马车的颠簸;王容恍惚之中又想起杜士仪昨天突然牵自己的手;继而直截了当地吐露出了好感;甚至自陈婚事自己做主;一时间她不禁发起了呆。她能够找出一万个此事难成的理由;可她自己更清楚;打从大安坊那野地里亲眼看到杜士仪折梅的时候;她就不知不觉留意上了他——不是传言中那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状元郎;而是那个站在梅树前洋溢着自信的少年;是那个在王家别业山第中;听得她一本万利大为赞叹的知音;也是在并州大都督府前为人阻拦便以目示意;想当然认为她能够帮上他的人;更是她在得知张说的安排后;想都不想便送上了那枚琉璃坠的朋友。
真的就这么走了?只是出城后让人给他捎个信?幼娘;如此回到了长安;在那等时时刻刻有人窥伺的情况下;真的能再相见吗?
马车出城时;王容不禁轻轻打起窗帘;看了一眼这座自己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来的北地雄城;长长吐出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她放下手的一瞬间;她突然听到后头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尽管明知道自己昨ri没告诉过他投宿之地;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这会儿怎么也不可能是他追上来;可她仍是不由自主地把头探出了窗外;下一刻就看到了那个穿过城门门洞出来的熟悉身影。
“啊”
王容突如其来的动作和惊呼让白姜吃了一惊;连忙也从另一边窗口探头出去张望;等发现是杜士仪;她眼睛一亮;立时把头缩了回来;却只见自家娘子也已经坐了回来;但那神情怎么看怎么不平静。
王容在长安时两次见到杜士仪;白姜都跟随在侧;尽管回去之后自家娘子半句不曾提起这些;可在她看来;正因为半句不提;方才证明娘子心中另有思量;因而之前在并州受命给杜士仪送东西的时候;她很好奇杜士仪的反应。果然;那位声名远扬的状元郎没有让她失望;飞龙阁上那次相会之后;娘子竟是启程来了幽州。只可惜那时候她没能一直跟随在侧;丝毫不知道杜士仪对王容说了些什么;可昨天蓟北楼上那些话她都听到了
娘子的婚事一直都是主人翁的心病;而那位杜郎君非但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便深谙生财之道;绝不是那些觊觎王家财富的公卿权贵
此时此刻;杜士仪已经追上了马车。拱了拱手后;见王家那些随从犹豫片刻便让开了路;他笑着颔首答谢后便来到了马车之侧;犹如敲门似的轻轻叩击了一下车厢;紧跟着;他便看到窗帘被人轻轻拉开了;现出了那张此刻不见自信狡黠;唯有挣扎和犹豫的脸。
“我是来送你的。”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虽然没有解释为何知道她此刻走;又是走的哪座城门;王容却不禁心头大震;那些假意责备抑或是强硬回绝的话都再也说不出来。然而;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她终究还是放下了窗帘;等到心绪完全镇定了下来;她方才用极低的声音开口说道:“杜郎君虽声名远扬;平步青云;可长安城中尚有外敌虎视眈眈;真的愿意放弃以婚姻结好公卿;而舍易求难?”
杜士仪心知肚明王容此言是什么意思。王毛仲如今正炙手可热;而他既然已经与其对上了;那将来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险。而不论是他娶了崔家这样的公卿名门;抑或是其他朝堂重臣的女儿;那便会多了一重最大的后援。但是;有好处也同样有坏处;那就是他会被牢牢绑在别人的马车上须知往后朝堂党争会越来越激烈;他需要相当的dulixing。但更重要的;却还有另一个缘故。
“若非两情相悦;而是单纯因利而婚;此刻固然可以轻松过关;焉知将来不会后悔?”
“那你就不怕人说;你是为了王家的亿万家财……”
“虽不敢企及王家长安首富;但我既然能振兴倾颓的家业;将来也能拥有足以⊥人无话可说的财富。只不过;恐怕你要等几年。”
王容看着杜士仪那自信的眼神;终于深深吸了一口气下定了决心;声音竟是几乎微不可闻:“杜郎君;回长安之后;我打算去金仙观;请求金仙贵主度我为女冠。杜郎君倘若真的甘心情愿舍易求难;那么便如你所说;再等几年吧我虽只有微薄之力;但也会倾尽所能自保”
她这不但是在顾忌她自己;也是顾忌到风头正劲的他她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想得这般长远;分明这个念头早就盘桓在她的心中
“好”
瞬息之间;杜士仪便迸出了这么一个字。然后;他盯着她那坚定的脸sè和眼睛;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策马后退两步便朗声说道:“既然王娘子没有胆量担当我所言的大生意;那么等我回到长安的时候;再邀千宝阁的刘胶东商量吧此去长安天高路远;还请一路小心些;就此告辞”
眼见得杜士仪拱了拱手;随即头也不回扬鞭离去;王容顿时怔怔松了手;那窗帘无声无息就滑落了下来。她刚刚出口的打算早就萦绕心头;刚刚不假思索说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竟然能够如此决绝;更没有想到;杜士仪竟然会二话不说答应了;而且更当众撂下了这样至少可让人少怀疑些他们关系的话他是真的相信她所言的倾力相助;更知道以王家长安首富的名头;并不一定能挡住他那些仇家;所以方才立刻撇清
“娘子?”
“娘子”
车内车外同时传来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王容立时抬起头来;用极其冷峻的声音吩咐道:“别耽搁了;立时启程回长安”
车外那些王家随从正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出而纳闷;此刻听到女主人的话;面面相觑了一阵子便无可奈何地照吩咐去做了。随着车轱辘继续转动了起来;车内渐渐又是一阵阵的颠簸;白姜终于忍不住低声说道:“娘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白姜。”王容轻轻伸手攥住了白姜握紧的粉拳;随即眼睛闪闪发亮地说道;“刚刚我和杜郎君说的话;不论是阿爷还是两位阿兄;你都不许透露半个字”
“可是……”
“没有可是。”王容不由分说地打断了白姜;又侧头紧紧盯着她;“这关系到杜郎君的将来;也关系到王家的安危。”
“我……可是娘子呢?”白姜犹豫了许久;最终轻轻点了点头;“那……我听娘子的就是了。”
“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王容终于露出了一个笑容;随即伸了个懒腰懒懒靠在了后头的软垫上。除了阿爷和两位阿兄之外;别人固然也有人惊叹她的能力;可多半总免不了闲言碎语;就连jing于如张说者;亦是让其夫人元氏婉转告诫过她;做女人不要太逞强。可是;他却不但说对她有好感;而且愿意信赖她;这种信赖对于她来说;才是这个天底下最珍贵的宝物。
而当杜士仪策马到了城门口的时候;见小和尚罗盈正探头探脑的;他稍稍放缓速度;言简意赅地说了一声回去。不过一小会儿;罗盈就纵马追了上来;不由分说挡在了他的马前头。
昨夜悄悄跟着王容一行;找到他们落脚的旅舍;又在附近随便找了个一家店过夜的小和尚满脸的纳闷和不解;此刻连珠炮似的问道:“杜郎君;究竟怎么回事?这不是赶上了;怎么又争起来了?而且这争的是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
“想知道?那就陪我去酒肆喝两杯。”
见杜士仪不由分说拨马便走;罗盈只觉得脑子里一团乱七八糟的浆糊;只能无可奈何地追了上去。等寻到了一家无甚客人的酒肆;眼见得店主殷勤张罗了米酒送上来;他见杜士仪连喝了三杯却根本不理他;只得索xing伸手抢过了酒
“杜郎君”
“无论今后谁问你今天的事;你都得说;我和王娘子生意不成翻脸了。”见罗盈险些把眼珠子瞪出来;杜士仪突然笑道;“当然;你又不可能一直跟着我;不会有人没事找你盘根究底……总而言之;你记住;你对谁都不能说;昨天我在蓟北楼上对她说过那些话。”
“啊”
“我仇人多。倘若不是如此;恐怕长安王家要遭池鱼之殃。”
罗盈这才想起岳五娘对自己说过的那些事情。他当初从洛阳安国寺被送到嵩山少林寺;还不正是因为王守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