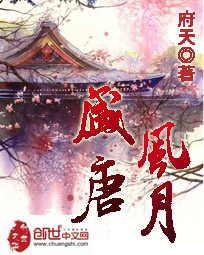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1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昨夜虽商量不少;但都是阳谋;早上师兄弟二人从王宅那偏厅中出来时;裴宁便低声说道:“王怡进了洛阳后;我便使人去查过他从前的为官案卷。此人极其强项;最初颇有刚正不阿的名声;甚至为人称作是治理州县路不拾遗;然则治狱素来严苛;乡间豪强但有犯法立时穷究;而即便是子弟犯有小错;也往往严惩不容情;商人之流就更不用说了;但凡民告;必重罪论处。久而久之官做大了;拿来立威的人也就越来越非同小可;对此有人送了他一个绰号;破家王。”
杜士仪登时醒悟到这王怡还真是名声在外的人;源乾曜和孟温礼王卿兰的担心;恐怕全都是因为此人的经历而来。于是;深深感受到肩膀上那重担的他不由得苦笑道:“看来;这次我还真是扛上了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不要死扛;那样万一没建树的话;别人是不会感激你的。”裴宁此话说得声音极轻;纵使四周围就算有悄悄偷听的人物;也难以听清楚他这细微的言语;“只消摆出一个态度;让人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却被王怡强势所阻。然后;让该吃苦头的人吃些苦头。或许大多数人确实是和权楚璧等逆党无涉;但敲山震虎;就是圣人乐见其成的。等到这王怡收不了手;再用最后一计。”
“先鸡蛋碰石头;然后示敌以弱;敌进我退;最后待骄兵之计用到极致的时候;再图穷匕见?”
“显摆你活学活用不成?不过……你说对了”
回忆着这番对话;此刻才换下那身风尘仆仆的衣衫;舒舒服服泡在满是热水的浴桶中;杜士仪忍不住轻声呢喃道:“破家县令;灭门令尹……王大尹啊王大尹;即便这是捅了天的逆谋大案;但这等时刻;破家灭门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长安一乱;天下不安;这等浅显的道理莫非都不明白?”
他自然不知道;当傍晚时分;之前熬了大半夜只睡了一个多时辰;这一整个白天又是连轴转审人犯的王怡面对手中那一张寥寥数语的供词;面上却是流露出了说不出的振奋。
“有了这供词;我看朝中还有谁敢觉得姜皎冤枉”
第三百四十五章 夤夜来客
两天两夜没怎么好好合眼;杜士仪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当他正沉陷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境中时;却突然被一阵有些粗暴的推搡给惊醒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的他发现床头竟是站着一个黑影;第一反应是自己仍在做梦;但下一刻;那一只突然死死掩住了他嘴的大手;瞬间把他从梦幻拉到了现实
“杜拾遗是聪明人;想来知道即便惊动了外头的人;总快不过我手上的刀”
见那只手缓缓移开;又听到耳畔传来这样的低语;杜士仪方才低声问道:“你意yu何为?”
“王大尹初来乍到就四处拿人;杜拾遗不会不知道吧?”
那黑影身穿黑衣;面目在此刻昏暗的屋子里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再加上他仿佛刻意模糊了嗓音;因而那声音显得嘶哑难听;甚至不辨男女:“杜拾遗同样奉旨而来;难道便放任此人罗织大狱陷人罪名?我不妨实话提醒一句;杜拾遗此前高义;于旁人尽皆三缄其口之际;封还了决杖流姜皎岭外的制书;可现如今那位王大尹却因为一份供词;便把姜皎一并陷了进去”
“你说什么”
杜士仪又不是神仙;哪里知道王怡的真实目的竟是穷追猛打;不把姜皎赶尽杀绝誓不罢休。此时此刻;倒吸一口凉气的他不知不觉声音提高了一些;而因为这动静;外头立时传来了一个声音:“郎君可是有什么吩咐?”
见那黑衣人浑身一震;黑暗中的那两只眼睛仿佛死死盯着自己;杜士仪便冷静了一下;直到外间又重复问了一遍刚刚的问题;他这才仿佛从睡梦中惊醒似的说道:“一路上太累;说两句梦话而已;没事……别再一惊一乍;我继续睡了……”
大约是听着房中再无动静;外间渐渐脚步声远去。直到这时候;杜士仪方才深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旋即淡淡地问道:“你夤夜来见;不会是单单因为想要知会我王大尹构陷楚国公的事吧?如有事情不妨明说;用不着拐弯抹角。”
“权楚璧及李齐损率屯营兵谋逆造反;他们身为首恶自是该死;可其中有许多不过是胁从。如今王大尹兴大狱严拷讯;罗织罪名;其中便有我的昔ri恩人被陷其中。我今夜来见;自当有罪;可杜拾遗既然以刚正清直著称;当此之际;莫非便只知道酣然高卧不成?倘若杜拾遗能够公正明允;还清白之人清白;那异ri此狱终结之ri;我自当束手就擒;从律法处置”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杜士仪听着听着;待明白此人是为了报恩而不惜犯险潜入杜家;他冷不丁想起当初听过的一桩旧闻;心中不禁一动。然而;他面上却不动声sè;依旧如同起头那样安然躺着;语气平淡地问道:“你的恩人是谁?”
“杜拾遗无需问这许多。据称王大尹秉持的意思是;此番案子权楚璧和李齐损固然罪大恶极;可他们不过无能庸碌的官宦子弟;做出这种事;焉知不是利令智昏;被人怂恿?说是夤夜斩门闯宫;拂晓自乱阵脚;因而乱兵杀此二人以首级乞降;焉知不是有人杀了他们灭口断绝线索?可他却根本不想想;正当长安动荡;圣人却在东都洛阳之际;倘若这一再牵连yu兴大狱;更是只会让民心动荡;让无数原本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破家县令;灭门令尹;更何况天子一念之间?从当年则天皇后到现在;好容易太平了十年;莫非又要让官民百姓胆战心惊;只觉得朝不保夕?”
此人绝非粗鄙;而是颇有见地的人
杜士仪此刻细细再看此人身形;心里决定不如试探一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便徐徐坐起身道:“这么说;尊驾倒是个悲天悯人的人……你说得不错;虽则王大尹不想让我插手;我却也不会坐视不理。可我自己的判断是一回事;被人胁迫又是另外一回事楚大侠以为然否?”
此话一出;他就陡然之间感觉到了一股凌厉的杀气和压力。不等对方开口承认或者否认;他的语气倏然转厉:“我之为人;你来之前应该也心中很清楚我立身处世;从来都是只凭心中意气决心;绝不受人挟制如若你的恩人真的冤枉;你想替他陈情;那便以真面目来说话。否则;此刻你就是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决计袖手不管;我杜十九说得到做得到”
“杜拾遗果然是一如传闻……”低低叹息了一声之后;那黑影终于放下了头上的风帽;就在床榻前单膝跪了下来;“倘若能够;我甚至敢豁出去大理寺劫狱;然则宫禁之中防卫比从前森严更甚;匹夫之勇终究不成杜拾遗既是垂询;我也不妨说实话;我之恩人;是权怀恩嫡长子权楚珏;权楚璧的从祖兄;如今袭爵卢国公。当初我从河北一路逃亡西域;若非他从西域任官回长安途中施以援手;我早已是沙海之中的一具尸体。他受了权楚璧挑唆;因知洛阳马球赛之事;想着家门败落;便请我带着几个权家李家子弟前往洛阳参赛;看看能否重振家名。等我得知长安惊变;悄悄跟着杜拾遗一行回到长安后;却因为权家被围来不及去见他;不想王大尹就已经先下手为强了。”
杜士仪不知不觉坐直了身子;口中喃喃念道:“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若只是从祖兄;又与逆谋无涉;本不在流三千里之限。”
“不错;还请杜拾遗明察秋毫;还无辜人一个公道”
见这昂藏大汉屈下另一条腿;一头磕在了地上;杜士仪连忙伸出双手把人扶了起来。可他的力气固然不小;耐不住对方力气更大;相持了好一会儿;他方才收回手无可奈何地说道:“你今夜潜入胁迫之事暂且不论;我还有要紧的话问你;你先起来再说”
楚沉这才缓缓起身;心情却异常复杂。他本想今ri胁迫了杜士仪答应;异ri若能让恩人昭雪;他这条命就是还出去也无所谓。可谁曾想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杜士仪好似认定了他的身份;而且言辞间流露出的鱼死网破之意;让他不得不有所取舍。毕竟;和他这些年见识过的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不同;年方弱冠的杜士仪一贯公正明允刚直清廉;他总不能因为报恩;真的对其以死相逼。
“你之前所言姜皎之事;从何听来?”皇城如今戒备森严;更何况是王怡坐镇的大理寺;所以;杜士仪绝不会以为这消息是大理寺打探到的。
“是傍晚时分有信使从朱雀门出来;因不少官民围堵为自家亲人讨公道;此人嚷嚷出来的。只怕一夜之间;就会传遍长安城上下”
竟然又是和之前姜皎落马一样;相同的人言可畏这一招可同样的招数用第二遍;还能够蒙骗天下人?
杜士仪暗自哂然;但并不敢小觑其中利害。他沉吟片刻;就又问道:“和你在马球赛上同队的那几个年轻后生;如今在何处?他们可还知道更多?”
“他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事发之后惊慌失措;一度都想着逃亡;是我稳住了他们;后来托付给一个相熟的友人;先把人看了起来以防做傻事;看样子不像是和权楚璧等人一丘之貉。要知道;他们的马球打得不过尔尔;身手也只是勉强过得去;难道还指望他们去行刺圣人?”
楚沉最后一句话只是随口一说;杜士仪却是猛地悚然而惊;眼睛突然死死盯住了楚沉。尽管在黑暗之中;寻常人不会注意到这视线;但对方却分明感觉到了;一时仿佛有些惊讶。在这种情形下;他微微定了定神;这才一字一句地说道:“他们自然是没有这样的能耐;可若是权楚璧真的在长安站住脚跟;而后以你那位恩人作为要挟;让你这个曾经为友人一怒杀进豪门的去行刺呢?你会带着几个差强人意的年轻人去打马球;应当并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冲着魁首去的吧?”
杜士仪顺势站起身来。即便是在黑暗的屋子里;他还是隐约看见了楚沉那一瞬间勃然sè变的面孔;看见了对方深深吸气;仿佛第一次想到这个推测。原本零零碎碎的线索如今终于被一颗一颗珠子地串了起来;他只觉得一切思路豁然贯通。
他所设想的这些乃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之一;可情况赶不上变化;马球赛还没有打到最后的决胜负之际;王皇后却已经危若累卵;而皇帝心中必然有过废后的打算;否则也不至于所谓姜皎泄露御言的传闻一出;李隆基的反应就这么过激。于是;这边厢东都处置了一个妄谈休咎的姜皎;长安便是紧跟着谋逆作乱;倘若本就只剩下一口气的姜皎再摊上这个案子;那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
“事关众多人的xing命前程清白;我会尽力。你先回去吧;不要再如今ri这般犯险。否则不是报恩;反而是陷你那恩人于险恶”
“那一切便尽皆拜托杜拾遗了;某今时冒犯;异ri一定会负荆请罪。先告退了”
看着此人那魁梧的身躯灵活地翻窗出了屋子;尽管长夜漫漫;杜士仪却只觉得睡意全无;竟是睁着眼睛一直看着头顶的屋梁;一直到外间雄鸡打鸣;晨鼓响起。然而;起床更衣洗漱之后;心情复杂的他到院子里练了一趟剑;满头大汗地令人提水来沐浴时;却是又有人急匆匆地上了前来。
“郎君;门外有人以纸包石;投书进来。”
这样简陋的传递消息方式;让杜士仪很是意外。可看过那皱巴巴的纸上寥寥数字之后;他不禁蹙紧了眉头。
“ri出月落;何人知汝心?”
第三百四十六章 抗争
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纵使谁看了都会陷入纠结。而当杜士仪问过之后;得知听到动静的人追出却没发现人影的时候;登时更觉得纳闷。回房仔细研究过这张皱巴巴的字纸;确定纸张上头并未做过文章;他便点起蜡烛;将其凑上烧了个于净;心里仔仔细细斟酌着这九个字的含义。当他思量过了有可能会给他传递讯息的人;然后用排除法将大多数的人一一排除在外之后;他的脑海中便一跃跳出了那个最可能的答案。
如果是王容;用的这种段;证明事情来得快;别人尚不知情。既如此;这隐语所指;应该是如今最热门的人和事。月落……月落……
杜士仪陡然之间想到了姜皎的名字;一时不禁生出了一丝明悟;继而便流露出了惘然的表情。殿庭行杖;果然九死无生;更不要姜皎以五十出头的年纪受杖;又是整整六十;撑不住死在路上也在料想之中;却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
既然最重要的字眼想通了;他快步来到书斋找出了地理图册;当即便明白了剩下的意思。如果他所料不差;就是在这几ri的拂晓时分;姜皎死在了汝州。须知汝州距离东都洛阳不到二百里;按照流配的行程绝不会超过七ri;也就是;姜皎在其子姜度护送于东都启程之后;最多只撑过了短短的七天而王家毕竟行商;各地消息渠道最快;因而他得到消息应该比河南尹王怡早
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踱了两步;再结合昨晚楚沉的话;杜士仪屈指算了算ri子;最终不得不苦笑了一声。就看王怡的信使和姜皎报丧的信使谁到京城更快;按照距离和时间来;应该是姜家占优;怕就怕姜度事到临头报丧的时候反而犹豫。不过;他身在长安;此前该做的也已经都做了;不必白cāo心。现在的他;要紧的不是上书告状;而是只需要按照之前和裴宁商量的主意;对王翰崔颢韦礼交待的进度;先把自己这兢兢业业的副钦差当好
值此长安城中上上下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际;杜士仪既然被王怡派巡查全城安抚官民;那位河南尹又不许流言蜚语再行散布;他便切切实实亲自上阵。次ri一大清早;他就先了卢国公权家;却发现外头兵员看得严严实实;纵使他亦拦在门外。他却也不气馁;依次按照名单了其余各家;结果无一例外全都是门外兵卒林立。
于是;他京兆府廨见了孟温礼之后;得到了这位京兆尹首肯;便大笔一挥写下了一篇榜文;然后立时刻印出来;一时间张贴得满城都是。榜文上的内容很简单;但凡有亲友牵涉到此次的大逆案子;求诉无门的;全都可以在榜文下投书;他将亲自与见安抚。
这下可好;相比那些在王怡的榜文下;怀着各式各样的打算投书首告的人;到杜士仪这榜文下求诉的何止多出一倍接下来整整三四天;杜士仪除了在京兆府廨辟出的厅堂之中见了不计其数的人;还亲自走访那些被捕拿的屯营兵家中;亲切聆听那些长辈同辈的哭诉哀求;同时剩余惶惶不安的屯营兵之中;他亦是安抚调停;又请京兆府廨和长安万年两大县廨调拨粮米;如此忙了个连轴转。而王怡虽仿佛忘记了他;他却依旧riri抽出空大理寺;即便换了人看守的大理寺官署他再也没能踏进一步;可他却再不曾像第一次那般大发雷霆;不见就走;仿佛气xing全都消了一般。
只不过杜士仪再拼命;也不至于和王怡似的没ri没夜审案;每天晚上都有夜禁;他什么事情都于不了;自然早早上床就寝养jing蓄锐;预备来ri再不厌其烦地对人律例讲人情耐心听取各种诉求…几ri下来;当他喉咙几近于嘶哑;面上也充满了疲惫;长安城中本来躁动不安的人心;在王怡的不懈抓人;他的不懈安抚下;勉强终于摁下了几分时;他jing心炮制的奏疏;以及写给朝中几位要紧高官和玉真公主金仙公主的私信;也从长安启程送了洛阳。
这一ri一大早;闭门审理不见任何官员的王怡;终于第一次打开了大理寺的门;却是主动命人把长安城内留守的各大官员全都请了来。其中京兆尹孟温礼和万年令韦拯;长安令以及留守的尚书省各部郎中员外郎等郎官;也全都一一请了来。自然;这其中少不了作为他随员从洛阳赶到长安;却几乎没见过他两面;没过几句话的杜士仪。
尽管消瘦了一大圈;眼睛里密布血丝;但王怡的jing神却显得很好。等人全都来齐了。他便指着书案上那一大摞高高的案卷;痛心疾首地道:“长安神州重地;京畿之重;却有宵小谋逆;所涉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圣人践祚以来;宽仁驭下;官民上下无不得益;可此番却有那许多人附逆;不但辜负圣恩;而且更是丧心病狂本府自从到了长安之后;旦夕审理;殚jing竭虑;如今终于把一应人等的罪状供词全都整理了出来;整整一百八十三人除了在长安的这些人;尚且牵连到东都洛阳的一些人;本府已经具折禀告陛下。”
今ri云集于此的官员全都知道王怡左一个右一个一直在抓人;那些收监的屯营兵就没有一个放出来不;接下来还一直在陆陆续续往里头抓人;据传言;这大理寺的监牢都已经被填满了——毕竟大理寺复核天下刑案;纵使偶尔也有案子需要押解犯人进京来重审;但那是极个别情况;哪里像这一次那般数目庞大?
因而;听到这个数字;京兆尹孟温礼立时又惊又怒:“王大尹莫非打算把这一百余人全都当成谋逆罪论处?”
“事情原本如此;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莫非王大尹是不曾读过永徽律疏不成?一个谋逆之罪;要牵连家中多少亲族;你这是想长安城中十室九空不成?”
“孟大尹何必危言耸听谋逆大罪;倘若不能杀一儆百;今天固然死了个权楚璧;今后还会有张楚璧;王楚璧”
眼见得孟温礼和王怡这一对京兆尹和河南尹竟是争了个针尖对麦芒;其他人颇有一种插不进嘴的感觉。可当王怡振振有词地将杀一儆百挂在了嘴边时;杜士仪终于瞅准了空子;突如其来地出言道:“王大尹既然是杀一儆百;那便显而易见;这谋逆之罪;有一和百的分别。倘若首恶和胁从全都是一个处置;那正如孟公之前所言;长安城中十室九空谋逆者;除却父子皆斩之外;妻女祖孙兄弟姊妹全数没官;伯叔父以及兄弟之子流三千里;照此办理;长安城中要少多少户人家;王大尹应该算得出来;而这些人家的姻亲友人;又是多少家?”
见王怡面sèyin沉不话;杜士仪便又提高了声音:“圣人令王大尹从洛阳疾赶到长安;是为了安抚官民;案子已经出了;不过善后而已。倘若由此被人误解圣人之意是整肃长安城上下官民;莫非王大尹就承担得起这个职责?”
“你……”王怡之前就领教过杜士仪那犀利如刀的言辞;那时候便是用官高数级压死人的一招;现如今堂下满是各位官员;他更不能就此示弱;当即声sè俱厉地道;“你莫非是生怕本府深究此案;查出了与你有涉的实情?”
此话一出;王怡清清楚楚地看到;下头众官一时尽皆sè变;他知道自己这一招杀锏终于是生效了;当即似笑非笑地道;“你和姜皎之子姜度本有交情;此前封还制书自诩为公心;但你真的敢没有丝毫私谊在其中?此番长安城中权楚璧等人谋逆造反;内中有人供述;楚国公姜皎曾经与权楚璧见过数次;权楚璧更与姜家有金钱往来;此事本府已经详细陈情禀报了圣人”
尽管之前就有传言;权楚璧权梁山之乱